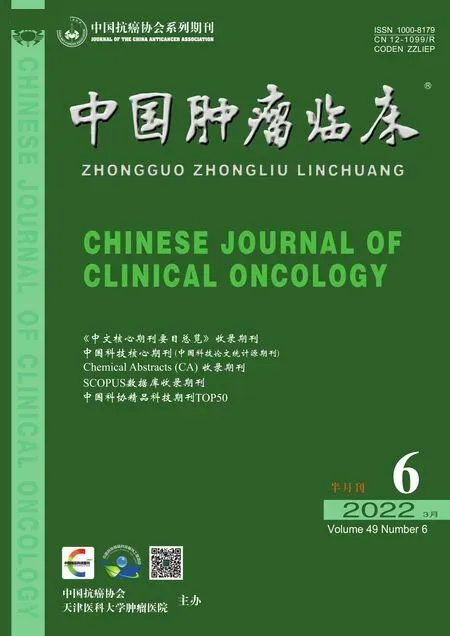EB病毒及EB病毒感染相关淋巴瘤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周小楠 综述 师永红 审校
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又称人类疱疹病毒4型,属γ疱疹病毒科。1964年Epstein与Barr首次在Burkitt淋巴瘤(Burkitt’s Lymphoma,BL)中发现该病毒,并命名为EBV。全世界约有95%以上的人口曾感染EBV,绝大多是隐性感染,部分形成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咽炎等急性感染[1-3]。此外,因在NK/T细胞淋巴瘤、BL、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s lymphoma,HL)、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等肿瘤及移植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PTLD)患者的组织中检测出大量EBV,从而认为EBV与这些类型的淋巴瘤的发生、发展紧密相关,其可能通过抑制免疫系统或诱导不受控制的增殖导致肿瘤的发生。
1 EBV的分子生物学特性及其感染模式
EBV是线性双链DNA病毒,呈球形,基因组长172 kb,主要编码产物包括EBV增殖感染相关抗原:衣壳抗原(viral capsid antigen,VCA)、早期抗原(early antigen,EA)、膜抗原(membrance antigen,MA),以及EBV潜伏感染时表达的抗原[潜伏膜蛋白(latent membrane protein,LMP),包括LMP1,LMP2A和LMP-2B。EBV核抗原(Epstein-Barr virus antibody,EBNA),包括EBNA1、EBNA2、EBNA3A、EBNA3B、EBNA-3C和LP]。EBV还表达两种小核酸RNA(EBV encoded RNAs,EBER),包括EBER1和EBER2,以及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s,miRNAs)。
EBV的生命周期分为裂解和潜伏两个阶段[2]。其在上皮细胞中进行裂解复制,并在循环记忆B淋巴细胞中建立终生潜伏期,从潜伏期开始周期性地重新激活。依据EBV表达潜伏基因种类的不同,可以将其潜伏感染模式分为0、Ⅰ、Ⅱ、Ⅲ型4种类型。0型潜伏感染即被EBV感染,处于休眠期的记忆B细胞,仅表达EBV编码潜伏的RNA即EBERs;Ⅰ型潜伏感染,EBV除表达EBERs外,还表达EBV核抗原EBNA1和BamHIA右侧片段(BamHI-A rightward transcripts,BARTs),如BL;Ⅱ型潜伏感染,EBV表达产物包括EBNA1、LMP1、LMP2、EBERs和Bam-HIA片段的转录产物等,鼻咽癌、DLBCL、NK/T细胞淋巴瘤和HL等属于Ⅱ型感染;Ⅲ型潜伏感染,多发生在急性EBV感染或严重免疫缺陷个体中,如艾滋病相关非霍奇金淋巴瘤、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器官移植、使用免疫抑制剂等,涉及6种EBNA、3种LMP和2种EBER[1,4]。
2 EBV相关淋巴瘤
2.1 BL
BL是一种高度恶性的B细胞肿瘤。几乎全部地方性BL均为EBV阳性。转录因子MYC调节细胞周期、DNA损伤修复、蛋白质合成等相关基因的表达,并且促进细胞的增殖[5]。BL的一个重要特征是MYC的移位和激活:MYC和免疫球蛋白基因位点之间的易位导致MYC的过度表达,促进细胞恶变,最后导致BL的发生[6]。p53是重要的肿瘤抑制基因,参与细胞生长调控,促进细胞凋亡。研究认为MYC不仅促进细胞增殖,也参与细胞凋亡的调控,如通过多种途径包括生长素响应因子(auxin response factor,ARF)/E3泛素连接酶(E3 ubiquitin-protein ligase Mdm2,MDM2)/p53途径、核糖体蛋白(ribosomal protein,RP)/MDM2/p53途径和DNA损伤应答途径等激活p53,引起细胞凋亡[5]。抑制p53依赖的长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浆细胞瘤多样异位基因1(plasmacytoma variant translocation 1,Pvt1)亚型Pvt1b,可增加MYC水平和转录活性,促进细胞增殖。p53激活Pvt1b来抑制MYC,进而抑制肿瘤发生[7]。EBV编码的LMP1也通过刺激促进细胞增殖、调节炎性反应的锌指蛋白(zinc finger protein A20,A20)基因的表达来阻断p53介导的细胞凋亡[8]。有研究表明,核转录因子TCF3的激活和EBV编码的LMP2A,激活B细胞受体(B cell receptor,BCR)调节肿瘤细胞的增殖和活化,导致细胞恶性转化,进一步与失控的MYC协同,促进细胞存活和BL的发生[9]。此外,EBNA1、EBNA3在BL肿瘤的形成过程中也是不可缺少的。EBV在增殖的宿主细胞中以染色体外遗传物质附加体的形式存在,EBNA1在DNA复制过程中使单链DNA发生交联,在宿主细胞的分裂过程中介导了附加体的复制和分配,并促进细胞迁移和可能的转移扩散[10-11]。由此可见,EBNA1对病毒DNA在感染细胞中的持续存在至关重要[11]。研究表明,EBNA1还可以发挥抗凋亡作用,增强肿瘤的致瘤性[6]。证明EBNA1与影响B细胞生长和功能的基因及细胞增强因子、白介素6受体、早期B细胞因子1等相结合,提高EBV潜伏感染细胞的存活率[12]。EBNA3A和EBNA3C介导各种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的抑制,同时还通过抑制病毒感染和转化的凋亡反应,如抑制促凋亡的B淋巴细胞瘤-2基因(BCL-2)家族成员BIM基因,加强EBV介导的B细胞转化和随后的病毒持久性,进一步促进病毒诱导的增殖和肿瘤发生。而肿瘤抑制因子EBNA3B与EBNA3A和EBNA3C作用相反,其失活则促进免疫逃逸和EBV驱动的淋巴瘤发生[13-14]。有研究表明,缺失EBNA2的基因组可表达细胞BCL-2的病毒类似物BHRF1,赋予BL细胞抗凋亡活性和促生长优势,EBNA2缺失的EBV基因组可以在人源化小鼠中引起类似人类BL淋巴瘤的发生[15]。
2.2 HL
HL的特征是存在霍奇金-李-斯(Hodgkin-Reed-Steinberg,HRS)细胞。利用EBV特异性原位杂交技术检测到EBER在HRS细胞中的表达,证实了EBV与HL的直接联系[6]。HL中的EBV基因组也表达LMP1、LMP2A和EBNA1。端粒重复序列结合因子2(telomeric repeat binding factor,TRF2)可通过结合染色体末端并确保基因组完整性来介导端粒保护。研究表明,LMP1可以下调TRF2,导致端粒功能障碍、复杂染色体重排和多核性,从而诱导RS细胞的形成[16]。LMP1还可模拟活化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CD40的受体,募集细胞内重要的接头分子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TNF receptor-associated factor,TRAF)家族成员TRAF1、TRAF2和TRAF3,激活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NF-κB)诱导激酶/抑制剂激活酶,使NF-κB抑制蛋白α磷酸化。进一步激活其下游NF-κB信号通路,通过抑制细胞凋亡来促进细胞存活[1,17]。此外,LMP1还可诱导HRS细胞中异常激活的细胞信号通路,如改变细胞中DNA转录与活性水平的Janus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子(the Janus kinase/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JAK/STAT)通路、激活多种与肿瘤有关的基因如细胞周期素、胶原酶、溶基质素等表达的激活蛋白-1通路和可诱导强效共刺激分子CD137表达的磷酸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AKT)通路[18],有助于HRS细胞的异常转录。而LMP2A通过激活脾酪氨酸激酶,不仅导致甲基受体蛋白和PI3K激酶等功能都与B细胞受体相似的分子的激活,促进HRS细胞的生存,还增加NF-κB蛋白核易位,从而增加趋化因子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α的表达,以维持肿瘤微环境,间接促进了HL肿瘤的生存[9,19]。白介素-2受体CD25、趋化因子配体20(CC chemokine ligand 20,CCL20)在调控免疫细胞分化、发育及定向迁移过程中起重要作用,EBNA1已被证明可诱导HL细胞中CD25和CCL20的表达增强,并通过降低Smad2蛋白的半衰期,下调Smad2的表达,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靶基因肿瘤抑制因子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受体K的转录,从而促进HL的生成[20]。
2.3 DLBCL
DLBCL是最常见的非霍奇金淋巴瘤[4]。研究表明,在EBV阳性DLBCL的绝大多数病例中均检测到克隆性重排和体细胞高度突变[21]。进一步研究显示,EBV阳性DLBCL的形成与NF-κB和JAK/STAT信号通路的激活有关[6,22]。Kato等[23]对EBV感染的DLBCL细胞系进行体外研究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也证实,EBV感染可促进由LMP1C-端胞质结构域触发的NF-κB的激活和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3的磷酸化信号,促进细胞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显示60%EBV阳性DLBCL的病例存在T细胞受体基因重排“受限”或寡克隆[1],并且在EBV感染下的T细胞衰老、减少或异常也促进淋巴瘤的发生。研究表明,EBV阳性DLBCL的Ⅱ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蛋白及其转录共激活因子被破坏,BCR信号的完整性及其信号转导受影响,导致EBV阳性DLBCL的抗原捕获和提呈系统受损,同时T细胞过度表达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ligand 1,PDL1),从而诱导T细胞抑制,导致免疫逃避[24]。此外,EBV还可以诱导DLBCL的肿瘤微环境成分的改变,如LMP1通过诱导STAT1依赖的干扰素-γ分泌,促进B细胞增殖;而LMP2A和EBERs潜伏抗原以及EBV基因组的即刻早期基因(EBV-BZLF1)裂解抗原均促进白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的产生;由病毒抗原如EBER2和BZLF1触发的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和白介素-13(interleukin-13,IL-13)的上调也可能诱导利于EBV感染的肿瘤细胞生长和存活环境的形成[4]。此外,EBV转化的B细胞下调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分子的表达、EBNA3B中免疫优势T细胞表位发生突变,有助于肿瘤细胞逃避宿主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杀伤,逃脱宿主的免疫监视[22]。
2.4 PTLD
PTLD主要来源于移植患者的B细胞,通常与EBV感染有关。有文献报道[25],约80%的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显示EBV阳性。EBV感染不仅使PTLD表达所有潜伏抗原,也改变了miRNA的表达。Felal等[25]研究表明,miRNA-194过表达可增加EBV阳性B细胞淋巴瘤细胞株的凋亡,并抑制IL-10的产生,PTLD患者的基因阵列显示miRNA-194表达被抑制。EBV通过抑制miRNA-194来增加IL-10的表达,IL-10过表达会引起免疫抑制,促进PTLD的生成。PTLD的发病机制不仅涉及病毒的感染的作用,还有一些细胞基因的遗传或表观遗传改变。部分PTLD病例的特征是DNA错配修复机制缺陷导致的微卫星不稳定。此外,PTLD中细胞基因改变还包括细胞凋亡相关的基因如MYC、B淋巴细胞瘤-6基因(BCL-6)、p53的改变、DNA的高甲基化和原癌基因异常体细胞高突变。此外,免疫抑制药物的使用也促进PTLD的发生。器官移植后免疫抑制药物的使用虽然提高了移植的成功率,但会导致EBV特异性T细胞耗尽,降低T细胞的数量和功能,破坏免疫系统和潜伏病毒之间的平衡,从而使EBV从潜伏期重新被激活[26]。除此之外,EBV特异性T细胞介导的免疫监视功能受损导致淋巴母细胞增殖失控,最终导致移植受者出现PTLD[27]。
2.5 NK/T细胞淋巴瘤
虽然EBV感染B细胞更常见,但也可感染上皮细胞以及T淋巴细胞或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细胞)[2]。EBV感染NK和T细胞,可导致结外NK/T细胞淋巴瘤(extranodal NK/T-cell lymphoma,nasal type,ENKTL)。ENKTL是一种以结外优先受累、EBV相关性和发病地域多样性为特征的淋巴瘤[28]。EBV在ENKTL发生中的重要性于1990年首次被认识[28]。尽管NK细胞不表达EBV的主要受体蛋白CD21,但由EBV感染的B细胞通过突触转移激活的NK细胞,使其获得CD21分子,这些异位受体允许EBV与NK细胞结合,从而引发病毒感染[29];Smith等[30]通过中和抗体试验,也证明EBV利用病毒糖蛋白gp350和CD21进入成熟的外周T细胞。ENKTL细胞属于Ⅱ型潜伏感染,表达EBV基因EBNA1、LMP1和LMP2[1]。上述基因的表达已经被证明能够结构性地激活JAK/STAT、NF-κB等信号通路,从而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存活。有研究认为,LMP1在ENKTL中的表达可通过NF-κB途径上调肿瘤细胞PDL1,来促进肿瘤免疫逃逸[31];此外,LMP1还通过诱导细胞表面黏附分子CD23、CD40、细胞间黏附分子-1和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3的表达,上调抗凋亡蛋白如BCL-2、髓样细胞白血病蛋白-1、BCL2A1同源体、A20,来抑制细胞凋亡并促进肿瘤的发生[3]。
虽然EBV感染被认为是ENKTL发病机制中的早期因素,但附加的基因改变对于淋巴瘤的形成也是必不可少的。最近的研究中,利用二代测序技术在ENKTL患者中发现了频繁的JAK3激活突变[32]。ENKTL的基因组分析也显示,最常见的突变 JAK/STAT信号通路家族的成员,主要是STAT3,其次是肿瘤抑制基因BCL-6辅抑制因子、TP53、RNA解旋酶基因等[28,33]。EBV是激活STAT3的外部因素之一:EBV潜伏蛋白LMP1被认为是STAT激活剂、EBNA2是STAT3转录增强子的辅助激活因子以及JAK/STAT级联反应的下游元件PI3K调节亚基在所有ENKTL样本中都表达上调,导致细胞增殖和存活。Li等[34]研究证明,鸟嘌呤核苷酸结合蛋白q多肽(guanine nucleotide binding protein q polypeptide,GNAQ)基因通过抑制AKT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信号通路,来抑制ENKTL的生长,体细胞GNAQ T96S突变促进了ENKTL的发病。还有研究认为,ENKTL存在染色体异常,如6q21的缺失,导致许多抑癌基因如自噬相关蛋白5、正性调节区锌指蛋白1、叉头转录因子O3、黑素瘤缺乏因子1和E3泛素蛋白连接酶的表达缺失,抑制肿瘤坏死因子驱动的NF-κB激活而导致凋亡抵抗,促进ENKTL的发生[28,32]。
进一步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发现,ENKTL存在细胞周期蛋白的甲基化、组蛋白修饰以及去调控的miRNAs。启动子甲基化异常是ENKTL常见的致癌机制,可导致BIM、凋亡相关蛋白激酶1、蛋白酪氨酸磷酸酶6、甲基胞嘧啶双加氧酶2、细胞因子信号转导抑制剂6和天冬酰胺合成酶等多种抑癌基因的沉默,以及多重肿瘤抑制基因如细胞周期素依赖性激酶抑制剂2A、2B和1A等细胞周期调控基因的沉默,导致细胞正负调节信号不稳定,引起细胞恶性转化,发生肿瘤[28]。通过负性MYC调控Zeste基因增强子同源物2(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EZH2)miRNA介导EZH2的上调,使其在ENKTL中发挥致癌特性,促进细胞周期蛋白D1的转录,并通过NF-κB信号通路促进肿瘤的浸润性生长和不良预后[29,32]。表观遗传的另一类调节因子是EBV miRNAs,作为癌基因或肿瘤抑制基因发挥作用,诱导转录后的基因调控。有研究发现ENKTL存在大量对肿瘤生长有抑制作用的miRNAs,包括miR-146a、miR-26a、miR-26b、miR-28-5、miR-101和miR-363的下调[28],进而抑制细胞NF-κB通路,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其下调则促进肿瘤的发生[32]。
EBV诱导ENKTL细胞分泌IL-9[29],进而刺激肿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ENKTL还可分泌IL-2,通过诱导IL-10和干扰素-γ的产生,活化T细胞,促进细胞因子产生,刺激NK细胞增殖,并通过JAK/STAT通路间接上调LMP1的表达,促进ENKTL细胞生长。肿瘤坏死因子CD70与其受体CD27的连接(CD70/CD27)通路,导致T细胞的活化和增殖。EBV阳性的ENKTL细胞株特异性表达可以调控T细胞活化、增殖的CD70,其可通过与可溶性CD27结合,以剂量依赖的方式在淋巴瘤增殖中发挥作用。另外,CD27/CD70信号可能被LMP1上调[35],加速ENKTL的进展。
3 结语与展望
EBV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人群中[1]。尽管EBV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病机制有关,但其发病机制尚未阐明;虽然EBV体外感染模型已建立多年,但相关潜伏感染和裂解感染的EBV感染的具体策略,尚未明确。未来的研究应集中在复杂的调控网络与众多转录因子、病毒裂解/潜伏抗原及其相关关系方面。随着对EBV与控制细胞生长和存活的关键细胞通路更多且更深的了解,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并探索其与癌症的密切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