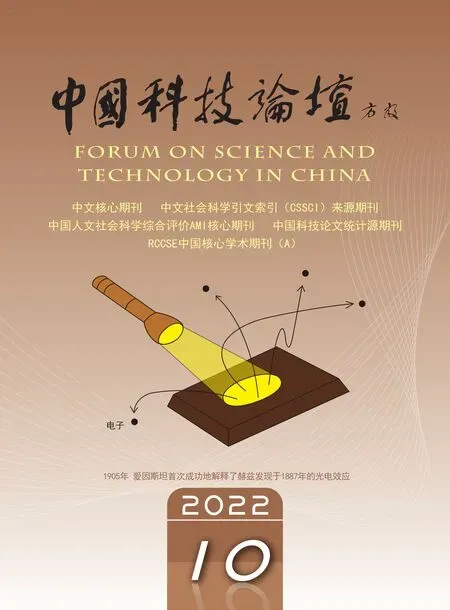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封凯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本刊编委)
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再次强调,要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面临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局,现阶段人们形成了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来解决重大创新问题的共识。但是,对于新型举国体制是否会导致政府扭曲市场,甚至导致重回计划经济时代,部分人士仍抱有担忧。要消除此类担忧,需要我们深刻地认识政府与市场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模式中应有的关系。
首先,政府角色不应是代替市场。政府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在于它在追求创新价值、承受投资风险方面的独特性。企业是产业创新的主力军,但由于企业的根本使命是追逐可预见的财务回报,它们对技术储备的投资始终是有限的。以美国作为成熟创新经济体的典型例子,政府部门 (如军事、能源、航天等)之所以在创新中扮演关键角色,正是因为它们所追逐的并不是自身的财务收益,而是本国对特定领域技术的主导权。这种政治性和战略性的行动超越了短期“经济理性”的约束,使政府各部门得以贯注于前瞻性和基础性的创新突破,从而使美国各政府部门得以与各种市场主体共同构建从关键科技发现、先导性应用,最后逐步过渡到产业化创新的全链条。换言之,由于政府的特殊属性,它对创新活动的参与产生了市场无法替代的作用,保持了创新经济的长期活力。由此,政府与市场之间是互为补充、互相协调的关系。如果政府将自身矮化为市场主体,例如国家为重要的基金设定追求稳定收益率的目标,那么它不仅挤占正常的市场空间,而且丧失了其应有的站位,使得真正需要长期冒险、系统性和开创性的技术创新无法得到投资,反而导致创新系统失灵。
其次,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是固定的。在国际竞争和产业结构性转型过程中,政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牵头投资于前沿关键技术,还在于帮助企业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完成本土创新生态的系统性转变。现代复杂工业产品往往涉及数量庞大的零部件和技术,大量 “卡脖子”技术本质上并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复杂的工程技术系统或者大量流程性技术的综合。后发国家企业很难单纯通过市场机制形成集体行动,这使得市场投资者无法对创新投资形成 “可计算” “可管理”的风险预期。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新型举国体制动员各相关领域参与者来解决瓶颈问题;同时政府通过采购提供初始市场、提供有退出时间表的补贴等政策手段,推动技术逐渐成熟、帮助市场投资者逐步形成可计算、可管理的风险预期。而风险预期的变化将不断重新定义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要求政府做出政策动态调整,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政府承担的任务应当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而不是财务性的。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在面临百年未遇之变局时推动创新转型的手段,政府既要解决特定领域关键技术有无问题,更要解决相应创新生态的塑造问题。为了培养创新生态,政府应当锚定于结果,重点关注是否形成国家重大使命对应的工业技术产品,而将实现技术产品的技术轨道、技术标准的选择权交予市场。政府应致力于通过提供产业创新所需的公共品,为更多企业进入降低门槛、提供条件。只有允许并鼓励多样性的技术方案,才能激励广大企业通过参与优胜劣汰的创新竞争来获取创新收益,而不是少数企业通过财政补贴、行政垄断来获利并导致创新枯竭,这样的创新经济模式才能真正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