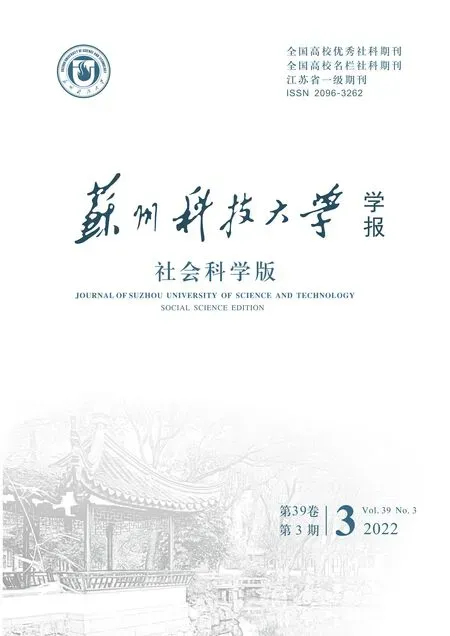从身份构成看“嘉靖倭患”的性质*
潘 洵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嘉靖倭患”的性质究竟如何,历来有多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是“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1]。尽管这种表述过于笼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追根溯源倭寇确实起源于日本,且后期真倭的罪行罄竹难书。所以说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是陈学文、宋烜等学者仍然坚持这种观点的原因所在。林仁川认为,嘉靖年间的“御倭”战争是一场“海禁”与“反海禁”、压迫与反压迫、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2]戴裔煊更加简洁,他认为“嘉靖倭患”归结到一点就是“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3]这个结论影响深远,得到很多学者的支持。樊树志更是将倭寇与“全球化”结合起来,提出“倭寇新论”,认为“倭患的根源在于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与日趋增长的海上贸易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1]。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是有的。吴大昕认为,“嘉靖大倭寇,只是大大小小不同集团的混称,根本从无统一的领导与相同的目标,从不存在‘反海禁’这样伟大的企图”[4]。“嘉靖倭患”源于走私贸易,肯定有“反海禁”的一面;但不管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正确与否,日本人以暴力的形式介入就改变了事件的性质。所以,笔者认为,“反海禁”一词并不能涵盖“倭患”的全部。
日本学界对倭寇的看法以“二战”为分水岭,前后有较大的不同。“二战”之前,日本学界普遍认为,倭寇是“日本人辉煌的海外发展”[5]5。“二战”之后,有学者将倭寇分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山根幸夫认为:
按其活动时间,通常把这种倭寇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即把活动于十四世纪中叶至十五世纪前半期的五十年间达到鼎盛时期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而把抬头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极猖獗地延续了数十年的倭寇称为后期倭寇。一般认为,前后期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前期倭寇的主体,正如文字所表明的那样,是日本人,其侵略的对象是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北部的沿海地区。这同日本国内南北朝时代的动乱是相对应的。与此相反,后期倭寇的主体与其说是日本人,还不如说是中国人。其侵略的对象也转移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6]
田中健夫没有沿袭前后期的分法,而是把倭寇分为“十四至十五世纪倭寇”与“十六世纪倭寇”,并强调“十六世纪倭寇的目的是强行走私贸易。暴行虽是倭寇的一个方面,但绝不是他的全部形象”[5]12-14。但在笔者看来,他们的目的并不单纯。(1)参见潘洵《试论“后期倭寇”概念中所隐藏的意图》,《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90~95页。山根强调“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田中更是将抢劫说成“强行走私贸易”,这是典型的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日本学者似乎有个通病,没有勇气承认本民族的历史罪行。
笔者认为,讨论某个历史事件的性质,除了要看它的具体内容及历史影响,还应该分析行为主体的身份构成。关于“嘉靖倭患”的具体内容以及历史影响,前人的研究已经颇为丰富,故笔者拟从身份构成的角度出发,重新梳理史料,探讨“嘉靖倭患”的性质,以求教于方家。
一、真 倭
《明史》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7]8353《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典籍也有相同记载。这些典籍所载的“十之三”应该只是个约数,并不确切。真倭究竟有多少,明代人没有讲清楚,现代人更加无从得知,但从其破坏程度来看应该不在少数。而这“十之三”的真倭身份究竟如何,却很少有人关注。
(一)有组织的真倭
有名真倭应该是真倭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受日本封建主派遣,有组织、有计划地在中国沿海实施抢劫犯罪活动。
1.有名真倭
李金明认为真倭都是由破产农民转变而来。[8]不可否认,倭寇队伍中存在部分破产农民,但他们应该不是真倭的主体。日本学者佐藤信渊指出,十六世纪初,伊豫国等处沿海的有关人士,“相商前往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他们“各集自己派下之浮浪人士”,乘船出洋,之后“四国、九州海滨之诸浪人、渔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2)参见佐藤信渊《御海储言》,转引自郑樑生《中日关系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22~123页。虽然佐藤没有讲明“有关人士”的身份,但既然他们有自己“派下之人”,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部属,这就表明其真正身份是封建领主,即日本战国时代的各级武士。
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
兵部尚书张时彻云,今奏拟五等赏功之例。曰首级:凡水陆主客官军民快,临阵擒斩有名真倭贼首一名颗者,升三级,不愿升授者,赏银一百五十两;获真倭从贼一名颗并阵亡者,升一级,不愿者赏银五十两;获汉人胁从贼二名颗者,升授署一级,不愿者赏银二十两。[9]338
了解日本历史文化的人都知道,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只有武士阶层才有姓氏(日语称为“名字”或者“苗字”),一般老百姓只有名字而无姓氏。显然这里的“有名”应该是指拥有姓氏的武士,而不是现代汉语中“著名”的含义。陈抗生称“倭首滩舍卖”为“不出名的倭首”[10],这显然是文化误读。明政府将“有名真倭贼首”与“真倭从贼”分开,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有名真倭贼首”是高级武士,或者说是大小封建领主。正因为他们的身份与“真倭从贼”以及“汉人胁从贼”不一样,所以赏格也比较高。
幕府时代的武士属于统治阶层,他们除了拥有姓氏,还享有“带刀”的权利,二者合起来就是“名字带刀”。倭刀制作精良,“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欹到,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11]。黄仁宇先生指出:“这种单刀的长度不过五尺,但在一个熟练的使用者手中挥舞,一片刀光,使‘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可以在一丈八尺的方圆内杀伤对方。”[12]242要达到这种熟练程度,必须从小练习。所以,黄仁宇先生认为,真倭是“职业化的日本军人”[12]243。这种观点非常有见地。
笔者认为,“有名真倭贼首”是日本战国时代的高级武士,“真倭从贼”则是指普通士兵以及破产农民。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较强的战斗力,是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巨大灾难的罪魁祸首,也是后来戚继光等人主要讨伐的对象。
2.真倭的组织
宋烜认为,“嘉靖倭寇的组成实际上是一种比较松散的组合体”[13]。就整个倭寇群体而言,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具体到真倭则值得商榷。倭寇不仅有“有名真倭贼首”,还有“真倭从贼”;既然有“首”有“从”,就说明真倭内部是有严密组织的。
《筹海图编》记载:
贼每日鸡鸣起,蟠地会食。食毕,夷酋据高坐,众皆听令,挟册展视,今日劫某处,某为长,某为队,队不过三十人,每队相去一二里,吹海螺为号,相闻即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队者,舞刀横行,人望之股栗远避,延颈授首。薄暮即返,各献其所劫财物,毋敢匿。[9]69-70
可见,他们不仅有严密的组织,而且在来中国之前应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将中国的城市村落,绘成图册,随身携带,然后有计划地按图劫掠。
又,赵文华《嘉靖平倭祗役纪略》记载:
(嘉靖三十四年)众贼合伴共有七百余船开洋,大者每船二三百人,小者三四十人,各自备饭米,在海十一个日,每日西南风不便,吃尽饭米复又转去。至六月十四日重开前船行驶,遇先来倭船二十一只回去,各相招呼问信。其回船上人说,今年不比上年,大唐官兵十分凶狠,三分中被他杀了一分,众皆惊骇,就转者不知其数,只有三船前来,约贼二百五六十人。[14]76-77
笔者认为,这种白描式叙事方式可能掩盖了问题的真相。首先,七百多条船只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不能令行禁止,很容易造成混乱。其次,海上风大浪高,如果没有相应的通信手段,则很难保持有效的联络,并可能导致混乱。因此,如此大规模的航海,其背后必定有一个严密的指挥系统以及信息传递系统。王直曾经“更造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15],其目的应是将它作为旗舰使用,以便指挥船队,而不仅仅是作为“徽王”的身份象征。庞大船队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真倭是个有组织的群体。
(二)无组织的真倭
除了有组织的有名真倭,真倭群体还存在一群数量庞大的落魄武士与野岛小夷。
1.落魄武士
应仁之乱后,被大明朝廷封为“日本国王”的将军徒有虚名,幕府已经不能号令天下,只是畿内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1491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群雄割据,互相攻伐,整个国家陷入战争之中。战败方的武士失去了原有领地,丧失了生活来源,于是他们蜕变为海盗倭寇,将矛头转向中国。
早期他们受雇于中国走私商人。海上走私并不安全,于是很多商人“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借其强悍,以为护翼”[16]36。许栋、王直盘踞双屿港时期,“许二、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骁勇而善战者,蓄于舟中,泊于双屿,列表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夷人欺其单弱,杀而夺之。接济者不敢自往,聚数舟以为卫。其归也,许二辈遣倭一二十人持刀护卫”[9]279。但是,这些落魄武士在完成护送任务后,也会乘机沿途劫杀其他商人,给走私贸易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日本战国时代,随着兼并战争的发展,破产武士越来越多,他们往往啸聚成群,来中国沿海劫掠。嘉靖三十四年(1555)九月,一股六七十人的倭寇自杭州北新关登陆,西剽淳安,途经安徽歙县、绩溪、旌德、泾县、南陵、芜湖、太平府,甚至一度威胁到留都南京,最后被明朝官兵剿灭在南京附近的杨林桥。这股倭寇深入中国内地,杀人放火,犯下滔天罪行。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很少有人追问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他们应是日本国内战争中失败的落魄武士,来中国的目的就是抢劫,由于没有同假倭、从倭相勾结,所以路径不熟,迷失了方向,以致惶惶不可终日,出现“一昼夜奔百八十里”[7]8353的现象。
2.野岛小夷
野岛小夷主要是指日本周边小岛上的农民。王直等中国武装走私集团流窜日本后,就盘踞在西南外海的五岛列岛。五岛位于九州西南海域,距离日本本土约100公里。就位置而言,五岛非常适合王直残余势力盘踞,也有利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
蒋洲、陈可愿到达日本时,见到王直“据居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7]8355。但实际上这部分日本人听王直的“指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有利可图。一旦失败,局势就会发生变化,甚至逆转。“直初诱倭入犯,倭大获利,各岛由此日至。既而多杀伤,有全岛无一归者,死者家怨直。”[9]285“死者家”表明去中国抢劫的倭寇在岛上有家属,是有家有业的常住居民,不是海盗。但日本学者却称之为“海盗”,比如木宫泰彦曾说王直“自称徽王,指挥日本三十六处的海盗,一再劫掠明朝海岸”[17]。这是偷换概念,推脱责任。
二、假 倭
《明史》将倭寇群体中的中国人统称为“从倭”。这种称呼是否正确,有待商榷。实际上,我们可以根据其是否髡首、是否着倭服等特征,将之细分为“假倭”与“从倭”两个群体。
(一)去而复返的假倭
双屿港之战后,许栋下落不明,以王直为首的徽州海商与以陈思盼为首的福建海商之间出现矛盾,走私集团面临重组。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移檄王直等拿贼投献,姑容私市”[18]207,就是分化利用,以盗制盗。王直一方面希望与官府维持友好的合作关系,达到实现互市的目的;另一方面排除异己,捉拿了卢七、陈思盼等献给官府。此后,官府虽然没有兑现承诺,但也没有明令禁止,而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嘉靖三十一年(1552)“壬子之变”爆发,黄岩县被攻破,俞大猷等“乃议王直为东南祸本,统兵击之于烈港,追至长途(岛),次马迹潭”[18]218。王直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他本人则乘台风突围去了日本。
张声振认为,倭寇是外来的日本人,并且强调:“我们总不能认为这3500人和20 000余人,是明朝乡民先乘船到日本,再从日本随徐海乘船劫掠明朝沿海各地吧?”[19]对此,笔者持不同意见。首先,王直集团本身就是被明军驱赶到日本的,这是事实。木宫泰彦认为,随王直突围到达日本的走私商人有2000人左右。[17]其次,王直到了日本以后,彻底绝了互市的念头,“遂起邪谋,招聚亡命”[15],完全从走私商人转变为海盗。在王直的招引下,更多的中国走私商人投向日本。《嘉靖平倭祗役纪略》记载:
嘉定知县杨旦禀称,该县逃回民人倪淮供:“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内被倭贼拦抢上船,跟到彼处,只见漳、温两处人无数在彼,衣帽言语一般,说这里是日本国所管,地名五斗山,种植稻禾、绿豆、大小二麦、菜蒜等物。但来打劫俱是漳州人指引。”[14]75-76
汉语“五斗”一词的日语读音与“五岛”相同,均为ごとう。笔者认为,“五斗”应是指五岛列岛。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记载:“审擒获贼首李哪哒亦称:渠魁沈南山等,安住倭国,分遣其党,同倭入寇。”[20]这说明他们确实是先乘船到日本,再回到中国劫掠,是真正的勾引者。
王直等到中国东南沿海劫掳时,往往“袭服饰旗号”[7]8352,并在船上张挂“八幡大菩萨”[21]旗帜,“每残破处,必诡云某岛夷所为也”[16]40,他们故意将自己装扮成倭寇。正是这个原因笔者称之为“假倭”。嘉靖二年(1523)的宁波争贡事件,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恐倭心理。[22]对于这种情况王直等应该是知之甚稔,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利用这种心理制造恐慌,便于其实施劫掠。
(二)由“被掳人”转变而来的假倭
“被掳人”也是假倭的重要构成部分。“被掳人”是指被倭寇劫掳的普通平民,他们本来无心为盗,一旦被掳,遭髡首之后,无法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只能同流合污,成为倭寇的一部分。尽管在早期的抗倭斗争中明军败多胜少,但在长期的战斗中,倭寇数量不断减少,需要补充兵员。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海因为兵员不够,连续三次设宴,诱骗驻地附近居民赴宴。第三次时,“远近壮夫赴席者至二三百人。酒半出刀剪,发髡其首,咸劫为用”[23]。这种情况在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冯梦龙《杨八老异国奇逢》中的杨八老便是“被掳人”之一:
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挨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24]
虽然这是小说家言,但它反映的是明代社会对假倭的认知,是可信的。
其实明代人已经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归有光就曾指出:“其内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25]李恭、郝杰讲得更为清楚,“昔为唐人,今为倭也”[26]。
三、从 倭
《明史》载,倭寇中从倭者达70%之多,其中除了部分假倭,大部分都是从倭。从倭是指真倭、假倭登陆后,主动投靠倭寇,乘机打劫的编户齐民。其主体是小民“好乱者”,当然也包括部分流民。嘉靖年间,自然灾荒以及吏治腐败等造成经济萧条、百姓流离失所。正如王邦直所言:
臣见近年以来,差繁赋重,财尽民穷。有司无优恤之仁,吏多科害之扰。丁户已绝,尚多额外之征;田土虽荒,犹有包摊之累;里甲浪费,而日不聊生;刑罚过严,而肌无完肤。民不能堪,往往流移他处,以全性命。自一州一县言之:大约流移之民,恒居其半。[27]
流民无以为生,“一闻倭至,又乐从之”[28],因而成为“从倭”。这些人基本上没有髡首,能够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徐宗鲁分析了倭寇数量的变化,指出倭寇“初以十计,渐至数百、数千之众”,不久“聚而为几万矣”,“名虽倭寇,实由漳泉宁郡之民勾结为乱”。[29]林希元《与俞太守请赈书一》记载:“海寇登岸,杀居民、栖淫妇女、索银赎命,闻皆各处穷民投附,助成其势,莫之敢御。”[30]将相关史料相互印证即可发现,“倭寇”中真倭不多,假倭也不多,真正大量存在的是“好乱者”以及“穷民”,或者说流民,即郑晓所说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31]。不过,他们不是下海,而是趁倭寇登岸之时加入其中,充当从倭角色。
福建民风剽悍,早期通番者多,后期从倭者更多。茅坤记载了一个“被掳人”的所见所闻:
归语海寇大约艘凡二百人,其诸酋长及从,并闽及吾温台宁波人,间亦有徽人,而闽所当者什之六七。所谓倭而椎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此可见诸寇特挟倭以为号而已,而其实皆中州之人也。[32]
《漳州府志》记载:
中丞阮鄂帅兵讨倭,倭走南澳。乱民从倭集梅岭且万家,众往屠之。……中丞曰:“其在浙直为贼,还梅岭则民也,奈何毕歼之。”[33]
景观评价是一种人们的感官判断,通过航拍测得的数据和影像可以使人们的判断更加可靠,景观评价的可信性就越高。这种系统的构建有助于提高景观评价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这个群体中真倭只有十几个,装束也与从倭不同。再据阮鄂“还梅岭则民也”的态度来看,他们应没有“发髡其首”,还能脱离倭寇队伍,重返正常的社会生活。
从漳、泉两地从倭者多达万家的情况来看,这种天然的地域联系使他们自成一体,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倭寇来时则趁乱抢劫。所以,章焕认为“此东南之大变,皆奸民酿之也”[34]。
四、真倭与假倭、从倭的关系
学术界对“嘉靖倭患”的性质之所以不能达成共识,除了没有认识到“假倭”与“从倭”的区别,还因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日本封建主利用王直集团
王直等走私商人逃亡日本后,处境颇为艰难。首先,日本对中国商品需求量很大,如果不能满足平户藩主松浦隆信的要求,王直等将失去利用价值,难以在日本立足。其次,随王直突围到达日本的约有2000人,王直必须找到足够的财源才能维持集团的运转,否则集团将面临解散的危险。王直与松浦隆信的关系究竟如何,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难以了解详细情形。但是,松浦家文书《大曲记》提供了一定的信息:
道可氏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的从大唐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的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开始驶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界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35]
“利用”一词表明,松浦隆信与王直之间不是对等的合作关系,而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西园闻见录》记载:“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显见叩头。”[36]可见,萧显见到日本船主时必须“叩头”,恐怕王直也不能例外。
日本地方大名收留中国走私商人,为他们提供基地,支持乃至直接参与抢劫行动,这是判定“嘉靖倭患”性质的关键点之一。
(二)互相利用
真倭群体不仅包括有组织的有名真倭,也包括部分破产的武士与农民。他们来到中国以后,由于语言不通、地理不熟等,需要假倭、从倭为之向导,而假倭、从倭又需要借助真倭的身份符号,利用明军的恐倭心理实施抢劫,他们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由此,我们既能看到有关中国人指挥日本人的记载,也能看到日本人指挥中国人的记载。
一方面,中国走私商人寓居日本,这为他们与真倭互相勾结提供了方便。万表曾参与抗倭斗争,对王直集团的成员构成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王直等“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借其强悍以为羽翼”[16]36。胡宗宪擒获真倭,“俱系日本所属野岛小夷,为中国逋逃所引”[37]。所谓的“野岛小夷”应该是指“贫倭”,也就是李金明所说的破产农民,如果没有人勾引,他们不一定有到中国打劫的念头。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副使许东在柘林生擒的“倭贼助四郎”[38],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在台州长沙之战中生擒的“倭酋五郎、如郎、健如郎”[5]257,即是此类。很显然,野岛小夷都有名而无姓,不是拥有“名字带刀”特权的武士。在这个群体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勾结、互相利用。但真倭居于从属地位,王直等仅仅是“借其强悍”来吓唬人而已。
另一方面,从倭则是在倭寇登岸后,再与之勾结,为之向导。萧显抓获杨元祥后,“问以城中金帛数。元祥言:‘府库之藏已迁入苏州,不若南翔之富也。’遂导之以南”[36]。又,唐顺之《条陈海防经略事疏》记载:“以臣所亲见,三沙千余倭子,起自瓜州,一被掳人冯三嗾其扬州取宝,遂至哄然远来。”[39]就史料记载来看,杨元祥是问而后答,冯三则是主动泄露信息的。何以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不得而知。正是这些从倭的参与,才使得倭寇能够深入腹里,荼毒东南。从倭者不仅为倭向导,而且泄露军情。《郑开阳杂著》记载了军中奸细与从倭私通的事件:“贼中多有水手,亲识前日苍山船尾前锋,遇贼交语而走。沙船等船从而俱走,可以鉴矣。”[40]南直地区缺少大船,难以抵抗倭寇,于是新建大型福船,同时从福建调来水手驾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闽人与倭寇勾结至深,不仅不抗倭,反而泄露军情,导致倭寇逃脱。
这些从倭与真倭勾结,不仅泄露地方财政信息,泄露军情,为倭向导,甚至还乘机打劫,是倭寇的帮凶。其危害之大,难以估量。
五、结 语
“壬子之变”之后,王直等人完成了从商人到海盗的身份转变。如果事情就此结束,那么很容易就能得出“嘉靖倭患”的性质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一场动乱,其目的就是“反海禁”。但问题是,历史并没有止步于此。随着真倭的介入,“嘉靖倭患”的性质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日本地方封建主不仅接纳王直,为他们提供后方支持,纵容他们与日本落魄武士、野岛小夷相勾结,甚至还直接派出规模不等的有名真倭参与抢劫行动。真倭的介入,使得王直等具备了抗衡明朝官军的实力,刺激了流民、不逞之徒参与抢劫活动的欲望,扩大了中国社会动乱的范围。尽管表面看来真倭仅占30%左右,但他们是这场动乱的核心力量。他们攻取州县,盘踞地方,私开府库,挖掘坟墓,绑架索赎,奸淫劫掠,无恶不作,其罪行罄竹难书。因此,“嘉靖倭患”从表面看是以中国人为主,但实际上是受日本地方封建主操控、有武士集团直接参与的、以抢劫财物为目的的社会大动乱。
追根溯源,“嘉靖倭患”源于明政府的海禁政策;究其本质,平倭战争是抗击外来侵略;归根结底,真倭的历史罪责不容否定。
——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