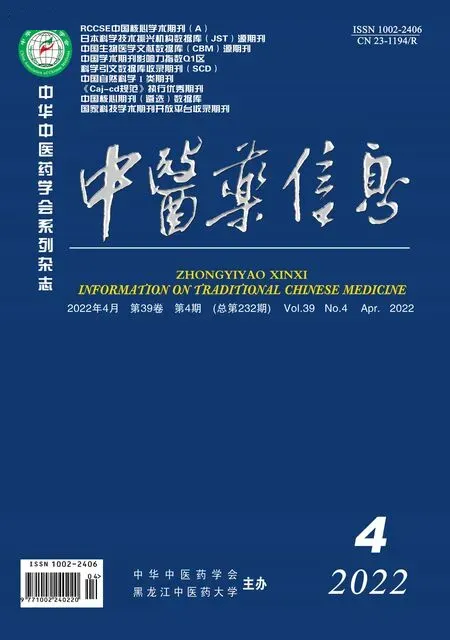针刺辨证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研究进展
徐妙,陈付艳,张香香,王芳,陈垲艺,韩林,吴帮启✉
(1.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1617;2.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381)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功能性胃肠道疾病,其症状是出现与大便性状或频率变化相关的腹痛、腹胀以及腹部不适[1]。该病为消化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在亚洲国家的发病率为5%~10%[2]。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环境的变化,本病发病率呈逐年增加趋势。目前,IBS 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尚不完全清楚,但考虑与脑-肠轴功能紊乱,内脏超敏反应和中枢神经系统改变相关[3]。根据罗马Ⅳ标准,通过Bristol 粪便性状量表,IBS 可分为4 种亚型,研究表明在我国部分地区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ith predominant diarrhea,IBS-D)在4 种发病亚型中占首要地位[4],西医治疗IBS-D 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心理治疗以及药物治疗[5],但临床疗效不尽如人意。
IBS-D 属于“泄泻”及“腹痛”的范畴。《医方考》云:“泻责之脾……脾责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泻。”IBS-D 其病位在肠腑,与肝、脾、肾关系密切。根据专家共识意见[2],IBS-D辨证分型通常为肝郁脾虚证、脾虚湿盛证、脾肾阳虚证、脾胃湿热证和寒热错杂证。中医治疗IBS-D 疗法多样,口服汤药、针灸、推拿等被广泛应用。大量系统评价及Meta 分析结果显示针刺治疗IBS 具有显著疗效[6-7],针刺治疗IBS-D,优于常规口服西药,可改善临床症状,降低患者的复发率[8]。针灸作为中医疗法的一部分,常用的辨证方法是经络辨证与脏腑辨证,此两种辨证方法通常与八纲辨证相结合,IBS-D 作为一种脏腑病症,在针刺治疗时通常采用脏腑辨证。笔者查阅关于针刺治疗IBS-D 的文献,总结目前针刺辨证在IBS-D 的应用及针刺治疗不同证型IBS-D的机制研究。
1 针刺辨证治疗IBS-D
据统计,针灸治疗IBS-D 的常用穴位频次由高到低为天枢、足三里、三阴交、中脘、脾俞、太冲、上巨虚、阴陵泉和下巨虚[8]。对于不同证型IBS-D 针刺取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1.1 肝郁脾虚证
《素问·举痛论》言:“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脾病者……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IBS-D 的发病与情志因素、素体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肝郁脾虚证有不同的取穴方法:①多选用太冲、百会、印堂,以疏肝调神解郁[9-11];②重用背腧穴,大肠俞、肝俞、脾俞,以健脾疏肝[12-15];③采用头针穴位,例如顶旁2 线、额中线,其安神定志之功效可以缓解肝郁之气表现的情绪问题[12];④独取足厥阴肝经腧穴,其疗效优于口服西药及中药组[16];⑤独取内关穴调节情志,疗效显著[17]。
1.2 脾虚湿盛证
《素问·六元政纪大论》言:“湿胜则濡泄,甚则水闭胕肿”。在临床试验研究中以针刺为主治疗IBS-D 脾虚湿盛证,其穴位主要分布在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脾虚湿阻证选穴方法为:①选用足太阴脾经特定穴大都、商丘、阴陵泉,手少阳三焦经经穴支沟,膀胱经的束骨与肾经的太溪,共同调节水湿运化,有利于水湿从不同的渠道外泄[18];②在高频穴的基础上以脾俞、肝俞、太冲调胃肠、补肝脾,取公孙、太白振奋脾阳、运化水湿[19];③在常规取穴的基础上联合其他疗法治疗IBS-D脾虚湿盛证,如穴位敷贴及TDP灯照射[20]。
1.3 脾肾阳虚证
《景岳全书·泄泻》曰:“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所以二便之开闭,皆肾脏之所主,今肾中阳气不足,则命门火衰,而阴寒独盛,故于子丑五更之后,当阳气未复,阴气盛极之时,即令人洞泄不止也”。在针刺治疗IBS-D 脾肾阳虚证的文献中,其辨证取穴频次由高到低分别为命门、肾俞、脾俞、大肠俞、关元、神阙、中脘和气海等。其主要特点为:①重用任督二脉及足太阳膀胱经上的背腧穴,其取穴方法以局部取穴的近治作用及俞募配穴法[21-26];②多用灸法以温肾助阳、健脾止泻[21]。
1.4 肠道湿热证
针刺治疗IBS-D 肠道湿热证,选用曲池、阴陵泉,此二穴为大肠经与脾经的合穴,“合治内腑”有健脾利湿、通利三焦之功,同时曲池可清泄腑热[22,27-28]。
1.5 寒热错杂证
高军等[29]治疗不同证型的IBS-D,对于寒热错杂证配上巨虚、大肠俞、阴陵泉、三阴交。该研究总有效率为90.63%,但各证型之间的疗效未明确。
1.6 其他针刺治疗IBS-D的取穴方法
当前临床治疗也有其他取穴方法,例如调神针法[30-31]、灵龟八法[32-33]、夹脊穴[34-35]或其他特定穴[36]治疗IBS-D,其中调神针法是目前针灸治疗IBS-D 的热点,其在常规取穴的基础上多加百会、印堂、神庭、本神和太冲,该选穴方法与肝郁脾虚证相似,但并未有文章比较调神针法治疗不同IBS-D 证型的疗效差异。亦有单独选用几个特定穴配伍来治疗,常用手阳明大肠经的特定穴,或只选用背俞穴和夹脊穴治疗IBS-D。
2 针刺辨证治疗IBS-D的机制研究
现代医学对IBS 的病理、生理学研究尚不完全清楚,其可能潜在机制包括脑-肠轴相互作用、内脏高敏感、胃肠道感染与炎症、肠道菌群紊乱、胃肠动力异常、遗传和心理社会因素等[37]。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当前针灸治疗IBS-D 的临床机制研究多聚焦于脑肠肽、肠道菌群及炎症因子,而患者以肝郁脾虚证为主,其他未辨证的患者多采用调神针法治疗。
2.1 肝郁脾虚证针刺机制研究
2.1.1 脑肠肽
脑-肠轴异常被认为是IBS-D 发病机制之一,脑肠肽是中枢神经系统、肠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联系的媒介,研究表明参与IBS-D 脑-肠轴异常调控的脑肠肽有很多种,主要有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血管活性肽、神经肽Y(Neuropeptide Y,NPY)、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CGRP)、胆囊收缩素、P 物质、胃动素、生长抑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等[38]。通常机体受到刺激的情况下,脑肠肽会异常表达,从而介导腹痛、腹泻的发生。布立影等[39]在西药治疗基础上给予健脾疏肝针刺,李桂英[40]在补脾益肠丸的基础予以针灸治疗均可以有效降低患者5-HT、NPY 与CGRP水平,显著缓解患者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状态。
2.1.2 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失调是IBS-D 发生的机制之一,生理情况下,肠道正常菌群各菌种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共同参与构成肠道的生物与免疫屏障,防止病原体通过肠黏膜进入人体。病理情况下,肠道微生物之间共生关系瓦解、肠道菌群失调,一方面以双歧杆菌、乳酸菌为主的益生菌数量明显减少,各菌群之间正常比例严重失调;另一方面是肠道正常菌的异位定植和一些机会致病菌,如致病性肠杆菌大量生长繁殖,从而导致肠黏膜屏障功能、肠道免疫功能的紊乱。张星星等[41]采用健脾疏肝方联合针刺治疗肝郁脾虚型IBS-D,与正常组比较,IBS-D 患者肠道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下降,肠杆菌升高,同时伴有明显的肠道菌群定植抗力减弱,针药治疗后能有效调节肠道菌群丰度,增加有益菌肠道定植力,改善患者的症状。
2.2 未辨证IBS-D的针刺机制研究
目前针灸临床机制研究主要讨论肝郁脾虚型IBS-D,有部分研究并未将IBS-D 辨证分型,多采用健脾调神针法治疗,能调整患者的脑肠肽、肠道菌群及炎症因子从而改善症状。例如,通过分析IBS-D 与5-HTT 基因多态性区的相关性发现,三种基因类型中,IBS-D 患者SS基因型的比例更高,且针刺组LS 和SS基因型患者的疗效优于LL基因型患者,这可能是针刺增加了SERT mRNA 的表达、加快5-HT 重摄取速率、降低突触间隙中5-HT 水平有关[42]。陈璐等[43]研究发现,IBS-D 患者肠道微生物中拟杆菌门相对丰度显著降低,厚壁菌门相对丰度显著升高,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高于健康人,“调神健脾”针法可改善IBS-D 患者腹痛、腹泻症状,可能与改变肠道菌群结构与多样性、降低粪便中短链脂肪酸含量有关。益生菌联合针灸治疗IBS-D 可显著降低患者腹部症状积分,改善症状,同时可以降低患者血清中促炎因子IL-8和TNF-α水平,提高IBS-D患者血清中抗炎因子IL-10 水平,调节患者体内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平衡[44]。
3 展望
根据专家共识意见将IBS-D 分为5 种证型[2],辨证针刺IBS-D 的文献主要以肝郁脾虚证及脾肾阳虚证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辨证取穴的应用中,其选穴方式多样,非辨证取穴中调神针法是目前的研究热点,其选穴与肝郁脾虚证类似。现代机制研究证实,针刺可有效调节脑肠肽、肠道菌群及炎症因子,从而缓解患者症状,而研究多以疏肝健脾、解郁安神的取穴为主。
通过回顾针刺治疗IBS-D 的文献,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首先采用辨证针刺治疗IBS-D 的研究较少,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结局指标多以主观量表为主,欠缺客观评价临床疗效的指标,临床疗效缺乏可靠性;其次,相同证型的IBS-D 取穴存在多样性,其疗效是否存在差异?不同证型的IBS-D 采用同一治疗方法,例如调神针法,作用疗效有无差异?各证型IBS-D 的中医病因病机不同,而现代医学机制研究是否也具有差异性值得进一步探讨。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根据循证医学模式建立针灸诊疗规范,优化取穴方案,加强针灸对不同证型的疗效观察及远期疗效的评估,加强中西医结合,以进一步评价针灸治疗IBS-D 的临床疗效,探究针灸治疗IBS-D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