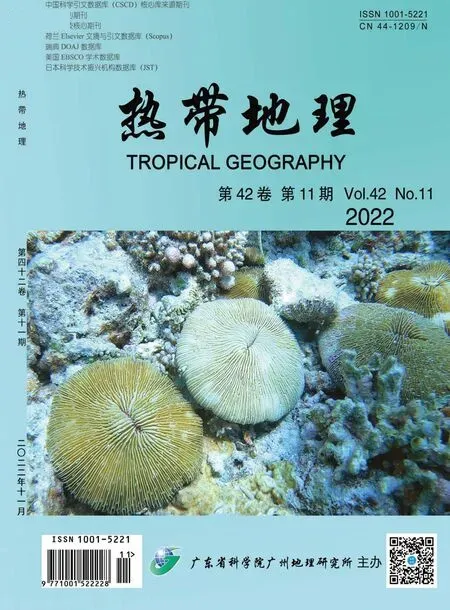城乡之间:当代农村家庭的空间生产何以可能?
陈景亮,潘小焮,张 冬
(闽南师范大学a.社会工作系;b. 科研处,福建 漳州 363000)
不同于西方的人口迁移流动,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的勾芡,催生出“农民工”(陆学艺,1989)、“留守儿童”(上官子木,1993)、“留守老人”(刘炳福,1996)、“老漂族”(刘庆,2012)等特殊群体。城乡二元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城乡家庭发展悬殊,进城(务工)成为许多农村家庭的生计策略,但家庭的根基依旧在农村。流动中国①段成荣、杨传开、朱建江等学者分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流动人口数据后,提出了迁徙中国、流动中国、迁徙时代等相关表述。时代,农村人口部分继续流入城市②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显示,全国流动人口37 582 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 484 万人,省内流动人口为25 098万人。,部分回流农村,部分继续驻扎农村。在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技术支持下,城市与农村往来更加便捷。即便是驻扎农村,家庭及其成员在生计模式、生活方式上与城市之间的联结也越来越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强调要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在时空压缩(戴维·哈维,2003)的当下,驻扎农村的家庭如何与城市联结,城乡联结背后家庭发展有何诉求,共同富裕目标又该如何精准因应当前农村家庭发展诉求?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城乡关系是中国农村家庭发展重要的情境要素。城乡二元体制下,家庭被禁锢在农村,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乡土社会中家庭发展空间有限,城乡家庭差距不断扩大。鉴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分割效应,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被陆续提出。拆除城乡二元分化的户籍制度藩篱,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被广泛建议(蔡昉,2001;赵燕菁,2003;邓海峰等,2010;梁琦等,2013;辜胜阻等,2014)。城乡可持续发展需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不平衡(肖雁飞等,2008),部分学者提出尽快实现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换(王国敏,2004),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城乡三元结构化(王春光,2011)。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并提出要推进完成1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乡村经济、乡村社会和乡村空间都得以重构(李红波等,2012),这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肖锦成等,2013)。但在这一进程中,农村家庭规模缩小速度快于城市,农村孩子接受优质和高等教育前景堪忧,家庭支撑孝道文化的制度和经济基础都发生变化(唐灿,2005)。农村中青年子代夫妇出外增多,三代直系家庭上升,标准核心家庭下降,隔代等不完整家庭类型增多(王跃生,2019),并发展出新三代家庭(黄宗智,2011)、城乡两栖(王春光,2019;白美妃,2021)、新联合家庭(齐燕,2019)等城乡家庭模式,以及“半工半耕”(黄宗智,2006;夏柱智等,2017;李永萍,2020)、非农化(杨善华,2009)、一家两制(杨重光,2009;吕德文,2021)、一家三制(刘超,2022)等农村家庭发展秩序。无论哪种家庭模式或发展秩序,城市或城镇的家一直都是农村家庭发展的重心,但进城并非农村家庭最佳发展路径,部分地区“农转居”后家庭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社会资本急剧削弱等问题(刘建娥等,2018)。
城市与农村的空间分割自古有之,城乡空间一元化并非农村的终点。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习近平,2022a)。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2022b)。因此,农村还将是中国重要的单位,是家庭重要的生活场域之一。上述研究勾勒了农村的区位角色以及农村家庭发展的政策路径,集中关注了农村家庭发展的外出行径,论述了农村家庭成员进城务工及其在城市生活压力、家文化等影响下,以进城为主导的代际合作式家庭发展情境。然而对于驻扎在农村,以农村为主要发展场域的家庭,从空间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并不多。为此,本研究以驻扎在农村的家庭为主体,尝试分析农村家庭在城乡之间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及其表征性空间,并试图在共同富裕视阈下寻找因应时代特征的农村家庭发展空间策略。以期深化和推进家庭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在城乡关系、乡村振兴等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
1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1.1 分析框架
格奥尔格·西美尔(2002)指出,空间总是被占据性地使用,而占据一旦形成,空间就会有自己的边界,继而产生某种程度的排他性。罗伯特·戴维·萨克(2010)进一步指出,空间本身是一个“构序系统”(ordering system),是特定的结构秩序的象征与表现。当代社会空间重建的结果已成为不平衡发展的结果(马克·戈特迪纳,20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户籍制度作为实施人口管理的主要政策,按照家庭成员关系及地理位置把人口划分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进而形塑边界清晰的城市和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城乡二元对立。但空间不只是地理工具或者社会交往的外部环境,也可能引导社会成员展开行动,追寻空间权利,实现空间诉求(营立成,2017)。与外出务工的家庭一样,当前驻扎在农村的家庭不断地冲击既有的农村空间迈向城市,农村家庭在生计模式及生活方式上与城市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亨利·列斐伏尔(2008)指出,空间在建立某种总体性、某种逻辑、某种系统中可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起决定性的作用。空间作为社会实践的场所与中介,不只有自然属性,还蕴含了符号、意义与意识形态等社会性,应该在“生产”语境下描述(Henri Lefebvre,2009)。他将空间与社会生产紧密联系,提出包含空间实践(Spatial Praxis)、空间表象(Representation of Space) 和 表 征 性 空 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3 个要素的空间生产理论(亨利·列斐伏尔,2021)。该理论在国内被应用在诸如老年流动人口(江立华等,2016;杨菊华,2021)、老年护理队伍(任杰慧,2021)、社会福利制度(陆影,2021)、社区治理(崔宝琛等,2020;操小晋等,2022)等领域。在农村家庭相关研究中,城乡空间表象下的社会关系被广泛关注,但空间多维的立体关系研究则相对较少。空间并不是农村或城市的专属或产物,而是农村与城市在一定情境下发生的新的空间性关系结果。对于被二元分化过的农村家庭的发展,现代化进程中新的城乡空间关系是需要被关注的一个面向。
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以“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等方式搭建起城市的家或者城乡两头的家,即便因为“家”触发回流意愿,但还需要“业”的强化(谢永飞等,2022)。城市化进程中,城镇或城市的家是否是农村家庭的必经阶段?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时代,农村家庭以农产品为主要资源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谋取生计,生成“居住在农村-从业在城市”的城乡二元物理空间镶嵌,并在教育、医疗等服务中对城市社会空间加以效仿,勾勒一幅农村家庭每日在城乡穿梭的空间实践图景,建构表象为农村家庭在城乡二元物理空间中共同富裕的发展诉求。但基于城乡现实情境,农村家庭仍表现出对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生活的不自信,农村社会的人伦与位育日渐式微。本研究构建的农村家庭的空间生产分析框架见图1所示。

图1 农村家庭的空间生产分析框架Fig.1 The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rural families
1.2 研究方法
采用案例研究法,选择W村作为案例,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式开展。W村地处东南沿海某一三线城市,所在县属于山区县,是省级重点林业县,农村与农业属性显著。区位上属于X经济特区半小时经济圈内,交通便捷,与周边城市往来密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的一手资料主要来自2020年12月—2021年12月在W村田间地头以及村庄内的访谈,访谈对象为居住在W村的村民。共访谈了9个个案,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个案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 interviewees
W 村包含10个社(即“自然村”),以种植业为主要产业。主要种植笋(13.4 hm2),占农民收入15%;蔬菜(33.5 hm2),占农民收入30%;柚子(33.5 hm2),占农民收入30%。还种植黄龙果6.7 hm2,另有蔬菜种植基地6.7 hm2左右。W 村所在镇区有1 家台资菌菇厂,每年用工大约120 人。截至2021 年12 月,W 村有924 户,共3 484 人。流入流动人口53 人,流出流动人口75 人,主要流向县城及Z市、X市③数据来源:2021-04-12在W村实地调研时,由W村村支书提供。。
2 农村家庭发展的空间实践
2.1 空间穿梭:家庭发展的“城乡日摆动”生计
2.1.1 “乡-城”生计模式 W 村位于镇中心,在W 村的地理中心点每隔5 天就会赶“圩”(集市),全镇各村以及邻镇村民都会集中在此买卖。W村村民一直都有种植蔬菜、饲养家禽等来集市售卖的传统。当前便捷的交通为W村村民提供了当日往返Z市、X 市、Q 市的可能。各家种植的蔬菜或饲养的家禽每天晚上7 点前被村民收购一空,第二天5 点左右被送往X 市或Q 市各社区门店售卖,午后2点左右村民自驾从X市或Q市返回W村再次收购。当日往返,村民没有房租压力(在城市租用摊位的费用及交通费用远低于租房费用),还可以兼顾照料家庭。
W 村目前约有250户从事这种生计,并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种生计模式主要采用中青年夫妻搭档、兄弟姊妹搭档、父子搭档或母子搭档的方式。搭档双方当日共同往返W村,也有个别搭档其中一方偶尔留在城市,一方当天返回W村。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聚合W村与周边城市的空间关系,并进一步凸显W 村的农村属性,“山里、无污染、农家菜”等乡村特征被强化。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为城乡之间的空间信任提供技术支持。手机拍照、录屏、微信视频、抖音等相关技术与W村空间的结合,可以给城市居民提供即时即景的在场情境,支持城市与W村之间的供需关系,进一步强化城市居民对农村的信任。
2.1.2 “城-乡”生计模式 W 村距离其所属Z 市市区仅30 km。早期靠山吃山的W 村村民日常生产及生活必需品,诸如五金、化肥、生活日用品等主要依靠个体户经由唯一的省道从Z市采购回来售卖。其中,圩日人流量最大,物品最为齐全,成交量最大。2015年高速通车后,从W村到Z市、X市及Q市的通行时间大大缩短。城市商品以更加丰富的品项、更加快捷的方式进入农村。近年来,除了日常生产及生活必需品外,来自大棚种植的蔬菜或瓜果也逐渐从城市进入W 村商铺,摆上W 村村民的餐桌,成为村民日常必需品。目前W 村共有10 家专门从事从城市采购果蔬回农村售卖的商铺。“本地菜压根儿不能吃,又老又硬,不像那些大棚的,酥脆得很,我就喜欢买大棚菜,不喜欢吃自己种的。”(CYY,2021-10-03)
“乡-城”生计与“城-乡”生计,一进一出,形成W 村特色的“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如果说,W 村的“乡-城”生计是在向城市递送城市所稀缺的来自农村的特产;那么,“城-乡”生计本质上则是在向农村递送农村并不稀缺,但却有所区别的家庭日常。在农村面前,城市曾经是先进与时尚的代表,是农村仰望的榜样。但在W村“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下,城乡之间以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起点,在彼此的空间中频繁穿梭,互通有无。
除了蔬菜、牲畜外,人员及货物运输等也是“城乡日摆动”生计的资源。此外,还有部分村民一大早从W村出发到周边县市工厂工作(每天早上厂车来W 村接人,下班后送回W 村),形成早7 点到晚8点的“城乡日摆动”就业模式。不同于“半工半耕”(夏柱智等,2017)的生计模式,W 村特色的“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是以农村为根基、以农产品为依托、以城市为平台,穿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生计。在这种生计模式下,家庭成本得以最小化,利润得以最大化,还兼具照料家庭、凝聚家族和村落的功能。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进城的生计是以“人”④《2021 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2022)显示,2021 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 309 万人,比上年增长1.6%。农民工:指户籍仍在农村,1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为主的生计,是农村人口放弃农业进城以劳务获取生计;那么,当前W村农民进城的生计则是以“物”为主的生计。以“人”为主的生计需要个体一定时长(统计上一般以半年以上)脱离农村生活场域,而以“物”为主的生计则因为“物”的生产及存储要求,农民不需要也不被允许较长时间脱离农村生活场域,并强化作为生产“物”的农业及农村的重要性。
2.2 空间镶嵌:家庭居住的城乡延展
2.2.1 村落内部家庭空间的延展 家庭内部居住空间的优化。1980年以前,W村以联合家庭为主,住房基本都是泥土夯建的大三间或大五间,在多子女的家庭中,住房总体较为拥挤。1995年前后,W村第二代子女陆续在老宅周边新建核心家庭自住房,主要以1层红砖水泥墙为主的套房,居住空间得到较大的改善。2010年以来,W村的第三代子女翻建或新建别墅式楼房,家庭内部居住空间得到显著提升。
村落内部居住空间的延展。村落是农村家庭重要的外部生活空间。传统村落中,村社边界和中心是清晰的。1980 年以前,W 村10 个社各自都有清晰的自然边界:县道或村道+连片住宅(本社村民住宅)+本社村民耕地。1995 年前后,各家新建的住宅主要以老房子为中心向边缘扩散,但大部分仍囿于社内。2010年以来,耕地价值的逐年提升以及交通的日益便利,原先作为边界的社内村民耕地陆续被用于盖房子,尤其是村社道路两旁的耕地,陆续被各社村民买卖或互换,曾经社与社之间清晰的边界日渐模糊。家庭居住空间及生活空间逐渐从社内延展并以村庄为大单位,重新聚合。
2.2.2 村落外部家庭空间的延展 W村地处其所在县南部,从W村自驾到Z市区仅需30 min,自驾到X市70 min,自驾到Q市120 min。作为经济特区的X市是W村从事“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家庭的首选。不同于街头流动摆摊,W 村从事“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的家庭在城市都有定点的场所。他们大都在城市社区租一门面店,大小不一,最小的只够支撑1个摊位的空间,最大的是1个完整的商铺,可以隔出家庭休息空间。但考虑到生计成本,仅有个别家庭选择租用完整的商铺,大多是选用能够隔出1个床位大小休息空间的普通门面。商铺主要经营时间以上午为主,从早上7 点到中午12 点左右,销售对象主要是社区的中老年群体,午后搭档双方在整理完摊位上的物品后便返回W村。
因此,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城市的商铺等同于镇中心5天一“圩”的摊位。但不同于“圩”里的摊位,城市的门面店除了是销售农家产品的主要场所,还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空间,可以为“城乡日摆动”家庭提供稳定的交流与休息空间,与农村的家一起构成“城乡日摆动”生计家庭“居住在农村-从业在城市”的城乡“镶嵌式居住空间”。
“肯定要有固定摊位的。我们这种大部分都是卖给那些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有固定门面,老人家才容易认得、记住你。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城里摆路边摊完全行不通了,你天天得提防着城管,那没法搞。有个固定的摊位,你就可以让这些(老)人安心地挑,我们自己卖起来也不用担惊受怕的。累了,还可以在躺椅上眯个半小时。城市我们是住不起啦,再说了城市的房子又贵又小,现在农村自己盖的房子比城市宽敞多啦。”(CHZ,2021-10-03)
2.3 空间效仿:家庭生活方式的城市化
2.3.1 进城就医的习惯生成 居住空间不仅影响个体对环境的体验,同时影响个体对公共服务的体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制度与医疗保险制度实施以来,农村家庭成员获得来自养老和医疗的基本保障。然而制度的“城乡价差”依旧存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的保障差距明显。此外,城市在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以及服务质量上显然都优于农村。城乡穿梭下,农村家庭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制度的差异,并形成制度差价的进城服务选择导向。
W 村所在地有一个乡镇卫生院,有3名从业几十年的乡村医生。村民往常生病主要以乡村医生上门治疗为主,或者到卫生院处理,紧急情况一般送往Z市三甲医院就医。但现在越来越多村民一生病(即便是普通感冒发烧)就直接前往Z 市或X 市就医。进城就医是基于城乡往来的便利,是农村家庭对城市医疗服务的偏好,也是对农村医疗的不信任。但不分病情地盲目进城就医也是对城市医疗资源的一种挤压。
“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了,他(乡村医生)不好用了,偶尔看个感冒还行,其他不行了,还是得去医院,人家有机器(仪器),一下就能把情况搞清楚。我老婆这次身体不舒服,我就和孩子说,不要管(担心)钱,以治好为主,直接去X市的医院看。”(CYY,2021-10-03)
2.3.2 进城上学的教育路径 在家庭及其成员“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下,儿童的养育方式也日渐“向城”。W村所在地有一所具有50多年办学历史的中学。但近10多年来,W村儿童不断被送到Z市民办学校读高中,部分甚至从小学就开始往外输送。与在W村接受免费义务教育不同,到Z市民办学校一年需要花费父母上万元。尽管如此,W村一些家长(有些家长是老师)认为当地教育水平较低,倾己所有尽可能地将孩子送出W村,送进城市。
“我自己也不想,毕竟我自己也是(中学)老师。但教育质量摆在那,让他在这里读,肯定考不上高中,我自己教副科,也辅导不了他,整体的学习氛围也不行,思考再三,在初二的时候把他送去了,今年就考上了他们的高中部。”(CWM,2021-10-18)
除了送进城市读书的儿童外,还有一部分在本地中小学就读的儿童,他们的养育方式也日益“像城”。W村中青年“城乡日摆动”的生计模式,生成了朝五晚七或朝七晚八的生计时间。劳累一天的父母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陪伴子女。传统的家庭陪伴逐渐由学校或机构替代,放学后W村儿童大都被送往午托班或晚托班。从早晨上学到晚上托班结束回家,家庭几乎只承担了“睡觉+早餐”的简约服务。儿童从父母、祖父母等家庭成员身上获得有质量的陪伴及关爱极为有限。闲暇时间里,手机、游戏、电视等成为父母的替代品。
“我早上七点从家里出发去上班,晚上八点回到家,一个月才休4天假。他爸爸做水电工也不定时,忙起来也是从早到晚的,我妈她们有时也要下田里,没法每天都有保障(接送和做饭)。我们都才初中水平,老大读初二,我们更辅导不了。女儿要读小学一年级了,也是准备像老大一样,中午和晚上都寄托班,这样作业也有保障。也是很烦啊,周末在家都是看电视、玩手机。暑假除了上补习班,在家的时间几乎不出门,除了看电视就是玩手机,叫都叫不动。”(CXM,2021-12-20)
3 农村家庭发展的空间表象
空间穿梭、空间镶嵌以及空间效仿,勾勒了一幅农村家庭穿梭于城乡之间的空间图景。“城乡之间”不同于“城乡两栖”。“城乡两栖”是在城市和农村各有家,在某个时期(可以是连续几年,也可以是一周的连续几天)以城市为主要居住及就业地点,在另一时期以农村为主要居住及就业地点。“城乡两栖”的农村流动人口既不完全城镇化,又不完全回归乡里,或者说既城镇化又回归乡村(王春光,2019)。“城乡之间”是家在农村,居住在农村,就业或从业在城市,每天在城市和农村来回往返。艾伯特指出,如果没有理解特定社会时空中特定社会行动者的社会安排,那么就不可能理解真正的社会生活(Abbott,1997)。不同于“离土不离乡”及“离乡又离土”的农村家庭务工模式,W村家庭发展的空间实践是穿梭在“城乡之间”的模式,是以农村为定居场所、以乡土为资源、“离乡不离农”的家庭发展模式,也是城乡融合的新形态,蕴藏着农村家庭对于城乡二元空间不分边界、不分内容共同富裕的发展诉求。
3.1 不分边界的共同富裕诉求
不分边界的城乡。W村家庭日常生活空间的外延与生产空间的村外化,是基于城乡之间交通及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空间实践基础。交通的日益便捷为城乡之间的互融互嵌提供空间前提。但城乡二元发展惯性下,城乡家庭发展的差距尚存,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在生计模式、代际关系、社会服务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异。农村既存的家庭结构、社会关系在城乡镶嵌的进程中,为农村家庭表征性空间的生成提供了土壤,打造了一个相互映射的当代农村肌理。然而,空间并不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农村家庭是在现代化变迁中,在一定时长中形成的相应模式,并将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城乡空间的进一步镶嵌而继续映射彼此。城乡“镶嵌式居住空间”“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都是农村家庭因应当代时空压缩的城乡互嵌与互融。
不分边界的村社。W村各社各家庭通过买卖或互换道路两旁的土地跨社建房、跨社居住,实际上是对村落内部“富裕”空间的共同追求。路边建房,既可以解决以往居住在村社内部交通不方便的问题,还可以将自家房屋做店面营生,实现家庭财富的增长。传统的村社边界在公共富裕的现代语境中失去既有的效用,共同富裕不再有场域区别。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也是村落的发展目标,同样是农民家庭、农民个体的人生目标。不止步于对与城市共同富裕的空间渴望,即便是在狭小的村落中,共同富裕的空间场域及其空间需求也未曾消失过。
3.2 不分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富裕诉求
共同富裕是农村家庭成员的共同追求。W 村“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主要以夫妻、兄弟姊妹、父子或母子作为进城生计主体,并以父母、亲属、乡里相邻的中老年群体为耕作主体。散户劳作方式下,农家菜、农家鸡鸭等产品相对稀缺。“农家-稀缺”为“城乡日摆动”提供了生计空间,但稀缺也意味着不稳定。因此,要确保“城乡日摆动”的可持续性,来自家庭、家族以及邻里的“稀缺”产品保障更为重要。如W 村的CH 夫妇负责在家种菜,两个女儿和女婿分别运往Z市和X市销售,并不时向亲戚及乡邻收购鸡鸭、猪肉等做补充,形成以联合家庭为主的生计主体。这种模式既是家庭成员共同富裕的优先选择,也是农家标签供需不平衡下的以“家”为本的共同富裕路径取向。
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城乡日摆动”生计中,一把青菜以农家菜的名义进入城市销售,既满足农村家庭对于收入增加的经济发展诉求,又实现城市家庭对于农村绿色食品的健康需求。“那些人,只要你的东西是真的(农家),钱不是问题。像我带去的地瓜,够甜、够糯,一下下就被抢光了。”(CJL,2021-12-25)。进城就医的日常化是农村家庭对医疗服务的品质需求;而儿童教育的“向城”与儿童养育的“像城”,既是农村家庭对于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集聚的追逐,也是农村青年一代家庭生计模式向城化的附属;是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共同享用优质均衡教育、优质均衡医疗等中层机会平等(王春光,2014)的诉求。青菜进城、就医进城、教育进城背后是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是农村家庭对于城乡之间不分物质、不分精神的全面富裕的渴求。
4 农村家庭发展的表征性空间
4.1 农业生产的弱化
农技的老龄化。W 村中青年是“城乡日摆动”的主体之一,他们主要负责从W村收购蔬菜、瓜果或家禽等农产品,并运送到城市出售。但这些中青年却“下不去农田”,他们不懂耕作、不会耕作、也不愿耕作,主要依靠老年群体的耕作来获得“城乡日摆动”的资源。“这些年轻人都不种菜,却都要跑去卖菜,每天下午4、5点就来路边等了,各种央求我给他们多一点不一样的菜,不是不给,真种不出来啊。你看一下,现在田里就我们这些老头了。种菜没啥钱赚的,现在种子贵得很,也不好种,得整天待在地里。”(CJ,2021-11-10)事实上,这些“城乡日摆动”的中青年从W村拿到农家产品及总量占其销售品种及总量的比重并不高,但这些蔬菜及家禽身上的“农家”标签却足以撑起整个销售摊位所有产品的卖点,进而架构起农家产品与城市之间的销售差价和利润空间。
“农家”标签的消费。事实上,中青年经营的农家产品本身并不“农家”。“不喷农药,菜都得让虫子吃光了,喷了农药也还是有很多虫眼。不过他们说就喜欢这种带有点虫眼的菜,买的人才知道这是农民种的菜,不是那种大棚菜。”(CJ,2021-11-10)W村的农耕传统为中青年在城市的经营提供了“农家”的市场标签,但又通过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来消费这一标签。“单靠回去(W 村)拿的那一点菜可能没法营生的,刚来卖的时候,拿(W 村)的菜比较多,现在去(W 村)拿菜的人越来越多,就那些人在种,根本不够卖。现在大家拿的猪肉基本都是饲料猪,只掺一点点家养的。想要整场卖的都是农家的,那你得饿死。”(CYH,2021-07-20。)
城乡的空间形态差异反映城乡社会生产及生活结构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乡之间的阶层固化。耕地是父辈为中青年提供“城乡日摆动”生计的依托,但却又是中青年“下不去的农田”。农技老龄化、农家标签虚假化、农村中青年下不去农田背后既是对传统农业、传统农村标签的消费,更是对农业发展与农村生活的不自信。
4.2 农村家庭的悬浮⑤项飙(2020)指出,所谓的“悬浮”是人人都在为自己奋斗,拼命干活,挣钱,都想着比别人快一步半步,害怕被甩在后面,自己当下的行为本身不能产生意义。本研究引用此概念在于描述本研究观察到的当前农村家庭,尤其是农村子辈想方设法赚钱,以期离开农村,或者生活得像城里人的状态。
悬浮的人们。房子是家庭最重要的居住空间。在中国社会,父母对所有子女都负有“无限责任”(周飞舟,2021)。城镇化进程中,高昂房价下,农村子辈在城市买房大都得到父辈的支持,甚至是家族式的支持。即便是驻扎在农村的子辈,父辈也忙着协助子辈买地盖房。人人忙着买房、盖房,以期能获得更加宽敞舒适的空间。为了子辈进城安家,父辈几乎是掏空一切地豁出去(如CMH)。对于驻扎农村的子辈,父辈给地、出钱盖房,一幢幢别墅式家庭空间扩展的背后都是父辈平生积蓄的消耗,健康的预支以及未来养老的几乎零储备。CJ夫妇为子女几乎毫无保留地付出后还要自己盖房住的事实,也没能终结W村其他父辈对子辈及孙辈继续毫无保留地付出的行为,甚至还出现相互效仿的现象。出钱、借钱帮助子辈几乎是W村中老年父母的标配行为。无论各个家庭的故事如何演绎,父辈倾尽所有协助子辈是W村各个家庭共同的悬浮。
CMH:55 岁,男,城乡半耕半商。夫妻将家里所有积蓄都拿出来,并向朋友借钱支持儿子城市买房。孙子出生后,儿子觉得农村家里房子(够住)格局不好,不方便偶尔回来居住,CMH 夫妻就借钱翻盖。CMH 为了还房债,从事非法运营被判刑一年。(2020-12-06)
“不敢奢望”的祖辈。在W村家庭代际模式中,农村经典的“反馈模式”(费孝通,1983)——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抚育与赡养的反馈所建立的家庭内部重要的代际联结日渐单向化。在W村家庭日常生活中,老人除了劳作获取收入外,其他时间和精力几乎都用于协助子辈抚育孙辈。在少子及少孙情境下,家庭发展强化了父辈向子孙辈单向代际的方向和强度,父辈对子辈及孙辈的付出几乎是毫无底线。
CJ夫妇:育三儿两女。老大生育两女后务工被烧伤,媳妇精神病,CJ协助其养育两个孙女直至结婚。2017 年CJ 夫妇将所有积蓄都分给子女。2019年CJ夫妇将原住房用地给老大、老三翻建新房,再多1万元给老大以便房屋建好后CJ夫妇可以住在老大家。入住半年后,大孙女与CJ产生矛盾,老大、老三也因盖房起冲突,CJ夫妇被迫搬出老大家,随后借钱在老大和老三新房旁边的空地上盖两间铁板房居住。(2021-02-10)
农技的老龄化、“农家”标签的消费、悬浮的人们以及“不敢奢望”的祖辈,表象上是个体或各个家庭的“位育”问题(潘光旦,2013),实际上是当代农村社会人伦与位育的式微。中国传统农村社会里,村民主要以礼来规范生活,编织一个基于伦常的精神世界,形成村庄基本生活范式,构建村庄基本秩序。但在传统村落文化与城市文明的碰撞中,传统村落文化不断被丢弃。位育不足,个体及其家庭难以得到滋养,个体及家庭的行为就容易失范。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探讨了农村家庭在时空压缩社会情境下的发展境况及其蕴含的意义。得到的主要结论为:1)当前驻扎在农村的家庭以农产品为主要资源谋取“城乡日摆动”生计,形成了“居住在农村-从业在城市”的城乡二元居住方式,并对城市家庭生活方式加以效仿,生成了农村家庭在城乡空间穿梭、空间镶嵌以及空间效仿的实践图景。2)当前农村家庭的空间实践是以农村为定居场所、以乡土为资源、“离乡不离农”的“城乡之间”发展新方式。在空间表象为农村家庭与城市互融互嵌、不分物质、不分精神的共同富裕发展目标。3)城乡二元惯性下,城乡差距仍部分存在。农技日渐老龄化、农家标签被消费背后潜藏着农业生产的弱化以及农村家庭对农村社会生活的不自信,呈现的是农村社会人伦与位育日渐式微的表征性空间。农村家庭通过在城乡之间“离乡不离农”的生产方式回应农村与城市生产空间的现实差异。这种“离乡不离农”穿梭“城乡之间”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家庭对城乡二元物理空间和一元社会服务空间的共同富裕发展诉求。当代时空压缩为农村家庭的这一诉求提供了来自空间聚合的前提保障,但城乡发展的落差也同时孵化了农村家庭悬浮的图景。
5.2 讨论
空间的生产过程,也是空间被生产的过程实践。农村家庭通过穿梭、镶嵌以及效仿等一系列行为作用于城乡空间,以农村家庭的身份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共同享用。这一系列行为既是农村家庭发展的行动目标也是农村家庭发展的行动策略。通过这一系列行为,实现农村家庭的再生产。依据列斐伏尔“空间生产—资本积累—社会发展”脉络,作为资本积累的空间,“城乡之间”的空间实践构成农村家庭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但也为农村家庭发展种下不安的种子。福柯指出,一部空间的历史,必然也是一部权力的历史(米歇尔·福柯,2021)。农村家庭“城乡之间”的行动目标及其行动策略构成农村家庭发展与城乡空间之间的联结,尤其是农村家庭对城市空间的权利诉求。“城乡之间”是农村家庭“用脚丈量出来的”的共同富裕空间路径。W村“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蕴含着农村家庭对以农业为本的农村生活的认可,但也聚合农村家庭对于城市福利制度、服务水平的向往。
马西指出,种种过程在空间发生,距离、闭合、不同地域之间的地理差异、特定的场所和聚集点各有其意义,这些对于社会过程而言,均至关重要(Doreen Massey,1984)。场所与场所之间的关系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与个体、地点、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场所”构成新的空间化权力网络,网状的权力治理结构透过“场所化空间”交织而成(米歇尔·福柯,2006)。空间成为权力得以运行的关键(营立成,2017)。因此,空间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在现代化情境下尤为重要。在推进共同富裕战略进程中,需要聚焦农村家庭扎根农村,并穿梭于城乡之间,自如地进行空间生产的现实情境。无论是城乡统筹还是城乡一体化,亦或城乡融合,新时期城乡发展的路径不是消除城乡二元空间,而是基于城乡二元物理空间,建构家庭自信、村落自信的农村发展空间以及城乡一元化的社会服务空间。由此,本文提出3方面建议:
其一,建设“零价差”的社会政策空间。空间实践标尺衡量下的农村家庭,呈现城乡同构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建构农村家庭发展的空间继替视角,将家庭放置在中国式现代化情境中,放置在新的城乡空间中。农村家庭的发展不是以村落的终结或农村家庭的城市化为目标,而是基于城乡社会共同富裕下的彼此独立,需要从制度层面建构城乡家庭发展的平等路径,为农村家庭自主落地提供平等的制度依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农村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的角色定位。但政策制度的城乡协同,才是城乡家庭共生共存、共同富裕的保障。因此,建立并完善与城市“低价差”甚至“零价差”的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策体系,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农村在场与城市同等优质供给,为推动村落自信的家庭发展空间位育保驾护航。
其二,再塑村落自信的农村家庭发展外部空间。村落位育的式微需要再塑农村空间的中心主体性予以应对,进而构建城乡互融却又各自独立的格局。农村不再盲目仿效城市,盲目招商引资,盲目请“农民上楼”(贺雪峰,2013)。农村不需要变为城市,也不是城市的边缘或附属。村落自信本质上要以村庄的客观现实为基础,挖掘村庄的农耕、文化、生态、社会等优势资源,为家庭发展建构稳定的物理空间。如W 村毗邻Z市区、X市及Q市,拥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悠久的农耕历史及生态资源,并初步形成“城乡日摆动”生计模式。因此,加强规划发展现代化、特色化农耕产业,加强农耕基础的乡村文化位育,构建“以农为商”的农村家庭可持续性生计模式。
其三,重构个体自主的农村家庭发展内部空间。农村家庭的发展既要强调村庄的主体角色建构,同时也要回归家庭个体,建立具有内在驱动能力的家庭发展内部空间。当前农村父辈依旧有较强家庭经济保障与照料支持能力,子辈有充足的家庭经济保障与风险应对能力。但父辈经济向下代际强化,老年风险加剧。因此,要加强对父辈“经济自主是养老基本要件”的主体意识培育,激发他们对隔代抚育能力的自我认可、对自我健康的认知、对家庭养老的诉求等主体意识;要加强对中青年农耕意愿的唤醒以及农耕能力培训,引导中青年一代落地农村,务实农业。只有家庭成员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有扎根于农村社区的职业能力与驱动力,才能推动家庭的良性发展。
此外,本文有3点政策启示。第一,共同富裕不仅是国家的发展目标,也是家庭及其成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目标,需要关注家庭及家庭成员的共同富裕诉求。第二,共同富裕的目标应置于城市和农村社会服务一体化的现代化情境中,与农村家庭生活发展相关的服务制度关怀应成为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的重点。第三,“城乡之间”“离乡不离农”的生计意味着农村家庭更加多元的发展可能,具有巩固农民安居农村和融合城乡的双重功能。但需要预防虚假消费“农家”的风险,落脚点在于做实生态振兴,还民众一个“青山绿水”式的农业、农家以及农村文化,构建家庭穿梭于城乡之间的农村空间自信。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农民流动形式不同⑥《202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2022)显示,2021年东部地区省内流动农民工占84.9%,中部地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56.6%,西部地区占47.8%。,不同区域农村村庄结构不同(贺雪峰,2017),家庭发展的基础要素也不尽相同。本研究以地处东南沿海的W 村为案例,上述论断是否适合中西部农村家庭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