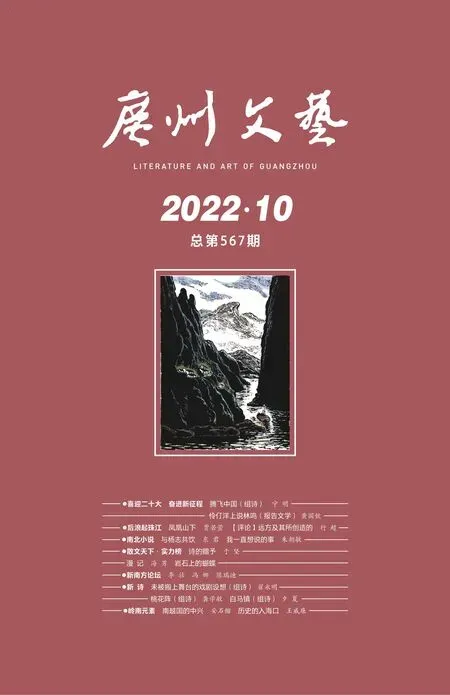岩石上的蝴蝶
海 男
蝴蝶是鲜活的,我遇见它们时,并不知道当它们变成标本时也会保存它们的斑斓色谱。我曾遇见过无数次蝴蝶,在树林的叶片上,它们伪装者的模样闯入了我的视线。蝴蝶最喜欢投奔的就是树叶,它们飞一段距离就要栖息,因为它们的身体太柔软。有人告诉我,蝴蝶的性命很短暂,只有几十天时间。当时,我坐在山坡上想象着性命与时间的关系。
要寻访蝴蝶,必须开始一段与山水相依的独立旅行。之所以说到“独立”这个词,是因为引出下面的文字时,我想到太多人旅行的杂乱和喧嚣会影响你分享每一段自然的习惯。除非你的意识深处不为某物某景所牵挂。其实,每一次在大地上的旅行,都是偶然降临的,是上苍的安排。蝴蝶是有翅膀的,注定要飞在我头顶。有翅膀的生命都是我所羡慕的,今世生而为人,来世再见!
今世生而为人,必须佩戴自己的锁链跳舞,才可能跳出人们在精神中所追求的自由和独立。其实,众所周知,身体上佩戴的那副锁链是看不到的,它是无形的。蝴蝶的身体上有锁链吗?那么小的身体啊,它如何戴上锁链飞翔?这是形而上的追问吗?很多事一旦进入了形而上层面,就进入了美学和诗的结构。那么,这一只只蝴蝶也像人一样,佩戴着无形的锁链飞翔。人看到蝴蝶时,更多的是在野外——很多年来,我似乎在野外生活的时间更多。房子只是我们栖居的地方。每次,我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家,需要洗一次澡,再加上一场睡到自然醒的睡眠,之后,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常态。
在我们的常态中,首先要活着,并每天与活着的自我在一起。早起是我的常态。我不是一个拥有好睡眠的人,很少会在睡眠中获得美丽梦神的护佑,以及拥有更多的梦中时空。白昼与流星加在一起,就是我的生活。夜晚对于我来说很漫长,所以,我在夜里的多数时段,会盯着天顶,那时候我似乎跟流星在一起。我过往的生命中似乎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深度睡眠,所以,我迎接黑暗中的晨曦时显得很轻松自如。在漫长的时间中,我床上三分之一的位置都堆放着书,起床时,我得事先告诉那一本本卧在墙壁下的书,我要起床了,我的脚和身体要落在地上了,我的身体要穿上衣服。
穿衣服这件事并不轻松,它就像写作,从一开始就很艰难。衣服,尤其是女性的衣服,不是只有衣服本身的含义,对于我来说,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意味着要做什么样的事,要见什么样的人。更细一些讲,你有什么样的情绪就会去寻找什么样的衣装。所以,女性的衣服永远都不够,永远在期待下一件衣裙。
为了节省时间,在就寝之前,我通常会将第二天的衣服找好放在床边。时间过得太快,面对时间,我每天都有仪式的,这可能也是我容易失眠的因素之一,一个认真对待时间的人,必然会更深切地感知时间的流逝。因时间流逝的无常性使我们必须寻找到属于自我的仪态和尊严,哪怕在头天夜里无眠,第二天我依然要保持我生活的常态。
寻找到明天要穿的衣服之前,已经规划和预感到了我明天的生活。我想,那只蝴蝶在出世之前或飞行之前,同样应该是猜测到了自己身上的色泽,所以,它们出世之后,会生长在不同的地貌,将自己斑斓的身体寄生在不同的地区。从岩石上的蝴蝶回到房间,实际上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从黑暗返回白昼,这意味着新的一天已经降临了。
那只蝴蝶也应该开始飞翔了……我自己也必须以身体的形象出现在镜子里,出现在窗外,远方的某座村庄里。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就预示了你的生命体将出现在什么样的空间。这就是活着的标签。我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蝴蝶是怎样变成标本的》。那时候,我还年轻,用很多个夜晚来耗尽自己身体中游离的忧郁和激情。
忧郁和激情是我的常态,是我写作和生活的乐谱架,我在上面弹奏着因天气、季节、社会所产生出的变幻莫测的乐曲。这两者似乎谁都无法离开彼此,有忧郁才会产生激情,这也是写作者所需要的情绪。对于我来说,任何情绪都是烟火。
这个冬天,我每天在黎明时分都要花20分钟清除院子里的落叶,它们是随大风呼啸而下的。刮风的夜里,我看枕边书,总会听到窗帘外的声音,这些声音是涡旋状的,仿佛波涛起伏跌宕。有时候,我会拉开窗帘,从有灯光的房间里往外看去,风吹落叶的景状非常迷人。那是一些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离开了树身的红枫叶,是完全被风的力量所吹落的,它们离开树枝之前,一定有难以承受的剧痛。在夜里的路灯下看见树叶离开树身后的挣扎,一片片树叶在风中仿佛在跳舞,落在地上时很轻,看不出会痛。第二天等待我的必然是满院子的落叶,在晨曦中我开始扫地。如果三天不扫,落叶就完全干枯了。头一天落下的枫叶,第二天早晨平平静静,已经完成了它们的涅槃。
叶面色彩斑斓。如果没有风,叶子应该还会在树上生活一段时间。离开了树,就离开它本身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像树一样生长,也必然像树叶一样斑斓,有一天也将会像树叶般凋亡。我扫落叶时,会拾几片色彩鲜艳的叶子带回去,夹到书中。书中有叶片,就像书签,但它干枯时很容易碎裂。于是,我不得不将它们“放生”回大地,让它们回到该去的地方。
树叶的颜色。它那饱满的色调中突然间飞出了一只蝴蝶,这是一个奇迹,在院里的落叶中,一只蝴蝶结束了它的梦想。这是一只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蝴蝶,但它仍然那么美。它是何时落下来的啊,可能是随树叶在风的呼啸中落下来的。我有些悲伤,这只已经断了气息的蝴蝶还是被我带到了书房。我将它夹到我最喜欢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套书中。多年以后,我忘记了它的存在时翻开了书的第一卷,在那个异常安静的下午我突然看到了书中的蝴蝶。
在普鲁斯特的书中,告别生命气息的蝴蝶,成为我自己制作的一只蝴蝶标本。这是一个意象,激动中仿佛已经忘却了初次看到它时的悲伤。蝴蝶似乎已经融入了书中那种关于时间的气息,在作家细腻的叙述中蝴蝶仿佛又飞了起来。如果普鲁斯特能够看见这只蝴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它成了我收藏这套七卷本巨著的一种个人现象。每一个生命都会创造它跟人类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珍惜这种微妙的感受,生命将不再孤独。那只蝴蝶至今仍在我书房中,它跟那些伟大的纸质书生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每天都在这间并不大的书房中说话,它们也会转世于时间,并因为时间而负载新的意象。
当我在澜沧江岸边行走时,蝴蝶又出现了,不是一只,而是一群。在正午的澜沧江边,我们途经了它们的峡谷。栖在岩石上的蝴蝶,仿佛要变成化石了,它们看上去一动不动,它们靠什么维持身体特征?虽然它们只能活几天,但只要活着,就不可能不需要食物。这些问题,回到现实面前,会让人揪心。我不敢惊动这群飞了很远终于找到这些岩石的蝴蝶,它们为什么要栖身于这块荒凉的、来自澜沧江的岩石?
我发现自己质疑的问题有些复杂了,便力图回到人的生命中去理解它们:也许这群色彩斑斓的蝴蝶飞到这座峡谷深处,就是为了避开自然界的喧嚣。地球上每一种生物,都拥有它们的语言和信仰。栖于岩石上的蝴蝶,看来是喜欢上了这些岩石的寂静,就像我那刻的心绪,站在岩石间感觉到身心都是那么干净自由,没有铜栏羁绊我的身心,没有那些不尽的欲壑需要我去填充和穿越。
艺术的色域之旅让我看见了这群岩石上的蝴蝶,我与它们保持适度的距离,不去打扰它们的安静。但这一幕屏息于内心的场景,终有一天会来到我的画布上。人在回忆时有几种生活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回忆成为计量数,让人回到某一刻某一现实某一历史时刻某一个人身边某一种契约书中某一场庆典某一个缘分某一个生命攸关的时刻……这样的回忆大都是为了剪辑人生观念的图片,是为了将这些图片装在自己的再生记忆库深处。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回忆。这世界除了为生存而必须掌握的技能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为精神发明出的技能,亦可以称为造梦空间。为了造梦,这个世界上茫茫人海中的极少数人也在回忆。我拥有画室的那一天,就将颜料画框搬了进去。看上去,这显得多少有些荒谬,因为我从未学过绘画,就像17岁那年,从未学过写小说和诗歌的人却开始了写作,并且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以在发表作品时使用。
画框立放在画架上。为了拥有专门的绘画空间,我当时还租下了画室。我感觉这一切就像当年在澜沧江边的岩石上寻找着蝴蝶。我先是发现了一只蝴蝶,沿江岸走了很长时间,因疲惫而渐觉枯燥,就在身体和精神都开始萎靡不振时,峡谷出现了。生活在钢筋水泥玻璃建筑中的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峡谷,会产生什么样的情绪?峡谷是冰冷的,相比于沙漠,它又是坚硬的。
坚硬而又冰冷的峡谷坐落在澜沧江岸边,这是地理的坐标。人,来到某个地理的坐标,肯定是为了寻找和验证某种东西的存在。我们不会漫无边际地漂泊,地球上的水域很浩瀚,但无人区也很多。蓝色的水域和看不到尽头的无人区域占据了地球很大的面积。在这个星球上,海洋和陆地占比面积悬殊。海洋上可以看得见人类的船帆,从古老的探险家开始,直到现在,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探索和海上旅行,也从未停止过对无人的荒野和原始森林的考察和探索。这个时代,对于个体来说,去到浩瀚的海洋和陆地无人区域,行动会受制于个人的渺小——人都是渺小的,所以,人必须依附于群体和庞大的社会机构。
在人的行为受制于契约律法和社会机构时,现实生活、公共道德衍生出了人的安全感和责任感。除此之外,人出生以后,就开始建立自己的美学。他们躺在摇篮中时就已经看见了蓝天白云。每一只摇篮都是放在天空之下的。为了让襁褓中的孩子晒太阳,母亲总是会将摇篮移到屋外。摇篮里的婴儿快乐地朝天空晃动着肉肉的小手。这是婴儿开始将自己的视觉从母亲乳房前移动到天空的时刻。他们到底看得有多远?不管怎么样,从那一刻开始,摇篮中的婴儿就开始了视觉旅行,有了探索世界的具象和念头。这具象从云朵回到母亲的怀抱,再回到尘埃中的奔跑,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人生规则。
岩石上的一只蝴蝶,准确地说,是澜沧江大峡谷中的一只蝴蝶,带领我的视觉往深处行走,灰蓝色与天空之镜融为一体。这感觉真妙,就像喝着酒,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醉意,在妙不可言中已经朝峡谷走了很长时间。在峡谷中行走,你要学习羚羊的姿态,才能稳定地跃过一道沟壑;要学习蝴蝶潜伏在岩石上的专心致志,才能站稳脚后跟,观测和享受峡谷中每一种细微的变化。
循着一只蝴蝶寻找到一群静卧于岩石上的蝴蝶,这就像一个孩子脱离了母乳和空中摇篮以后,在尘埃中奔跑寻找到幼儿园的积木和糖果屋,再以游戏中的奔跑寻找到学校和社会。人和蝴蝶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只有在群体中学会生存和审美的生命,才会寻找到孤独,发现梦想的出发地,找到方向感。
岩石上的一群蝴蝶成为多年以后我语言中的意象。第二次、第三次再沿着澜沧江行走时,我又去寻找那座江岸的大峡谷,但我找到的是另一座完全不一样的峡谷。我依然往里面走,想遇到一只蝴蝶从而引领我去找到一群蝴蝶,但我走了很远,也没有遇到一只蝴蝶。这座峡谷更深、更陡峭,也更复杂。我向当地人描述着之前去过的那座峡谷。当地人告诉我,澜沧江有许多峡谷,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和岩石结构中。我谈到蝴蝶,当地人又告诉我,不同的海拔高度会有不同生物体的繁殖生存空间。
也就是说,我出入过的那座峡谷是很难再次遇上了。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岩石上的蝴蝶,但我深信那群岩石上的蝴蝶会出现的。至于它们以哪种方式出现,需要的是时间的转换。时间,是我们生命中注定不会错过的旋律,它造就了我们在不同空间和地点的人生。
涂鸦中的某个下午,我突然想起了那座澜沧江岸的大峡谷,这是一个令人激动而眩幻的时刻:面对画布上的色彩,这种宿命感让我接受了那次骨折。那个黄昏,我在昆明钱局街一个不高的坡地朝下行走时,突然摔了一跤。其时正值深秋,钱局街是一条笔直的街,两边有交错的街巷,有历史上的染布巷,还有通向闻一多先生遇难时的台地。我就是在走下这片台地时摔在地上的。脚下一滑就骨折,等待我的是从深秋到冬天的疗伤。那个冬天昆明还下了几场雪,因为寒冷,疗程非常漫长,足足半年才扔掉拐杖。也就是在这次疗伤中,我开始了绘画。我几乎是撑着拐杖开始画画的。在骨折前我已经订了画框颜料,但那是出自一个虚拟的幻想而已。
在那个异常寒冷的时空中,我撑着拐杖,面对画布,忐忑中有许多不安和焦虑感。
但我却有那么强烈的冲动去触摸:想调研色彩,想伸出手去触碰雪白的画布,想面对画架,仿佛想面对全世界。画布上的一点点色彩就可以弥漫开去,可以消磨时光。在云南很多村庄里,妇女们都还保持绣花纳鞋垫的习惯,她们做完一天的农活,收拾好锅碗瓢盆就开始坐在家门口聊天做手工活。
手工活计缓慢,需要耐心,现代人已经无法让速度慢下来。高科技就是要让速度快起来,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高科技首先让列车快了起来。列车,让我想起了绿皮火车,想起第一次乘火车的记忆,那时候我才18岁。我乘两天两夜的客车从滇西小县城来到省城昆明,那时的省城对我来说,就像大海一样遥远,就像星空般浩渺。18岁,是一个需要践行幻想的年龄,一个女孩悄然出走于滇西县城,身上只携带几件衣物,没有钱包,少数纸币塞在内衣里用别针固定。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但依然任自己被召唤和诱惑,往客运站走去。
客运站站着一个妇女,叫卖着。她怀中有用草绳扎好的粉红色蔷薇花,我知道蔷薇花美但有刺。幽香从妇女怀中飘过来,我忍不住走上前,一块钱的大束花用旧报纸包着,随同我上了车——这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现实生活。怀中的花有刺有香有色有味有艳丽有柔软有形有体有陪伴有喜悦……
两天两夜,那束花始终在我怀里,陪同我坐在长途车上颠簸着,陪我去旅馆。过去的云南驿站,有许多旅馆,这里在古代就是滇西的重镇要道,马帮途经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远征军曾在这里操练并运输战争物资。云南驿,一个多么诗意的地名。我抱着已经开始枯萎的野生蔷薇花,终于寻找到了一座用旧砖搭起的花台。我弃掉旧报纸,将那束花插在了花台中央,并给它们浇了水,我仿佛觉得那些花朵又活了过来,心里便有了些安慰。第二天早早离开前,我又去看那些花朵,它们完全活过来了。
我离开了,去追梦。18岁,是开始追梦的年龄,从县城追到了省城追到了昆明站,绿皮火车来了。我忘却了怀抱野生蔷薇花的妇女,忘却了那带着棘刺和花香的长途列车,忘却了云南驿古老石板路的传说。一个女孩从18岁开始追梦,要追到天边尽头时,应该是垂垂老者了。这不解的时间之忧,从花儿开始绽放吧!
时间之慢从绿皮火车开始。那一节节烟雾弥漫的车厢啊。20世纪80年代最后的慢生活,就是从绿皮火车开始的。我在陌生人中终于寻找到一个座位,像是寻找到稳定的支撑点。车厢里有果皮和啤酒的味道,有德州扒鸡和南京盐水鸭的味道,还有人身体汗淋淋的味道——从气味就可以判断人生的后面。后面是我们的背景,是我们从车窗外延伸出去的某座乡村小镇。
我看见陌生的站台上走来一个穿风衣的男人,30多岁。他的风衣不长不短,是时下非常流行的款式。转眼之间,穿风衣的男子竟然来到我身边,他没有座位——中途上车的人都没有座位。他只看着窗外,眼里没有任何人。慢慢地,我不再去注意他了。我发现当我不再注意他时,他反而开始注意我了。我半闭双眼,假寐着,能感觉他的目光在我身上逡巡。这慢火车上的相互观察注定转瞬即逝,在我假寐中的下一站,穿风衣的男子下车了。人生就像一列火车,每到一个站台,有人下去就有人上来。
岩石上的蝴蝶在哪里,我就会出现在哪里。是的,这一点从来也不会改变。我指的是意象,一个作家在其生命中会被种种意象所迷惑、笼罩。什么是意象?我想,当你站在春光和黑暗中时,会被关于春光和黑暗的现象导向一个生命所感知的色彩中。春光是令人喜悦的,而黑暗则是令人彷徨和不安的——在这两种不相同的关联中,你会产生关于喜悦的想象力,也会产生关于彷徨和不安的情结,或许这些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写作中的意象。我带着意象去访问生活的源头,这必然需要行走。是的,行走是必需的。
行走中,需要一双很舒适的鞋子。脚,我们的脚一定是身体中最为辛苦的,它期待我们为它配置上一双能适应在各种地理环境中行走的鞋子。穿一双好鞋子可以走很远吗?这是必需的,行囊中不可能让我们装更多的鞋子,只有身体轻盈才能走更多的路。这是常识。从儿时我们就穿上了鞋子,鞋码随同年岁增长。在我来到澜沧江边岸时,我穿着36码的咖啡色靴子,我以为只有穿上这种颜色的靴子,我才能走得更远。其实,这是一种意象,幻想更缥缈,而意象转眼之下就变成了岩石上的那只蝴蝶。
站在岩石上往下看,是平静的澜沧江。多少年来我总是在云南的三江流域行走,其中,与我相遇最多的就是澜沧江。不知不觉间我就看见了澜沧江,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只或一群岩石上的蝴蝶。它们栖在了画布上,我将画架立于露台。阳光很强烈——那几天阳光总是很强烈,这就是我的云南,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栖息地注定了身体中潜存的色彩。我是一个非常宿命的人,看见岩石上的蝴蝶时,我还没有开始学绘画。然而,一种异常热烈的心绪让我有些焦灼,写作无法表达的某种艺术情结仿佛带着我在行走。
离开了澜沧江,总要往前行走。山坡上有一个妇女,一个人在挖土豆。她挖出了那么多土豆。多年以前我就开始礼赞土豆这种地球人通用的食物。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土豆。站在山冈上看妇女挖土豆时,还能看见澜沧江的剪影。有时候,我发现只要出入于伟大辽阔的滇西,就总能在不同的情致中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相遇。这时候,我身体中个人化的忧郁和孤独蜕变成了充满生机的世态。
一个妇女挖出了堆成小山的土豆,她在等待开手扶拖拉机的男人来,这些土豆足以装满一车厢了。妇女告诉我,土豆要运往30公里外的小镇,那里有商贩收购。这些土豆是沙地上长出来的,很好吃。她说话时已经站起来,并告诉我地里的土豆基本挖完了,还有白萝卜、胡萝卜可挖。她站在土豆旁边,身体上全是泥土,只有头顶的三角围巾是鲜艳的。我想起了城市农贸市场的土豆,各种西餐厅里的土豆条。这些都是社会生活的具象,而眼前的这个妇女守着一座山冈,她是那样满足和惬意。
人类的生活状态就是由无数这样的场景所构成的。在这里看不见流行的抑郁症,也看不到疯狂的物欲横流者——山冈下的澜沧江静静地流逝着。突然间,听见了手扶拖拉机的声音,妇女望着山冈上的那条土路。那条路只可能让村里的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通过,因为路面实在太窄了。
我站在阳光明媚的露台上绘画,我在寻找记忆中那只岩石上的蝴蝶。而眼前是我手中的调色板,所有的文学艺术功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有意象。
我带着意象亲临世界,意味着我的生活与这个世界密切相关。那个热烈的季节,露台敞亮,有蝴蝶跑到画布上——我梦想的就是这样的“色情”游戏。来吧,岩石上的蝴蝶,无论你是一只还是一群蝴蝶,都请你们到我的画布上来栖息吧!
我正在战胜生命中的那种虚弱——由于没有受过专业绘画训练,我的色域世界显得有些虚弱,就像一个初次攀岩者面对直入云空的岩壁。尽管如此,我是喜悦的,来自虚弱的一丝丝喜悦,使我的笔更显笨拙:越是这样的时刻,表达的愿望却越是强烈。色块可以大面积地延伸出去,这是我行走过的高原,也是我内心的高原。我画上了烈焰,它们如此灼热啊,我的灵魂仿佛来到了画布上——在苍茫的人世间,我又寻找到另一种表达时间和生命的方式。
我抱着纸箱中的颜料上了台阶。如今我的画室坐落在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这里是抗战时期原西南联大的老校区原址,台阶下面就是联大路。在幻觉中,我经常在这条路上与他们相遇:闻一多、沈从文、刘文典、朱自清、陈寅恪、胡适、梁思成、汪曾祺、穆旦……沿着联大路往前走,就是当时留存下来的铁皮屋顶的教室。我很幸运,初学绘画,就在原西南联大的校址中有了140平方米的海男画室。每次走在联大路上,心里都会激荡起与这些伟大人物相遇的感觉。从联大路回到画室,面对的是画架,我会随同光线,一次次地移动着画架。
光线能产生出不同时态的作品,不仅创作需要光线,人生也需要不同时空的光线。
光线是什么?我们睁开双眼,目光遇到的就是来自光所笼罩的小世界。用自己的双手创建的小世界,类似鸟巢,每年开春,我都会看到鸟儿在我写作坊外的露台上筑巢的情景,能听见鸟儿们飞来的声音。
声音太重要了,万物万灵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你与它们有缘总会聆听到某种声音。因为世界太大了,生物圈都在我们难以细细体察到的时间里,在静谧中发出了声音。而人类永远在一个忙碌不休的社会体系中。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学着在尘土飞扬中行走奔跑;偶尔停下来,又开始面对黑暗。造物主让我们周转于世界,也会让我们栖息。这是澜沧江边的一座小村庄,我因为迷路来到此地。天色已晚,在这座被称为江舍的村里,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村妇打开门看着我说:“你是来找住处的吧?经常有人到这里会迷路。”这个50多岁的妇女让我进屋,告诉我说,她的男人和儿子都到城里去打工了,她留下来是为了种植庄稼地。我住在了她家。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看见岩石上的蝴蝶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