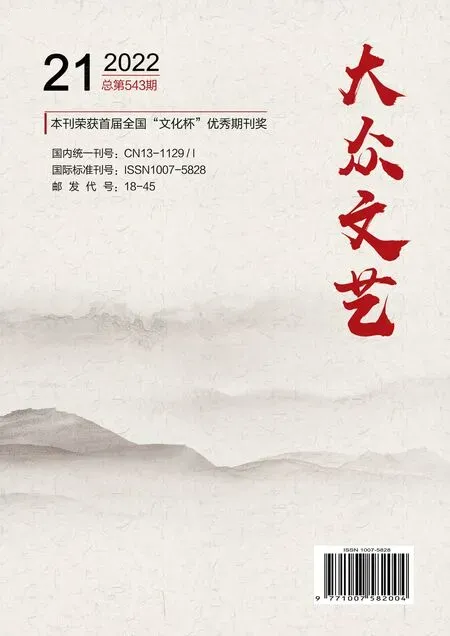扩张·消解·建构:谈顾城中后期诗歌的“弧度”空间
丁 瑶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芜湖 214000)
弧度是现代数学中的基本概念。“天圆地方”,是对古代朴素宇宙观的简单概括,表现为把一切运动视为直线运动。欧式几何对直线的界定是没有端点,笔直地延伸到无穷远。随着时代发展和科学科技的进步,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人们认识到传统意义上的直线运动在地球上并不存在,“角度”“弧度”便是人类认知发展催生的产物。如果说角度的出现是源于对圆周运动的观察,那么弧度就是从圆周运动的进行者的角度来看待圆周运动的。理论上,传统意义中的直线运动并不存在,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运动都是有一定弧度的弧线或不规则弧形。大到日升日落,小到一阵微风、一个微笑。
在顾城众多作品中,《弧线》是一首颇具争议的诗歌,描绘了四个独立、看起来毫无关系的画面。读者通常认为这首诗是诗人将自身所经历的自然美与社会丑之间的差异进行对立处理,但诗歌阅读的大忌便是片段与孤立。联系诗人其他作品和人生经历,在诗歌,乃至小说散文中,顾城总是对“圆环”“弧线”“弧度”等有着弧度特征的意象情有独钟。
大量聚合的表象其之下的创作动因总是盘根错节。首先体现在诗人对宇宙的物理感受上。“眼睛是第一个圆,眼睛所看到的视野是第二个圆,在整个自然之中这种原初的形态在周而复始地发生,永远没有尽头。圆是宇宙密码中的最高象征。”①古老的天地是顾城心中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冥冥。行走在人生的逆旅中,诗人感觉天地是荒凉的,“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神明留下的痕迹》)。当顾城醉心于东方文化的古老、美丽与可敬之时,他看见“青铜器上的花纹,上边有一个圆圆的眼睛,像婴儿一样圆圆的睁着”(《恢复生命》)。顾城在的日常生活中,他也喜爱戴一顶圆帽子。这种弧形创作情结投射在诗人的作品之中,使得诗人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以非线型运动轨迹为表征的意象群。这些意象间、主客体间形成的非线型运动关系形成了一块隐喻的阴影,乃至构成了一个颇具寓言性质的庞大语义场,这是顾城诗歌中一块不容忽视甚至颇具研究意义的领域。顾城创作后期谈及他的诗歌创作时,直言要完成“由童话向寓言的转向”。可见,顾城本人并不满足于“童话诗人”的评价。这种创作转向与对诗艺不懈探索,也在这个语义场中得到了一定的呈现。
在弧度的隐喻外扩的过程中,其前中期诗歌的童话属性被解构,并形成了一方独特的诗歌空间。
外扩:对解构的催生
顾城“童话诗人”的称号,最早可追溯于另一位朦胧诗派代表人物舒婷的一首诗《童话诗人——给G·C》(1980.04)。
出离诗人以儿童视角创作诗歌所固有的天马行空与轻盈浪漫,以及其对童话世界青幻想,顾城对自己诗歌所具有的童话特质的解释是:“童话对我的另重安慰是对付外部世界的”,②即怕黑的孩子面对恐怖时所逃回的家——一个有妈妈的安眠曲,关上了窗就可以与恐怖隔绝的童话城堡。
童话城堡通常由圆柱形的建筑主体加上尖尖屋顶构成。顾城是一个痴爱戴帽子的人,“总爱用一块布围成一顶形似烟囱的圆圆帽子”,③童话城堡可视为帽子情结在其诗歌创作中的投射。帽子宛如故乡、家庭一般予人安全感的“圆圆的城堡”:“在这里/我不怕了/这里草比人高(《我怕,我不怕》)”诗歌本身就可引申为童话中才存在的“弧度”意味颇丰的“帽子城堡”,是诗歌中的灵魂避难所。
弧度在顾城中后期诗歌中发生了充分外扩,由一个个片面、单一的诗例重复、组合、并置成了一个斑驳的诗性空间,也正是这种外扩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完成了对童话城堡的消解,在废墟之上建立起了一座包罗万象的“弧度空间”,也实现了诗人所说的“由童话向寓言”的转变。
正向:有温度的力量
由童话的庇护性正向外扩出的意象群形成了一种有温度的力量。首先,渗透出一份如光与树般散发温暖的关怀意识。
树木一次次入侵我的帽子
扁圆的鳍四下动动
——《丹麦》 节选 1987.07
建构城堡的初衷,本质是寻求自我保护,随着诗人年纪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虚构的城堡在白昼的焰火中不过是空中楼阁。青年顾城“生起病来”,发了一场精神高烧,而使病症得到缓解的正是自然。他用手掌抚摸树桩,“清凉的光明在我心中醒来”。醒来可以理解为超我与本我在矛盾无法调和时,发生的分裂。随着本我作为“心中的另一个我”睁开了认识世界的自然之眼。这标志着以树木为符号对“帽子”城堡的成功入侵。
尽管顾城的性格中有着敏感而忧郁的底色,但其绝不是一个避世悲观者,顾城相当多作品中透漏出浓厚的人道主义光辉。光不仅是其诗歌的源头,更是生命的内核。顾城是自然观是独特的,他认为人的伊始同自然万物无二,“人类就像是时刻生长着衰落着的树木。”④
树身上有许多圆环
转一转就会温暖
——《然若》 节选 1992.08
光的弧度消解了弧度城堡,这里的弧度是一种保有泛我论、泛神论色彩的“神道主义”关怀精神。树身上的圆环是太阳光辉形成的圆形弧度,“转一转”亦是一种以弧度为运动轨迹的、非直线型的动作指令。在文学作品中“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⑤诗人与树合而为一,“我”既是写诗的人,也是被书写的树,“我”在大地上沐浴着阳光的美好温暖,同时“我”还扮演着传递温暖者的角色。
在顾城国内时期的诗歌中,“本我”往往潜入太阳、树、青草的意象中,打破物与我的界限,完成主体客融合。用自然之耳来聆听万物、以自然之体去获得生存的体验,渗透了诗人关照人类心灵与存在的人文理想。顾城言,他要用生命、大自然和未来的微笑,去为孩子们铺一座草地、筑一座诗和童话的花园,使人们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像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都会实现。
其次,“弧度”又是一种富有力量、充满韧性的生命态度的展现。
“弧度”是走出孩童时代,进入社会的顾城提出的一种具体的生命态度、值得践行的人生哲学,即“做一片会游泳的黄金”。“游泳”一词的选用准确又耐人寻味。
是树木游泳的力量
使鸟保持它的航程
——《是树木游泳的力量》 节选 1985.5
我们的不幸有所区别
我们都是睡瓶中扭转的纹饰
……
没有书我们就读叶子
我也许是那些还会游泳的黄金
——《瀑布》 节选 1986.5
游泳是一项靠四肢规律性摆动产生动力的运动项目,双臂向前滑动、双腿上下摆动的轨迹就是一种弧线。游泳的本质,是一种身体感受所生发出的超现实、超自然审美体验。顾城在12岁那年全家被赶出北京,在潍河之畔“下放改造”。那样拮据、连粮食与猪饲料都捉襟见肘的岁月里,无书可看,盛夏阳光里,猪群低头忙着觅食,父子便扎入河流中游泳。“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他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生命狂想曲》)人生的逆旅就宛若在烈日中游泳,水流的阻力锻炼的是他的肉体,而烈日的曝晒锤炼了他的灵魂。游泳是树木茁壮长成所必须经受的一次次残酷洗礼,是鸟儿为了争取天空的自由不断拍打翅膀的必要行动,是万物对峙命运阻力与自身劣根进行的一场场坚韧搏击。这样深刻的诗写,打破了关于物与我、自然与人类、肉体与灵魂二元对立的界限,超出了灵感写作的范畴,有了形而上的思辨意味。
进入诗歌语言的深处,我们终将会触摸到一个永远注视永远微笑的诗者灵魂。
友人们谈及对顾城,都达成了某种共识——“彬彬有礼”“温柔”“很少激动”“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微笑是人类的一种表情,嘴角有弧度地扬起。结合顾城的童年与少年经历,这种温和敦良并不是美满幸福的殷实家庭环境积淀成的性格底色,而是作为一个所必须拥有的习惯了长期“用黑眼睛寻找光明”后坚持在痛苦中嘴角永远扬起弧度的诗者灵魂。
我会呼吸像青草一样
把轻轻的梦想告别天空
我希望会唱许多歌曲
让唯一的微笑永不消失
——《我会像青草一样呼吸》 节选 1982.3
弧度呈现为嘴角的微笑这样具体的内容。微笑也是顾城前中期诗歌的主要气质之一。这种气质与“轻灵”相结合,构成了顾城前中期诗歌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艺术风格主要源于诗人的生理年龄、对自然的情有独钟以及老庄文化对其思想的初步影响。顾城将微笑作为痛苦的对立面,如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种充满了具有鲜明理想主义色彩的希冀,微笑与痛苦被诗人置于天秤的两极。
但随着春天的离去,顾城不断经历着幻想破灭的过程。他旁观了痛苦与微笑的相互纠缠,在一种寂静的状态中,让老庄思想渗入了自己。古老而寂静像水一样无声流淌的中国文化,它“不留向希望也不流向失望,”连绘画也没有色彩。于是他选择以微笑地静观取代微笑着对抗。“无为”贯穿了顾城后期的思想与创作,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无不为”,自我就像穿行在天地间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的风,而诗歌就成为自然的生长在天地间的一朵花、一棵树。因此,笑看众生苦痛、万物寂灭,是顾城生命态度的一种“道法自然”,是一种从宇宙角度看待人世的“以道观”。这首歌的内容呼应了后来顾城在谈及大诗人应具备的条件时,所做的表述:“我认为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微笑而痛苦的灵魂……”⑥
侧向:明面的伴生者
博尔赫斯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没有隐喻关系的物体,隐喻发生的条件在于创造与阅读。同时他将隐喻根据感情色彩的不同分为积极、中性、消极三种模式。消解了弧度城堡之后,如果将正向外扩性意象定义为明面,那么侧向外扩性意象则为暗面。
暗面并没有作为明面的对立面出现,它是区别于正向外扩性意象,伴生而来侧向外扩。
这种暗面投射同样来自顾城构建童话世界的过程,自身性格的执着与敏感使童话城堡的上空笼罩了一片充满焦虑的乌云。五岁时,顾城就知道他会死亡,他看着白白的墙,觉得“像死人的灰烬,他们无言地看着我,等我到墙上去。”(《忘了录音》)童年在窗户细缝中看到马路对面武斗,便“恐惧了,脸色惨白”。这些经历如同一颗终将破头的种子深深埋在了顾城的心。这种令人惴惴不安的“被无言地看着”“被老虎追着跑”的感觉在顾城重回北京后,被辗转的工作经历、拥挤的生活状态与情感的背离与失守等诸多因素不断催发,再无法被温暖的童话城堡所安抚,上升成了一种侦破万物终将湮没虚无的死亡意识。
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
不会丢下一穗大麦
——《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 节选 1982.7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间安放我的愿望
……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墓床》 节选 1988.01
“死亡好像一种季节让万物得到休息。”⑦死亡同光一样公平,被赋予了神明般的公正慷慨。顾城并不是唯物主义的坚定拥趸。生与死在顾城在作品中界限模糊,死亡只是人切换两种生存状态时进入的一种“待机模式”,“休息的季节”。过多创痛生命体验与顾城被自然滋润形成的个性间发生了矛盾性的割裂,使其涉及死亡与虚无的诗歌中所呈现的弧度大多呈现出清醒着疼痛的悲情色彩。
首先,“弧度”是一种肉体或灵魂被扭曲、不得舒展的生命状态,更是充满危险的危险本身。
“睡瓶中被扭曲的纹饰”这样对于人被挤压的生命状态的描述在孤城诗歌中不在少数。“这个世界是一个刮风的地方,这个时代是一个刮风的季节。”⑧尤其是在他步入婚姻生活之后,他对这种不健康、被扭曲的生命状态往往有着更为深切独到的感悟,“我结婚住的小巷只有八十公分宽”,狭小的空间充斥着各种密集而胶着的声音,“让我无法呼吸”。(《忘了录音》)
那些弯曲的锚链
多想被拉得笔直
铁锚想缩到一边
变成猛禽的利爪
摆脱了一卷绳索
少年才展开身体
眯起细小的眼睛
开始向往天空
——《港口写生》节选 1982.4
写生是一种力求写实、准确地对客观事物变现方式。质言之,是作者为所观照的生命状态所做得真实复写,是世界的扭曲与现实的挤压对人心理暴力的直接投射。诗中有两类弧度意象群,一是被束者,以及“扫荡过山间的巨树,被一只强手扭曲。(《微小的心意》)”中被扭曲的树,都是不得舒展的生命状态的变形。二是摆脱了绳索之后,进入舒展的人生阶段:向往天空。换言之,有希望、有向往的人生是以舒展的生命形式为前提的。肉体与精神的界限被打破,强化了诗歌象征主义的隐喻效果,表达了更深层的审美体验与更强力的情感共鸣。
诗歌中作为扭曲运动的执行者也值得我们注意。卷曲状的“锚链”“绳索”,明面弧度类意象群在构成上的根本差异之一在于力是否被施加。卷曲是一种绵软无力的状态,而“多想被拉得笔直”,也说明借由“力”的施予可以实现扭曲角色的退场。铁锚可以由工具变为生命体(猛禽)的利爪。同时“多想”说明执行者的工具属性并不是出于自身意愿——自己无法控制自己命运。
城市就是那些影子
光那么危险
稍稍一拐
就弯了
——《他工作得很好》 节选 1988.02
城市在文学中总是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而高楼林立使得街道上充满影子。顾城在回到城市后,诗歌中自然书写特征可疑地消失了,“我”潜入某类城市的代言人(影子)之中。影子的扭曲实际上就是在城市中工作的被叙述者“他”,以及诗歌的讲述者“我”。在这里,扭曲的执行者,由工具属性的“铁锚”“绳索”延伸到自然属性的光,其的温暖公平变变异成了危险性。厄运的到来由于执行者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不可捉摸。这也是暗面与明面意象群的根本差异之二:不可控、不可捉摸性。“这所有的生命中间,都被一个宿命贯穿着。”⑨万物都逃脱不了“更高一层”的控制。
试探又迂回的“弧度”性矛盾
“生命犹如充满暗礁和漩涡的大海,虽然人类曾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然而即使用尽手段和努力,侥幸能够顺利航行,人们也知道他们正一步步地接近遇难失事的时刻和地点。”⑩不同于前期“做一片会游泳的黄金”的炽热直白,顾城中后期作品的感情波澜显得更为平静。他很少在诗歌中提出接受阳光暴烈洗礼的“生命狂想”,更多的是带有生命体验的沉着思考,诗歌的现实性与哲理性明显增强。对于迷雾重重看不清方向的前路顾城已然明白“如果前途无法看清,/徘徊也许更加有益。”(《马驹》);“人生需要重复/重复是路”(《不要在那里踱步》),徘徊与重复代表了一种不再迷信勇气,左右斟酌的行进守则。这份徘徊极具两重性,它既是一个忧思敏感的灵魂在看不清前路时产生的焦虑,更是一个视“生也平常/死也平常”(《“生也平常”》)游离人世的灵魂固有的平静与清醒。
从这个台阶
到那个台阶
每个转弯 都必须
十分合适
——《转弯》 节选 1987.4
有人说顾城真正梦碎是在英儿离开的时候,但笔者认为,顾城早已梦醒了,他早已明白生命需要转弯,而想要梦中的童话城堡中穿行,路线必须如同圆满的圆一般“十分合适”,也许他更清楚人类的力量注定无法达到“十分合适的转弯”,小心平衡才使得他一直走钢索般走出圆满的转弯,直到内外界的双重重压让他难以承受,他才脱轨于“十分合适的转弯”,从梦中跌落,肉体也归复与虚无。
宿命注定的扭曲也好,思虑心灵的徘徊也罢,将顾城灵魂引向了对关乎存在与虚无的形而上思考。
在那样一个连呼吸也充满了矛盾的年代,孩童也无法无忧无虑的成长。关于存在与虚无的思辨在他的脑海中纠缠不休。13岁时,他写下这样一首小诗:“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曾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很难想象这样沉重思辨性的话语是以何种语气从一个孩童口中说出的。人从何来,到忘何去,何以写诗,何必发表,何必发问,一切无异于煮鹤焚琴。一切的意义都是虚无,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莫比乌斯环”式的巨大悖论。
由于无限的自由
水鸟们疲惫不堪
他们把美丽的翅膀
像折扇一样收起
——《港口写生》 节选 1982.4
缚住翅膀而无法自由,自由了却疲惫不堪,主动折起翅膀换取休息的权利。这是对生存与理想间悖论的深刻阐释。“梦太深了 你没有羽毛/生命量不出死亡的深度”(《不要在那里踱步》)在生命与死亡这个极为真实而讽刺的“莫比乌斯环”式的悖论面前,顾城明白:一切生命从虚无中来,曲曲折折做迂回往复的尝试,最后终将回到虚无的起点。
你们死了
那一刻
你们在花朵中复活
在山川大海蓝天中复活
我们都是你们的身影
——《悼词》节选 1988.具体时间不详
在矛盾与悖论的纠缠之下,顾城终于在老庄思想的深层影响下,与思索击掌和解。他选择抹除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将死视为生的另一种形式,死亡从“休息的季节”这种待机模式升华为一场“在万物中复活”的神圣仪式。“我不用走了/路已到尽头/虽然我的头发还很黑/生命的自尽还没有开始”,生命与死亡是一体共存的。生活与生命是才是永恒母题,时间停滞不会生命使终止,内心的荒芜与枯槁才使脚下之路步步都是尽头。
结语
“变化是中国文化中最有生气的部分”。(11)顾城诗歌是极具变化性的,隐喻作为其常用的艺术手段,不仅解构了童话,构成了一方无尽的“弧度空间”,还产生了许多现实性、艺术性的诗歌价值。顾城离世距今已约三十载,其诗歌中所蕴含的多样性、变化性宛若被时代海面所遮蔽的冰山,亟待读者、评论家去发掘与阐释。
指导老师:杨四平
注释:
①(美)Emerson,R.W.《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刘礼堂、李松译,崇文书局,2007年版,第2页。
②顾城:神明留下的痕迹,1992年6月7日,伦敦讲话。
③朱小平.《我所知道的顾城》.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④顾城:你是前所未有的,又是久已存在,1992年11月26日,柏林访谈。
⑤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⑥顾城:1986年“漓江诗会”诗话录。
⑦顾城:神明留下的痕迹,1992年6月7日,伦敦。
⑧顾城.从自我到自然,1992年12月16日,波鸿大学演讲。
⑨顾城:唯一能启示的是我的梦——同西蒙谈《歌颂世界》《海蓝》及其他,1992年6月6日,伦敦。
⑩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白冲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1)顾城:我们是同一块云朵落下的雨滴,1993年2月23日,西班牙诗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