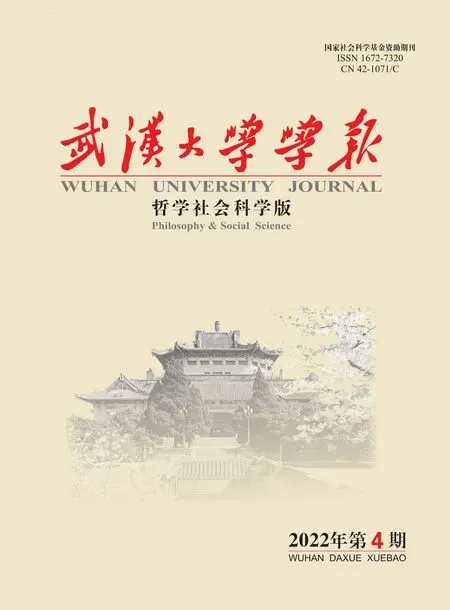“动物解放”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析
蔡华杰 王 越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兴起以来,动物解放一直是“深绿”思潮的核心性议题,其引发的动物保护运动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因囿于生态中心主义而陷入困境。本文意在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围绕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是否是物种歧视主义者的争论,阐释如下三个相关问题:第一,动物解放的本体论依据何在;第二,人是怎样异于动物的;第三,究竟如何为解放动物创造条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究,以期对动物解放作一种“红绿”层面的阐释。
一、差异中的统一:动物解放的本体论依据
马克思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璀璨明星,总是绕不过人们对他的褒贬。在人与自然以史无前例的速率互动境遇下,马克思的思想再次遭遇国际学界苛刻的指责甚至谩骂,人与动物的关系议题就是如此。对马克思人与动物关系思想进行诘难的经典性文献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特德·本顿(Ted Benton)发表的《人道主义等于物种歧视主义:马克思论人与动物》一文。正如这篇论文的标题所言,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秉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的本顿,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等同于歧视动物的物种歧视主义,认为马克思尽管存在着诸如“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样的类似深生态学的观点,但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观点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和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在对私有制下工人的异化劳动进行道德批判时,马克思采用了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法来加以阐释;二是马克思在人类解放愿景的设想中,谈及了“自然的人化”。本顿指出这两点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悖论。马克思将有意识、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视为人的类本质,以此来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因此,马克思正是这样以一种人与动物的彻底二分法来描述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物”何以可能,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又如何出现类本质的异化。如果要让人类摆脱这种异化状态,就意味着要将类本质归还给人类,同时消除人与动物的差异。而在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愿景设想中,人类的解放有赖于“自然的人化”,如果这里的“自然”包括动物的话,那么,这意味着动物要被人类改造以符合人类的需要。由此一来,本顿认为,马克思在对未来愿景的设想中就出现了悖论[1](P4-18)。
为了捍卫马克思思想的生态性,福斯特细究了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动物的相关论述,其核心论题在于论证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动物同样具有类似人类的生理性特征”[2](P1-20)。福斯特指出,这些批评马克思是一个物种歧视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只是断章取义地从一两个文本中取几句话,而忽略了马克思更广泛的论据和他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主体。为此,福斯特考察了马克思与伊壁鸠鲁的关系,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受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影响。伊壁鸠鲁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密切的物质关系,所有的生命都源于地球。动物和人一样被视为一种经历了痛苦和愉悦的感性存在物,而本顿却引用马克思的“伊壁鸠鲁哲学笔记”来说明马克思的人与动物二分法,即下面这一句话:“如果一个哲学家不认为把人看作动物是最可耻的,那么他就根本什么都理解不了。”[3](P85-86)福斯特指出,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是批判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攻击,伊壁鸠鲁抵制以恐惧为基础的宗教。因此,在这句话之前的一句话是:“既然在恐惧中,而且是在内心的、无法抑制的恐惧中,人被降低为动物,那么把动物关在笼中,无论怎么关法,对它来说反正都是一样的。”[3](P85)
从福斯特引用的这段文字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与伊壁鸠鲁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承认了动物的心理与人的心理之间的亲缘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为了批判普卢塔克的宗教目的论,强调了人在以恐惧为基础的宗教面前的受动性,而人的这种受动性,与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受动性是一样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的“人被降低为动物”其实是一种误译,应该译为“人像动物那样受动”,在英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中,原文是“For in fear,and indeed an inner,unextinguishable fear,man is determined as animal,and it is absolutely indifferent to the animal how it is kept in check”[4](P452-453),从“man is determined as an animal”来看,马克思确实将人同动物作了比较,强调了人与动物在受动性上是一样的。我们也知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样强调了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是一种受动的“肉体”存在物。
本顿认为,马克思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物种歧视主义方法论陷入了笛卡尔的主客二分哲学范式,在笛卡尔那里,动物被贬到了机器的地位。对此,福斯特指出,在本顿对马克思所谓笛卡尔二元论的描述中,缺失了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德国的哲学和心理学对笛卡尔动物机器概念批判的任何认识,而马克思恰恰是这一批判的继承者。福斯特这里所说的德国哲学和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是赫尔曼·萨缪尔·赖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他对笛卡尔的动物机器概念提出了挑战,对动物和人类心理学产生了革命性理解。赖马鲁斯的主要贡献是引入了“欲望”(德文是Trieb)这一概念,明确指出动物也有类似于人类的追求有益目的的欲望,并将动物的欲望分成10个大类和57个次级类别,其中最重要的是动物也具有为其某些行为制定规则的内在“欲望”。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身上拥有“欲望”[5](P209),在《资本论》中将蜘蛛的活动类比织工的活动,将蜜蜂的活动类比建筑师的活动[6](P208),从这些可看出马克思并不是笛卡尔式的人物,而是坚持人与动物的某种亲缘关系。这一观点显然是受到了赖马鲁斯的影响,因为马克思曾经在青年时期细读了赖马鲁斯的《关于动物的复杂本能》,并对这本著作“下了很大功夫”[3](P16)。
除了讲述马克思与伊壁鸠鲁、赖马鲁斯的关系外,福斯特也论述了达尔文、林奈、居维叶等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指出在这些生物进化学家的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并没有将人类看得比动物更加高级,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在本顿之后,从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论述为出发点几乎成了批评马克思物种歧视主义立场的基本方法。批评者先是概括了马克思在论述人的类本质时凸显出的与动物相异的人的独特性,然后列举了近代科学发展以来人们对动物所拥有的类似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以此来批评马克思在人的本质的界定上的不严谨。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概括了马克思区分人与动物的六个方面,包括自我意识、意向性、语言、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和合作。但是,根据本杰明·贝克(Benjamin Beck)的《动物的工具行为》,像螃蟹、海鸥、艾姆猴这样的动物同样具有意向性、生产、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行为[7](P61-66)。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物解放运动,其立论也是将动物的生理和心理感知作为动物权利、福利和道德地位的本体论根源,将道德对象扩展到动物身上的确是动物解放论的重心所在。
其实,对这样一种批评马克思的路径进行反驳和辩护是相对容易的,除了福斯特列举的马克思与诸多唯物主义者和生物进化学家之间的思想关系,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的其他文本考究中加以辩护。但无论是以人与动物的差异性来指责马克思是物种歧视主义者,还是以人与动物的相似性来为马克思进行辩护,都还不足以构成控辩双方的有力证据。因为对二者的任何事实的描述都未必得出某种共同的价值判断,即控辩双方都陷入了马克思有无对动物的似人性的事实描述,然而,无论事实是“有”抑或是“无”,也都无法得出马克思是物种歧视主义者或不是物种歧视主义者的判断。倘若能从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论述来证明马克思不是物种歧视主义者,那就为控告马克思是物种歧视主义者留下了反驳的空间,因为人与动物的差异性显然从表面上胜过相似性(1)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种族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之间,特别是近年来对远古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组测序的研究结果,表明现代人类的DNA并不都与智人相似,而是与前二者相似,例如现代美拉尼西亚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最高有6%的丹尼索瓦人DNA,这就为种族主义者提供了证据。。这也是动物解放论者进行论证时存在的问题,因为动物解放论者总是试图以动物的生理和心理性特征类似于人类来证明动物拥有权利、福利和道德地位。其实就连辛格都曾谈到,不能基于事实的平等来论证物种歧视主义的错误[8](P79-83),否则我们如何进一步论证那些真的没有痛苦情感的土地岩石的权利?只是辛格本人似乎也陷入了自己提出的这种错误之中。因此,将马克思对动物似人性的论述挖掘出来,其实意义也不大,若由此得出马克思就是一个人与动物的平等主义者将是荒谬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动物是否像人或者人是否类似于动物这样的事实,“动物解放”的意涵不应当基于动物与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相似性而指向动物拥有了与人平等的权利、福利和道德地位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换句话说,对这种同等权利、福利和道德地位的认可,并不会意味着动物的解放,而是跌进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陷阱中,是从抽象自然观出发,一方面把动物看成是与人无涉、不应受人干扰的抽象存在物,另一方面又要赋予动物与人同等的权利、福利和道德地位,这样一来就使其陷入难以言说的悖论中。这样一种“解放”意涵不仅会导致要求所有人都成为素食主义者的道德绑架,更是一种虚无,因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9](P335),把动物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存在物,对人来说也是无,“动物解放”这个命题根本无从谈起。
与建立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上的“动物解放”命题不同,我们应将这个命题置于经劳动实践中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语境中考察,这一语境就是要揭示自然界从原初自然向人化自然的生成过程。在人类劳动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对“动物解放”命题就有了出场意义。人与动物在整个生态圈中的“关系”是怎样的,对此问题的探究和阐释揭示出的事实将影响人在生态圈中如何行事。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显然,人与动物之间是一种共存于生态圈中“差异中的统一”的关系。尽管马克思有对人与动物相似性特征的描述,但人与动物之间明显的差异是马克思所要强调的,在将蜘蛛活动与织工活动、蜜蜂活动与建筑师活动进行类比后,马克思的笔锋就转向了人类特有的特征:“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6](P208)从肯定人与动物的相似性到强调人的独特性,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常见的叙述方式。但历史唯物主义在揭示这种差异的同时,从来不否定自然物质条件(包括动物)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中的前提和基础性作用,自然史和人类史是彼此相互制约的,从而人与动物的差异又有着“差异中的统一”的特征,即人是不可能脱离动物而存在的。这既体现在人的生存必须依靠外界自然的供给,也体现在外界自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存在,这里的自然包括除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体。所以,人与动物就在这种差异下统一于生态圈之中。从这种关系出发,对人该如何行事显然作出了限制,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动物面前,动物本身的存在构成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底线,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讲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由此一来,相比于对人与动物生理、心理性具有相似性事实的揭示,对人与动物在生态圈中的“关系”事实的揭示,更能打破贬斥马克思物种歧视主义的诘难,为动物解放提供正确的本体论依据,即人与动物是生命共同体。就此而言,当我们再审视“动物解放”的意涵时,就不是所谓的动物与人拥有平等的权利、福利和道德地位,而是人与动物在生命共同体中的和谐共生,即人靠动物界生活,动物是人生存的自然条件,人在同动物的相互作用中生产、生活和发展,人善待动物就等于善待自己。由此,动物在这种生命共同体中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二、统一中的差异:人异于动物的唯物主义殊途
如前所述,无论福斯特如何为马克思进行辩护,挖掘马克思关于人类与动物的相似性的论述,马克思还是通过阐述人的独特性而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区别开来,从而开启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运思路径。因此,退一步讲,如果暂不考虑人与动物在生态圈中的统一性,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对人与动物的差异性描述同样隐含着物种歧视主义的倾向?其实,在思想史上,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也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论之分,不同的方法论会引致不同的人类对待动物的可能结果。
对人与动物差异性的唯心主义阐释,是一种从主观方面刻意将人异于甚至优越于动物的独特性展现出来的运思路径,这种路径在描述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先验地绘上了人支配动物的主观色彩。通过对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进行追溯,我们发现早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就埋下了人区别于动物的直接证据。《旧约》宣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基督教教义中这种对人与动物的预设,是直接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并且直接赋予了人与动物在自然中的地位,动物是服务于人类的工具性存在物,由此一来,基督教教义就同时直接预设了人与动物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在马克思之前的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当然可以基于自己生理性上的差异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但这还不足以构成充分条件,而是存在着一种“认识你自己”的主观过程,即人之所以为人,也会从人自身的内部、从主观上极力将自己视为一个人。换句话说,那些不具备人之外形的动物,也有可能基于自己的能力,将自己视为人,比如《猩球崛起》中的凯撒和《西部世界》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而人在“认识你自己”的主观过程中,同动物区别开来的关键是,动物只会沉浸在对自己有意义的载体构建出的封闭循环的生态圈之中,人类则拥有打开这一封闭循环的生态圈的能力,拥有一种可以看到生态圈之外的世界的“敞开”能力[10]。阿甘本的论述是从人的主观过程开始,演进到人与动物相异的“敞开”能力,由于人极力想证明自己是人,极力想同动物区别开来,这就为人对动物的支配从主观方面开辟了道路。
那么,马克思对人异于动物的“类本质”的阐释是否也是一种从主观方面展开的解析路径呢?对于“类本质”,马克思的认识也是渐进展开的。1842年,青年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文章中,在新闻出版议题的“类本质”认识上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他谈到,“要真正为书报检查制度辩护,辩论人就应当证明书报检查制度是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而他不来证明这一点,却去证明自由不是人的本质。他为了保存一个良种而抛弃了整个类,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吗?”[11](P171)而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及其异化的阐述出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总体上看,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是这一手稿中占统摄地位的逻辑线索和话语,由于它先验假定了人的非异化状态下的真实存在,然后将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与之进行比较得出异化的非真实存在,由此论证了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从而这种论证是一种隐匿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如果从这种统摄性的话语来审视其中包含的马克思对人的类本质异化的论述,是否马克思也同阿甘本一样,陷入一种也是从主观出发来论证人与动物的差异,即人是一种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的人,为了与动物相区别,人极力试图通过展现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形成对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的支配?其实不然,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是就异化理论总体而言,在异化理论之中,其实同样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线索,而这正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与动物相异性的论述上,我们就来揭开这条线索。
人是什么?或者说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已经隐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在谈到工人的生存状况时指出,工人不是作为人、不是为繁衍人类而得到他所必要的那一部分,那么,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作为人且为繁衍人类,工人到底应该是怎样的生存状态?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在第一笔记本阐述异化劳动之前,马克思对此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反面即人不是什么作了初步的说明。在这些说明中,马克思将人同动物作了类比:“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5](P124,125),也就是说工人不应该像马等其他动物那样只获得维持肉体需要的东西,那些指责马克思是物种歧视主义的人认为马克思在此有贬低动物的意思,其实,从“像”“只”“仅仅”这样的类比方法常常运用的词汇来看,马克思在此不是贬低动物的地位,而恰恰透露出人与动物在维生方面的共性,人与动物一样都有为了生存而去获取肉体需要的东西,马克思谈及工人的“非人”的生存状况,并不是要否认工人也有同动物一样的这种特征。与动物相比,人无论如何特殊,也包含着这一特征。笔者认为,对这一点的指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从共同之处中才能找到二者的不同之处,不以共性为前提的对象,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在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也曾探讨过人的本性,他也是在与动物的比较中得出人的本性,即人具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可是这种倾向却在动物中找不到,只是为人类所特有[12](P11)。斯密没有从人与动物的共同之处谈起,而是直接断定了人具有交换的天性,那么,比较的对象既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其他生物甚至非生物。这样一来,动物就没有作为比较对象的意义了,由此所得出的人的本性也就成为一种主观臆想。而从共性出发寻求差异作为出发点,则打开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书写,我们随即可以在第一笔记本的后半部分对异化劳动的讨论中看到。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是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如果按照异化的逻辑演进链条来看,首先产生的异化是第二个异化,即劳动者同劳动过程相异化,进而才有同劳动结果——劳动产品的异化,有了这两个异化最后才推出第三、四个异化规定。依此顺序我们发现,动物一开始就成为马克思加以比照的对象,而且是从人与动物的共同之处进行比照,即在劳动过程中,人只是在运用自己的吃、喝、生殖这些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人,而在自己的人类机能方面,即在自己的劳动过程中,却觉得自己是动物。接着在劳动异化的第一个规定中,马克思讲人的对象化却表现为对象的奴隶,也是指明人与动物的共同之处。只是马克思对这种共同之处的比照,是为了说明人本不应当像动物那样劳动。那么,人究竟是怎样的?这就要到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中去寻找,正是在这个规定的论述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指认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人是一种从事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类存在物。
马克思是怎样确证这一事实的呢?是像阿甘本那样,认为人从主观上有一个“认识你自己”的过程吗?不是的。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5](P162)。人是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是如何“发现”而不是像唯心主义那样“发明”这一点的呢?他同样是从人与动物的共性之中找出了差异,“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5](P162),“也”这个词意味着人与动物最初是一样的,都进行生产活动,只是后来在各自生产的进程中,人的生产活动逐渐表现出与动物的巨大差异。例如,人与动物在最初的生产活动中都懂得利用自然力,而人在这种活动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逐渐习得“摩擦生火”这第一个具有“世界性的解放作用”的能力,从而走上了同动物界分开的过程[13](P121)。再往后,人与动物在此意义上的分离就更多了,包括人的生产变得更全面,人不受直接的肉体需要进行生产,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尺度进行生产,人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所有这些差异是马克思“发现”而不是“发明”的人的类本质特性。
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马克思、恩格斯将动物和人类的演进史上升到历史发展高度来讲述。在他们看来,历史可以从自然史和人类史两方面来考察,但这两个方面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人类的历史起初与动物一样完全受制于自然界,“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5](P534);而人类的历史除了从这些自然条件出发,还需要从这一进程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正是通过这一方面的考察将人类历史和自然历史区分开来。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将人与动物作了“比对”:“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P519)因此,无论如何人就是在自己的实践进程中逐渐脱离动物界而“越走越远”,这意味着人与动物的差异程度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反而是逐渐增强,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差异依然存在并最终完成。恩格斯指认了这一点:“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14](P564)这里还需提醒的是,如前所述,无论如何演进,这种差异及其差异的最终完成,不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进程,而是在人与动物的“统一”前提下完成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确阐述了人与动物的差异,但与基督教教义中明确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以及阿甘本的主观过程视角不同,马克思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方式,书写了人与动物的差异。马克思不是先验就假定人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者,而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指出在自然界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员,起初和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意义上二者是“统一”的。只是在各自的劳动中(假如动物也有劳动),人从最初的“似动物性”,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这一载体渐进地走出了一条“非动物性”的类存在物的“差异”道路,最终获得了类似于阿甘本所说的“敞开”能力。因此,马克思描述的人与动物的差异是一种唯物的、自然历史性的差异;也可以说,人与动物是在共同演进的过程中各自演绎了自己的不同“精彩人生”。与前述的人与动物的“差异中的统一”对应,我们可以将这种“精彩人生”称为“统一中的差异”。由此,与从主观过程出发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思路径并不产生人与动物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关系,是一种自然历史性的描述,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马克思不是本质主义者,将马克思关于人与动物的论述解读成笛卡尔式的二元论纯属无稽之谈。
三、超越资本宰制:动物解放的唯物主义路径
如果说在阐释人是怎样异于动物的问题上存在着唯心主义的运思路径的话,那么同样地,在如何解放动物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唯心主义的运思路径。唯心主义将获取正确的思想视为采取道德行动的首要任务,是先有正确的意识,而后才有正确的行动。将这种运思路径运用到动物解放论中,就意味着要教导人们进行价值观的变革,由原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转变。为了获取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必须贬斥思想史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挖掘生态中心主义的思想资源。由于宗教在规制教众行动方面的力量,上述基督教教义中对人类形象的塑造就出现了其他学者的不同阐释路径。他们认为,基督教教义中人对动物的管理关系实际上并不是怂恿鲁莽、破坏自然的态度,人类被上帝创造出来充当上帝的管理员,应当保护地上的生物,因此,完全可以从基督教教义中发展出一套生态伦理。除了基督教之外,中国传统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等思想也常常被捧上生态价值观的位置。树立正确的意识、挖掘生态价值观当然是重要的,但认为由此能够并且必须将其转化为生态行为则存在着误区:一方面,在具有生态价值观的传统中国社会里,同样存在着生态破坏的行为;另一方面,将生态价值观强加于人们身上带有普世教化的韵味,它不顾特定的历史时空和具有阶级属性的人群,要求所有人遵守同样的道德律令,是一种非历史性的“普世价值”。
唯心主义的动物解放论是“从天国降到人间”,马克思的动物解放论则完全相反,是“从人间升到天国”。马克思对人与动物在生态圈中“差异中的统一”或者“统一中的差异”这种“人间”事实的揭示,即把人当作生态圈的一个成员揭示人与其他成员的关系,仅是“影响”到人能做什么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就会形成共同的、不变的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过程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过程,人类社会最终会作出怎样的价值选择往往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其中,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对人类的价值选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上述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之所以无法得以实施,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受现实生产生活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规制或者掣肘,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对“人间”不断变迁的生产方式的揭示中隐含的对动物解放论的另一个意涵,即它揭示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人类对待动物的不同方式及其后果,并为我们提供了让动物走上彻底解放的真正道路。由此我们同样可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考察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与动物关系的动态演进,特别是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存在状态(2)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就认识到,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下,动物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他谈到笛卡尔主客二分的思维方法时指出,笛卡尔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法将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动物界定为机器,而在中世纪甚至在更久远的年代,动物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是助手:“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做人的助手”[6](P448)。。
在原始的狩猎采集时代,动物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动物是作为人的食物而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动物受制于人类,反而是在固有的生理性特征下,人类为了生存而受制于动物。摩尔根曾经指出:“从生理结构上看,人类是一种杂食动物,但在很古的时代,他们实际上以果实为主要食物;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否积极地找寻动物作为食物,这一点只有付诸猜测了。”[15](P19)的确如此,同动物相比,远古人类并不显得更加高级,为了存活,人类必须了解周遭环境,包括动物的生活习性,有些部落还发展出禁猎某些动物的图腾或每隔几年才到一个地区捕猎的猎杀模式,以此保护动物资源便于维持食物的长期供应。正因为获取动物为食如此困难,在人与动物的地位上以及人类获取和占有动物的方式上,远古人类社会均带有共同性特征,即在动物面前,人类就是“三无产品”:无人名、无私产、无交易。在美洲各地的土著中,所有氏族都以某种动物或微生物命名,例如,狼氏、熊氏、海狸氏,从没有以个人命名,氏族成员甚至声称自己就是本氏族命名的那种动物的子孙,大神把他们的祖宗由动物变成人形,他们也不吃本氏族命名的那种动物。可见,在动物面前,人类毫无个体性。马克思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则摘要了人类将狩猎和捕鱼作为相同的营生,在美洲大陆,北美的达科塔人的“狩猎物不是私有财产,而是整个狩猎者集团的共同财富。每人都获得‘相等的’一份”[16](P2)。而在交换关系上,斯密、李嘉图假定人类具有交换倾向的天性是没有证据的,在原始的狩猎采集时代,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的人类具有交易肉类之类的消费品倾向。
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后,由于人类对火的发现、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由于人类语言的产生以及人脑意识和合作能力的发展,人对动物越来越具有优越性,人与动物的关系也逐渐发生改变,从受动物的制约阶段演进到驯化动物的阶段。在农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就驯化了狗,它成为人类捕猎时的助手。后来,大约公元前9500 年至公元前3500 年,在中东、中国、中美洲地区开始驯化绵羊、山羊、牛、猪、鸡、驴、马、骆驼等动物,此后动物就分成两类: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随着上述这些动物的驯化以及野生植物逐渐被转变成栽培植物,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较之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人类社会迈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变革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权力关系,也带来了人与动物关系的变革。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用途表现为以下三种:一是仍为人类食用,二是用于皮毛交易;三是在家庭、商贸往来和战场等场所上用作役畜。除了用途的改变和拓展,更关键的是,人类社会由此开启了将动物视为财产、拿动物进行交易的道路。
马克思在摘抄摩尔根《古代社会》笔记中有关财产观念的部分就指出,对财产的最早观念是同获得生活资料的基本需要紧密相连的,随着生活资料依赖的生存技术的增进,财产的对象也随之增加起来。也就是说,当人类获取驯养动物这一生存技术后,人类就有了“财产”观念的可能。的确如此,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描述了中级野蛮社会和高级野蛮社会下,饲养动物这一生存技术的增进,促使动物归个人所有的财产观念的形成,以及动物在人类社会中的用途越来越多样化的倾向,包括其成为商品用于交换。对摩尔根的相关论述,马克思都作了摘要,并加了着重线。
那么,动物在人类社会发生这种转型后的生存状态如何?我们发现,那些被驯化的动物由原来野生状态下被随机性地杀食转变为现在被选择性地杀食,其生长的天然进程和活动空间逐渐受到人类干预和限制。因此,从自由程度来看,动物与奴隶制下的奴隶并无异样,且在奴隶解放后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发生改变,在农业社会,动物就是“动物奴隶”。不仅如此,被驯化的动物在奴隶制的社会形态下还会遭受奴隶的虐待,因为奴隶和被驯服的动物一样只是生产工具,而奴隶为了表现自己是人,就将奴隶主平时虐待奴隶的行为用在了动物身上。对此,奴隶主只能选择那些更能挨疼的动物充当劳动资料。
行文至此,我们先对远古的狩猎采集时代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的人与动物关系作一个小结:一是就获取、生产动物的目的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从食用这一单一使用价值生产向食用、皮毛交易、祭祀、搬运等多种使用价值生产的转变;二是就获取、生产动物的方式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从随机性杀食向选择性、干预性驯养的转变;三是就人与动物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从人与动物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到人类“有限”地控制某些野生动物的转变。
那么,当历史继续前行,演进到工业化生产的资本主义时代后,人与动物的关系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资本主义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流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比较动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流通中与动物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流通中的不同,从而揭示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商品流通的公式是:W—G—W,资本流通的公式是:G—W—G′,我们就来看看动物在二者中的差异。
从形式上看,动物在商品流通中可以位于公式的任一阶段和位置。动物既可以位于“W—G”售卖阶段的“W”位置,作为一种商品被人类出售,也可以位于“G—W”购买阶段的“W”位置,即作为一种商品等待人类购买。同时,动物在历史上还曾经作为货币意义的牲畜而存在,作为一般等价物促成两种商品的交换。马克思指出,在不同公社间的物物交换中变成商品的那些特殊使用价值,如奴隶、牲畜、金属,大多成为公社本身内部的最早的货币[17](P443)。后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再次指出,在交换过程中,货币形式曾经固定在本地可以让渡的财产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6](P108)。而动物在资本流通中只能位于“G—W”购买阶段的“W”位置,但它充当的角色却比较复杂。如果资本流通的总公式在这里指的是生产资本的总公式,那么,动物首先作为一种商品被资本家买入充当生产资料,“农业越是发达,它的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不仅形式上,而且实际上作为商品加入农业,也就是说,这些要素来自外部,是另外一些生产者的产品(种子、肥料、牲畜、动物饲料等)”[18](P54)。此时的动物要么成为工人的劳动对象,要么成为工人的劳动资料,或者同时充当二者,如马克思所说:“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6](P213)。当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和驯养的牲畜)作为劳动对象存在时,经过工人的劳动作用,它最终又会变成一种商品——W′出售给消费者;而当动物作为劳动资料而存在时,它就始终处于这一存在方式直至“终老”。如果资本流通的总公式在这里指的是商业资本的总公式,那么,动物在此被当作商品买入后又被当作商品卖出,这种情况主要存在于野生动物的交易中,既可以表现为供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方面的交易,也可以表现为供人类观赏野生动物方面的交易。
从内容上看,动物在商品流通中从属于获取使用价值、满足需要这一生产目的,而在资本流通中从属于获取剩余价值、满足资本增殖这一生产目的。可以说,人类获取、生产动物经历了从使用价值生产向使用价值为载体、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转变,动物不仅变成商品,而且变成资本增殖的工具。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动物都曾作为商品被人类进行生产和交换,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对动物进行交易的目的尽管随着动物使用价值的多样化发展而相应变得多种多样,但无论如何都是为了获得动物的使用价值。而在资本流通中,获取剩余价值、满足资本增殖成为生产目的,从量的层面上看,这是没有限制的发展。因此,与商品流通中的动物相比,在资本流通中必然要求动物在量上的无限繁殖和驯养的倾向,而相应的,在消费端则要求家禽消费的大众化发展。
在资本流通中,更重要的是质层面的变革,表现为动物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资本家买回动物充当生产资料,成为不变资本,其价值是过往劳动的凝结。在雇佣工人的劳动作用下,其原有价值就转移到新产品中,构成新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如果其本身就作为劳动对象而存在,那么,在生产结束时它就作为新产品被售卖,不仅不变资本的价值回到资本家手中,而且还从中获得剩余价值。因此,虽然动物不创造新价值,没有直接促进资本增殖,但它和工人共同成为资本增殖必不可少的工具。如前所述,从形式上看,在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中,动物都可以被当作商品被购买或售卖,但从内容上看,动物在商品流通中被购买或售卖是由其自身的固有的物质属性或者自然属性所决定,也就是由其使用价值所决定,体现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动物在资本流通中被购买或售卖是由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决定的,即由它的社会属性决定。我们可以根据前述它在资本增殖中转移旧价值的作用将动物归入不变资本范畴,也可以根据它在资本周转中的价值转移方式将动物归入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的范畴,动物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因此,我们不能将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中的动物等同看待,尽管二者在形式上都可以作为商品存在。马克思就曾批评斯密等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在这些概念上陷入混乱。他说:“他们把那种由价值流通引起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和物质的属性混同起来,好像那些就本身说根本不是资本,只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内才成为资本的东西,就它们本身说天生就可以是具有一定形式的资本——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牲畜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作为肥育的牲畜,则是原料,它最后会作为产品进入流通,因此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19](P180-181)也就是说,牲畜本身不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即被资本家作为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时才成为资本,而斯密等人却认为牲畜天然就是资本,或者牲畜天然就是固定资本,从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去历史化、永恒化、自然化。
当动物处于资本流通之中,它的存在方式就必须服从资本流通获取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规律。例如,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角度看,动物的存在方式受到资本周转速度的影响,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大小受到资本周转时间的影响,资本周转速度越快,越有利于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周转速度又受到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一致以及劳动期间长短的影响。资本周转时间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生产时间包括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生产资料在非劳动时间内不起劳动吸收器的作用,不吸收工人的剩余劳动,此时的固定资本也中断发挥职能,生产资本不会增殖。但“如果这个固定资本由役畜构成,那么,发生中断时会同干活时一样,在饲料等等方面继续需要同量的或几乎同量的支出”[19](P270),显然这是很不利于资本家的。因而只有减少非劳动时间,资本家才能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就出现了工厂中的换班制度,将工人在工厂中的一切时间都变成劳动时间,而当诸如马、牛等动物成为役畜作为固定资本时,工人的这种劳动状态当然也会相应导致这些役畜劳动强度的加大,从而缩短役畜的寿命,“役用马常常遭到残忍对待。过度负重的马匹,连挽具都来不及取下就一命呜呼,在体力耗尽而崩溃时,被无情地扔进沟里喂狗。……几乎所有马匹都要面对过度劳累的一生”[20](P250)。
当牛、羊这些动物成为驯养的牲畜作为流动资本时,生产这些牲畜的劳动期间由一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羊的生产可能需要两三年,牛的生产可能需要四五年,这对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需要来说太长了,因为劳动期间越长,资本周转的速度就越慢,还有遭遇经济危机风险的可能,所以,为了缩短它们的劳动期间,通过科学技术干预牛羊等牲畜的生长就成为必然。马克思注意到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拉韦涅的著作《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这一著作对英国农业经济在加速动物生长速度方面大加赞赏,因为“饲养牲畜的人现在用以前养出一只羊的时间,可以养出三只来供应市场,而且这种羊长肉最多的部位发育得更宽大浑圆了。它们的全部重量几乎纯粹是肉。”[19](P264)马克思也介绍了英国农学家、畜牧家、育种家贝克韦尔的科学研究成果——新莱斯特羊:“要在五年期满之前提供一个五年生的动物,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限度内,通过饲养方法的改变,使牲畜在较短时间成长起来供一定的用途,却是可能的。贝克韦尔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以前,英国羊,像1855年前的法国羊一样,不满四年或五年是不能宰的。按照贝克韦尔的一套方法,一年生的羊已经可以肥育,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以前可以完全成熟。迪什利·格兰奇的租地农场主贝克韦尔,由于精心选种,使羊的骨骼缩小到它们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的这种羊叫做新莱斯特羊。”[19](P264)。但是,对动物的这种遭遇,马克思表达了厌恶之感:被改变的动物“以早熟、全身病态、骨质疏松、脂肪和肌肉大量发育等为特征。这些都是人工制品。真恶心!”[21](P209)将拉韦涅的著作翻译成德语的威廉·汉姆(Wilhelm Hamm)也高度赞赏英国改进动物的农业经济,对此,马克思也质问:将这种在“盒子中饲养”动物的行为比作将动物投入“细胞监狱系统”一般,动物在这一监狱中出生直至被宰杀,问题是,这一体系与那些只是为了获取纯肉和大量脂肪而终止骨骼生长的动物繁殖体系相结合,是否会最终导致生命力的严重退化[21](P209)?马克思对牲畜生长周期遭人为干预的描述,使我们明白了当今时代产生“催熟”鸡鸭的缘由,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获取利润使然,“贝克韦尔仅靠出租他的优质公羊,就能获利3000多金币(相当于今天的5000美元)。……用肉食和羊毛赚钱是贝克韦尔永恒的追求”[20](P246)。
至此,要实现动物的彻底解放,只有置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前提下才有可能。尽管对此的制度设计还有待进一步细究,但从所有制和生产目的的维度来看,必须坚持野生动物的公有属性和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需要的生产目的。就野生动物保护而言,首要的是坚持野生动物资源的公有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区别资本主义的重要制度设计,为的是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条明确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这是公有制在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制度规定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未来开展像国外那样的野生动物狩猎旅游的消耗性旅游形式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就驯养动物的生产而言,应以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为旨趣,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区别于资本逻辑的生产目的。在此目的下应规制企业在动物制品生产过程中纯粹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出现的滥为行径,从而为人民提供符合动物生长规律的制成品。最后,我们将马克思如下这段话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来结束全文的论述:“托马斯·闵采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下述情况是不能容忍的:‘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5](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