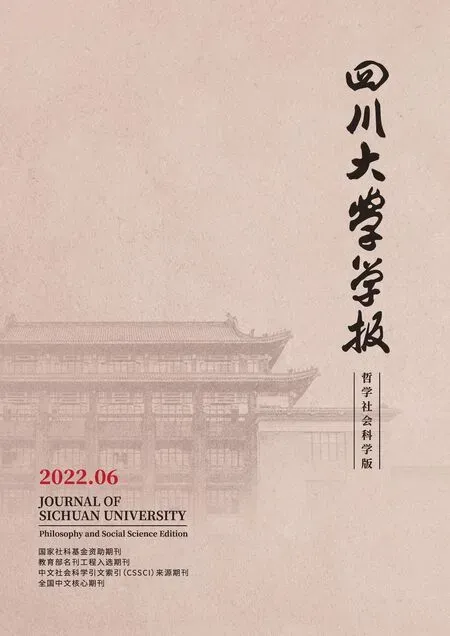日本列岛装饰古坟中圆纹的象征意义
方 艳
装饰古坟是日本列岛的一种壁画墓形制,是将适合加工的石材当作画布的特殊古坟。“在古坟内部的石室、石棺或横穴墓的壁面上施以彩色、浮雕、线刻的古坟被称为装饰古坟”。(1)熊本県立装飾古坟館『黄泉の国の彩り』、2009年、3頁。这种装饰古坟4世纪开始出现,5世纪到7世纪流行,以熊本为首,以九州岛北部为中心。由于这一时期的日本是史书的空白时代,所以残存在邻国史籍中的少量记载和8世纪的“记纪”神话,以及古坟壁画的考古材料,特别是装饰纹样,成为本文的研究依据。
一、装饰古坟中的圆纹
根据2018年的统计,日本国内发现的装饰古坟总数为721座,(2)坂本圭太郎など「全国の装飾古墳一覧」、『熊本県立装飾古坟館研究紀要第14 集』、2018年、1頁。其中九州地区428座,分别为福冈县81座、佐贺县31座、长崎县15座、熊本县205座、大分县30座、宫崎县66座。古坟装饰的纹样大致可以分为:(1)几何纹样:直弧纹、圆纹、三角纹、菱形纹、蕨手纹等;(2)器物纹样:靭、盾、大刀、弓、船等;(3)人物鸟兽纹样:人物、马、鸟、蟾蜍等。从4世纪末到7世纪,圆纹在装饰古坟中最为常见。
(一)圆纹的分布
装饰古坟中圆纹的形态有近30种,主要形状有圆、同心圆、旋涡纹与轮状纹等。(3)斎藤忠「図文の考察」、『日本装飾古墳の研究』、講談社、1973年、30-68頁;乙益重隆『装飾古墳と文様』、講談社、1974年、102-103頁。日本721座装饰古坟中,装饰种类完全不明的有139座,可以辨认或者部分辨认的有582座,其中绘有圆纹的古坟有187座,分别是:熊本78座、福冈50座、大分19座、佐贺10座、福岛6座、宫城4座、茨城4座、福井3座、大阪3座、岛根2座、长崎2座、神奈川1座、兵库1座、鸟取1座、冈山1座、香川1座、宫崎1座。遗存集中在九州地区,尤其是熊本、福冈两地,占比达70%。
(二)圆纹装饰的特点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仅仅以圆纹一种纹样进行装饰的古坟有:福岛1座、福井1座、兵库1座、福冈15座、佐贺2座、长崎1座、熊本27座、大分9座,仍以熊本和福冈两地居多。以单一纹样来装饰古坟的现象并不罕见,单一的装饰纹样有直弧、三角、家屋、马、鱼、鹿、船、木叶、靭、盾等,这些装饰纹样出现频次很低,基本以个位数计,有的甚至只出现了一两次,而仅仅绘有圆纹的古坟分布广泛,显然具有与众不同的重要性。
从历时性看,与圆纹同时出现的几何纹是直弧纹,而与圆纹共同装饰古坟的纹样中最多的是三角纹。(4)丸林禎彦「円文·三角文の展開」、『装飾古墳の展開-彩色系装飾古墳を中心に-』(第51回埋蔵文化財研究集会発表要旨集)、埋蔵文化財研究会、2002年、137-154頁。不过,伴随着圆纹作为主体性装饰图案被突出呈现,其与三角纹的结合慢慢分离。
从现有材料看,圆纹与具象纹共同装饰的古坟数量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与圆纹同时出现的具象纹多为武器,如刀、靭、鞆、矛、镞和楯等;其次是交通工具,如舟船、马等;还有人物、骑马者以及鱼鸟、鹿猪等动物图像。圆纹与具象纹结合后往往非常繁复,有精美的线刻和浮雕,主要采用以红色为主、绿白相间的彩色图案,尤以大量的红色实心圆为主体的装饰引人注目。
二、圆纹的象征意义旧说与反思
通过考古材料梳理和相关理论辨识,笔者认为有必要反思现有圆纹象征意义研究的相关成果。
(一)镜子说
关于圆纹的象征意义,有一种被普遍认可的理论是“镜子说”。在装饰古坟中首先出现的是直弧纹。松本清张曾推测,直弧纹是以镜子碎片为基础设计而成的:“这个图案可能是故意破碎的镜子碎片。”(5)熊本県立装飾館(桑原憲彰)執筆編集『舟と馬と太陽と』、熊本県文化財保護協会、2001年、28頁。他认为当时贵重的东汉镜在九州地区已近枯竭,所以要用碎片去代替,以此为基础便产生了直弧纹。可能与直弧纹为破碎的镜子这一思路有关,有学者提出圆纹也是镜子:“由直弧纹和镜子构成的避邪图案,作为石棺系和石障系装饰古坟的基本主题使用。井寺古坟的石障圆纹就是镜子,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6)木崎康弘「幾何学装飾絵柄とは何物か-菊池川流域の装飾古坟伝統の成り立ち-」、『熊本県立装飾古坟館研究紀要第12集』、2016年、8頁。也有这样的看法:“古代的装饰古坟上有彩色的花纹,线刻则以浮雕圆纹为主。这些圆纹外区有梳齿,用绳子吊着,可以认为是古坟时代的镜子。”(7)福田匡朗「圆文と三角文がウミダシタモノ」、熊本県立装飾古墳館『熊本県北の装飾古坟』、2016年、15頁。确实,有些古坟中出现的圆纹容易让人联想到镜子,例如小鼠藏1号坟、3号坟及大鼠藏尾张宫古坟的圆纹,白石太一郎就认为是镜的具象图案。(8)白石太一郎「装飾古坟へのいざない」、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装飾古坟の世界図録』、1993年、11-15頁。尤其是大鼠蔵东麓1号坟中,画有带皮鞘的太刀上挂着两根绳子的圆纹,笔者也认为可能是镜子。也就是说,圆纹为镜子的情况不能完全排除。
有学者将古坟壁画中的绘画图案与陪葬品的功能等同,认为这意味着献给死者的财宝;“因为没有得到镜子,所以应该是通过雕刻在古坟内描绘了镜子”。(9)中村幸史郎「集中的分布の背景をさぐる」、熊本県立装飾古坟館『装飾古坟-蘇る古代·装飾古坟の世界-』、1993年、28頁。但是,在装饰有圆纹的古坟中镜子作为陪葬品出土的情况又有很多。(10)下垣仁志『日本列島出土鏡集成』、同成社、2016年;岡崎敬「熊本県の古鏡-弥生時代と古墳時代-」、『肥後考古』第3号、1983年、1-11頁。例如,冢坊主古坟出土了四兽镜,臼冢古坟出土有位至三公双龙镜、四兽镜等。最引人注目的是5世纪的冈山县备前市鹤山丸山古坟,其石棺盖上线刻了圆纹和家屋纹。同时出土遗物亦有:内行花文镜4面,变形四神镜2面,变形兽带镜1面,二神二兽镜2面,四神四兽镜1面,三神三兽镜1面,变形神兽镜2面,盘龙镜1面,变形四禽镜2面,变形五兽镜1面(全部是仿制镜)。(11)熊本県立装飾古坟館『中国·四国地方の装飾古坟』、1999年、62頁。可以说,遗存中陪葬品数量多,似乎并没有因为物质匮乏而不得不以纹饰替代的必要性。
并且,大和王权的三神器中,剑和玉作为古坟壁画的题材,出现的次数非常少,可以说是很罕见。剑纹在熊本县有3例,即大村4号横穴墓、大村5号横穴墓、京峰1号横穴墓;佐贺县有1例,即田代太田古坟。而勾玉的图像,仅见于爱知县的天灯冢古坟。二者与圆纹的出现频率不成比例。换言之,大和王权的三神器——剑、镜、玉,作为实物性的陪葬品,都有大量出土,而作为古坟壁画的装饰题材,其他二神器的纹样,则很少见到。从这种现象出发,很难设想圆纹作为装饰题材的镜子在古坟中单独大量出现。事实上,在熊本县立装饰古坟馆的常设展示图录中,圆纹被分为圆、同心圆,以及所谓“模仿镜子”的同心圆。(12)熊本県立装飾古坟館『黄泉の国の彩り』、34頁。但其中“模仿镜子”的同心圆纹古坟,数量确实非常有限。
与此同时,从构图上来说,圆纹不仅被广泛地单独使用,而且在很多高等级古坟中是作为主体性的图案来设计的。例如:古畑古坟、小田良古坟、乳山古坟、永安寺东古坟、横山古坟、日冈古坟等,其特点是多在玄室奥壁的中央、天花板中央,或者是左右袖石等重要位置,以一个或多个大型圆纹为主体构图,或搭配有小的圆纹,其中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黑谷2号坟的玄室内墙中央采用凹入的技法,描绘了外形约25厘米的同心圆,这种装饰特征是其他纹样不具备的现象。并且,装饰古坟中的圆纹,有些明确是用圆规类的专门工具来画的,例如西隈古坟、四山古坟、千金甲1号坟等,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圆纹的盛行程度以及超乎寻常的重要性。
质言之,将圆纹简单地理解为具象的镜子,显然无法涵盖其全部意义。
(二)太阳说
在图像语言中,作为太阳的象征,最重要的是其光芒的表示:放射纹。在装饰古坟中,直接描绘放射纹的很少,仅有鸟取县的土下229号坟、福冈县的一本松冢古坟、佐贺县的天山1号坟及茨城县的权现山横穴墓群1号墓等。宫崎县西都市穗北横穴墓群,建造于6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其中上江15号墓的玄室大致呈长方形,装饰是通过线刻进行的,天花板北侧中央有直径37厘米的三重圆形,刻有从外圆向外放射状的约30条直线。(13)熊本県立装飾古坟館『宮崎県の装飾古坟と地下式横穴墓』、1995年、39頁。宫崎县考古学会会长日高正晴曾从三重圆纹和放射状的线刻捕捉到太阳及其光线,以此推测当时的太阳信仰。
在没有与放射纹结合的情况下,古坟中的圆纹也曾被认为是太阳的象征(图1)。如珍敷冢古坟:“正面中央顶部巨大的蕨手纹,左下有一个右下两个,左上部绘同心圆,那个下面画着船首有一鸟停留的船,……据说左端的鸟及其上的同心圆是太阳的标志。”(14)松本信廣『東亜民族論攷』、誠文堂新光社、1968年、266-267頁。从比例上来说,圆、蕨手的形态巨大,且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人像则比较小,壁面右侧还有一个小一点的同心圆。在装饰古坟中,与珍敷冢的构图非常相近的还有弁庆穴古坟、原古坟、鸟船冢古坟、观音冢古坟、五郎山古坟、濑户14号横穴墓、仓永古坟、妻山4号坟、穴观音古坟等,他们共同的装饰特征是有(鸟)船、(骑马)人物、多个圆或同心圆纹。事实上,装饰古坟中的圆纹单独一个出现的情况几乎没有,都是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同时出现,这些大小不一的圆,并出在一座古坟中。
华夏文化中有所谓“十日并出”神话:“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淮南子·本经训》)又记:“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燋枯。”(《论衡·感虚篇》)不难看出,其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十日并出”的危害,所谓“万物燋枯”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肯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在日本列岛,作为其国史起点的“记纪”神话中并没有“十日并出”的叙事,民间传说中虽有提及垂仁天皇时期,出现了一个真的太阳和八个乌鸦变成的假太阳的故事,却是强调“天无二日”,天孙皇族具有唯一的王权合法性。(15)冈正雄『異人その他』、言叢社、1979年、159頁、参照:井沢長秀「旅と伝説」、『広益俗説弁』正編巻五、國民文庫刊行會、1912年、17頁。事实上,在日本列岛,构筑装饰古坟的是以太阳女神为祖先神的文化族群,如果以圆纹为“众日”,这种“并出”的叙事内涵显然与其信仰背景相龃龉。所以,将圆纹都理解成太阳,不合常理,且与历史背景不符。
概而言之,关于古坟壁画中圆纹象征意义的旧说皆不能自圆其说。“镜子”说的缺陷在于绘有所谓“模仿镜子”的圆纹的古坟数量很少,以圆纹装饰代替实物性镜子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而“太阳”说的最大缺陷在于“众日并出”的文化逻辑谬误。那么,圆纹究竟象征什么呢?

图1
三、眼目:圆纹的象征意义新说
人在本质上是符号的动物,“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16)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1页。《古事记》序言曰:“所以出入幽显,日月彰于洗目。”(17)大野晋編『本居宣長全集 9 』、筑摩書房、1968年、67頁。日本列岛早期的文化传统中,以目生神的神圣性文本叙事与强调性艺术表现普遍存在。这种普遍存在是否关乎古坟壁画中圆纹的象征意义呢?笔者提出以下观点。
(一)正体圆纹具有眼目象征意义
乳山古坟在石屋形内壁上绘有红白两色,左侧石用斜格子文填满,菱形格子中数处置有同心圆。里墙用4块板石(1块已遗失)砌成,墙的中段和上段各画有两个并排的圆纹,“中段的圆纹像眼珠子一样增加了中心点”。(18)原口長之「チブサン古坟」、高木正文編『熊本県装飾古坟総合調査報告書』(『熊本県文化財調会報告』第68集)、1984年、42-46頁、原文:“目玉のように”。同样,横山古坟石屋形袖石上的同心圆纹中心也有黑色圆点,与人眼之睛类似,守护着尸床上的亡灵。这种两个并列的同心圆纹还见于6世纪后期的呰见大冢古坟和7世纪初的虎冢古坟等处(图2)。加之,乳山古坟又与其西北面的负山古坟,“作为连成一体的神圣的女性‘神’被人们深深信仰”。(19)文化財保存計画協会編集『熊本県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87 集 オブサン古墳第2分冊』、熊本県教育委員会、1987年、1頁。因此,笔者推测,圆纹具有作为祖先神的太阳女神之眼的象征意义。
在弥生绘画中,祖先神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金关恕考察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青铜器与木制品中的鸟形,提出弥生祭祀中出现的鸟,除被视为谷灵的搬运工之外,很重要的功能是作为“招神的鸟”。(20)金関恕「神を招く鳥」、小林行雄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委員会編『考古学論考』、平凡社、1982年、281-304頁。上井久义也认为:“在《风土记》的世界里,强烈地保留着祖神来访这一固有民俗的风貌。”(21)上井久義「祖霊来訪の説話的展開」、上田正昭編『風土記』、社会思想社、1975年、85頁。对于先民来说,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最尊崇的都是祖先神,因为一切的生产生活都是在他们的注视下进行的。

图2

图3 鸱鸮土偶
作为女性神祇的鸱鸮土偶,其标志性的大眼不仅寓意驱邪,更象征再生。日本的关东地区有一种常见的土偶名为鸱鸮土偶(图3),东京国立博物馆便藏有1尊,崎玉县崎玉市岩槻区真福寺贝冢出土。解说词描述:“此为绳文时代后期后半叶到晩期前半叶见于日本关东地区的土偶,被称为鸱鸮土偶。脸部用施有刻文的隆带勾勒轮廓,贴上圆板以表现眼部和嘴部。因这种滑稽的面貌与鸱鸮相似而得名。本作品也是名副其实,心形的脸轮廓上有着可爱的大圆眼和嘴巴。”显然,鸱鸮土偶是从形态上、尤其是可爱的大圆眼睛这个明显特征来命名的。目前为止,鸱鸮土偶最多见于千叶县北部从东京湾岸到印旛沼地区,其次埼玉县东半部即现在荒川以东台地上的各个遗址中也有较多发现。(22)吉川國男「みみずく土偶の分布と前頭の装飾」、『埼玉考古学论集』、埼玉県埋蔵文化財調査事業団、1991年、445-460頁。东北龟冈文化、关东地区安行文化中鸱鸮土偶亦被大量发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女神信仰具有生产与增殖的二重性,而这两者都与鸟神信仰密切相关。鸱鸮土偶的头上一般有发髻、梳子、耳环之类的装饰。“表现耳饰的土偶不限于鸱鸮土偶,之前的山形土偶上也可以看到,……关东地方从绳文时代后期后叶到晚期前叶,从鸱鸮土偶的耳饰表现类推作为土制耳饰的穿着者,至少符合‘女性’‘怀孕’等关键词的人物浮现出来”。(23)吉岡卓真「土偶の装飾表現と装身具-ミミズク土偶と耳飾りー」、阿部芳郎編『土偶と縄文社会』、雄山閣、2012年、210-215頁。应该说,鸱鸮土偶作为女性神祇的身份是明确的。
“鸱鸮土偶繁盛于晚期前半期,晚期中期从东北地区传来遮光器土偶后,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制作为参考,开始制作大型的东西。渐渐地鸱鸮土偶本身就消失了。可能是受到遮光器土偶的强烈影响的结果,鸱鸮土偶的传统被破坏了”。(24)八戸市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是川縄文館『みみずく土偶と縄文人——関東の晩期安行文化』、2013年、32頁。尽管这样,对于眼部的突出刻画这一点上,遮光器土偶(图4)与鸱鸮土偶仍然完全一致。所谓的遮光器为椭圆形,作为区分中间画了一条横线,这种土偶形象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其变形的大眼。

图4 遮光器土偶
为什么要塑造这种大眼偶像呢?白川静依据甲骨文的造字原理解释说:比如在领口加上祝词,这就是“哀”,再加上“目”,然后把环放在胸前,就成了“還”字。同样,上面放“目”,领口放“玉”,就是“環”。“還”“環”都隐含复活的意思。梅原猛也认为,“目”与死而复生相关,遮光器土偶的大眼睛闭得紧紧的,应该是死人。土偶为什么会有大大的眼窝呢?梅原猛在读了《尤卡拉》(25)尤卡拉(yukar)是流传于阿伊努民族的叙事诗的总称。后指出,有眼睛的死人和没有眼睛的死人不一样,有眼睛的意味着是可以再生的死人。所以为了展示可再生能力,才加上了大大的眼睛。这里,眼睛是再生的象征。(26)白川静、梅原猛『呪の思想』、平凡社、2002年、188-189頁。我们也可以联想到:“新几内亚的原住民会用黏土涂抹死者的脸来修正脸型,一般会将子安贝戴在眼睛上。”(27)高山純『民族考古学と縄文の耳飾り』、同成社、2010年、20頁、図4。这个子安贝与土偶的遮光器,在体现先民的再生信仰方面应该有异曲同工之效。
综上,笔者推测,正体圆纹象征眼目,日本古坟壁画中绘制圆纹是日本古人驱邪信念和再生信仰的体现。
(二)变体圆纹也具有眼目象征意义
古坟壁画中的圆纹,最常见的是圆与同心圆,但也有一些变体圆纹,也就是变形的圆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涡纹、蕨手纹(双涡纹)、(双脚、六脚)轮状纹。
目前为止,出现蕨手纹的古坟除了在岛根县有1例,其他都在福冈县,有9例。出现涡纹的古坟分别是:福岛5例,大阪1例,福冈2例。福冈县蕨手纹出现的古坟非常集中,基本上都在现在的久留米市和浮羽市。与涡纹不同,蕨手与圆或同心圆,往往同时出现。福冈县的9例中,就有8例是这种情况,即药师下北古坟、鹿毛冢古坟、珍敷冢古坟、重定古坟、乘场古坟、王冢古坟及日冈古坟。这些古坟装饰都有以圆纹为中心的特点,例如日冈古坟后室奥壁上描绘有六个巨大的红绿相间的同心圆,间以10个蕨手纹,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福岛县25座装饰古坟中,出现圆纹的有6座,除了南相马市浪岩10号横穴的圆(3个×2段),其他都是涡卷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6世纪后期福冈县福冈市的吉武熊山古坟,其后室奥壁的壁画上出现了十来个“の”字涡纹,且与人物同时出现。又,同一地区的其他古坟的相同位置,多见同心圆纹。
有脚的轮(圆)纹,在装饰古坟中出现得不多:熊本2例,福冈2例,大分1例,佐贺1例。熊本县还出现了3例所谓的(车)轮纹。熊本平原北部的装饰古坟中有2座采用双足轮状纹这一特殊图案,分别是釜尾古坟和横山古坟。双足轮状纹在福冈县的王冢古坟和弘化谷古坟中也有发现。7世纪中期大分县宇佐市贵船平下的里山横穴墓群,羡门位置装饰有同心圆和六脚轮状纹。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形态的圆纹出现在同一古坟的现象并非罕见。如鸟栖市的田代太田古坟,内壁的装饰是正面配置连续三角纹,中段绘有同心圆纹、骑马人物、旋涡纹、有脚的圆纹等,下方右侧画着4个盾牌,装饰文样非常丰富,尤其是各种圆纹集中出现。又,6世纪后期重定古坟,在其后室、前室、羡道都有彩色赤青的壁画,题材有同心圆、圆等。再,作为首长墓的王冢古坟,也同时出现了圆、同心圆、双脚轮状、蕨手等纹样。似乎等级越高的古坟,对于圆纹的表述意愿更为强烈。并且,王冢古坟的蕨手纹有正反两种形态,体形巨大,尤其是其旋线部分在外侧做成了心形,引人注目(图5-1)。

图5
我们可以联系中国相关遗存,以便于理解。中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商周金人面像(图5-2),是与王冢古坟的蕨手纹极为相似的图案。其解说词曰:金质,整体呈弧边圆角三角形,片状,卷曲状眉和鼻,阔嘴,尖下巴,素面。另有商周铜人面形器,解说词曰:青铜质,整器形如呈上大下小的人脸,片状,上部中央内收呈桃形。宽额,圆脸庞,圆下巴。墨绘勾勒圆眼和阔嘴,并施以朱砂。这两例中的蕨手纹与王冢蕨,极为相似,在商周金人面像中,这个文样被解释为“卷曲状眉和鼻”,而商周铜人面形器则曰:“墨绘勾勒圆眼和阔嘴,并施以朱砂。”或以为:“铜人面形器亦约略可辨夸张的口裂和眼轮匝肌。”(28)段渝、范小平:《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119-120页。其在指出这种圆纹与眉眼的关系上,至关重要。李零等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还是从河南安阳、郑州传到湖北盘龙城,然后溯江而来的。另外,三星堆的玉器,比如玉戈,跟安阳、盘龙城出土的简直是一模一样,显然受到商文化非常大的影响。”(29)李零等:《了不起的文明现场》,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第125页。金沙文化继承三星堆文化而来。而日本著名学者白川静又曾经明确提出大和朝廷与殷商之间具有特别的渊源关系。(30)白川静「皇室は遥かなる東洋の叡智:なぜ皇室は大切なのか、存続のみを論じるなかれ」、『文芸春秋』83、2005年4月号、156-164頁。
因而,这种纹饰的相似性,不应轻易地被视作偶然共生的现象,尤其是变体圆纹(蕨手/旋涡)与眼目之间的关联值得重视。
(三)圆纹的眼目象征意义与东亚地区太阳神信仰存在高相关性
东亚地区自史前时代开始,圆纹图像就已经存在。近年来,圆纹为眼目的语言符号与东亚地区太阳神信仰的联系逐渐凸显。
中国史前彩陶中的旋纹,广泛见于庙底沟、大汶口、红山、大溪、马家窑等文化的彩陶上。王仁湘认为旋目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神面的组成部分,可以名之为“旋目神”。(31)王仁湘:《凡世与神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3页。邓淑苹称之为“神祖”。(32)邓淑苹:《黄帝之时以玉为兵——我对“玉器时代”一说的看法》,《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84 页。朱利峰分析人面岩画中的旋目,提出具有“瞪视”特征的同心圆、重环双目和涡旋纹双目等三种眼睛类型,是比人类眼睛轮廓更圆的动物眼睛,表现的应是鸮面或猴面。他认为这是东亚地区普遍性的艺术现象,并且“鸮面岩画在亚洲东部和东北部的集中出现,可能与亚洲中国先商民族的神鸟崇拜有关”。(33)朱利峰:《环太平洋视域下的中国北方人面岩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6、171页。叶舒宪注意到红山文化中大量出现的“勾云形玉器”“带齿兽面形玉器”等,其造型中央突出表现的是两只“漩涡眼”,“漩涡眼是以局部代替整体方式表现的鸟女神象征,其原型为猫头鹰能够自由旋转的眼睛”。(34)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44页。整体看,商起于东北,与红山文化之间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35)于建设:《殷商传统看红山文化》,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胡厚宣说,所谓“玄鸟生商即太阳生商”。(36)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北京: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4年,第1-52页。玄鸟即猫头鹰,也就是从史前到殷商时代,被热烈崇仰的太阳神鸟——凤。(37)方艳:《从鸮凤之变论商周鼎革中周人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第2期。质言之,可以认为“旋涡眼”即太阳女神之眼。
在东亚地区,日本列岛统一王权的大和皇室也以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为其唯一至高无上的始祖——皇祖神。正是她命天孙率众神下凡,去治理苇原之瑞穗国。鸱鸮土偶与遮光器土偶等绳文土偶作为“女神像”,(38)渡辺仁『縄文土偶と女神信仰』、同成社、2001年、65頁。又被认为是“扮演了祖先神”。(39)樋口隆康編者代表『日本文化の歴史1 先史·原史』、小学館、1979年、195頁。他们除了有大而圆的眼睛之外,躯干部分也多以旋涡纹作为装饰。(40)毎日新聞社「重要文化財」委員会事務局編集『重要文化財28 考古1』、毎日新聞社、1982年、66-70頁。日本列岛的绳文晚期,还有一种旋涡纹人面土版、岩版,是比较常见的。例如,晩期安行文化原谷户遗迹出土的人面土版上密布着旋纹。又如,奈良濑户遗迹出土的土版,正反两面是四个旋目上下堆叠组成的图案(图6)。龟冈文化岩版中,这种表现就更为繁复。旋纹与旋目,在东亚地区广泛存在,它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而应是一种认知体系的覆盖。

图6 土版
壁画之外,古坟时代在畿内等地的陶俑中,还出现了“有脚的圆(轮)纹”,像帽子或者说冠一样被顶在头上的这种形象,发人深思(图7)。有学者提出:“稻荷山古坟的同心圆纹上带有放射线的图案大概也是双足轮状纹的变形吧。”(41)高木正文「肥后における装飾古坟の展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80集』、1999年、142頁。放射线图案作为太阳光芒的表现,其与圆纹的结合,可以说明确了圆纹、变体圆纹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而双足轮状纹作为变体圆纹,被“置顶”,应该是一种信仰膜拜的表现。古坟壁画中圆纹的大量使用又是日本列岛统一王权的意志表达:“如果是同心圆纹或圆纹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有这个图案的地区有可能是由同一位统治者统一了葬仪权。”(42)熊本県立装飾古坟館『福岡県の装飾古坟』、1997年、14頁。事实上,出现圆纹的古坟中有不少人物形象,甚至王的形象。例如乳山古坟中有戴王冠的人,其头上的冠是山字形冠,显然是太阳王权的象征,从古坟壁画的圆纹装饰中,不难看出其借助祖先神的象征性存在而获得庇护与力量,这样一种信仰的存在。

图7 头戴双足轮状文形冠帽的人物陶俑
结 语
从东亚地区文明发展整体看,对于眼目的崇拜与东亚普遍的太阳崇拜密切相关,太阳神最为重要的神性体现在他的眼睛上:眼睛放射出的光芒照亮了人的世界。可以说古坟壁画中的圆纹图案,以其原型象征提示了理解区域文化共通性的关键线索,如果将同心圆(双重圆纹)的中心点理解为睛,则是有睛之目;而圆(单重圆纹)为无睛之目,三重圆可以理解为(眼睛、眼珠、眼圈),是最复杂写实的表示。它们与鸱鸮土偶、遮光器土偶共同演绎了列岛的祖先神信仰。而旋涡纹等变体圆纹又与大陆文化中的旋目神纹息息相关,古坟壁画的装饰纹样中隐喻了基于神话思维的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存在。
要之,在东亚文化中,以圆纹为眼睛的符号语言,与本地区共有的太阳神信仰密切相关,而古坟壁画中大量的圆纹图案,就其系谱而言,是对日本列岛绳文、弥生文化的延续,尤其与绳文土偶有着深刻的关联。同时,将圆纹视作祖先神之眼的艺术象征,不仅可以追溯到列岛更早期的信仰传统,也可以在华夏大陆的文化系谱中寻找到其脉络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