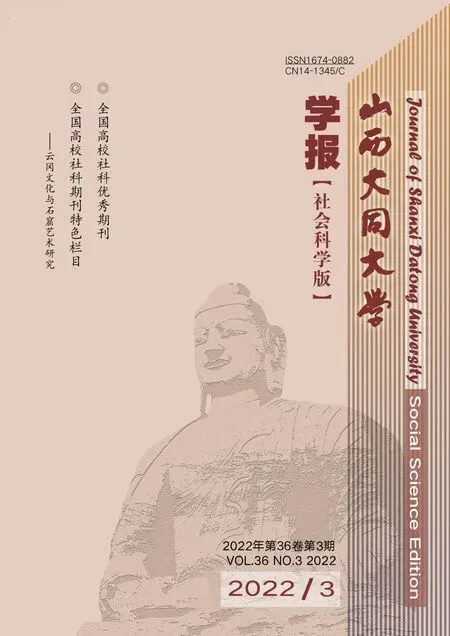抗战后中国电影的“接收”叙事及对公共领域的建构(1945-1949)
郝 瀚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北京 100089)
抗战后(1945-1949)以《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还乡日记》《乘龙快婿》《乌鸦与麻雀》等片为代表的优秀中国电影,以其鲜明的时代精神、自觉的批判意识和执着的艺术追建构起中国电影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这些影片虽在类型、风格、情节上不尽相同,但都指涉“接收”这一战后的特殊历史事件。从接收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出发,综合社会学、传播学、历史学与文本分析等视角,试图为当下重新审视战后电影之进步性提供新的方向,旨在重新发掘战后中国电影努力建构公共领域之可能性。
一、接收叙事进入电影公共领域:发生、转移与互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正式投降,随后国民政府开始对日本在华的控制区进行全面接管,史称战后“接收”。接收对象包括各式工厂、金融机构、矿山、建筑物等产业实体。由于国民政府在接收过程中的内部倾轧、监管无力,引发社会各界强烈不满。面对如此混乱的状况,甚至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此次接收“系统紊乱,权责不明,权利相争,遇事相诿,形成无组织状态”。[1]接收中经济问题尤为突出,体现在“接收大员”们对于各式经济实体的强占与勒索和对日占区百姓的强取豪夺,致使接收沦为所谓的“劫收”。上海作为战前中国大陆的经济、贸易、工业中心,自然成为接收的首要对象。
与此同时,上海更是旧中国时代电影及媒介文化最为丰富发达的场域,并建立了初步的公共领域。所谓“公共领域”,其概念源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旨在论述传播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之关系。公共领域是公众赖以表达、传播自己意见并使之对以国家权力为主体的公共权力形成影响、约束乃至监督、控制的媒介和场所,可统称为“公众媒介”与“公众场所”。在现代社会中,它们主要表现为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如哈氏所言:“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2](P172)而战后中国社会正处在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期,作为大众媒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电影深受国际/国内等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在表达方式、表现手段、题材内容、类型元素上均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也从观念上渐次完成从营利教化向公共领域的转变。与此同时,上海作为战争前后中国之电影中心,为电影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提供物质条件。另外,因接收导致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为战后电影提供了丰富的书写资源。接收亦作为公共话语不断以各种形式的媒介(新闻、漫画、广播等等)所言说,成为其作为电影叙事的基础事件,从而进入电影公共领域之契机与缘起。
电影成为公共领域,使彼时的进步影人看到电影作为“最为有效的社会宣传、动员与整合的政治工具”,[3](P12)并汲取当下社会现实作为批判工具,熔铸于电影叙事之中。而接收叙事碍于国民政府战后的严苛媒体制度与舆论管控,难以进入主流媒介的公共领域,但接收话语难以凭借传统媒介(报纸、刊物)获得较大影响力,只能借助电影这一大众媒介力量才得以更大程度进入公共领域,发挥更强的传播效果。两者之关系并非单向度的选择/被选择,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双向互动与融合。一方面,战后电影采用接收叙事,直指当下政治弊病与社会乱象,是其延续左翼电影进步性的特质所在,亦是战后建构中的电影公共领域所需要的话语条件;另一方面,自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运动以来,中国电影的公共领域从萌发到崛起的速度惊人,战后各种政治、社会力量深切认识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强力功用,并纷纷介入电影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争夺之中,接收叙事进入电影正是进步影人对于公共话语权积极争夺的体现。
接收叙事与主流媒介公共领域相抵牾的原因与国民政府战后舆论管控不无相关。国民政府战后通过经济与政治上的各种隐秘手段介入新闻媒介市场,帮助党媒占据舆论高地,又以官办方式管控大部分主流新闻媒介,如报刊,电台、通讯社等。甚至不惜采用动用国家机器强力的举措,“据统计,自1946年1月到8月,单是全国报纸、杂志、广播电台。通讯社等言论机关被查封的就有二百六十三家之多。”[4](P157)正如著名导演汤晓丹所言:“胜利以后的一连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令人不快,即使官方的通讯社也不能讳言‘惨胜’与‘劫收’”。[4](P184)
由此可见,接收叙事想进入官方掌控的公共领域必然会采取一定策略。借助文艺形式,用隐喻、寓言等等看似“温和”的言说手段包裹敏感的话语实质则是最为安全的手段之一。彼时报刊上出现了许多以接收为题材的诗歌、小说、漫画等的文艺作品。如以诗歌形式反应接收事件的“劫收谣”:“说劫收,道劫收,原来接收是‘劫收’,‘劫收’大员真富足,可怜百姓遍地哭,劫罢前方又后方,接受队伍好忽忙,九岁女孩成俘虏,劳工医院变监房,天变地变人事变,统统出在胜利年,人身保障今何在,举头无语忘青天”,[5]又如“胜利后到,接收先到,有升官,有发财,无怪乎,演戏庆祝唱几台”;[6]又或以讽刺漫画形式进行包装。但无论诗歌、小说,还是漫画,都无法出现在主流大众传媒之中,难以发挥较大的传播影响力。
综上,考察接收叙事进入电影公共领域的过程,亦即两者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国民政府官方控制的主流新闻媒介对敏感话语的排斥,促使接收主动依附电影这一大众媒介,而就中国电影自身而言,战后电影在类型、表达、制作上高度成熟迎来又一个“丰收时期”,其传播效果远超其他媒介。另一方面,20世纪30、4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尤其在抗战所催化下,电影的宣教功用被迅速放大。中国电影急速成长为政治、商业和大众文化等多元话语交错缠绕的公共领域。在战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官方意识形态/商业资本/大众文化一同介入电影传播的公共领域,促进电影成为重要的公共领域,实现电影媒介社会角色——“社会权力综合体”[2](P224)的功能演变。战后电影向着公共领域迈进,亦会主动吸纳批判性、进步性的话语,而接收正是最具时代特色,直指当下社会弊病的绝佳话语。
二、接收叙事与战后电影之双向互动历程:暗和、阉割与禁止
战后采用接收叙事的电影随当局政策与时局变换历经暗和、阉割与禁止的历程。作为最早进行接收叙事的两部进步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与《一江春水向东流》被誉为战后史诗悲剧电影的“双子星”。《八千里路云和月》将接收大员周家荣的腐败行径与演剧队员江玲玉、高礼彬的生活进行对比,以批判立场抨击战后社会环境。而《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部《天亮前后》则描绘了张忠良返回上海后,借助接收大员的身份抛妻弃子、醉生梦死的嘴脸。
长久以来,两部影片一直被视为进步电影的杰出代表,其内容又都抨击战后的接收乱象,却不妨碍两者位列“1947年度十佳电影”之列。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斩获头名,获得“卅六年度中正文化奖金金牌奖”,即象征官方认可的“中正文化奖金”。[7]而“中正文化奖,邀请影剧人士,各大学教授,各机构首长等三百余人参加评选,以考量编剧、表演、摄影及其他等五项艺术成就为基准,选出年度十部影片”[8]从评委阵容来看,该奖项的评选确实有着艺术至上的倾向,但参评人士中不乏官方代表,例如国民党中央常委、《晨报》董事长潘公展等人。两部电影的接收叙事看似获得官方认可,彼时待遇也并非传统电影史中所言的“采用种种恶毒手段对进步电影加紧迫害”。[4](P154)
事实上《一江春水向东流》与《八千里路云和月》所获“官方认可”之愿意,实则在于两片均有意无意间暗和时代主流话语。十部获奖影片(按照排名依次为:《一江春水向东流》《裙带风》《母与子》《八千里路云和月》《遥远的爱》《玉人何处》《春残梦断》《天字第一号》《中国之抗战》《松花江上》)作为彼时电影的主流代表,虽种类、类型、题材、风格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都对抗战进行不一而足的描摹:如《遥远的爱》依托“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会战事变”等抗战中重要历史事件表达女性的觉醒;《天字第一号》依托谍战类型,描写抗战时期国民党间谍地下工作;《春残梦断》则以“七七事变”为背景进行叙事;《中国之抗战》为美国摄制中国抗战的纪录片;而以八年抗战时期为时间背景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更不遑多论。
由此可见,直接取用抗战题材或依托抗战这一历史背景叙事可视为战后初期电影界的主流运作。在战后民族情绪高涨、两党冲突日益激化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取用抗战题材,或以抗战为历史背景叙事的电影可以为大众无意识情绪的宣泄提供疏导通路,甚至具有转移大众注意力的功效。这也可以解释以上两部影片可以取得官方舆论认可的主要原因:两部电影的叙述重心在于战时而非战后,并统一于彼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语境——抗战之“惨胜”上。或者说,对于战时场面的表现更为突出。究其愿意,抗日战争带给人民的创伤性体验一直延续到战后,成为战后中国大众无意识与社会集体心理的一部分,同时构成两部影片浓厚悲情意识的来源。此外,两部影片自身艺术上的高度成就获得民众官方一致认可,两部影片显示出抗战爆发后影片中所罕见史诗风格。其中尤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甚,其上映之时万人空巷,“该片上映十六天,真是天天满,场场满”。[9]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并获得当年的票房冠军,打破昔日《渔光曲》所创立的国片票房记录。[10]总而言之,与其说国民政府认可两部进步电影,不如说是对于抗战题材的主动指认。
随着解放战争爆发,国民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并希望以“戡乱动员”达到所谓团结民众、稳定社会之目的。戡乱法令的颁布使国民政府对于舆论的钳制更加剧烈,紧缩的局势必然波及文艺政策。由于接收叙事针对国民政府战后的混乱治理与社会乱象,显然不利于战争白热化阶段国民政府的形象建构。“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向电影检查处发出了要依法严格检查影片的训令,”[4](P157)迫于社会环境的压力,“戡乱动员令”后的进步电影更难以进行接收叙事,并被电影检查制度阉割与改写,甚至遭受禁拍。
赵丹导演的《衣锦荣归》讲述知识分子、中学教员林道君(顾而已饰)在战时弃学从商大发战争财,战后摇身一变为接收大员,返回上海接收“胜利财”的故事。在“戡乱动员令”的钳制之下,该片“有不少暴露性场面及插曲中‘胜利竟成灾’的歌词,都被剪掉了”。[4](P186)而电影《乘龙快婿》在国民党的电影检查制度下同样做出种种妥协,亦被当时舆论评价“结局的含糊和软弱便是全片最大弱点。”[11]而《还乡日记》也如《乘龙快婿》立足于导演自身的知识分子视角和经历,即导演张骏祥本人所言,“根据自己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找房子的痛苦经验”所摄制。[12]影片的主角和叙述重心自然转移到对于战后知识分子生活与社会地位的考察之上,面对“戡乱法令”的进步电影显然要面对更多的创作限制与言说禁忌。
直接讽刺接收事件的进步电影必将直接遭受禁拍的命运。1947年6月,昆仑公司筹拍新片《天官赐福》。原定由大导演史东山执导,为确定影片进步色彩,“特地拍电报喊卫禹平南来,中电喊黄宗英,国泰喊黄宗江,于是北方演员大胜利,南方演员顾也鲁等只能再南向香港发展矣。”可见其班底或来自昆仑公司或来自左翼影人,甚至对有“孤岛电影”背景的演员顾也鲁持排斥态度。该片由著名左翼戏剧家陈白尘编剧,作为他1945年于重庆创作的著名三幕讽刺政治喜剧《升官启用新人图》的姊妹篇,《天官赐福》在剧作上更为直接、尖锐地讽刺从重庆返沪之接收大员的腐败行径。如此激进的《天官赐福》显然难以通过官方电影审查,最终未能成拍。
而另一部以接收叙事建立主要戏剧冲突的的政治讽刺喜剧《乌鸦与麻雀》则更为命运多舛。作为中国电影史之经典,该片由昆仑公司摄制于1949年4月,彼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其抨击力度也随着时局的白热化达到最高峰。该片除建构起接收大员强占民宅的常规叙事结构外,亦展示解放战争末期因当局不利在上海制造所制造的种种社会乱象,如恶性通胀、货币贬值、黄金买卖等。该片令接收大员侯义伯身着军装,直接指涉其官方身份,并以侯义带领情妇伯仓皇逃窜至台湾作结,影射解放战争结束默契国民党濒临溃败之态。如此激进的表现难逃被禁的厄运,于是“1949年4月下旬,反动派警备司令部对影片进行直接干涉,下了一道禁令,说它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4](P147)昆仑公司也不得不公开声明“最近为了电影审查会对剧本审查未予通过,即日起该片已暂停拍摄”。[13]而实际上拍摄活动转至地下,据导演郑君里回忆:“公开的拍摄工作不能继续了,我们就索性对剧本作一次较大修改,重新分镜头,准备一旦解放就重新开拍……”。[14]接收叙事无法逾越强力政治规训,影片的命运亦是如此。盖因该片的摄制时间具备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偶然性,才得以完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综上,诸多电影采用接收叙事结构全片,甚至获得官方褒奖,似乎说明国民政府官方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接收这一敏感的话语进入电影公共领域。但究其实质,原因在于这类影片暗合抗战刚刚结束后特殊社会文化环境。
三、接收叙事中两种基本人物形象:“接收大员”与“重庆人”
接收叙事中最为常见的人物形象之一便是“接收大员”。所谓接收大员,原指战后国民政府委派的前往日占区接收战时日伪产业的官僚群体,因其位高权重故统称接收大员。而在具体接收过程中,接收大员们缺乏有效监管,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内部派系的倾轧导致争权夺利,更有一些见风使舵、投机倒把者混入其中。故而以接收大员身份的反面形象衬托知识分子身份的正面人物,成为接收叙事中的常规人物塑造手段。如《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周家荣与救亡演剧队成员江玲玉高礼彬夫妇对比;《还乡日记》中的老洪与老赵、小于夫妇对比;《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张忠良与其弟张忠民夫妇对比。碍于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制度,接收大员的政治背景、社会身份只能隐晦的借助台词、动作交代,或以脸谱式的造型(油头/西装/皮鞋/八字胡)作为观众指认其身份的符码。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下篇《天亮前后》中,战后摇身一变为接收大员的张忠良去机场迎接重庆的朋友,朋友对张忠良笑道:“金条发了不少,大概五子登科了吧?”,意指张忠良在上海的接收作为。影片中虽未直接展示张忠良前往上海后接收的具体动作,而是直接表现张忠良接收后的“成果”:住进了已经被捕入狱的附逆人士温经理的豪宅;与温经理的情妇何文艳勾搭成奸;按重庆夫人王丽珍的要求购买了八件最时髦的昂贵大衣;接机、出入豪宅都以豪华小汽车代步。
另外,“重庆人”也是接收叙事中最常见的人物形象。所谓“重庆人”,又称“重庆来的人”,在战后特定的文化/社会语境下,“重庆人”特指战后从重庆大后方前来接收的各式官僚。重庆的地缘色彩指明战时“陪都”的身份,同时又避免因直接表达所引发的政治敏感,话语的编码/解码已成为彼时观众与作者的“共谋”。正如彼时新闻舆论评论:“于辞书中加入‘重庆人’一条,其解释为中国之特种民族,高高在上,并不必有真才实学”。[15]与接收大员不同,接收大员在语义上直接规定主体身份,多以反面角色出现。而重庆人除了指涉接收大员以外;另指涉虽来自重庆大后方,却有着操守与抱负的爱国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张骏祥导演的《乘龙快婿》,其剧本原名即《乘龙快婿——原名“重庆人”》。[16]该片以主角司徒炎的身份移置建构喜剧情境,所谓移置是指一事物正常属性/假定属性间的置换。故事展示来自重庆的清贫记者司徒炎被误认为具有接收能力的“重庆人”,致使其未婚妻文兰与亲戚空欢喜一场。但身份移置并非司徒炎主动选择,而是被动误认。正如台词所言:“为什么你们都认为每一个重庆人都是长满八只手的贪官污吏?”。可见在战后的社会语境中,重庆人自渝抵沪上是为了接收,显然已然成为共识性话语。
四、接收叙事的两种基本表达策略:家国同构与伦理批判
接收叙事具备两种基本表达策略:家国同构与伦理批判。究其原因,一是碍于舆论管控与电影检查,接收叙事需要一定的特殊策略规避风险,以达到进入电影公共领域,展开批判之目的。二是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范式中,家/国往往密不可分。这种文化心理深刻影响了中国文艺悠久的“家/国一体”与“伦理/政治一体”的叙事传统。因此战后电影为规避审查风险,从而采用在叙事上采用“家/国一体”和“政治/伦理一体”两种主要表达策略。
首先,战后电影中接收叙事往往围绕民宅(房子)的接收呈现。一方面,接收大员追求的“五子登科(车子、房子、票子、金子、女子)”里,房子可排到头号地位,而接收过程中对于民宅的侵占也属于常见状态,亦可以激发绝大多数观众的共鸣。进步电影围绕争夺房子归属权,抗战后返乡却无家可归等的社会现实进行叙事,具有很强的隐喻意味。另一方面,从电影修辞的角度考量,用房子/家作为浅显的喻体来指涉国家更易于为一般民众所理解。接收中对于民宅的侵占、房产的争夺被确认为接收大员对于民众家庭的破坏、国家的争夺上。这一隐含的叙事逻辑遵循“家/国一体”式叙事模式,在接收这一确切的社会历史事件前显得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例如《还乡日记》开篇便将老赵、小于夫妇在重庆大后方生活的现实家庭空间与想象中返回上海后的超现实家庭空间进行对比。影片先以中近景的狭窄景别、灰暗低调的摄影风格展示现实中的逼仄空间,以及夫妇二人不得不睡在双层床之上的窘迫。而两人想象中的画面则以开阔的全、远景,明亮、高调的摄影展示返回上海后居住的宽敞别墅,更有两人未来生育的一儿一女在草坪上尽情玩耍。但两人返回上海后却面临社会上空屋大把但无房可住的荒诞情景,两人被迫住进环境更为恶劣的阁楼,比战时更为糟糕的家庭空间无法满足两位知识分子建立正常三口之家的人伦愿景。其原因在于上海大批房产遭受接收大员强占,大员借机收取金条作为高昂租金。同《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样,《还乡日记》同样旨在表明接收事件对于家庭/国家结构的破坏上。
而在特殊背景下创作的影片《乌鸦与麻雀》中,其家/国一体式叙事达成强烈的批判效果,无论影片创作动机还是内容本身都有强烈的政治寓意。以“天下一般黑”的乌鸦隐喻国民政府溃败前挣扎的接收大员侯义伯,以麻雀隐喻居住在同一房子中的平民,并精心将人物身份进行符号化设置,建立人物身份/阶级的归属关系:小广播夫妇(小资产阶级)、华氏夫妇(小知识分子)、佣人小红(无产阶级)。在叙事过程中,众人从互相推诿到联手保卫房子,从惧怕侯义伯到勇敢与之斗争。影片的结局选在除夕之夜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时刻,将侯义伯仓皇出逃的狼狈姿态与众人共同辞旧迎新、亲如一家的温情场面进行对比。以此隐喻不同阶级、社会身份抹去裂隙,在保卫房子的过程中建立近乎亲缘的关系,由此将保卫共同的房子/家庭/国家这三重关系同构。
政治/伦理的同构则是接收叙事的另一种策略。同样碍于电影检查制度的规训,以及1947年后“戡乱动员令”的发布,电影难以无法直接对接收大员进行政治层面的批驳或法律层面上的审判。进步电影往往以伦理化的叙事的策略将正面人物,即进步知识分子或受损害的平民与对立面的反面人物,即接收大员进行伦理姿态上的高下对比,以伦理批判同构政治批判,借以缓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确保影片进入公共领域的安全路径。
其策略在于接收大员/反面人物往往被塑造成“反伦理”代言人,而其所反的伦理大多体现在性伦理层面,即性观念上的非道德处理。如《乌鸦与麻雀》中的接收大员侯义伯的恶行主要在于缺乏性道德,他以自己接收来房屋的居住权为要挟,几次试图对华太太(上官云珠饰)进行性剥削。华太太因搬家问题首次找到侯义伯时,编导使用大量特写展示强化侯义伯面部表情所流露出的不轨之意,用密集的反打展示侯义伯对于华太太充满色情意味的凝视,以及贞洁的华太太并未给予目光的反馈。最后侯义伯以救华先生为借口将华太太请到餐厅,将她逼迫到包厢的角落,此时华太太的面部渐渐隐没在阴影中。两人的面部特写交替正反打,华太太处于俯拍,侯义伯处于仰拍,这一视觉处理完全遵循伦理化视角。
而《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当代陈世美”张忠良则完全符合这一伦理定式,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身为夜校教师的知识分子,张忠良缺乏基本的性道德,他不但对原配素芬始乱终弃,战时又在重庆与旧相识王丽珍勾搭一处,返回上海后又与附逆人士温经理的情妇何文艳打得火热,而何文艳与王丽珍又有着表姐妹的血缘关系,这一处理强化张忠良对于伦理禁忌的僭越,最后张忠良因懦弱无力又逼迫素芬用自杀方式维护尊严。另外《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接收大员周家荣以物质条件为砝码,不断引诱已经成婚的表妹江玲玉,对于已经同居的未婚妻,将其称之为“一个朋友”;再如《还乡日记》中的反派人物老洪自重庆前往上海后,迅速霸占汉奸老裴的妻子小桃,而老裴通过种种手腕将自己洗白成“地下工作者”后出狱归来,老洪不但拒绝“归还”小桃给老裴,竟又叫来帮手与老裴进行闹剧式打斗,女性在此被反面角色物化为随意易主的性工具,其作为已完全丧失基本的伦理道德。
由此观之,接受叙事采用特定的策略以此规避政治规训的风险,而家/国同构、政治/伦理同构的叙事模式又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与中国民族文艺文化范式,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进步影片的观赏性。
五、结语
基于重写电影史的环境下,回溯战后中国电影中独特的接收叙事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理论层面上的价值,即对于1940年代中国战后电影进步性的再度体认;另一方面则是现实层面上的意义:电影如何反映时代、如何处理与社会历史的关系都是这门艺术形式所面对的永恒命题。此外,作为公共领域的中国电影仍在建构之中,我们应清楚地认知电影传播的公共领域应是普世的、公众化的、作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被大众深度参与的。另外,中国电影的公共领域无论在史述亦或现实之中都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本土化形态,对于电影传播,尤其是建构中国电影作为公共领域的认识和实践始终处于不断演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