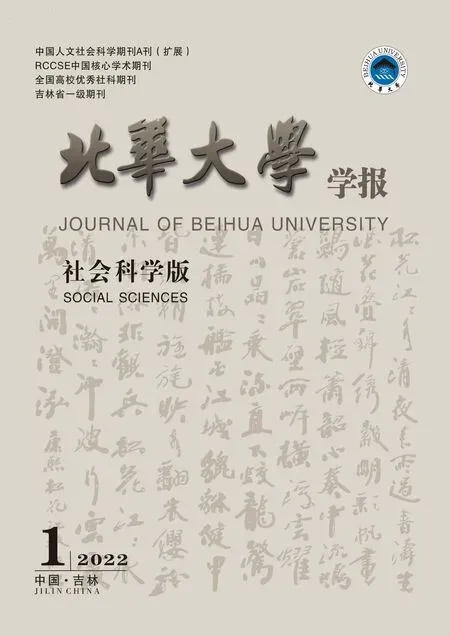从“文明象征”到侵略利器:近代日本在华图书馆的职能嬗变
万亚萍
引 言
近代日本图书馆事业是明治维新文明开化政策的一环,日本社会的变革又为其图书馆文化发展提供了契机。近代日本人在华创办图书馆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一个特殊现象。1901—1945年,在我国台湾、东北、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开办了大大小小近百所日本图书馆。目前,学界针对日本在华图书馆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以个案研究为主的图书掠夺和破坏、文化摧残、殖民教育等文化侵略方面,对其本源性、根本性问题的探究还不够。事实上,早期日本侨民“有志者”在华创办的图书馆,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文明象征”而设立的。后来,受国际局势及中日关系的影响,大量的职业图书馆人来华“谋业”,图书馆“社会教育”机构的功能凸显,军政当局试图利用图书馆这一“工具”加强在占领地的文化统制。二战前后,尤其是在战时日本总动员体制下,在华日本图书馆背负起特殊“文化使命”,越来越多的从事各种带有殖民侵略色彩的文化、教育活动,成为日本对华殖民文化侵略的“利器”。系统考察近代日本在华图书馆社会功能的嬗变,将对客观描述近代日本在华图书馆活动的文化侵略性质提供依据。
一、作为“文明开化”象征的在华日本图书馆
明治维新以后,作为文明开化的成果之一的日本近代图书馆事业得到发展。日本文部省书籍馆从开始的居无定所,后几经辗转,又回到上野公园旧址。图书馆与上野公园无形之中便形成了地理上的牵引。在明治年间出版的风景图绘,尤其是明治维新后不久出版的各种名胜图绘,如《开化东京名胜图绘》《东京名胜之·上野山一览图》等均把上野公园作为人文景观倍加推崇。位于上野公园的“近代图书馆”,自然也是被标榜的近代文明开化的产物之一。1890年,小川尚荣堂出版的《东京名胜图绘》中,东京图书馆已独立于上野公园单独在列。[1]在日本的宣传引导下,当时赴日参观考察的外国人大多将“上野图书馆”作为主要“景点”游览之地,在他们的游记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日本图书馆的相关记载。随着日本殖民扩张步伐的加剧,在国内被宣传、标榜的图书馆文明逐步带至海外。早期日本侨民在海外创办的图书馆,很大程度上都是作为“文明象征”而引入的。
(一)作为“新地标”的台湾文库
中国台湾是日本最早的海外殖民地。发端于1898年的台湾文库,被认为是日本在台湾图书馆事业的嚆矢,也是日本在海外殖民地创办的第一个图书馆。对于其“文明象征”的职能,从其“成立宗旨”便可窥知一二。
“台湾乃南海一个孤岛,所在僻远,人文未开。由此,居住于斯土者,条件不若中央之水准,可谓理所当然。更因社会秩序未上轨道,有使人们行为未臻理想之嫌。如今,欲矫正此种弊端,实有强化自学充实之必要。而所谓自学充实,则非设置公共图书馆不可。”(1)据台湾学者林景渊《日据时期的台湾图书馆事业》(台北:南天书局,2008)一书,该宗旨发表于1898年创刊的《台湾协会会报》第18期。
依“宗旨”所言,台湾“人文未开”,设置公共图书馆是以丰富知识促进台湾民众的“文明开化”,而公共图书馆即是文明的象征。1901年1月27日,台湾文库举行开馆仪式,馆址设在当时的“淡水馆”。“淡水馆”的前身是清光绪六年(1880)由台北知府陈星聚等募资创建的登瀛书院,光绪十六年,知府雷其达奉命修缮,建筑新舍,此后即成为台湾的文化地标,“四方学者就读于此者甚众”[2]。日本据台后将此文化地标改为官员俱乐部,并更名为淡水馆。背负“文明象征”的台湾文库选址于此,是希冀此处能成为台湾的新文化地标。
台湾文库存续时间不长,由于受到台北市区规划变更以及“淡水馆”的木质结构腐朽老化、文库经费短缺等因素的影响,于1906年8月正式关闭。其馆藏13 000册图书几经辗转后被1915年开馆的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继承,也正因为如此,台湾文库被认为是该馆的前身。但二者的职能有着根本的区别,由日本官方指导成立的台湾总督府图书馆乃是日本在台进行文化统制、“思想善导”的机构。
(二)日本模式的“清国日本图书馆”
近代天津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可追溯至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天津设立的都统衙门时期。都统衙门总秘书处的汉文秘书丁家立曾提出在天津兴建公共图书馆的设想,并提交了具体方案。但直到1902年8月都统衙门关闭,该计划并未付诸实施。1905年8月开馆,由井上勇之丞、原田俊三郎等十余名在津日侨发起建立的“清国日本图书馆”,是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最早创办的图书馆,也是近代天津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该馆仿照日本俱乐部经营模式,采用会员制,选举推荐会长1名、评议员20名,缴纳会费的会员可以免费阅览图书,非会员则要另外收费。该馆的创办初衷是为居住在天津的日本人及其子女提供文化、教育上的便利,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将日本图书馆模式搬至中国。
“清国日本图书馆”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转变,并随着管理者的变更而几易其名。1908年以后,随着军政力量的介入,该馆表面上看来是为普通日本居留民提供服务的通俗图书馆,实质上是为侵华日军提供了大量书刊资料和重要情报信息的参考图书馆。学界对此也有诸多研究,不再赘述。
二、作为文化输出工具的在华日本图书馆
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学界、政府在文化输出的动力下主动向中国知识分子输出文化——德育、法律等都成为文化产品。而在华图书馆是日本“对华文化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文化输出的“产品”,又是输出文化的“工具”。利用图书馆这一“工具”加强在殖民地的文化统制,这并非日本原创,英国早在殖民地经营中实践过。日本学习西方殖民经验也有迹可循,如由日本外务省拓殖局编辑的《拓殖局報》(第22辑)列举了英国在殖民地的经营机构,其中便有“殖民图书馆”的描述,涉及殖民省附属图书馆及各殖民学校附属图书馆等。[3]然而,日本人将图书馆在殖民活动中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在朝鲜及中国台湾、东北地区创办的日本图书馆均可窥见端倪。
(一)“满铁”图书阅览场的社会教育属性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办图书阅览场是遵照官方要求,其最初定位便是作为“文明输出”工具的社会教育设施。1910年2月3日,日本文部省向各地方行政长官发布关于建设图书馆的训令[4],同年6月18日勅令第278号,更正了原图书馆令中的第五条[5],文部省随即于该月30日发布“图书馆令施行规则”[6]。作为日本官方代理,“满铁”有在当时开办教育设施的义务,并根据“关于图书馆施设的训令”要求,所开办的中小学内需附设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因此,“满铁”附设的图书阅览场,几乎与其沿线小学校的建设同步进行。
1910年9月3日,“满铁”《社则》(第5号)上发布了“图书阅览场规程”,明确了阅览场的图书分为三种,即巡回书库、常备图书和临时备用图书,各类图书的选择是在地方课的指导下由调查课具体实施。[7]在“满铁”沿线主要地区开设的图书阅览场增设巡回书库,主要是为了借助图书阅览扩大影响。1910年10月中旬开始,各图书阅览场逐步开放,最早建成的有瓦房店、大石桥、辽阳、奉天、公主岭、长春,而后是铁岭、开原、本溪湖、安东等地,至1913年6月已达10处。各阅览场的特色不一,针对各阅览场各自为政的情况,当时的“满铁”已然开始组织各馆间的联络合作,试图建立一种总分馆模式。[8]仔细推敲图书阅览场的性质便会发现,图书阅览场虽名为公立,经费由政府和“满铁”公共承担,但是图书的选择和配置权均为“满铁”所有。公立的图书阅览场和私立的调查部图书室,人为地想要促成总分馆的关系。“满铁”从一开始的定位便是“殖民会社”,其下属的调查部图书室的经营目的,自然与“满铁”的宗旨保持一致。名义上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图书阅览场,实质上从一开始便是“满铁”文化政策的一环。
由于经营差异,各阅览场存续时间不一,但其命运殊途同归。以奉天图书阅览场为例,虽然该阅览场建立较早,但由于奉天的“寒村”地位,一直不受重视。直到经张作霖治理,奉天在“满洲”的地位上升之后,奉天图书阅览场于1918年更名为奉天简易图书馆。1920年4月,公费运营的奉天简易图书馆归“满铁”私营后,奉天简易图书馆又更名为“满铁奉天图书馆”。作为参考图书馆的“满铁奉天图书馆”,可谓日本“文装的武备”殖民侵略思想的直接产物。
(二)“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文化渗透职能
如前所述,“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继承了原台湾文库的藏书,但二者职能截然不同。如果说台湾文库等早期侨民自发建立的图书馆还曾具有“文明象征”的功能,那么,“官方”设立的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是不折不扣的文化渗透工具。1914年4月13日公布的《“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官制》第一条便明确规定该馆以“广泛收集,妥为保存古今国内外图书”为主要任务,并且明确该馆“受台湾总督管理”,即由台湾“总督”任命馆长,馆长和司书均由台湾“总督府”高官担任。[9]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图书馆历任五位馆长,分别是隈本繁吉、太田为三郎、并河直广、若槻道隆、山中樵。首任馆长隈本繁吉曾任“总督府”督学,于1915年8月6日就任,但其只是挂名的官吏,真正推动馆务的是太田为三郎。第四任馆长若槻道隆为代理馆长,其任期仅为两个月,因此在某些资料中并未提及此人。可以说,“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是在太田为三郎、并河直广、山中樵三位职业图书馆人担任馆长期间得到了继承性的发展。
太田为三郎曾任日本帝国图书馆司书官,受隈本繁吉邀请赴台参与“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草创事业,于1916年就任馆长。在其任上,太田为三郎设立巡回文库,设置儿童图书馆,并开始有系统地蒐集中国南方、南洋群岛文献资料,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规模大抵奠基于太田氏手中”[10]。并河直广于1921年就任馆长,在此之前曾担任日本石川县图书馆馆长达10年。在任期间,除了延续了太田的管理制度,还注重图书的宣传推介,在训练馆员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山中樵于1927年9月接任馆长,赴台前曾长期担任新泻县立图书馆馆长、新泻市社会教育课课长,对开拓日本北海道地区图书馆及社会教育事业功勋卓越。[11]山中樵到任后,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殖民统治,积极筹划建立台湾地区的图书馆网。1927年12月,在台湾筹办的第一届“全岛图书馆协议会”,着实扩大了“总督府”图书馆的影响力,这也为1929年日本图书馆协会在台举办全国图书馆协议会作了铺垫。在这之后,“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的影响力愈发增大。然而,在台湾的日本职业图书馆人将自身定位为“文化工作者”,其图书馆活动是建立在“文化殖民政策”基础上的,在台推动和发展图书馆事业,只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日本当局的殖民统治。“台湾总督府”图书馆从一开始就是不折不扣的文化渗透工具,乃是不争的事实。
三、作为文化侵略利器的在华日本图书馆
如果说早期日本图书馆人在华创办的图书馆还曾具有“文化输出”的功能,对当地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一定影响。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日本图书馆已全然变成日本进行文化侵略的利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相继建成的北京、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便是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背景下建立的。“满铁”各馆组成的“满铁图书馆业务联合会”、以“台湾总督府”图书馆为首的“全岛图书馆协议会”等成立后,甚至出现了成立“大东亚图书馆协会联盟”的幻想,试图在东亚范围内搭建以日本为中心的图书馆情报网。这些机构的主动权被日本当局牢牢控制,其发展轨迹自然与日本的对华政策相辅相成。
(一)北京、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的“使命”
“华北事变”后,日本为了配合即将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而在文化事业上做了方向性的调整,日本外务省随之转变以往“对‘支’文化事业”之根本方针,出台了“新规事业”(也称“新计划”),即筹建中日学院附设农事试验场、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北京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以及上海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以此为契机,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相继建立。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于1936年12月5日正式开馆,成立初期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主管,其运营经费从“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助成金”中拨付。1939年以后,该馆转由兴亚院主管,外务省严格限定该馆经费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图书馆的日常经营、北京西城日语讲习所兼新闻杂志阅览处的经营、选购日本近代科学之图书、举办以普及日本科学知识为目的之集会等。日本当局大力支持该馆推广日语教育、举办各种展览会等集会活动,目的是通过宣传日本文化和精神,以增进北平市民的“亲日意识”,巩固其在华北的殖民统治。
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于1937年3月正式开馆。成立伊始,由于人事与管理机制不完善以及战事开始等原因,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的初期运营不甚理想,一度闭馆。1938年6月复馆后,通过调整人事与管理机制、改善馆藏、强化阅读服务等手段,使得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的发展迎来“短暂的春天”[12]。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也于1939年以后转由兴亚院补给经费。日本当局不仅从经济上严格管控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的运营,还加强对该馆的日常管理,规定该馆馆则、运营规程的制定与改废、图书馆出版物的采购发行等事项,除了必须经过外务大臣或上海日本总领事批准审核外,还得随时向外务大臣及上海日本总领事汇报该馆的运营和利用情况。这一方面是为了操控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以全面配合其侵华国策,另一方面是欲通过此类调查,刺探文化情报。
日本当局非常重视在上海的“文化事业”,认为在上海租界的文化工作比中国其他地区具有更重要的“使命”,即通过鼓吹“东洋民族觉醒”,排挤欧美国家在沪之势力及清洗租界内的抗日力量,以实现日本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主宰地位。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对于贯彻加大日本文化宣传,强化对华文化楔入的“使命”不遗余力。在日本当局政治动机的支配下,北京、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无不成为日本侵略、控制我国华北、华东地区的重要机构,沦为日本对华侵略的帮凶。
(二)“中日图书馆提携论”的本质
打着“中日提携”的幌子进行文化侵略,是日本人一贯的伎俩。借助庚子赔款金成立的东方文化图书馆,便打着“对‘支’文化提携”的旗号,大肆收掠中国善本古籍。在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该馆最终成为日方在华的“独占事业”,不但未能给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带来有利影响,更是成为不折不扣的日本倒卖中国古籍的据点。[13]“中日图书馆提携论”是在近代“中日提携”思想泛滥的大背景之下提出的,建立在日本殖民文化扩张和日本近代图书馆事业大发展的共同作用之下。其主要提倡者是在华日本图书馆人。从最初成立的日本图书馆协会的“满洲”支部,到最终夭折的“大东亚图书馆协会联盟”,均是日本意欲在华进行图书馆文化统制的直接证据。
卫藤利夫(2) 卫藤利夫,1883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毕业后,曾留校担任司书。1919年7月,受“满铁”邀请来到中国东北地区,任“满铁”大连图书馆司书。1920年2月,抵达奉天,担任公费运营的奉天简易图书馆主事。1920年4月1日,奉天简易图书馆改归“满铁”私营,卫藤利夫任“满铁”奉天图书馆长,直到1942年1月辞职归国,是近代在华日本图书馆界的主要头目之一。正式提出“中日图书馆事业协作”是于1921年4月在日本召开的第16次全国图书馆大会上。他以促进中日图书馆协作为由,迫切期望成立东亚图书馆协会或日本图书馆协会“满洲”支部。卫藤利夫就“如何在图书馆事业上实现中日合作”提出了具体方案,即远景目标是寻找一个适当地点,营建一座汇集东亚文献的大图书馆,并以之为中心,形成一个东亚研究的机构抑或是大学;近景目标是扩大如日本图书馆协会之类组织的范围,将中国容纳进来,成立一个东亚图书馆协会之类的组织,方便日本各地的图书馆馆长及其从业者在中国开展“亲善”活动。卫藤利夫认为,在“满洲”地区从事图书馆行业的日本人,已达百人以上,从地利上而言,与中国方面的接触机会更多些,双方互相协力,可行之事数不胜数,实现这个目标“不一定是难于登天之事”,而第一步便是建立“满洲”据点。[14]卫藤利夫在“满洲”从事图书馆工作长达23年之久,一生致力于“满洲”文化史研究,被日本人誉为“满洲文化之父”。“中日图书馆提携”始终是其执念,他曾表示“很乐于做些工作,以使‘满人’真正地敬爱日本,一直都在为此努力尽绵薄之力。”[15]
在近代中日战争局势下,在华日本图书馆无不成为日本侵华势力的帮凶。卫藤利夫所经营的“满铁奉天图书馆”,从一个馆藏3 000册的简易图书室最终发展成与“满铁”大连图书馆、哈尔滨图书馆齐名的“满铁三馆”之一,在“满蒙”文献收集与整理、汉籍收掠等方面的“成就”斐然。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满铁”各馆逐渐走向联合,并发展壮大,成为日本侵略者扩大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七七事变后,北平、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与“满铁”图书馆遥相呼应,构成在华日本图书馆网。日本图书馆人卸下伪装,在殖民地和占领区大肆进行文献掠夺,开展殖民文化活动的同时,战时环境下畸形发展的日本图书馆管理制度、文化精神被带入中国。太平洋战争后,在华日本图书馆界还阴谋策划“大东亚图书馆协会联盟”[16],但由于日本当局各方势力在“满洲”的权利角逐,卫藤利夫的离职回京,日本战局扭转等因素影响,这一谋划进展迟缓,并最终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而彻底流产。
四、近代在华日本图书馆功能嬗变的动因
侵华战争时期,在华图书馆成为日本对华殖民文化侵略的利器,其进行的文献掠夺、日语教育、文化展览、战地文库等一系列活动,都是赤裸裸地为战争助力。日本在华图书馆的行为正是近代日本文化扩张性的表征。而日本在华图书馆的这一属性特征,与其本土图书馆文化发展不无关系。
(一)近代日本图书馆文化的扩张性
近代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一样面临这个两难的问题,即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力,并使之成为实现近代化的精神动力。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选择了“东西思想文化融合”的路径,而这也成为近代日本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日本文化的“摄取性”属性,决定其文化兼具主体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特征。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近代日本经济发展及国力的提升,其对外扩张的步伐越来越快。在日本的殖民地、占领区等地,日本文化逐步渗透,图书馆文化亦在其中。近代日本主动对外扩张输出图书馆文化的突出表现是其海外殖民地图书馆的建设。
20世纪初在华创办的日本图书馆,其发起人以有志者或民间团体居多,其办馆初衷多是便宜来华日本人及其子女教育,故而藏书建设以日文书刊为主,也极少举办日本文化相关展览会。而随着日本官方的介入及日本殖民势力的增强,日本在“满洲”地区政治、经济能力的提升,以“满铁”图书馆为主的在华日本图书馆开始大肆收掠中国古籍文献,包括“满蒙”文献、中国方志、地图等。另一方面,在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范围不断扩大,中国读者人数大幅上升。而面向中日两国人的文化展览活动、语言培训、图书馆教育活动等也在馆内多次举办。日本政府和军方打着文化扶持的幌子,在中国实施文化渗透与文化侵略。近代日本图书馆文化输出中的扩张性,在其侵华战争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以卫藤利夫为首的在华图书馆人提出并大肆宣扬“中日图书馆提携”“大东亚图书馆联盟”的口号,意在塑造日伪政权“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假象。以伪满洲国为例,其“国立中央图书馆”从策划到成立均是出自日本人之手,“(伪)满洲国国立图书馆”成立后所开办的“资料文献讲习会”“开拓地读书资料讲习会”等图书馆教育活动、伪满洲图书馆协会(3)1939年12月,伪满洲图书馆协会在长春成立,第一任会长荣厚。协会成立后,发行会刊、开办讲习会等图书馆员教育活动相继开展。组织召开的“全国图书馆大会”均受日本人控制。
(二)战时日本图书馆思想畸形发展
近代日本图书馆事业的每一次大的变革均与其国家政策息息相关,而依附于此的近代日本图书馆文化的演进也是变革的产物。1896年,在首任帝国图书馆馆长田中稻城等人向帝国议会提交的《帝国图书馆成立方案》中,将东京图书馆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所发挥的参考咨询作用作为东京图书馆的主要功能之一加以详细说明,以达到其扩建东京图书馆为帝国图书馆的目的。文中指出,在甲午战争期间,到东京图书馆查阅地理、财政、政治、战事等相关参考资料的个人和机构大有人在,记载朝鲜、中国情况,尤其是一些与战争结局相关的藏书,为国务提供了重要参考。文中还强调“倘若当时该馆不具备这些,定会造成诸多不便,后果不堪设想。”[17]文中标榜东京图书馆的战争助力作用,暗含东京图书馆扩建为帝国图书馆,将能够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为战争服务也是帝国图书馆的“使命”之一。帝国图书馆第二任馆长松本喜一(4)松本喜一(1881年8月12日—1945年11月13日),初为文部省官僚,1921年被派遣进入帝国图书馆就职,继田中稻城后成为帝国图书馆第二任馆长。则将这一“为战争服务”的使命诠释的淋漓尽致。松本喜一担任帝国图书馆馆长长达20余年,入职之初,因其非专业背景担任馆长职务,日本图书馆界颇为不满,虽然后来松本曾留洋学习图书馆学,但终其一生都是“与文部省关系紧密”的官僚教育者的人设,用日本图书馆史学者石山洋的话来说是个“对图书馆一无所知的人”[18],与首任馆长田中稻城的图书馆学家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然而,松本喜一任职期间不断打压异己,最终达到日本图书馆界权力的巅峰。
松本喜一是狂热的战争鼓吹者,在其领导下,不论是日本图书馆事业还是图书馆教育的发展轨道都有所偏离。松本喜一于1923年1月接管图书馆员教习所(1925年更名为文部省图书馆讲习所)。作为文部省图书馆讲习会的当权者,松本喜一在进行演讲时频频发表鼓吹战争的言论。他曾说道:“近代战争并非单纯的武力战,也是经济战、文化战、体现国力的总体战,因此在振兴国民精神乃至涵养国力方面,扩充图书馆等文化机构便迫在眉睫了,……图书馆人在‘圣战’中的重要任务是收集和活用文化财产。”[19]
随着文部省图书馆讲习所的壮大,历届毕业生成为日本国内和海外图书馆的主力。据“芸草会会员名录”记载,截至1931年图书馆讲习所成立10周年之际,“满铁图书馆”已派出10余名馆员赴文部省图书馆讲习所进修,1931年后,“满铁”图书馆仍以每年二至三名的惯例派遣进修学员。而这些人也正是松本喜一所说的“图书馆人的重要任务”的实践者,他们大肆收掠“满蒙”文献、中国方志、地图等图书资料,进行文化调查刺探战争情报,成为侵华势力的马前卒。总体战体制下的日本战时政策迫使其近代图书馆学术研究中断,图书馆职能突变,图书馆精神文化扭曲,在华日本图书馆在其“国策方略”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学术传播活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总而言之,近代日本人在华创办的图书馆经历了从“文明象征”到“文化输出工具”再到“文化侵略利器”的社会职能的嬗变。这一嬗变轨迹正是近代日本文化扩张性的表征,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战时日本图书馆事业的畸形发展。日本在华图书馆的发展轨迹也是日本对华文化政策演变的缩影。通过深入挖掘近代在华日本图书馆史,探究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之本质,能更大程度上还原日本侵华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