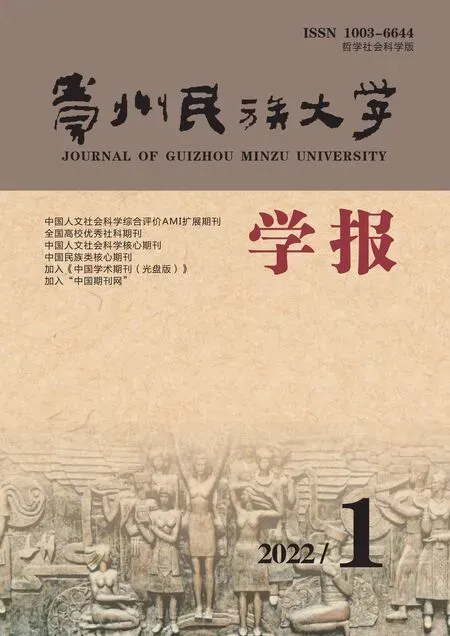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医患信任
朱 清 蓉
一、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对这样的俗语耳熟能详,“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疾病,还有意外事故,不仅伴随着个人短暂的一生,也在人类发展进化的历史中如影随形,并同步走向未来。任何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会和医护角色、医疗活动及医疗体制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医患关系是日常生活中极为重要,也十分敏感的问题。
何为医患关系呢?著名医学史家西格里斯特(Henry E.Sigerist,1891—1957年)曾说,“医学以两种人为先决条件:寻求帮助的病人和施与帮助的医生。医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两种人之间多种多样的关系”。(1)西格里斯特:《西医文化史:人与医学》,朱晓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这个近一世纪前的定义显然对于当今社会来讲较为粗疏。席焕久主编的《生物医学人类学》中对医患关系有如下定义:(2)席焕久主编:《生物医学人类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68—469页。
医患关系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与另一个个体或群体,在诊疗或缓解患者疾病中所建立的各种关系,这其中包含了广义的和狭义的医患关系两层含义。所谓广义的医患关系是以医生为主的群体与以患者为主的群体在诊疗或缓解患者疾病中所建立的关系。这里的“医”不仅指医生,还包括护士、医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等医疗群体;“患”也不仅指患者,还包括与患者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亲属、监护人,甚至患者所在的工作部门和单位等,此时患者的有关人群便成为其利益的代表者。
狭义的医患关系就是指一对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这是目前较为主流的看法,许多论著和文章都如此定义,并常常将之归为医疗伦理的范畴。“医患关系”本来是个中性词语,但在新闻报道中被提及时往往暗含着双方存在一定的矛盾对立。为什么应该并肩作战、通力合作的双方有时会站在对立面呢?对此,有相当多的文章和著作讨论了我国医患失和的成因和对策,宏观层面,认为其与社会结构变迁、医疗体制和医院管理市场化、现代医学模式等有关,(3)宋华、宋兰堂、黄涛等:《对医患关系现状的多维思考》,《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3年第9期;曹永福、王云岭:《论当前我国医疗市场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医学与哲学》2005年第2期;宋田:《社会转型背景下医患关系的变迁》,《现代管理》2010年第5期。微观层面则主要源于对医疗结果、医疗技术、服务态度、医疗费用、医疗时间和其他医疗过程中发生的某些负面情形等情况的不满。(4)张文娟、郝艳华、吴群红等:《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对策》,《医学与社会》2014年第4期;朱力、袁迎春:《现阶段我国医患矛盾的类型、特征与对策》,《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6期。
如何改善和提升医患关系,这其实既是一个历史性问题,也是世界范围内广受关注的话题。在这个话题上,“国内与国外的研究不论是在侧重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存在很大差别。我国国内研究基本都是从宏观层面对影响医患关系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原因进行分析,而在一些针对医患沟通或医患双方的研究中,也基本上都将分析局限于中观层面的概括。与之相比,国外的研究针对性很强,更加细致,大多针对某一问题从微观层面探讨医患关系,并且医患关系主要体现为较单纯的业缘关系,因而关于医患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和生命伦理学的范围之内,学者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医疗过程中医患关系的行为特征以及医患关系的发展历程”。(5)殷东风、王立波:《社会转型期医患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西方医患关系研究中较为知名的有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病人角色理论(6)威廉·考克汉姆:《医学社会学》,高永平、杨渤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114页。,萨斯和荷伦德(Thomas S.Szasz and Marc H.Hollender)的医患关系三种模式:主动—被动模式,指导—合作模式以及相互参与的模式,(7)Szasz,Thomas S.and Marc H.Hollender,“A Contribu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The Basic Models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A.M.A.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vol.97,no.5,1956.伊曼纽尔夫妇(Ezekiel J.Emanuel and Linda Emanuel)提出的家长式、信息式、解释式和商议式。(8)Emanuel EJ,Emanuel LL,“Four Models of the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JAMA,Apr 16,1992.马克·西格勒(Mark Siegler)提出医患共同参与的决策方法,乔治·恩格尔(George Libman Engel)提出的“生物—心理—医学”模式。(9)Engel GL,“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Science,New Series,Vol.196,No.4286,1977.在此领域享有声誉的还有埃德蒙·佩莱格里诺(Edmund D.Pellegrino)和大卫·托马斯玛(David C.Thomasma)等。不计其数的狭义医患关系发生过程的叠加和相互影响铸造了广义医患关系的时代底色,广义医患关系又会影响到医患相遇的过程,狭义医患关系和广义医患关系并不存在很清晰的界限。本文主要着眼于广义的医患关系,在结合狭义医患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意图为医患关系在当前的现状提出一些解释。
有研究指出,医院医务人员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相比,更感到不被患者尊重与信任、不被满意、自评社会地位的满意度更低。(10)王帅、张耀光、徐玲:《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之三——医务人员执业环境现状》,《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14年第4期。有学者注意到,“医疗暴力通常发生于医院,较集中于门诊、急诊以及急重症病房”。(11)徐昕、卢荣荣:《暴力与不信任——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2000~2006》,《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也有研究观察到,“有医生认为与自己的老病友关系更融洽,或者认为住院患者比门诊患者更好沟通”。(12)谢铮、邱泽奇、张拓红:《患者因素如何影响医方对医患关系的看法》,《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09年第2期。再结合新闻报道,就反衬出一种有些模糊的现状:与西医相对而言,中医的医患关系较为平和;(13)刘俊荣主编:《医患关系调查报告(第一辑)》,北京:华龄出版社,2018年,第40页;王梅红、裘梧、程旺主编:《中医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北京中医和谐医患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年,第8页。与城市相比,乡村的医患关系更为和谐。这种带着旧日浪漫色彩的印象多少有几分来自生活经验的道理,那么跳出医学领域的研究框架和视野,梳理中外医患关系发展史,并着重考察近代以来中国医患关系的正面案例,应该能为探究当前城市的医患关系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中外医患关系的历史面貌
纵观历史,医患关系可以大致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阶段,何时跨入现代,根据国情和地域有所不同。根据罗伊·波特(Roy Porter)的观点,西方“医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大约从1850年开始。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前,医学治病救人的作用还显得很微弱,几乎没有人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14)罗伊·波特主编:《剑桥插图医学史》,张大庆主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68页。19世纪40年代,治疗怀疑论开始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医学中心,进而影响到美国。到19世纪90年代,这种对冒险治疗的怀疑已蓄积了足够的力量,推翻的不仅仅是放血和通便疗法,而且是整个的传统药典。正是在这样一个逻辑困境中,视病人为人的运动产生了。这是自19世纪80年代到二战期间贯穿初级保健阶段的一个宗旨。“过时的全科医师”,作为一种愿意坐下来聆听病人诉说病史、耐心建议病人如何处理自己问题的人物形象再度赢得声誉。但作者在此强调,这并不是指老式医生必然比他的前人或后人更细腻敏感或更富有人情味,这仅仅是指他在治疗方面已感绝望,并认识到他除了给予病人那通过咨询获得的心理支持外别无办法。这也引起了兴趣在于整体治疗而不是在病理结构的医生的重视和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5)罗伊·波特主编:《剑桥插图医学史》,张大庆主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87—90,96页。也就是说,此时重视病人的感受主要是因为受限于技术瓶颈,但这种关心赢得了病人的认可,“再度”一词也表明这个时期良好的医患关系在历史长河中并非绝响。
席文(Nathan Sivin)指出,治愈疾病有三种情况,他称之为身体的自响应,也就是自我恢复;技术响应,就是利用物理和化学治疗来影响人体过程并战胜疾病;身体对仪式和其他意义象征的响应,有些人类学家将此称为意义响应。所有这三种响应都可能同时发生。(16)席文:《科学史方法论讲演录》,任安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32页。当前的状况是社会生活医学化,对身体的自响应接受度因人而异,意义响应较为边缘和衰微,技术响应一家独大。随着病理解剖学、麻醉术、无菌术、各类医学器械和药物的渐次发展,过去的床边医学逐渐变成医院医学,并进一步向实验室医学转变。专家化渐渐成为主流,家庭医生或者全科医生渐渐边缘化。(17)英国的家庭医生在初级保健中仍占重要比例,美国的全科医师在1900年前后就开始流失。罗伊·波特主编:《剑桥插图医学史》,张大庆主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92—93页。结果病人的话语权下降,医学知识的生产被医学研究群体所垄断。(18)N.D.Jewson,“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ick-man from Medical Cosmology,1770—1870”,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Vol.38.No.3,2009.医生对疾病的重视超过了对病人本身,疾病被分门别类,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标准化诊疗方法。疾病逐渐成为社会实体,这来源于三个关键因素:一是诊断能力的提升和治疗方法的变革;二是医院作为研究、教育和治疗的场所,其主导性不断增加;三是官僚结构和实践,及其对数字和分类的使用。(19)查尔斯·罗森伯格:《当代医学的困境》之“绪论:目前困境之溯源”,张大庆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年,第22—25页。
二战后生化和药理研究使人类有能力战胜诸多疾病、减轻痛苦,由此进入了波特所说的后现代医学阶段。1950年后,视病人为人的运动陷入停滞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对治疗效果充满了自负、用影像学和实验测试来代替病史记录和触诊的新一代医生,他们并不重视满足病人的心理需求,导致了医患关系的长久对立。也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现实:在西方,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健康、长寿,医学的成就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而社会大众对医学的失望和怀疑也前所未有,部分是由于技术至上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医学高消费。(20)罗伊·波特主编:《剑桥插图医学史》之“导言”,张大庆主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除了这些技术因素外,社会组织方式也在转变。西格里斯特认为,“医患关系上的根本变化要到19世纪下半叶通过社会保险才会发生”。(21)西格里斯特:《西医文化史:人与医学》,朱晓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此后,医生的数量显著增加,就医人数和频率也随之增长。政府也加入到了医生和病人之间,成为三者中最有权力的一方,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变成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力量。
对于百年来的变化,波特感慨,“过去那些总是殷勤地倾听病人述说、富有同情心的老医生,在反对卫生保健体系非人性化方面的激烈争论中已成为囗囗画像”。(22)罗伊·波特主编:《剑桥插图医学史》,张大庆主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96页。而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也从未停止过对主流生物医学模式的批判,和对理想医患关系的追求。例如以南丁格尔为代表的现代护理,既关注医院的硬件设施,也关注病人的心理状况,对护理细节的无比重视体现了对病患全身心的关心爱护。(23)南丁格尔:《护理札记》,庞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著名的精神研究和治疗中心——位于英国伦敦的泰史塔克(Tavistock)诊所在精神治疗师米歇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的带领下,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坚持组织全科医生进行关于医患关系的小组讨论,研究作为“药物”的医生的药理学,改变医生作为“修表匠”的形象以及医生角色中的父权主义。(24)巴林特主编:《医生、他的患者及所患疾病》之“重印介绍”,魏镜主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第6页。凯博文1976年提出的“解释模式”(explanatory model)这一医学人类学概念,强调要重视患者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化情境对所患疾病的叙述。(25)A Kleinman.“Concepts and a Model for the Comparison of Medical Systems as Cultural Systems”.Social Science & Medicine,Vol.12,1978.他在《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一书中区分了疾痛(illness)和疾病(disease)(26)克莱曼:《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方筱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2页。,提示不要将患病局限于生物医学的解释框架。
瑞塔·卡伦(RitaCharon)提出了“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将之定义为运用叙事理解能力促进医学实践的医学,但不局限于书写,也使用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和音乐。因为“患者和医疗照护者是以整体进入病痛和治疗过程的——他们的身体、生活、家庭、价值观、经历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全部进入这个过程。恢复健康、帮助他人好转的努力不能从生活的最深处剥离。”(27)卡伦:《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之“原版前言”,郭莉萍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5年,第16页。也就是说“叙事医学”类似于大众常说的重视“沟通”,但比一过性的沟通、仅限于医患之间的沟通更为全面深入,是在所有医疗场景下活生生的人之间的心灵碰撞,以此来弥合现有医疗常规的缺憾。
中国当下的医患关系与西方有同有异,不仅共同面临了传统与现代的变迁,还有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具有自身特色。席文教授指出,“中医历史中最具当代意义的一环,便是传统中医的医病关系:医生来到病人家中探访,因而有机会了解病人的居家环境与社会关系,倾听并了解病人对自感症状的描述,也较有时间和病人交换对病情的意见,并提供心理的支持”。(28)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465页。这类似于波特推崇的老医生形象,他们在医学欠发达的时期并不稀缺,以儒家思想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重视品德修养。医生的社会角色并不具有独立性,儒生转为医生、久病成医的例子数不胜数。
虽然历史上关于中医名家高超医技与医德的故事屡见不鲜,令人感佩,但这并非医患关系的全貌,类似战国名医文挚、西汉淳于意、三国时期的华佗等医者被王室或权臣所害的例子从不鲜见。而传统社会中医疗水平普遍不够高明,且从医缺乏权威考核标准,庸医、巫医向来大行其道,因此可以确定百姓生活中医疗资源匮乏是常态,医患并不天然和谐。清朝乾隆年间的江南名医徐大椿著有《医学源流论》一书,《医家论》和《名医不可为论》等篇对当时医家的种种乱象提出了批评,吐露了医生难当的心声。《病家论》开篇即言明,天下之病,误于医家者固多,误于病家者尤多,历数了病家常见的十项过失,并提出了择医的方法。(29)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78—79,81—82页。因此,病人择病而医、频繁更换医生、医生之间互相诋毁,医生对病家采取自保态度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常态,病家握有主动选择权,医生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30)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466—476页;李明:《明清医案中的医患互动考查》,《医学与哲学》2020年第23期。所以说,“古代社会的医患关系同样是一种复杂和多层次的人际关系,医患模式不能一概而论”。(31)胡妮娜、程伟、车离:《中国古代医患关系模式初探》,《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年第3期。
总而言之,医患关系并不能简化为一句“今不如古”,它不是一条下行线,而是较为曲折复杂,既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也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研究医疗史的学者认为医患关系的发展并不是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前进,这一点在中国医疗——病患体系中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有研究者认为,“医患关系在人类医疗文化发展史中的变动轨迹当为‘被动—主动—被动—互动’型模式,而这一发展模式的终端就是今天医患关系改革者们的目标”。(32)刘祺:《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1840—1911)——医术、文化与制度的变迁》,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96—97页。
三、良好医患关系的中国案例
清朝末年西医逐渐进入中国,引入了医院、诊所这种公共空间来取代中国传统以家庭为主的封闭私人诊疗模式,例如在杭州建设广济医院的梅藤更(David Duncan Main)、1905年在长沙创建雅礼医馆的胡美(Edward H.Hume)等。虽然语言、肤色、诊疗方式等差异使得西医在开业之初不那么容易,但他们与中国百姓长期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消除了彼此在文化上的陌生感。百姓的淳朴善良隐忍使双方建立起了信任和感情,也使大多数从事医疗活动的异乡人“认为中国民众是世界上最好和最通情达理的病人”。(33)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囗囗囗医疗囗囗囗与地方社会(1835—1911)》,《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
现如今提到西医体制主导的医患关系,常给人一种较为紧张的印象,似乎天然如此。但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医学组织也可以制度化地传递人性的温暖,例如老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社会服务部于1921年成立,由出生于中国山东的美国人浦爱德女士担任主任。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麻省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社会服务部学习,个案工作特别出色。
张中堂《社会服务部二十年》一文对社会服务部的工作情况有详实记录。社会服务部在医院门诊服务台、分科处及住院处都设有社工人员,有职工社会服务部、怀幼会、调养院、救济部等几个附属机构。每个医疗科室都有一两位社工人员,1939年最多达到约30位。病人求诊有困难时,由社工人员接手,通过访谈填写“病人社会历史记录表”以供医生参考:
“病人社会历史记录表”有如下项目:门诊号、住院号、姓名、性别、婚否(单身,已婚)、原籍(省)、日期、北京住址、老家(县、村镇)、职业、家庭成员(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亲戚(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朋友(姓名、年龄、职业、住址)、住房、经济情况、履历、现在情况、问题、社工人员处理意见、采取行动(措施)等。这个表格全是用英文写的,填写病人的社会历史也要用英文。写完后交病案室装在该患者的病历后面,如需继续填写就向病案室打借条取出。主任及各科教授可以随时参阅。(34)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话说老协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60—373,374—380页。
社会服务部的工作内容甚至包括收容弃婴、安排婴儿寄托、救济伤兵难民、帮助病人谋生等。同书收录有吴桢所作的《我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一文,也指出“‘社会治疗’是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的社会学系都被撤销,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也随之取消。目前,协和医院仍然很重视这一遗产,并建立了“浦爱德”门诊志愿服务部,各楼层以及自助服务区均有工作人员耐心地答疑解惑。
哈佛大学著名医史学家查尔斯·罗森伯格(Charles E.Rosenberg)说,“现实的医学是一种过度自信和缺乏反省的技术医学,通常与之相比较的是:医学应该对情感需求、生物个体、特定的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等作出回应。”(35)查尔斯·罗森伯格:《当代医学的困境》,张大庆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年,第148页。老协和的社会服务部依托雄厚的资源投入无疑达到了这个目标,在技术发达、物质丰裕、国泰平安的当下,昔日温情也在逐步得以重现。
下一个中国医患关系较为和谐的案例是计划经济时代。彼时医疗卫生体系由国家主导、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乡、医药分离、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以低成本尽可能覆盖到广大城乡居民最基本的医疗需求。其中,具有在地化优势的赤脚医生制度在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医疗保障工作方面享有盛誉。据曾做过赤脚医生的刘运国博士回忆:
其实当赤脚医生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以为技术水平低,就会出什么大乱子。那会儿没有什么医患矛盾或者纠纷,也没有什么危险。为什么呢?当赤脚医生的好处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哪个病人以前有什么病史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他们来看病,只是以前毛病的复发或引发,我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看了。不像现在医生和病人是陌生人,病人又没有仔细交代病史,医生也没有多少时间和兴趣问,结果出现误诊。而我们那会大家都特别熟了,一看能治的就治,治不了的赶紧送公社和区里,社员不会认为你水平低的。
另外,赤脚医生本人就是社区的一分子,都是这个地方共同生活网络中的一个点,他不可能对病人不负责,不尽心。我当赤脚医生时,社员特别尊重我,在我们小地方特别有社会地位,如同民办教师、大队干部一样。……(36)吕兆丰、线福华、王晓燕主编:《碧流琼沙——赤脚医生时期口述史》,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第152—153页。
有学者在探讨患方因素造成现代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时总结出如下几点: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期望值过高、患者医疗花费负担过重、患者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患者的“病人角色”对医疗服务水平提出更高要求。(37)吕兆丰、王晓燕、张建主编:《医患关系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全国十城市医患关系调查研究报告》,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48—53页。而这几点在过去的乡村恰恰都不存在,如刘运国所言,不会出现医术和品德方面不符合期待的情况,当时也没有因病返贫的可能,更不会有以消费者心态进行百般挑剔的情形。《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38)张开宁、温益群、梁苹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碧流琼沙——赤脚医生时期口述史》等著作记录了许多活跃在乡村的医生们无私奉献、被乡亲们敬佩的例子,杨念群认为是“相对较为优厚的报酬、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网络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医成长的图景”。(39)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26页。
值得注意的是,集体经济体制结束之后,社会转型带来的医患关系失和更明显地发生在城市。不管是赤脚医生时期,还是一度国家退出后、需要自负盈亏,而新医改尚未来临的乡村医生时期,经济更为落后、医疗卫生资源非常匮乏的农村地区,反而一直保留着医患之间的脉脉温情。
笔者的父亲1963年生于鄂西山村,高中学历,通过拜师和卫生学校培训之后获得行医资格,一开始在家开业,务农和行医并重。后来由于“一村一室”、家室分离的规定,以及照顾外公的需求,上世纪90年代回到他当学徒的地方,也就是外公居住的天桥村行医数年。直到1999年夏,外公不堪多年病痛折磨、割腕自杀后,父亲才搬回家。经过几年不合规的动荡期——曾被没收药品和罚款,最终成为邻村卫生室的负责人至今。在那个本镇最穷的山村,他的足迹踏遍村子的各个角落,直到现在无论去哪里都随身携带银针和手电。认真尽责使父亲收获了极好的口碑和尊敬,搬回家后由于当地没有医生常驻,有的乡亲便跋山涉水来家里住下治病。有时长达十天半月,食宿不另外收费,当然他们一般会顺带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每年秋季柑橘收获时,天桥村会有多位乡亲和亲戚自发相约来帮忙采摘,不要报酬。本身不是亲戚的乡亲也由于诊疗关系而成为彼此在红白事上进行礼物交换的圈内成员,建立更日常、更长久的情谊。(40)朱清蓉:《乡村医生·父亲——乡村医患关系的变迁(1985—2010)》,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四、医患关系的压舱石:持续交往产生的信任和温情
当然,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医患关系也并不是桃花源式的。除了医疗水平不足以满足需求之外,还大量存在欠缴医药费,部分村民对医生的医德医术评价欠佳等问题。另外,打工经济兴起后对医生的尊敬也不如从前。要达到彼此亲厚的状态,不仅依赖医生本人辛勤付出积累的道德资本,也少不了医生家庭甚至家族成员的支持和帮扶,医和患从来都不会呈现为单独的个体。患者在乡土生活空间中没有病人的标签角色,土生土长的医生也只是村落生活中提供服务的一分子,医生和病人没有角色鲜明的分化。由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彼此知根知底,治疗之前已有感情基础。也就是说,“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不仅表现为病人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支配的自主性,还表现为更加看重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程度,即整个诊疗过程是否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4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14页。
但“低头不见抬头见”并不足以产生全然的信任,雷祥麟的文章中提及古代刚开业的医生往往要度过一段艰难时期,甚至有的会自费雇佣轿夫来营造出自己受欢迎的境况以吸引病患。(42)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李建民主编:《生命与医疗》,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467页。因此,在彼此熟悉的基础上,能够满足治疗需求同样重要。例如,笔者父亲虽然行医多年,但身为体制内退休工人的祖父从不把他当作最信赖的求医对象,稍有较严重症状便求助于市区大医院,生命最后一两年里长期住院至病逝。祖父的解释是自己“不信他的手”,意思是虽然父亲的医术对很多人有效,但恰恰不适合自己这个个体。而被市里最好的医院几次下达病危通知书的曾外祖母,——她因为儿子非常有出息,能享受本地最好的医疗条件,出院后却完全是在父亲的照管下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信不信谁的手”,这是本地村民在和至少一位村医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一种身体感受和微妙的经验,常是他们择医或者始终如一的理由,内中真意不足为外人道,甚至同一家庭中的老人和孩子也许会有不同的选择。这种来自彼此熟悉又不止于熟悉的信任,内涵是含混而丰富的。
郑也夫认为:“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43)郑也夫:《信任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4页。“信任与熟悉,如前所述,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信任产生于熟悉,在熟悉的基础上人们建立起‘人格信任’。其次,随着社会生活从熟悉走向陌生,人类逐渐建立起‘系统信任’——货币和专家系统。从此,两种信任共存共荣,相辅相成,支撑着社会生活的展开。”(44)郑也夫:《信任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32页。“系统信任”与“制度信任”含义相似,常混用——作者注。上文中乡村医患关系与人格信任密切相关,双方在共享相似道德观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机缘建立起私人联系,医生对不同的病人、病人对不同的医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评价,深受差序格局的影响。因此,乡村医患关系不可能一视同仁,而天然具有个性化特征。当然这也建立在符合常规诊疗期待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对技术能力有一定要求。但也需要注意,这种医患互相信任而彼此制约的状态并不意味一定有益于村民们的健康。有学者发现庇护角色互为根基的医患关系应被视为农村抗生素不合理使用问题的主要成因之一。(45)景军、黄鹏程:《医患关系对农村抗生素滥用的作用:以五个乡村诊所为例》,《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现代社会生活日趋复杂、人口迁移和流动前所未有,是因为广泛存在涂尔干所说的社会分工,由此产生的有机团结代替了以前个体之间因为相似而产生的机械团结。(46)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33—134页。契约和成文法取代了通行于小范围的伦理道德成为社会交往的规则或者说共识,系统信任势必会越来越重要。信任存在的意义就是卢曼所说的,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简化机制。(47)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医院的存在本身就代表着内含系统信任,以简化陌生人社会中的求医需求。因为现代生活中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和流程越来越复杂,使得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等的情况越来越突出。医生上门变为病人前往医院,求医活动出现了从个体行为到群体行为的转变。以疾病分类、实则差异极大的患者群体面对的是受过标准化训练,但也极为细分的医护群体,彼此都清楚己方的多样性,而无力把握对方的多样性,但他们要在规定的有限空间和时间内建立较为单面的医患关系。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将要面对的其实都是一群共性有限的陌生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被实体化了的疾病,如何迅速建立个体化的信任就是一个困难而十分必要的环节。考克汉姆的《医学社会学》提到网络求医的例子,“在线用户显示出较少的对医生的信任”。(48)威廉·考克汉姆:《医学社会学》,高永平、杨渤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这种医患不直接相见以及程序化、流水线似的短暂相见都不令人满意,所以说陌生人社会的医患关系在人格信任方面天然具有劣势。并且国内的调查表明,医方认为医患关系不好的比例要超过政府方、社会方和患方,这种差异表明以往评价医患关系时更偏向患方,“而较少考虑医方的权益”。(49)吕兆丰、王晓燕、张建主编:《医患关系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全国十城市医患关系调查研究报告》,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18页。医方对患方同样缺乏信任。
而制度信任在现实情况中更是经常处在一个让医生和病人往往都不满意不信任的尴尬境地,负面影响不可小视、原因极为复杂。(50)徐昕、卢荣荣:《暴力与不信任——转型中国的医疗暴力研究:2000~2006》,《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这个层面也是许多医院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探讨医患关系时的主要着力点,此处不再赘述。
一项在湖北中部D镇进行的转型期乡村医患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人际信任在日常生活中最被看重,但“在农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农民对医疗专业化预期提高、医疗服务更加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背景下,未来村民对于村医的信任逻辑将是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的叠加”。镇卫生院就是因为制度信任方面不处于优势,又相对村医而言人际信任也不占优势,因此在当地村民的口碑中评价不是最高。(51)房莉杰、梁小云、金承刚:《乡村社会转型时期的医患信任——以我国中部地区两村为例》,《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2期。一项基于河南某市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一级医院患者样本对医护的技术信任低于二、三级医院。但一级医院患者样本对医护的人格信任高于二、三级医院。一级乡镇医院的医患信任主要基于互动的熟悉程度,三级医院的医患信任主要基于医院分级制度产生的资源技术优势,不同级别医院信任度的差异符合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的一般逻辑”。(52)李泽:《转型期中国医患信任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因此可以推断说人格信任能够弥补医疗资源和技术的不足,如果资源技术达标,那么也可以在人际信任相对缺乏的场景下维持较为和谐的医患关系。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以过硬技术为依托的制度信任和以人为本的人际信任的强强联合、互为表里,而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的仍然需要改善的状态与上文中卫生院的处境类似,源于制度信任和人际信任的双重因素。
五、为何信任度不高?
陌生人社会中为何医患之间信任度不高,既有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是医学领域内部演化的结果。医学知识不断细分,一步步将作为整体的人分割得支离破碎,忘了医学的功能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自然无法起到疗愈身心的作用。批判西方生物医学缺乏人文关怀的书籍文章已是汗牛充栋,也一直有人在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而持续努力,此处不再赘言。让我们把着眼点放到大背景上,医患关系暂时不和谐是整个社会转型期社会信任尚未重建完成的一个缩影,与食品安全、家校沟通矛盾等性质类似。赖立里指出,“相当多的医患冲突发生在处于不同阶层的医师与患者之间,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医患纠纷,背后隐含的是由于社会分化与不公所带来的社会信任与稳定问题”。(53)赖立里:《医患关系链社会文化与知识权力》,王岳、丛亚丽主编:《2015—2016中国医患关系蓝皮书》,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7年,第168页。阎云翔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处于道德转型期,医患关系融洽度不够既与过去医疗领域的市场化有关,也是个体化社会中个人道德自我重塑的结果,双方都希望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得到尊重。(54)Yan Y,“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Patient-physician Mis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Dev World Bioeth.Vol.18,No.1,2018.因此,如何重建社会信任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信任与产业结构和大规模组织的创建密切相关,由中国传统上缺乏自发形成并能长存的大型企业来推断得出,中国是一个在陌生人之间低信任度的社会。(55)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郭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80,35页。这种重视家庭价值、对陌生人心怀恐惧的取向使得中国人在现代化、城市化的道路上步履维艰,制度建设也总是滞后于社会的需求。信任尤其是人格信任这种主观感受可以视为福山引用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内容之一,“社会资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56)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唐磊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22,13,22页。社会资本存在信任半径,信任半径指的是“像诚实和互惠这样的合作性社会准则在一定限度的人群范围内共享,并且拒斥与同一社会中该群体以外的其他人的共享”。传统村落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由这种社会资本来调节的,并且信任半径具有一定的实体性,因此能呈现出自治和稳定的特征。而在出现“大断裂”的陌生人社会,尚不存在一致的非正式价值和规范,而是在走向多样化、圈层化。因此都市中个体的信任半径类似于差序格局,具有极大的弹性,面对同一制度无法自然生出同等的信任。
“非正式规范和价值将随时间推移被理性的、正式的法律和规则所取代,这一直被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支柱之一。”福山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非正式规范可以大幅减少经济学家所谓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即对契约进行监督、缔结、调整和强制执行所需的费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社会资本还可以造就高水平的社会创新力和群体适应能力”。体现在诊疗活动中就是,严密精细的契约关系、高技术高效率的流程、肉体得以康复的预期结果等可以被量化的内容仍然不足以满足病人的需求,能够抚慰人心的环境、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不易复制而是发自内心的人和人之间的同情与关爱——它们是产生信任的基础,便是仍然稀缺的社会资本。说到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终究是要建立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链接,它关乎双方的感受。有研究者注意到,“医院的服务水平特别是细节服务上的缺失是医患关系紧张医方原因中不可忽视的原因”。(57)吕兆丰、王晓燕、张建主编:《医患关系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全国十城市医患关系调查研究报告》,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40页。
六、结语
综上所述,良好的医患信任有两个基石: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制度信任最低限度的要求是提供符合期待的医疗技术,技术不要求尖端,而人格信任的丰盈能够对冲技术的不足。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和社会的演化,全球的医患关系都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一个清晰的脉络是对医学的人文关怀孜孜以求,即摆脱重视疾病、轻视病人的割裂取向,尊重病人的整体性和自主性。一大举措是在医学教育体系中为人文素质教育留出一席之地,(58)王恬:《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李清华主编:《医学语言与文化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1—70页。以期在医生的培养阶段着手解决这个医学制度的痼疾。但朱剑峰认为,现阶段医学院的人文教育往往仅限于不被重视的医学伦理,单纯在现有医学院的教育体制下增加人文课程也仅仅是强化了生物—文化的两分法,在学生中没有真正培养出整体论的思路。她认同凯博文倡导在医学院训练中用解释性模式开展民族志工作的做法,以达成医患双方的理解,培养医学生对生物医学和自身文化的反思。(59)朱剑峰、何煦:《文化与文化能力:浅析医学人类学对医学人文教育的贡献》,《复旦教育论坛》2014年第5期。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不能标准化复制,是一个充满挑战、但意义非凡的努力方向。
在完善现有医疗制度的过程中,既需要吸收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也需要重视我们本有的优势。比如,中医具有强调整体观、个体化诊疗和治未病的特点,(60)王梅红、裘梧、程旺主编:《中医和谐医患关系模式研究——北京中医和谐医患关系研究》,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年,第154—155页。非常适合当前社会的需求,这种建基于身体感的技术和整体关怀可以弥补西医战争思维和还原论的不足。
还有一种解决取向是从患方入手,不把改善医患关系当作医生的独角戏。格雷爵士(J.A.Muir Gray)认为,进入21世纪,医学的权力正在经历着由盛到衰的转变,借助于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他认为医学在智慧权威、道德权威、行业权威和魅力权威这四个方面中都在下降。我们的时代已经出现了掌握足够知识和决策能力等资源的“聪明的病人”,也需要培养聪明的病人以实现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和医患共同决策。(61)格雷:《聪明的病人》,秦颖、唐金陵译,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6年,第6—26页。彼得·于贝尔(Peter A.Ubel)的《生命的关键决定:从医生做主到患者赋权》也探讨了如何决策的问题,虽然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医患关系从权威型向患者赋权逐渐转变,但医学实践和生命伦理学往往把重点放在知情同意等程序上,因此他提供了一些实操经验来帮助医患共同决策。(62)彼得·于贝尔:《生命的关键决定:从医生做主到患者赋权》之“序言”,张琼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15页。总而言之,医患双方都需要为了弥合知识鸿沟、建立共情和同理心而付出个人化的努力。
医患关系虽然表面看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医疗体制常常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以都市为代表的陌生人社会中。所以把解决的视角仅仅放在医生和病人身上是不对的,也是不够的。我国已经持续多年的医改就是为了促进个体、社会、国家在医疗卫生资源方面的优化配置,尽力用高质量、高满意度的医疗服务为百姓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与城乡医保并轨、公立医院改革、医药集采等一系列举措不断与时俱进,虽然有经验有教训,但整体向好、未来可期。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既是由于传统中医体系受到了西方生物医学霸权的冲击,也受到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剧烈变迁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在仍然具有低信任度传统的社会中,如何重建医患信任紧迫而重要,任重道远,其中制度建设就是重中之重。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疾病谱和医疗需求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医患关系也需要不断迎接新的挑战,这是人类共同体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可喜的是,中国成功应对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表明,中国制度在推进医患关系和谐方面不仅已经取得实质性进步,而且会在未来显示出独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