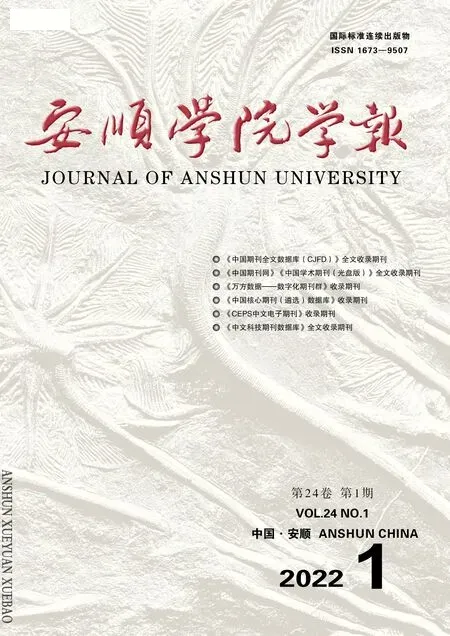盘江流域的卫所屯堡与共生秩序
——以贵阳青岩集市为个案的研究
陈 斌
(安顺学院旅游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地处云贵高原的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的关联,肇始于秦朝。在经历多次改朝换代后,王朝国家在此实施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内涵日趋丰富。尤其是自元朝以降,该地基本纳入王朝国家的政治框架。明朝洪武年间,随朱元璋“调北征南”行动而建立的卫所屯堡制度,不仅进一步将该区域囊括进王朝国家的政治版图中,而且为后续贵州建省之举奠定制度基础。
明清以前,盘江流域之于王朝国家,象征意义重于治理实践。当地自发自主的多民族混融共生和民间自我治理,是其社会秩序的主要内涵。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对盘江流域的诉求发生变化,治理实践跃居象征意义之上。因卫所屯堡制度而迁居于此的中原移民,附着其上的汉文化、以稻作为核心内涵的农耕技术、以平原为基础而建构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逐渐嵌入到盘江流域的社会秩序之中。客观地说,自秦朝以来历代王朝国家在该区域实施的治理制度,可视为中央集权制度的衍生物。其制度体系和中原汉文化对其社会秩序的型塑和维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作用。
鉴于此,“中原中心主义”主导的文献记录和学术研究,一方面,将这种积极作用无限放大,认为历代中央王朝、中原社会及汉族移民合力,是推动盘江流域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型塑的主要或唯一力量。另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此举在该区域的适应性问题。总之,这些历史记录和学术研究,把边疆治理和发展作为王朝国家单向度“同化”“汉化”(Cultural assimilation)的过程,而较少探讨这种治理和发展过程依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很少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去讨论和分析边疆治理和发展过程中当地民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明确历代王朝国家边疆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生态环境,将有助于认识共生何以可能、如何可能等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以贵阳青岩集市为例,回应和讨论上述研究问题。
一、流域构成与自然生境
“盘江有二源,其出乌撒境内者曰北盘江,……其出云南境者曰南盘江。”[1]“北盘江,界滇黔于西南,源自威宁州西界山,入滇沾益、宣威二州界,仍流自黔。东迳普安厅、普安县、安南县、郎岱厅、永宁州,而由三江口东合于红水河。……南盘江,导源沾益州之花山东,经南宁县东,为东小河,又经陆凉州东,为中延泽。又经宜良县东北,为大赤江。又南经路南州西,为巴盘江。又东南经师宗、弥勒二县,环曲靖、云南、澄江三府、广西一州之境,至罗平州入贵州界,经郡城南,谓之红水江,亦曰巴皓河。经册亨,亦曰八渡江,划黔粤之界,会北盘江入粤达于海。”[2]
考现代地图可知,盘江流域是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其交汇而成的红水河诸支流共同构成的水系。均源自乌蒙山系,是珠江上游主源之一。该流域覆盖滇、黔、桂三省(区)五十多个县市,流域面积八万多平方公里。其中,北盘江26,557平方公里[3]914。按当前行政区划,其主体覆盖黔西南州府兴义市及普安、晴隆、安龙、册亨、兴仁、贞丰、望谟等7县市;安顺市的普定、紫云、镇宁、关岭4县;六盘水市全境暨水城、六枝、盘州3区县;毕节市的威宁县。南盘江54,900平方公里[3]910,自兴义市坝达章入贵州境后,主要流经黔西南州安龙、册亨、兴仁、普安以及六盘水市盘州等县市,最后在望谟县蔗香双江口与北盘江汇合。
另外,以贵阳为中心的黔中和黔南部分地区,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地带,尤其是位处贵阳而南的部分县区,其境内的诸多支流,最终皆汇入红水河。《贵阳府志》记载:
贵阳之为郡,北阻乌江,南极红水,岭亘其中。在岭之北者曰贵阳,曰贵筑,而修文、广顺踞其西,开州、龙里、贵定拓其东。西以滴澄为限,而中赅清镇之城;东以瓮城为池。而外连平、清之势,《水经》沅水谷即贵定东南之朵蓬山也,沅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洞庭。瓮城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乌江。乌江者,延江也,水势东北通于荆梁,故其民有荆梁之风。在岭之南者曰定番,而大塘传其东南,长寨、罗斛蔽其西,广顺之地亦大半在南。其水西以为桑郎划界,东以藤茶分山,皆北出而南注于红水。红水即盘江,《史记》、《汉书》所云牂牁将者也。上流蟠屈于滇东,而下控汇群川,经两粤以入南海。[4]
由此可见,位处贵阳以南的花溪、龙里、贵定、惠水、罗甸等县区亦可归入盘江流域。质言之,贵州境内的这些县、区、市,是盘江流域主体区域。
从长时段的时间角度看,该流域所处之地,“在二十亿年前,与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一样,还是一片汪洋,即古地中海。”[5]85地质构造学的研究发现,云贵高原的形成,主要源于后来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大约六千五百万年前(古新世早期),漂移中的印度板块向欧亚大陆冲撞和挤压,由此揭开了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序幕。”。[5]86这种地质构造运动,有上升,亦有下降。上升就导致原为汪洋的部分隆起为陆地。云贵高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但由于是掀斜式上升,即今云南部分上升速度较快,而今贵州部分上升速度相对较慢。从而造成云南部分的海拔均高于贵州,且有显著的高原面。但总体海拔均超过800米,因而统称云贵高原。由于海拔落差大,今贵州部分常受到来自云南高原面上的水流冲蚀,不仅导致贵州地形地貌支离破碎,而且也使得盘江流域在贵州境内支流如人体的毛细管一样,遍布黔中、黔南地区。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在更大的自然空间中,就会发现贵州不仅是云贵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矗立在周边诸多盆地或丘陵之中。东面是两湖(洞庭湖南北)盆地、南面是广西丘陵、西面是昆明盆地,北面为四川盆地。且西面乌蒙山、北部大娄山、东北面武陵山将贵州与云南、四川、湖广等地阻隔开来。这些盆地或丘陵,由于海拔较低,生产条件相对优良,且有较为可观的生计资源,从而导致这四个区域是成熟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发展。而贵州作为这四个地理单元的过渡地带或分割线,正处在斜面上。海拔较高、地表崎岖不平,多喀斯特地貌。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且成熟的地理单元。
二、边关通道与人群层累
明朝以前,包括盘江流域在内的贵州版图,分别隶属四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如黔北遵义地区,隶属四川;黔东铜仁及黔西南一带,隶属湖广;黔西北一带,隶属云南。黔中贵阳、安顺一带未曾隶属周边行省,均由夜郎、罗殿等方国实施自治。由此可见,贵州曾经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与历代王朝国家的接触沟通,均是作为四川、湖广、云南等行省的组成部分而发生,并且扮演这三个行省边关的角色。这种状况一直到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立贵州行省才得到彻底改变,标志着贵州由此成为王朝国家政治体系中独立的政治单元。其与周边行省及王朝国家的关系有了根本性改变,政治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自然地理的阻隔作用。“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必然被纳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体系中,按照吉登斯的观点,伴随着地方上社会关系的‘脱域’(disembeding),国家的渗入对地方而言是一种社会时空的延展,也就是社会关系结构的拓展。”[6]由此,盘江流域的人文生态也就具有更多一层的新内涵。
正因如此,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周边省区,盘江流域均与之保持一定关联。人类对山脉与河流集区隔和交流为一体的结构性特征的熟稔程度,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导致他们能根据山形水势、地形地貌构建适宜通行的道路,即通道。若将历代王朝国家经略盘江流域的意图考虑进来,该区域“通道”的出现、延伸、拓展,将具有更加鲜明的人文意图。因而,这些通道不仅沟通了不同地理单元,“而且因为其超越时空变迁的稳定性”[7]7,一方面,为把握盘江流域与历代王朝国家的关联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为理解当地人群形成图景提供了长时段的历史视角。
以当前的族称来看,布依、苗、汉是居住在该区域的三个主要民族。结合文献史料和田野调查,他们既有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彼此又无法清楚地划分居住边界。
布依族,又称“仲家”,是盘江流域内一个非常重要的居民群体。“仲家的中心区在靠近广西的边境,册亨、望谟。”[8]39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分布区域:一为黔南州罗甸、长顺、惠水、平塘等县;一为自贵阳、安顺至贞丰一带沿线,如安顺市镇宁、关岭、紫云等县。总之,“在地理分布上看,仲家是在贵州的西南部”[8]40,即云贵高原上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
根据罗大林的研究[9],当前居住在盘江流域的布依族,是自公元前214年起,到北宋皇祐年间的一千多年里,由原居广西的越人、俚人、柳州八姓兵和侬人先后四次北上迁徙而来。分别进到王朝国家势力介入相对薄弱的望谟、册亨、安龙、贞丰、罗甸等县,即今贵州西南部。在日常生活中,根据时势和自身需求,借助境内水系支流众多的便利条件,在不同区域间迁徙,以致形成不同聚居区。该区域的苗族,主要居住在苗岭山脉中段。在当地民间叙事中,蚩尤与黄帝、炎帝战败后,苗族先祖从黄河流域往南迁移,进入长江流域,然后再西迁至贵州。这一说法,虽史无确载,但基于山形水势构造而成的自然通道,为其提供了地质构造学上的理论依据。“绍兴—萍乡—北海断裂带不但联系了整个华南地区最主要的水系和平原(洞庭湖盆地、鄱阳湖盆地、金衢盆地),而且西接云贵高原,东入黄淮海平原,承接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南部,无愧于东亚大陆南部人群迁徙‘大动脉’的称号。”[7]19由此,可以明了贵州苗族迁入贵州的大致路径。之后,基于自然地理生成的“通道”对其在贵州境内分布格局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经过长期的内部迁移和发展,形成三大分布区:铜仁和湘西的接壤区域是东部分布区、黔东南是中部分布区、贵阳-安顺一带是西部苗族分布区。中部分布区是贵州苗族的聚居中心区。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先生对贵州苗族聚居中心区有明确界定:“在地图上,把炉山(今凯里市)、台江、雷山、丹寨四个县城作为四点,用铅笔画成一个四方形,这个四方形就是贵州苗族的中心区,里面的山地大部住着苗族。”[8]23这种聚居结构的形成与横贯贵州的苗岭紧密相关。
苗岭本来是长江水系(北部)和珠江水系(南部)的分水岭,这一点类似于秦岭。但苗岭却不能像秦岭那样将南部和北部完全隔离开。因为苗岭除个别地方有较高山峰外,整体海拔均低于秦岭,难以对贵州南北两个部分起完全阻隔作用。海拔较低的山脊线适于人类通行。沿着苗岭应该有一条可用于民间沟通交流的道路,并通过南盘江及其支流与广西相通。
据杨庭硕先生考证:“苗岭山脊上是高山草原区,地面无大阻碍通行较为方便。”[10]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东苗首领干把猪率领族众就是沿着这一山脊去攻劫都匀卫及其周边屯堡的。
盘江流域的汉族居民,可追溯到汉代。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经略西南。“政治上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经济上在西南夷地区设立盐铁官,实行盐铁专营制度,文化上将汉文化大量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西南夷地区。”[11]遗憾的是,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均未曾有大规模的汉人迁入。自明朝洪武年间始,中原汉人大量迁入。
首先,军士及其家属进驻卫所。明朝洪武年间,盘江流域先后建立8个卫所:贵州卫、新添卫、龙里卫、贵州前卫、普定卫、安庄卫、安南卫和普安卫。有研究指出,“在贵州,目前还未发现卫所士卒由土人充当的情况。”[12]质言之,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皆由外地迁来,中原是主要来源地。以明朝卫所的设置标准,每卫5,600人,八卫计44,800余人。加上其家属,总数应接近10万。相关研究发现,卫所军士及其家属主要居住在城中。“贵筑县与贵阳府同城,城内居民主要是明代贵州卫和贵州前卫汉族军户的后裔,……龙里县城内居民也主要是明代龙里卫汉族军户的后裔。”[13]
其次,商屯诱致四川等地汉族农民到此屯田。建立商屯,募商人纳米中盐,是明朝解决卫所军士粮食需求的一种重要手段。洪武十五年(1382年)和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王朝先后在贵州发展商屯,将内地盐商招募到此“开中”,盐商招民屯田耕种,以换取盐引。据统计,“洪武年间,先后在播州及普安、普定、毕节、赤水、层台、乌撒、平越、兴隆、都匀、偏桥、镇远、晴隆、铜鼓、五开等卫‘开中’,招募四川等地的汉族农民到此屯田,仅正德、嘉靖间至黔的移民就不少于数万人。”[14]具体地说,以贵阳为中心,沿西南方向纵深分布,贵阳市花溪区,黔南州龙里、贵定、平塘等县,黔西南州安龙、普安等县,以及安顺市普定县等是盘江流域内主要的汉族聚居区。
总之,当前盘江流域的人群,的确是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不断层累而成的。纵向看。在自秦至清的两千多年里,布依族、苗族和汉族先后因不同原因、借助不同“通道”、从不同方向,规模不一地迁入盘江流域。即使是同一民族,经多次迁徙后,形成当前之状。如布依族,先后四次向盘江流域迁移。或者在进入贵州后,向省内纵深区域多次迁移,从而形成不同聚居区,如苗族。横向看。不同民族的民众在进入后,虽有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但未有明确边界。明清时期,这种特征更加明显。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沟通,随之出现。一方面,导致盘江流域的民族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形成多族(布依族、苗族和汉族)混融之状。另一方面,不仅对明清王朝国家治理和发展该流域提出挑战,且在相当程度上重组、融合和再构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
三、集市塑造共生
青岩,又名青崖(明代文献多书为“青崖”,而清代文献则皆书为“青岩”)明朝以前,此地为仡佬族、苗族和布依族聚居区。布依语称“青岩”为“四只把”,意指“人用四肢从大山里扒出来的地方”[15]。苗语将其表述为“格养”(GeilYangx),意为地处相对靠北的羊场。意味着生活于此的民众,与自然生境、人文生境的关系已发生明显变化。明朝洪武年间,随着贵州前卫的建立,“青岩”之内涵,进一步丰富,指“军队驻扎的地方”或“大兵们住的营房”或“屯兵住的房子”。
青岩东北面是花溪区高坡乡,为“背牌苗”(因其女性服饰上有一块背牌而得名,又名“红簪苗”“印牌苗”“高坡苗”)聚居区;南面为八番土司区,是布依族聚居区,如惠水、长顺、贵定、龙里等地,亦有“海葩苗”(因其女性服饰上缀有海贝而得名,又名“海楩苗”)居于其间;北面的花溪,曾名“花仡佬”,因该地曾为仡佬族居地。就生计资源而言,以南为“长顺-惠水丘陵低山坝子小区”,地势起伏小,农耕历史悠久,土壤熟化程度较高[16]。作物可一年两熟,水资源充分,历来有“贵州粮仓”之称。
就交通条件而言,湖广、四川通往云南的诸多驿道在此交汇。黔桂驿道虽建于元朝,且途经青岩,但因当时贵州在全国政治版图上处于邻近四省的边地,“不同民族以无政区统辖、更无规模化内在关联的地理和文化碎片状态‘锁居’于自己的狭小环境之中”[17]174,导致通行性较差。明朝统治者将贵州视为战略要地后,开始整修驿道,提升通行性,并且,广顺、长寨、惠水为“贵州粮仓”,由此更能凸显其青岩交通要道的现实意义。
青岩不仅是多民族汇聚之地,而且是连通粮食产区(八番土司)与粮食消费区(卫所屯军)的交通要道,更是将广西与贵州关联起来的冲要之地。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贵州前卫建立时,将青岩作为其权力系统拓展延伸的重要节点,在此建立青岩堡。鉴于其便利的交通条件。外来人群源源不断的迁入,并在此定居生活。在今青岩镇辖区诸多姓氏民众的记忆中,其先祖都是从外地迁徙而来。江西籍赵昉即在此时携带千金入黔,购地居于青岩堡附近,以致形成今青岩谷通寨赵氏一族之盛景[18]。无论是汉族或者苗族等,都在商业或农业的名义下,紧紧地嵌入到青岩堡的地方社会中。
青岩堡首任百户王荣“爽朗慷慨,广交朋友,和睦四邻,善待商旅,且对本寨弟兄们之事十分关心”[19]。因而,当地及外地迁来的民众,将青岩堡称为“王荣堡”。其治理方式和过程,彰显出两方面理论内涵。借助自然地形的有利条件,联合周边其他屯堡,共同控扼要道。“青岩堡背靠狮子山,面由青岩河环抱,居高又守险,控制当时贵阳通往惠水、长顺、罗甸、都匀的驿道,一兵屯此,万军难过。”[15]狮子山地势较高,山顶宽广且视野开阔。并且,“狮子山后有杨眉堡,顺河而下三五里有余庆堡,均是屯兵驻扎的地方”[20],二者形成犄角之势,共同守护驿道,使之成为贵州卫、贵州前卫与全国驿道网络相连通的重要节点,又是连通定番(今惠水县)、广顺粮仓的关键之处。在“建卫设堡——商人迁入——各族融入”的螺旋式进程中,随着交往频度的增加,青岩堡的社会变迁过程呈现出集市化的趋势。“青岩场原系屯堡,……因地当柜员通往广顺、定番道上,市集繁荣,故有二场,一场在寅未日,一场在己亥日。”[21]自此开始,青岩堡在承担卫所军事职能的同时,还承担着“郡邑”的民事职能,成为周边区域闻名遐迩的集市。
此后,青岩虽有从青岩堡变成青岩司的经历,也有从青岩土城向青岩石城华丽转身的过程。无论如何,其集市职能始终未变。进入民国后,随着公路修建,青岩集市的规模和吸引力受到明显的影响。但是,无论其市况如何萎缩,青岩作为“贵州粮仓”惠水、长顺与贵阳间商业要道的地位始终未曾变过,并且由于青岩无甚产出,同样吸引周边民众将农特产品运往此处销售。时至今日,青岩仍是盘江流域地方社会中非常典型的集市,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集市。
不管是青岩堡,还是青岩司,其作为明王朝治理盘江流域的重要政治设施和制度安排,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将不同自然区域或不同人群区隔开来。但是囿于不同自然区域的生产条件,或者不同人群的生产技能差异,导致他们之间需要通过“物”的交换才能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总之,青岩作为集市,自其源起的那一天起,在以物品交换为主要形式的基础上,不仅满足了明朝卫所屯军粮食需求,以及不同族属民众日常生活需求,而且也将盘江流域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以及原先被作为政治设施的青岩堡区隔之后的民众关联起来,成为一个和谐共生的整体。
以青岩集市为个案勾勒的盘江流域民众经济生活图景,表面彰显该区域苗族、布依族和汉族等人群在喀斯特地貌中的生计特征,实质表征的是王朝国家在边疆治理和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与理想的制度预设存在一定距离。盘江流域中的村庄,并非可自给自足的生计单位。王朝国家在此实施的土司制度、卫所制度,并非万能,尤其是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强硬武力弹压手段,并非解决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所有诉求的灵丹妙药。集市作为创造、维续盘江流域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土司与卫所屯军以及不同族属人群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在弥补上述缺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随屯军卫所设立而生成的集市,是明王朝在盘江流域实现“早期国家化”目标的重要手段。据统计,“在贵州全省的1939个集镇中,处于交通线和设立过卫所的地区的有714个,占总数的36.82%;其中,位于主驿道上的有434个,占总数的22.38%。”[17]188若将统计时段限定在明清时期,这种结构特征会更加明显。“明朝时期的集镇处于交通线及卫所所在地的有24个,占总数的68.57%,明清两代处于交通线及卫所所在地的集镇有42个,占总数的52.74%。”[17]188它们在推动盘江流域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型塑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满足大量卫所屯军的粮食等生计资源的诉求,即通过集市的交换功能,将产自于土司聚居区的粮食等生计资源,协调分配给卫所屯军。为将集市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在卫所权力系统不断向土司地区纵深延伸过程中,集市也随之拓展到土司长官司驻地。
第二,“改卫设县”“改土归流”后,在延续原有集市的基础上,产生数量不菲的基层集市。这是大量外来商人和地方民众,基于地方物产与民众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此时,集市主要扮演将不同区域、不同族属之间的物产进行协调分配的角色,以满足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需求。尤其当不同区域、不同族属人群的生计资源、生产技能、日常生活等方面存在差异时,集市的协调分配功能得到凸显,且蕴藏在物品交换背后的跨族属的文化互动与社会交往,集体无意识地消弭了原有的文化边界。
结 语
盘江流域的集市,是长时段历史过程中,王朝国家、地方社会基于共同诉求发展出的诸多集市总和,包含区域中心集市、乡镇集市和村集市。不同层级的集市,虽辐射范围不一、覆盖人群不同,但乡镇集市、村集市与交通线或卫所所在地的区域中心集市共同形成集市体系,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在卫所城镇的城市商业的推动下,城乡之间、汉夷之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22]当这种经济往来与文化生态互嵌时,集市的功能性特征更加凸显。既是王朝国家治理边疆的重要载体,更是协调分配生计资源的主要平台。表面看,是生态、文化以及理念方面差异导致“物”的交换。实质上,在这种交换背后,蕴藏着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博弈,更潜隐着不同人群间的社会交往、文化融合和边界重组。在这个意义上,明清时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边疆治理和发展,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中原移民和地方土著,并非是斗争哲学视野下的对立二分,而是彼此融合形成新状态、新样式和新机制的共生过程。昭示出王朝国家体制下,边疆民众社会生活和文化实践中的重组、融合和再构过程,实质是一种以二元或多元为基本内涵的治理与发展过程。它在延续传统的边疆治理与发展理念的前提下,彰显了边疆民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丰富和巩固民族区域自治内涵的同时,更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