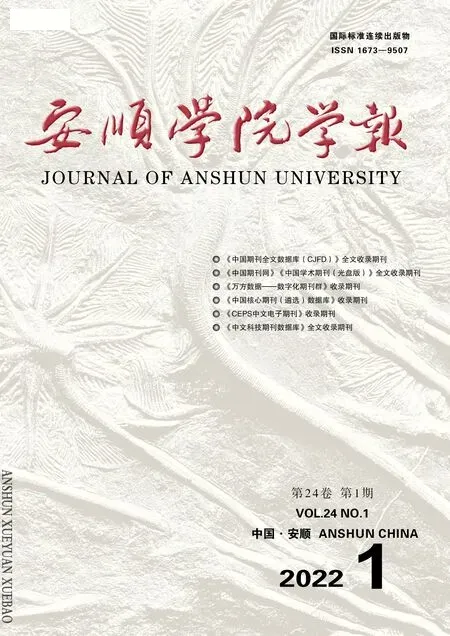明代贵州兵制变迁刍论
孟凡松
(贵州省高校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安顺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安顺 561000)
明代贵州地方兵制的演变大势与其他省区并无根本不同,但由于地理环境、财政处境、族群分布等方面的原因,贵州兵制演变在西南省区仍具有一定代表性。概括而言,明代贵州军事制度约略经历了以卫所军制为主向卫所—募兵相混合的兵制转变过程:中前期,贵州军事制度以卫所军制为主;至中后期,除传统卫所军制以外,编军余入卫所比类正军,拣选招募原住民为兵,原卫所军制逐渐向卫所—营兵相结合的兵制转变,地方文官系统及监察系统介入地方武力建设,募兵制度得到相应发展。
一、土军及军民千户所
明代边省卫所多有土军卫或土军千户所,贵州亦曾有过土军卫所,但其存在形态却与他省有异。明代中前期,西南地方的军事力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代表国家军事力量的卫所旗军和接受征调的土军,还有具有地方民兵性质的巡检弓兵。土军或编入卫所,或未编入卫所,编入卫所的土军具有永久性;未编入卫所的土军大多数时候属于土司能够调集和统帅的武装力量,这种武装力量更多地具有某种临时性,平时为民,接受调遣时方编制为军。
明初贵州境内所设卫所编土军入伍者不多,若洪武十五年(1382年)于播州沙溪筑城,曾以官军一千人,土军两千人戍守之[1]卷141,洪武十五年正月乙酉。又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置思州千户所及思南左、右千户所”[1]卷216,洪武二十五年二月丙子。设置该三千户所的记载又建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正月[2]卷136,永乐十一年正月己酉。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在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流的基础上设置贵州布政司。在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流并设立贵州布政司的背景下设置三个土军千户所,于理难合,应以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设置三所为确。永乐十二年(1414年)年底,“置贵州之思州、思南二守御千户所吏目各一员”[2]卷159,永乐十二年十二月庚辰。再二年之后,时任贵州左布政使蒋廷瓒奏请将思州、思南土军千户所由前军都督府改隶“仍旧”,“专守军律,不得务农”[2]卷175,永乐十四年四月庚午。贵州都司属右军都督府,二土军千户所由前军都督府改隶“仍旧”,则此二千户所此前当属贵州都司。洪熙元年(1425年)八月,此二千户所被废。当时,行在兵部奏陈二所设置本末云:当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思州宣慰使田琛各奏设千户所,由本处夷人充土军,“聚则为军,散则为民”,“其百户、镇抚皆用本土头目”。后来,罢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设八府并置贵州布政司以领之,“土军悉复为民,独思州、思南二千户所官尚存”。二千户所军散而官存,到底是重建还是解散,兵部奏请朝廷定夺,得到裁撤二所而其流官千户仍归“旧卫”的意见[3]卷8,洪熙元年八月甲申。梳理前述记载,洪武间设置的思州、思南等三千户所当属宣慰使田宗鼎、田琛等分别奏设,原系土军千户所,后因废宣慰司改流仅余二千户所,且呈现为军去官存的状态,保持如此状态数年之后终于彻底废除二土军千户所[4]595。
实际上,前述思州、思南二土军千户所并没有绝对意义上被裁革,其千户所千户仍旧调回原属卫所之后,部分土百户之职仍在传袭绵延。例如,镇远府属邛水长官司有土百户王思恭,思南府婺川县随县办事土百户谢鼎新、田惟载,石阡府石阡长官司土百户王如昌,龙泉坪长官司土百户冉文虎,土百户何嗣昆等。据万历《贵州通志》载:
土百户王思恭,系思州宣慰司头目,洪武二十五年功授土百户,永乐十一年革司,洪熙元年三世孙昇袭,送镇远府邛水司土百户,至八世孙廷钺故绝。龙弟廷裕及男朝俱未袭,沿至朝男必选承袭。[5]324
随县办事土百户谢鼎新,本县官籍,前元任本县知县,男复隆以宣慰使田仁智保任主簿,三世孙政弼以田大雅保任思南千户所百户,沿袭至镗。
土百户田惟载,本县官籍,前元授思宁进忠宣慰司宣抚,洪武五年改设思宁长官司,改本司长官,男茂常改授信宁巡检司巡检,三世孙仁弼洪武二十五年宣慰田大雅保授思南千户所千户,洪熙元年革所设县,改授本县土百户职,沿应纪。[5]368
土百户王如昌,本司土官,洪武三十三年授思州千户所百户,洪熙元年革所,男显文改随司办事。[5]385
土百户冉文虎,思州宣慰司头目,洪武二十五年功升千户所百户,沿袭至元。
土百户何嗣昆,任石阡司长官,洪武十五年改千户所百户,永乐十九年五世孙文斌袭前职,拨本司管事,沿袭至安庆。[5]385
前述诸土百户,除龙泉坪长官司土百户何嗣昆“洪武十五年”(1381年)由长官司改任百户、石阡长官司土百户王如昌系洪武三十三年(1400年)授百户、婺川县土百户谢鼎新不载时间外,余皆作“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何嗣昆原任石阡司长官,后改千户所百户,从千户所设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判断,其“洪武十五年”当为“洪武二十五年”缺“二”字而讹。梳理前引有关土百户的记载,大概可以断定:《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思州等三千户所[2]卷136,永乐十一年正月己酉,“设”当作“革”。当时,诸土军千户所实处于军散而官存的状态,又历数年至洪熙元年(1425年)终于官、军俱革。此后,虽然仍有数名土百户,但仅为土百户职衔,并非领有卫所编制体系下的一个百户单位的土军。
此外,明播州境地又有“千户长官”宋氏,“洪武四年,其裔道纯同播州宣慰杨铿纳土,后授千户长官,管辖沙溪等里”。洪武十七年(1384年)七月,敕命“授播州承值千户指挥长官之职”。隆庆三年(1569年),“杨应龙夺宋氏田庄,害宋恩等十七命,宋宗富赴京奏讨贼。万历间五司七姓讦奏应龙,宋亦与焉”[6]84。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月,“城播州沙溪,以官兵一千人,土兵二千人戍之”[1]卷141,洪武十五年正月乙酉。沙溪筑城并以官兵、土兵戍守,为征南背景下的措置,稍后千户长官之设方为制度性措施。
此后,直至明末播州、水西改流之后先后设置威远、镇西、敷勇等卫及属所,贵州才再次较成编制地吸收贵州地方原住民势力编入卫所。例如,敷勇卫指挥佥事袁氏,“先任赤水司长官,平播献土有功题授四川威远卫世袭总旗”,后又因“援辽、恢复遵义等处节次有功”“剿蔺招斩有功”“援黔征西有功”“修筑修文、息烽各处城垣、开垦屯田功”,“捐助续修青岩城垣,督兵挟抚化沙献印有功”,等等,因累次历功升授敷勇卫指挥佥事[7]202。
二、地方军政职官与分防之地
明代中前期贵州地方武力以卫所军制为根本,贵州都司及所属卫所、湖广都司所属“边六卫”为主体军事力量。此后,在都司卫所系统外,逐渐又有参将、守备等职事流官武职分辖地方,与守巡、兵备等文职共参军政,地方军事管理体制也相应地由卫所制度向卫所—营兵相结合的兵制转变。
至嘉靖时期,贵州军政管理已经形成卫所—营兵制度相结合,文武职官并治、省内分守与邻省兼制相配合的局面。总体而言:
贵州都指挥使司辖卫一十八,所二,俱隶右军都督府。自本司军政、掌印、佥书、管屯、管操、督捕外,设参将三员,守备指挥六员,以都指挥体统行事而分辖以各府、卫、州、县、所地方,与守巡、兵备文职并治焉。[8]305
在贵州军政管理领导体制上,明初所形成的原贵州都司卫所系统仍旧保留,而布政司、按察司官员亦开始参与其中。具体来说,贵州布政司右参议一员分守新镇、思仁二道,左参议一员分守贵宁、安平二道。按察司佥事、副使各二员,其佥事一员,建治思南府,分巡思仁道思石兵备;副使一员,建治都匀府,分巡新镇道都清兵备;副使一员,建治普定卫,分巡安平道威清兵备;佥事一员,建治毕节卫,分巡贵宁道毕节兵备。
都司卫所系统以外,又有参将、守备等武官来自卫所世袭武职而以都指挥以上流官职衔任事右参将三员、守备四员:右参将三员,各分守思、石等四府地方,协同镇守贵州兼提督平、清等卫地方,提督四川叙泸坝底及贵州迤西地方;以都指挥体统行事之守备四员,包括守备思石等府地方一员,建治铜仁府,辖思州、思南、石阡、铜仁四府,兼制湖广镇筸并四川平茶、播州等司;守备都清等处一员,建治都匀府,辖镇远、都匀、黎平三府,龙里、新添、平越、清平、兴隆、都匀、黄平等六卫一所,兼制广西南丹等州,湖广偏桥、镇远、平溪、清浪、铜鼓、五开等卫;守备普安六卫、程番府、永宁四州一员,建治普安卫,辖程番府,永宁、镇宁、安顺、普安四州,威清、平坝、普定、安庄、安南、普安等六卫,兼制云南霑益州、广西泗城州等处;守备迤西五卫所,四川乌撒等四府一员,建治乌撒卫,辖贵州宣慰使司,贵州、贵州前、毕节、乌撒、赤水、永宁等六卫与普市一所,兼制四川乌撒、东川、乌蒙、镇雄等府与永宁宣抚司[8]305-306。前述四守备辖区,至万历时期各作思仁守巡道地方、新镇守巡道地方、安平守巡道地方与贵宁守巡道地方。其中,守备稍有增加,如安平守巡道地方增坝阳守备一员,驻平坝卫,专管威清、平坝、普定三卫,安顺一府地方[9]445;新镇守巡道地方,增清镇等处守备一员,驻镇远卫,专管镇远一府,镇远、施秉二县,平越、新添、偏桥、镇远四卫地方[9]452;思仁守巡道地方,增铜仁等处守备一员,驻平头司镇远营,专管铜仁一府一县地方[9]456。贵州地方军事辖区由各“守备”到“守巡道”发生称谓上的变化,四守巡道又共增守备三员,又有原属新镇道的龙里卫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改分属安平守巡道等,但由贵州巡抚统辖的“外则四兵备道”[9]444的分防格局并无本质上的变化。
三、旗军、募兵与各色地方武力
从卫所制度的整体发展态势而言,因卫所旗军逃亡而导致世役制衰颓和招募制兴起的说法大体属实。所谓旗军逃亡,更准确的表述应当为旗军失额,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卫所地方真实居住人口的逃亡,而只是旗军及其家族脱离卫所管理册籍的反映。简言之,明代卫所旗军在册籍上确实表现为严重减少的发展趋势,并因此引起地方文官系统——布政司府州县及监察系统的介入和募兵制度的发展。
明代卫所旗军实数多与标准配置不符。明制卫所的标准编制大概为每卫旗军5600名,每所1120名。在卫所旗军世役和旗军勾补的二重制度保障下,卫所旗军原额便成为影响其规模大小的根本性因素。但是,以明代卫所标准配置比照贵州都司所属各卫所则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差甚远。以嘉靖《贵州通志》所列旗军原额为例,旗军数最高的普安卫达30,093名,其次赤水、安庄、清平、乌撒等四卫分别为10,307名、9976名、9803名、9338名,各在1万名左右,5600名以上且不足6000名的有贵州、安南、平坝、永宁、威清、新添等卫,其余毕节、贵州前、平越、都匀、龙里、兴隆、普定等卫各在6000至9000名之间[8]305-306,18卫共计旗军157,354名,卫均8742名,超出标准编制幅度达56%以上。诸卫所共计旗军159,928名,前述诸卫中,普安卫在城千户所除常规编制左、右、中、前、后五千户所外,又有在城中左、中右和在外安笼、安南、乐民、平夷四守御千户所;赤水卫在城五千户所外又有层台、阿落密、摩尼、白撒等四守御千户所;毕节卫有七星关千户所,安庄卫有关索岭千户所,各卫及所又多有带管站百户,其乌撒、普安、赤水等卫带管二三百户至六七百户不等,即便包括各卫带管百户站所在内,统计在城在外贵州诸卫所每千户所平均旗军数额仍在1450~1550名之间。嘉靖《贵州通志》在各卫所“旗军原额”[8]305-306普遍偏高,是确实如此还是另有原因,仍待追究。
万历《贵州通志》与万历《黔记》记载贵州诸卫所旗军“原额”基本相同,据万历《贵州通志》“合属志”卫所各卷“兵防”统计,贵州都司所属18卫2直隶千户所共125,107名,相较于嘉靖《贵州通志》“原额”合计减少近35,000名,减幅接近22%,但以直隶并卫属在城在外各千户所104所计之,所均旗军约1200名,与一般卫所的编制标准更为相符。其中,除个别卫所相较于嘉靖《贵州通志》相同或略高外,大多数要短少数百名至二三千名不等,其普安卫更是相差12,000名以上。但是,在万历《贵州通志》中,“各卫所原额旗军及铜仁、思、石等府戍守汉土官兵”通计158,707名,与前述嘉靖《贵州通志》各卫所原额旗军统计总数159,928名仅相差1200余名,二志数据前后相差四十余年,军兵总数后者相较前者稍有减少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否说明嘉靖《贵州通志》所载各卫所原额旗军数实际上包括了卫所以外各府州地方戍守的汉土官兵在内?换言之,万历时期两种通志的卫所旗军“原额”仅指卫所而言,而嘉靖《贵州通志》却包括了戍守卫所辖境以外各府州哨、堡地方的“汉土军兵”,这些“汉土军兵”在前期要更多地接受都司卫所系统的调遣和管理。从嘉靖到万历时期,实际上经历有一个地方文官系统更加深入地介入都司卫所军事管理系统的过程。
但是,前述判断并不能支持普安卫“原额旗军”从3万余名减少到不足14,000名这一现象:一来没有证据表明普安州地方在普安卫以外尚有数量庞大的汉土军兵群体;二来普安卫即便所辖旗军数实际上达两个卫以上的规模,但并没有达到超过5个卫而逾3万之数的规模。普安卫的旗军原额,嘉靖《普安州志》载作:“洪武年间原额官军”32,519员名,“见在城食粮旗军”共911名[10]27。嘉靖《贵州通志》载该卫原额官军30,093名[8]306,万历《贵州通志》与万历《黔记》各载该卫原额旗军13,777名,见在913名[5]193[9]448。普安卫为洪武十五年(1382年)初开设的卫所之一,旋又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改普安军民府为军民卫,调毕节卫指挥郑珍领兵戍守[1]卷195,洪武二十二年三月癸巳,郑珍等戍守普安卫应属原设普安卫增添军力,而非普安卫至此新设。但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六月,明廷遣尚宝司丞杨镇阅试贵州、普定、普安、平越、兴隆五卫及旧平夷、黄平、新添三千户所军马,当时共有官371员,士卒29,659名[1]卷202,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庚寅,设若五卫皆属5千户所,五卫三所共28千户所,均计每千户所士卒1059名,未足以证明此时的普安卫已经扩编达约略2个卫的规模。普安卫旗军规模稳定的具体时间,应该为其在城中左、中右二千户所和在外四守御千户所悉数开设之后,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三十一年(1398年)安南、乐民、安笼等守御所先后开设之后[10]27。据嘉靖《普安州志》载,该卫指挥、卫镇抚共18员,千户、所镇抚共39员,百户73员,共计世职130员[10]28,卫属在城左、右、中、前、后、中左、中右等七千户所,在外安笼、安南、乐民、平夷四守御千户所及新兴、亦资孔等百户站[10]26-27。卫属在城、在外共11千户所[11]卷5《职官·普安卫指挥使司》23a—b,估算其旗军数额与万历《贵州通志》与万历《黔记》所载“原额”较为接近。
明中期以降,召募而来的汉土军兵在贵州防御兵力的占比逐渐提高,而实际上仍以卫所旗军为主体。万历《贵州通志》“通计”“各卫所原额旗军及铜仁、思、石等府戍守汉土军兵”158,707名,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查存”得26,840名[5]23-24,失额比例达87%。汇总该志所记载贵州都司各属卫所旗军“查存”之数实为25,080名,相较26,840名短少1760名,此或即该志缺载的永宁卫“查存”旗军之数[5]227。大概而言,万历《贵州通志》“查存”之数实际上仍以各卫所仍在册籍内的旗军为绝对主体,防守卫所及府州各地“营、哨、关、堡”共281处[5]23的各色军兵并未统计在内。
万历《贵州通志》“合属志”记载各处“兵防”除卫所“旗军”之数外,又有各处营哨关堡军兵之数,其“省会志”之“军政”亦云“各卫所原额旗军及铜仁思石等府戍守汉土军兵”[5]23,说明全省武装力量实际上由卫所旗军和“汉土军兵”两部分构成。统计贵州巡抚、总兵下标兵,各府卫州县所等地方守备、坐镇指挥和营、哨、关、堡等分防各处营哨关堡军兵总数共16,999名(从“合属志”各卷“兵防”统计分数汇总,具体分数因太琐碎而从省略)。包括巡抚军门与总兵标下军兵共2000名在内,所有“查存”旗军、汉土军兵中分防各处营哨关堡的兵力占比达63%,其余约37%应主要为卫所治城守御和屯田旗军。从分防各处营哨关堡军兵及其头目名色来看,地方防御武力中既有旗军、军兵,又有土兵、苗兵、夷兵、仲兵、红兵等显然来自地方少数民族的各色民兵、乡兵,又有打手、民壮等召募而来民兵。汉土军兵名色虽繁,大体不外乎两类,其一为与卫所有关的军,其一为召募而来的兵。诸如总旗、小旗、旗军、旗甲、军、军兵、屯军、官军、卫兵、哨军等名色头目与兵力种类,大概率来自卫所旗军或从军舍余丁中召募而来。其他称“兵”诸类,军兵、卫兵以外,哨兵、募兵、防兵、勇兵、总甲、小甲、甲兵等,既可能来自卫所谪发或召募,也可能来自府县召募,应视具体情形而定,而民兵、打手、民壮、乡兵、鸟铳枪刀手等则多属召募民兵而来。民兵之中,又有少部分以耕地确权代替召募之赀的,如永宁州马跑等13哨,“各哨兵不等,俱系顶营、募役、沙营、阿果等处粮民防御”[5]166。贵州宣慰司之巴香,原有官兵坐镇,后“令宣慰司土舍召兵自耕防御”,其鸡场、黄花二哨亦以若干罗兵“耕食防守”[5]98。
尤当注意者为铜仁府兵防,嘉靖、万历间俨然一方重镇。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镇筸铜仁苗变之后,以原铜仁分守参将石邦宪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贵州,兼提督平、清等卫”[12]卷391,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亥,贵州镇守总兵官亦由贵州会城移镇铜仁,该府地方及镇筸一带兵力空前加强。万历十一年(1583年),巡抚都御史刘庠、巡按御史毛在奏题总兵标下募兵1000名,每名月饷9钱[13]卷139,万历十一年七月甲申,原有总兵家丁130名外,选募870名,内200名相兼原调各为官军守城,600名分作2哨,200名分发守备随住平头哨,充为游兵巡逻坝带[5]395。以召募守城总兵标兵、铜仁哨抽调各卫旗军等主要来自卫所的军力1400名为基干,以分守各处营、哨、寨、隘、堡的地方苗兵、土兵、仲兵及其头目共4700名以上为枝辅,其兵少者设头目,其兵多者间以千百户领之,构筑起铜仁府地方的军事防御体系[5]395-396,并与镇筸参将辖区相呼应。分守各处营、哨的原住民士兵多系召募而来,然月饷相对较低。又有个别如万安堡的防守情形,系“将附近洞民并入堡内,且耕且守”[5]396者。
铜仁府兵备大为强化的同时,万历十年(1582年)前后的思州知府蔡懋昭也曾有募勇守城之议,蔡氏概括思州兵制变迁历史云:
查得洪武二十五年,设有思州守御千户所,而千百户以土人为之。至洪熙元年,革去千百户,改为正、副长官,守御遂废。后因残破,又议调平、清、偏、镇四卫官军共一百六十九名赴府防御,至万历元年复又撤去。今虽召募革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给银一钱八分,米三斗,把守关隘,然亦生苗等耳,非久安长治之术也。旧额土兵一百二十名,每名月给粮四钱五分以充守御,然皆柔懦不堪,惟供看门、提铃、更夫、吹手等役,而无衣甲武勇之具,以此因循怠玩,屡遭失事。合无比照各府事规,量募壮勇艺能之兵五六十名,月给工钱九钱,专令习熟鸟铳、快枪、弓弩长技以壮武备。[5]475-476
思州府兵制经历土军千户所、卫所军分防,革兵防守关隘而土兵防守府城等阶段。换言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至洪熙元年(1425年)以前系土军千户所守御地方,此后系抽调附近卫所军分防,再后则为思州府地方自行募兵防守。所募之兵有地方少数民族苗兵,有守城充役的土兵,土兵由汉人或与汉人更为接近的群体组成,二者在待遇上有较大不同,官方的信任程度也有差别。从思州府知府蔡氏提议可以看出,拟召募守城的壮勇艺能之兵月给9钱,原守城土兵4.5钱,而把守关隘原住民1.8钱并量给米。铜仁府的情形应与此大体相当,如其总兵标下召募之兵亦为月饷9钱。
在世役旗军向召募营兵发展的过程中,募兵经费成为最大困难,当初召募移镇铜仁总兵官下标兵时,标兵月饷每月900两,每年10,800两,“除将裁革打手银抵充外,尚该银八千两”,巡抚刘庠申请以贵州“开纳事例处给”[13]卷139,万历十一年七月甲申,以开纳所入开支常项兵饷,将一时权宜之计转变为制度化安排,无疑反映出地方募兵之时所面临的左支右绌的财政窘境。
小 结
明代贵州兵制变迁大势,整体上与其他省区并无二致。其所当注意者,贵州并无类似云南、陕西、湖广等地的土军卫所,此并非贵州原无此类卫所,而是在永乐中期思州、思南等宣慰司改流进而设置贵州布政司的过程中裁撤了洪武时期所设的土军千户所。明后期因改土归流而新设置的敷勇、镇西等卫及属所,其旗军来源于地方从征官军,既有原设卫所旗军之裔,也有调征土司武装,可谓“土军”卫所的另一种形式。至嘉靖时期,贵州军政管理已经形成卫所—营兵制度相结合,文武职官并治、省内分守与邻省兼制相配合的局面。在地方文官系统——布政司府州县及监察系统逐渐介入地方军事管理的过程中,地方军事分防区参照府州辖区划定而有所整合,表现为分防分巡诸“道”,地方流官武职仍主要从原卫所世袭武职群体中选任;分守各处营哨关堡之“军”来自卫所军余,与各处招募原住民组成的“兵”一起构成地方军事防御力量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