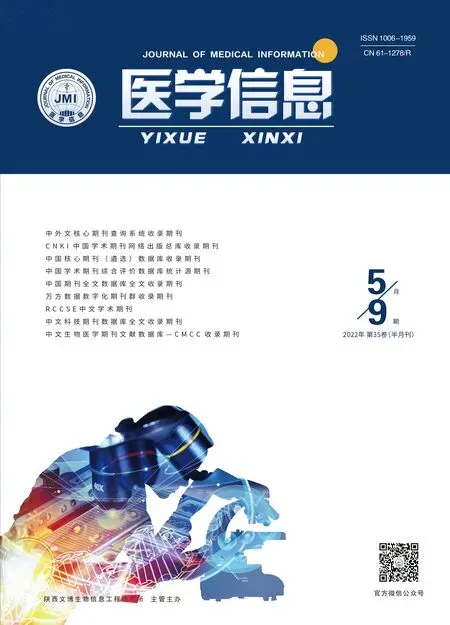溃疡性结肠炎中医干预治疗研究
李 伟,徐 伟
(1.内蒙古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2.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中西医科,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种由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具体表现为结、直肠黏膜的持续性炎症反应,常形成糜烂、溃疡,临床以反复发作和缓解交替为特点[1]。本病以腹痛、腹泻、里急后重、便黏液脓血便等肠道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其病变呈连续性,病程漫长,反复发作,不易痊愈,任何年龄均可发病,以20~50 岁人群多发。现代医学根据症状的轻重将UC分为轻度、中度与重度。轻度UC 主要应用水杨酸制剂(如柳氮磺吡啶),中、重度根据病情轻重程度联合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免疫制剂(如环孢素)等治疗,虽然有一定疗效,但不良反应较多,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如高血压、糖尿病、库欣综合征等。近年来,中医在UC 的治疗上取得很大进展,治疗优势得到充分体现,现对近几年有关中医治疗UC 的研究进行综述,综述如下。
1 病因病机
溃疡性结肠炎(UC)并不是具体的中医病名,但根据其肠道症状将本病划分在中医“肠澼”“痢疾”“泄泻”“肠风”“脏毒”等疾病范畴。对本病的认识起于《黄帝内经》,后经历代医家医学实践的填充而逐渐成熟和完善。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记载“食饮不节,起居不时……入五脏则瞋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其中指出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导致发病。《素问·举痛论》记载:“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指出情志不畅会发病。《诸病源候论》:“痢由脾弱肠虚……肠虚不复,故赤白连滞”,指出其发病基础为脾胃虚弱。《素问玄机原病式》:“利为湿热甚于肠胃,郁而成其病,皆热症也”,指出湿热邪气可致病。《景岳全书》曰:“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认为其病位在脾胃。《类证治裁·痢症》认为:“症胃腑湿蒸热壅,致气血凝结,……化脓血下注”,认为湿热为发病之标。随着中医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当代众多医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同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也对UC 的病因病机、施治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徐文强等[2]基于络病理论,将UC 的病机分为早期(络气郁滞)、中期(湿热蕴络)、后期(络脉阳虚)。芦煜等[3]通过对《金匮要略》相关条文分析,将UC 病因病机概括为素体虚弱,外邪乘之;饮食不节,积滞致痢;湿热互结,迫血妄行;邪正相持,迁延不愈。徐景藩教授主张“袪邪导滞”及“脏腑相关”为治疗原则[4]。总之,中医认为本病发病与饮食不节、起居无常、湿热浸淫、情志郁结、脾胃虚弱等因素息息相关。本病发展、变化主要在于正气不足,阴阳失衡,虚实夹杂。
2 治疗方法
2.1 中医内治法
2.1.1 经方、时方治疗 经方是指《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方剂,以六经辨证为主,其配伍严谨,药物精简,效如桴鼓而久用不衰,故被后世医家所推崇,时方是指唐宋时期医家所用之方剂,以脏腑辨证为主,其在经方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补充和完善。代安超等[5]认为UC 发病主要是因为肾气不足,脾胃虚弱而致气血失和,治疗当温补脾肾,益气温阳,故予温补特点明显的真人养脏汤治疗UC,结果表明其能明显减轻肠道炎症水平。吴萍建[6]认为脾虚为发病之本,浊气为发病之标,以疏肝健脾、升清降浊为法,以柴芍六君汤为基础方治疗60 例肝郁脾虚型UC,发现其疗效优于常规西药治疗。薛晔等[7]认为脾虚湿盛是UC 初期发病的主因,治疗当以健脾柔肝,佐以祛湿,故予痛泻要方合四君子汤治疗50 例肝郁脾虚型UC,结果显示可改善患者炎症因子IL-6、IL-10水平。沈灵娜[8]认为UC 有寒热错杂的特点,故予可平调寒热之甘草泻心汤治之,结果发现甘草泻心汤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且可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减轻机体炎症反应。
2.1.2 经验方治疗 经验方即医家基于理论基础,根据临床经验对疾病进行辨证论治而产生的用药经验。现代医家对UC 的治疗经验也是不可或缺的。白兆芝教授认为大肠湿热是UC 发病的首因,主张治疗应清肠热,兼顾脾胃,应用自拟清肠化湿方(太子参15 g,炒白术12 g,茯苓15 g,陈皮10 g,炒白芍12 g,防风10 g,木香10 g,黄连6 g 等)治疗,大多数患者在使用该处方后,症状较前明显改善[9]。芦煜[10]认为本病核心病机为湿热蕴肠,气血失和,运用祛风宁溃方(防风10 g,荆芥10 g,白头翁10 g,马齿苋20 g,败酱草20 g,麸炒白术15 g,白芍12 g,炙甘草10 g)治疗UC,大多数患者使用后,腹痛、腹泻、便黏液脓血便等症状明显减轻,也可增加患者肠道益生菌的丰度,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张玉梅[11]认为脾虚是疾病迁延不愈的主因,故以驱邪扶正并重为治则,应用健脾除湿汤配合柳氮磺吡啶肠溶片治疗脾虚湿阻型UC,治疗8 周后,结果表明其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席岚岚等[12]总结了宋光瑞教授应用补阳止泻法治疗脾肾阳虚型UC 的经验,并应用于临床,发现其能调节机体的过度炎症反应及免疫功能,降低促炎性细胞因子水平。高雪亮[13]基于“脑-肠互动学说”使用化浊解毒方治疗UC,结果表明本方可改善结肠黏膜病理改变,调节脑肠肽水平、调控神经递质。从中医内治的治疗结果来看,中医对UC 的疗效确切,既可以修复胃肠黏膜,又能改善患者症状,减轻炎症反应。
2.2 中医外治法
2.2.1 中药灌肠治疗 本病主要侵犯直肠和乙状结肠的黏膜层及黏膜下层。中药灌肠不仅可以使药物直达病所,使药物与病灶接触,促进溃疡愈合与炎症吸收,也不会损伤肝脏和肾脏。崔茜等[14]以清热祛湿,调和气血为法,运用白头翁汤加减灌肠联合葛根芩连汤口服治疗UC,疗效总体优于常规西药治疗,总有效率为91.18%。刘冰[15]研究发现,相对于美沙拉嗪栓剂,使用八味锡类散或者云南白药等中药灌肠治疗UC,能够降低过敏或胃肠系统并发症等不良反应。何宗琦等[16]采用清热祛湿解毒之法,予黄葵敛肠方(黄蜀葵花、凤尾草、地锦草各30 g,茜草、紫草各15 g,五倍子5 g)灌肠治疗UC,发现本方治疗远端UC 疗效确切,且不良反应少。徐伟[17]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人群嗜食辛辣、过食肥甘、饮酒无度,生活极度不规律致湿热内积于胃肠而见本病,常用黄连素联合八味锡类散保留灌肠治疗UC,治疗3 个周期后,患者腹泻、黏液便等症状较前明显减轻,疗效显著。
2.2.2 栓剂纳肛治疗 栓剂纳肛治疗具有见效快,操作简单等优点,栓剂纳肛后,药物与病灶接触,从而使得肠黏膜能迅速吸收药物,确保药效。杜骏等[18]认为中药灌肠可使有效成分直接在肠道吸收,能够有效促进溃疡的愈合,运用肠炎Ⅰ号方(黄柏、苦参各6 g,白及10 g,锡类散1 g)保留灌肠,结果显示血清IL-6、TNF-α 含量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吴亚宾等[19]认为栓剂纳肛可使药物直接作用于肠粘膜,尤其活动期疗效更明显,故用溃疡灵栓剂(苦参30 g,儿茶15 g,青黛5 g,槐花15 g,马齿苋30 g,五倍子10 g,山药30 g,田七粉5 g,蒲黄15 g)纳肛治疗UC,疗效确切,总体有效率为86.67%。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外治法在UC 的治疗上疗效确切,在一定程度上皆能减轻肠道的炎症反应,有效促进溃疡的愈合。
2.3 针刺疗法
2.3.1 针灸治疗 针灸具有疏通经络、行气活血,调和阴阳之功效。现代医学认为针灸能够作用于机体的免疫机制,神经内分泌机制,能够对胃肠道进行有效干预。刘杨[20]认为针灸治疗具有镇痛的效果,刺激穴位能对体内微循环起到改善作用,采用中医针灸治疗(治疗穴位为关元、气海、长强、大肠俞、天枢、三阴交、足三里)UC,结果显示针灸治疗组患者临床症状结束时间、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优于药物组。薛丹等[21]基于前期俞募配穴温针灸疗法的研究,通过该疗法治疗50 例UC 患者,发现俞募配穴温针灸疗法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全身炎症反应,且与口服美沙拉嗪效果相似。张艳君等[22]通过温针灸治疗(取中脘、关元、气海、天枢、双侧足三里、阴陵泉)UC,再配合口服补蔻补虚方,以此来达到扶正补虚,健脾温阳的作用,治疗2 个月后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4.23%。从各位医家应用针灸治疗UC 经验来看,其疗效确切,能够改善临床症状,促进溃疡愈合。
2.3.2 穴位埋线 穴位埋线以针灸学理论为指导,通过特制的针具将羊肠线埋入穴位以达到调和气血,治疗疾病的目的。现代研究认为穴位埋线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肠蠕动。杨茜等[23]采用“老十针”穴位埋线治疗并与单纯口服柳氮磺毗啶肠溶片进行疗效对比,结果表明穴位埋线能明显减轻患者症状及肠镜、病理检查下慢性炎症。龚鸿[24]通过穴位埋线治疗(选取足三里、关元、脾俞三穴)UC,治疗6 周后,患者的炎症指标(IL-6、IL-8和TNF-α)、结肠镜检评分均明显降低,总有效率为96%。闻永等[25]将120 例UC 患者随机分为美沙拉嗪组与针穴序贯组(针刺联合穴位埋线治疗),治疗12周后发现序贯组患者的中医症状评分、缓解情况以及复发情况均优于单一药物治疗。从治疗结果来看,穴位埋线可有效改善患者情况,且安全性高、不良反应少,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3 总结
本文从中医病因病机、中医内治、外治、针灸治疗角度总结了中医治疗UC 的发展现状,发现中医疗法治疗UC 优势明显,有自身独特的治疗特色,其不但能有效缓解临床症状,而且也能改善患者肠道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不良反应也少于西医治疗,适合长期应用。但中医在UC 的治疗上也存在以下问题:①缺乏统一、标准的病因病机以及规范化评价标准;②中医的临床研究在“对照、盲法、随机、重复”原则上亦有所缺陷,部分研究还停留在理论上。在日后的研究过程中,应重视UC 病因病机的客观研究,规范治疗,使得中医治疗UC 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合理化,以此发挥中医的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