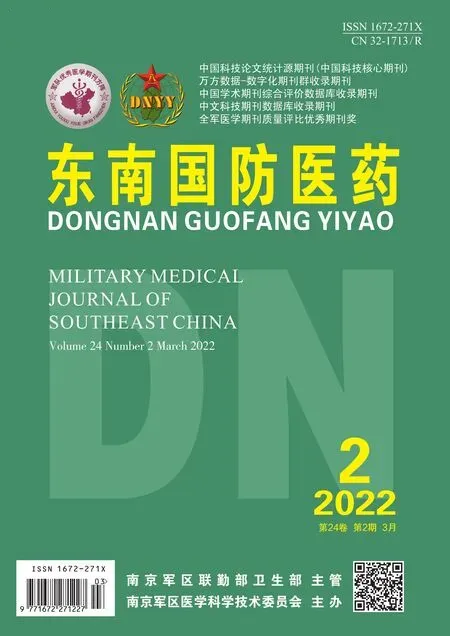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主要伤情及其救治进展
虞大为,王忠祥,徐东升综述,王诗波审校
0 引 言
众所周知,现代武器的杀伤力与杀伤范围都较传统武器有了极大提升,各国军队单兵防护及车辆装甲也有了很大加强。本文通过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战伤救治相关文献的复习,对其战伤伤员的主要受伤机制作简要回顾,并对其间战场救治的进展作一综述,以期对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军事冲突造成的伤情类型提供参考,并为高质量的战现场及后续救治提供依据。
1 现代战争主要伤情类型及其机制
对于从事军队卫勤工作的人员来说,充分了解现代战争中的主要伤情分布变化及其受伤机制十分重要。此外,还需充分认识到当前各国军队单兵防护装备的更新换代十分频繁,同时各类装甲车辆的自身防护能力也较前有了很大强化。这些“矛与盾”的进化共同决定了现代战争战场环境的“升级”,进而也对参战人员的受伤类型及伤情产生了很大影响[1]。当具体到特定战伤时,还必须了解不同战场环境、不同气候条件以及地理位置、不同战斗规模的综合影响,包括后续发生战斗所造成损伤类型、损伤对即时生存状态的影响、战创伤对伤愈后继续服现役可能性的最终影响等。
1.1 现代战争战场环境的变化在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文献分析表明,美军参战人员在这次战争中所受的伤害模式不同于美军以往参与过的多个战争[2-3]。这些差异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交战中美军的对方主要采用非传统作战方式,如多采取间接伏击和爆炸装置等,而双方正面的直接交火较少[4-5]。将该战争期间的伤情分布与以往美国所经历战争的伤情分布进行比较后发现,四肢创伤在所有战创伤中所占的比例更高[2,6]。该战争期间,美军第一次广泛使用了个人防弹衣和凯夫拉头盔,因此胸部战伤的总体比例降低,同时躯干部位发生即时致命性创伤的可能性也呈下降趋势。以往战争中有大量伤员死于胸腹部战创伤,但随着现代战场医疗条件的提升,许多士兵得以幸存,但仍会因各种毁损性创伤而需大量后续治疗[7-8]。
1.2 战伤主要原因总的来说,自20世纪起至21世纪初,较为重大的战争中枪伤的比例呈逐渐下降趋势,而诸如炮弹、地雷、手榴弹等造成的爆炸伤逐渐增加[1]。本世纪关于战伤的研究数据结果较多,且结果相似。有文献报道,2001-2005年间81%的战伤和73%的骨科创伤由爆炸引起,而枪伤仅占16%,其他创伤则由机动车和直升机坠毁、航空事故、跌倒、刀伤和其他原因造成[9]。此后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05-2009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收集的数据,提示75%的骨科损伤由爆炸造成,仅20%由枪伤引起[10]。还有研究以一部分增兵至伊拉克超过15个月的美军为研究对象,作了更加直接的战伤机制评估,结果发现,这部分美军中发生的战伤中87%由爆炸引起,其中骨科相关战伤高达81%[11]。这些关于近代战争中战伤机制与伤亡率的研究,通过具体的量化结果有预期地在现场采取救治措施,稳定伤势严重的伤员,使其有机会尽早安全转移到盟国或美国行进一步治疗,对战现场救治的效率与质量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和提升作用。
1.3 战伤的主要分类在发生率最高的骨科战伤相关研究中,2005-2009年部署至伊拉克或阿富汗的1 992 232名士兵中,累计有6092人发生17 177次较显著的肌肉骨骼损伤;在所有战斗伤亡中,77%的人遭受至少1次骨科损伤,年均发病率约3.06‰,其中骨折约占所有骨科战伤的40%,截肢约占所有骨科战伤的6%[10]。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虽然末端肢体损伤仅占所有战伤的50%左右,但却相比其他战伤消耗更多的医疗资源[12]。具体来说,肢体战伤平均住院时间最长,占总住院资源的64%,且最终仍有超60%的战伤人员遗留伤残。此外,肢体战伤在所有战伤后再次住院中的比例及医疗负担亦最高。
当然,不同兵种、不同作战任务的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战伤种类与比例也不尽相同。有研究选择了骑兵侦察兵作为研究对象[7],472名士兵发生了四肢、脊柱或骨盆的一处或多处损伤,研究共记录了1500个以上不同部位的骨科损伤,平均每名伤员约有3处损伤。在这些骨科损伤中,46%发生在下肢,32%发生在上肢,21%发生在脊柱和骨盆。截肢约占骨科战伤的11%,大多数为踝关节或腕关节附近的截肢。研究发现该兵种创伤性截肢率升高,甚至与越战时期的截肢率接近。此外,骨盆、脊柱或脊髓的损伤发生率也有增加。研究者认为,这类战伤发生率的变化主要由士兵驾驶简易交通工具时更易遭遇爆炸袭击造成。尽管军用运输车辆的强化装甲可能会降低肢体骨折、头面部及胸腹部创伤发生率,但高强度爆炸仍会使脊柱与骨盆等中轴骨有遭受严重损伤的风险。
2 现代战争的战伤救治
与以往战争的形式相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对方使用主要武器有较大变化,由传统的枪支炸药变为简易爆炸装置的广泛使用。这些爆炸造成的伤害常可导致复杂伤口,约占总战伤的四分之三左右。但即便如此,与美军以往的战争相比,该战争虽然经历时间最长,但士兵的存活率最高,主要原因归咎于第一目击者救治能力提升、转运流程和复苏方法的改进等。
2.1 战创伤伤口处置进展
2.1.1 战术战伤救护的程序化改进战术战伤救护(tactical combat casualty care, TCCC)指南于1996年首次出版,目前已经过多次版本更新,主要用以指导战场救治。因其针对性与实用性极高,现已广泛用于美军现代战争中的伤员救治,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好评[13]。通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死亡率的回顾性研究发现,90%的战场死亡由出血引起,其中大多为躯干出血,其次是交界部位和肢体出血[14]。为降低战场死亡率,TCCC指南强调使用肢体或交界止血带作为现场止血的主要工具,对于无法使用止血带控制的出血则提倡使用止血敷料和氨甲环酸等止血药物[15-16]。除出血外,气道损伤则是现代战争战伤导致死亡的第二大常见原因[17]。因此,TCCC还强调院前积极开展环甲膜切开术,尤其是颌面部创伤伤员[18]。此外,战伤导致的张力性气胸也是战现场死亡的原因之一,因此指南建议对所有胸部创伤合并循环崩溃的伤员行现场胸腔闭式引流术。
近年来TCCC指南中的创伤液体复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通过对以往战争经验的总结和现有研究相结合,将大量晶体液复苏方案修改为目标导向性液体复苏或红细胞∶血浆∶血小板1∶1∶1的液体复苏方案[19]。此外,TCCC还制定了针对野外开放性伤口的标准化抗生素预防方案,战场镇痛也由肌内吗啡注射改进为按需使用NSAIDs、鼻内或肌注给予氯胺酮及口服芬太尼等[20]。
最重要的是,TCCC指南的持续更新内容已被纳入美军的军事版创伤生命支持教科书,进而可对所有院前战伤救护人员和大多数军队非卫勤人员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21]。
2.1.2 止血带的规范化使用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初期,因担心止血效果不确切及其潜在的并发症,止血带并未在美军中广泛使用。关于止血带使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其存在导致肢体缺血的风险,此外,长时间肢端缺血还可通过释放全身炎症介质而造成内脏灌注不足,进而导致肠系膜缺血,对全身产生不利影响[22]。近年来一直使用止血带的以色列国防军的研究数据显示,该国战伤院前恰当有效使用止血带的比率很高,且并发症的发生率很低[23]。此后,在受伤的美军士兵中广泛使用止血带也证明其在战场上挽救了许多士兵的生命。一份回顾性研究证实,院前使用止血带甚至可避免高达57%的战伤死亡[24]。
2.2 战伤外科救治虽然现代战争中的战伤以骨科损伤为主,但战现场的外科救治重点却又有不同。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前期,某支前沿手术队在5个月时间内接受了1400多例战伤伤员,其中约50名伤员死亡。约20%战伤发生在胸部和腹部,大多数由爆炸装置造成[25]。该手术队期间共进行了40多例手术,包括剖腹探查、血管移植术、动脉修补术等。
另有报道称,某手术队在7个月时间内共对90名伤员进行了112例手术,其中79%由战创伤所致[26]。该手术队部署于某国际机场废弃航站楼一角,展开一所44张床位的战地医院。伤员由救护车、当地交通工具或医疗直升机送达,并在必要时用固定翼飞机后送。手术伤员中67%为阿富汗民兵或平民,30%为美国士兵,3%为其他联军部队士兵。受伤机制包括枪伤(34%)、爆炸(18%)、车祸(14%)、刺伤(5%)和其他创伤(7%)。按系统则分为肢体创伤(44%)、头颈创伤(17%)、多系统创伤(13%)、躯干创伤(8%)和血管创伤(3%)。总的来说,拟行外科手术的重伤员在该医院主要实施损伤控制性手术、积极控制体温防止低温,稳定生命体征的同时后送至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关于前沿手术队的相关研究报道众多,因其部署地点、配属军兵种、战斗激烈程度、是否接收平民伤员等情况而有所不同,所开展手术类型、手术数量、外科医师专业需求等也不尽相同。
战争后期,美军在战区内部署的医疗组已非独立运作,而是组织成为较完整的创伤救治体系,形式类似其国内的创伤中心。后勤领导机构掌握了每个医疗单位的设施配置及人员组成,并对其医疗与手术能力十分熟悉,因此特定伤员可迅速转运至相应地域特定医疗组以满足专科需求。当美军占领当地固定医院设施后,又会进一步加强其所提供医疗和外科支持类型的延续性[27-28]。此外,还有部分医疗机构被指定为特定伤病员收治点,如烧伤救治中心等,伤员在其中可停留更长时间,也确保了特殊伤员受到的救治质量更高,延续性更强。
2.3 战伤转运进展现代战争中,美军已建成较为完善的医疗后送体系,且条件允许时对重症伤员多采取空中转运[29]。早期美军参与的主要战争中,前线医院多设置在战事所在地区后方或附近,伤员在整个恢复期都安置于前方医院而很少返回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开始逐渐启用航空转运将重症伤员运送至美国本土以接受进一步治疗。危重伤员仅在重症医护人员陪同下才能撤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这一渠道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应用,转运机组人员都具备处置重症伤员的能力[30]。一般情况下,重症伤员首先从前线转运至二级或三级救治机构,伤后24~48 h内可转运至盟国医疗中心,48~96 h可回到美国本土医疗中心[31]。
美军的重症航空转运小组由1名重症医师、1名重症护士和1名呼吸治疗师组成[30]。医护团队在航空转运途中可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抗生素、镇静与麻醉药物等,同时具备完善的气道管理能力,负责管理便携式呼吸机,可输注血液制品,并完成基础血液学检查。一个小组可同时负责6名危重伤员,最多同时为3名伤员实施机械通气。
当然,转运途中也存在诸多潜在的不良事件风险,如长途转运时发生病情变化时缺少关键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如血压下降、尿量减少、氧饱和度降低和神志状态改变等。后送时间选择也是研究者的关注点之一,但大规模的回顾研究并未发现后送时间与伤员死亡率之间存在相关性[32]。近年来,美军重症航空转运小组还广泛应用于自然灾害的后送救援,已被证明是一种安全可靠的空中医疗后送方法,彻底改变了应急状态下重症伤员的救治与后送模式。
2.4 战伤后期康复进展
2.4.1 静脉血栓栓塞众所周知,战伤会增加伤员静脉血栓栓塞(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的风险,尤其是严重创伤伤员。由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产生的血栓栓子有导致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的风险,也是创伤伤员后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研究对10年间超过2.6万名战伤伤员进行了回顾性研究,结果证实双下肢截肢或膝以上截肢的伤员DVT和PE的风险显著增加[33]。另有研究表明,大量输血的伤员DVT和PE的风险也有增加[34]。该研究还表明,每日2次30~40 mg低分子量肝素静脉泵注可有效预防VTE。对已发生VTE的伤员来说,还可考虑放置临时下腔静脉滤器,以预防PE导致的死亡[35]。
2.4.2 创伤性颅脑损伤的康复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期,美军的简易爆炸装置的暴露频率增加,躯干部位的防护增强,共同导致了创伤性颅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的发病率增加。相对于四肢伤来说,TBI带来的后期康复压力更大、周期更长。据美国国防部估计,自2000年以来,有超过30万名美国服役人员遭受了不同程度的TBI,其中82.4%为轻度,8.5%为中度,1%为重度[36]。TBI的远期影响因损伤严重程度而差异显著,但仅轻度TBI中即有高达15%的伤员会发生脑震荡后综合征,如头痛、睡眠障碍、情绪障碍、认知障碍和神经功能障碍等,且伤员产生自杀倾向的风险也有增加[36]。中重度TBI患者中,上述并发症发生率可能更高。
TBI的诊断从前线的战地医护人员与士兵开始。在TBI的诊治过程中,前线医务人员和后方军医都应接受标准化的救治训练,以改善其早期识别与诊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 美军对TBI的治疗技术和经验相比以往有了显著提升。美军国防和退伍军人脑损伤中心建立了一个新项目,旨在帮助TBI相关伤员恢复到其伤后可能达到的最高神经功能水平。具体的治疗措施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感觉刺激,药物使用有安非他明、多巴胺能药物和生物兴奋剂等,感觉刺激技术则更加个体化,主要以改善伤员对感觉刺激的反应为具体目标[36-38]。
2.4.3 假肢技术进展如前文所述,创伤性截肢在现代战争的肌肉骨骼损伤中的占比并不低。由于年轻患者活动强度大,加载在假体上的冲击力大而频繁,易形成假体的无菌松动,新型假肢的设计应用是未来的趋势之一[39]。目前已研发出新型的“动力”假肢技术,可最大程度地恢复截肢伤员的运动功能。研究表明,与没有先进技术假肢的越南老兵相比,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截肢术后安装假肢的功能水平更高,在高强度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也更高[40]。
总的来说,功能性上肢假肢相比下肢假肢的技术发展落后。基于此现状,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于2006年创建了革命性的假肢开发项目,旨在为截肢患者提供精细的运动控制和感觉产生。其中部分上肢假肢可提供手指、手腕、肘部和肩膀的全面功能,可完成以往假肢无法执行的任务,在测试过程中受到了上肢截肢老兵们的欢迎,目前该假肢已获得美国FDA的批准[41]。还有公司开发出一种模块化假肢,允许用户通过植入大脑运动皮层的皮质电描图电极来控制假肢且成功完成了测试,可令伤员手指活动和手腕转动,使其残肢功能恢复更佳[42]。此外,美军还有少数因战伤而截肢的伤员成功地进行了肢体移植手术,如右前臂远端移植、双上肢移植等[43-44]。
3 结 语
21世纪初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旷日持久,战伤伤亡情况较以往战争有了巨大变化,由此催生的战场医疗技术也有了诸多进展。与此同时,战争中美军官兵战伤所造成的沉重负担对其后续的军事准备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现代战争的模式较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引发的伤病员伤情也随之改变,且根据战争性质、规模及具体环境的不同,伤情严重程度、受伤类型及伤员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而言,战场环境对作战人员造成的毁灭性损伤主要集中在肌肉骨骼系统,包括四肢、脊柱和骨盆等,与上世纪战争中大比例的颅脑与胸腹部损伤有显著区别。TCCC指南的持续更新、新技术装备的出台、战伤研究与实践的完善、转运与康复手段与技术的高速发展等等,共同构成了现代战争战场救治的多维度发展。本文主要回顾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战创伤类型、伤情机制及其救治原则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战伤救治和后期康复进展,希望能以此为借鉴,对我军未来的卫勤准备方向与重点提供参考,发展更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补充更加完善的战场救护器材,切实提高我军卫勤力量在未来战争中的应急保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