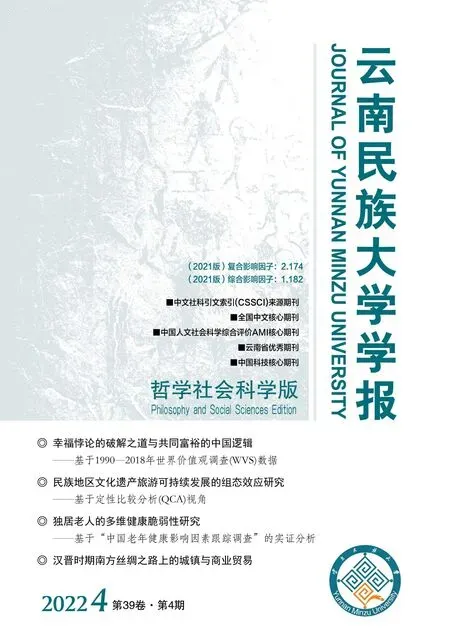汉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城镇与商业贸易
方 铁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汉晋是南方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及运作活跃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城镇建设与商业贸易往来,由于资料零散等原因,迄今未见专文研究,因试为考述。
一、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城镇
中原王朝对南方边疆的经营可追溯至秦代。春秋时期,蜀国、巴国分别据有四川盆地的西部与东部。巴与蜀为世仇,蜀王讨伐与巴结盟的苴侯,巴求救于秦。(1)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91页。周慎王五年(前316),秦军伐蜀,蜀国亡。随后秦灭巴,蜀、巴之地尽入秦国版图。(2)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1《巴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2页。秦于蜀国旧地置蜀相与蜀国守,封蜀王后裔为蜀侯。周赧王三十年(前285),蜀侯绾因“谋反”被杀,秦未复置蜀侯,在蜀地实行郡县制。秦蜀守李冰开凿成都两江,溉田万余顷,“姑皇得其利,以并天下”(3)虞世南:《北堂书钞》卷74注引《风俗通》,清光绪十四年刊本。。经过秦国、秦朝110余年的经营,至西汉代秦,四川盆地已称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土。
对位于蜀郡(治今成都)南面的今云贵等地,秦始皇不甚注意,大致以蜀郡附带管辖的今云贵地区为徼外。秦国统治四川盆地,官吏常頞开通五尺道,“诸此国(按:指宜宾至滇东北)颇置吏焉”(4)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五尺道因道宽秦五尺而得名。(5)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正义引《括地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其道始于僰道(治今四川宜宾),经今滇东北迄于郎州(治今云南曲靖)。另据《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6)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6页。。可见秦曾于滇东北部若干区域设官守,在今四川西昌等地拓路置郡县,但详情不可知。《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言,秦朝“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7)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1页。。秦朝的势力以及影响曾达今贵州西北部、云南的滇池地区与今川西南。秦朝统治15年,未对西南边疆有进一步经营。
西汉初年的60余年,百废待兴,且忙于抵御北方的匈奴,除继续经营巴蜀之地外,西汉暂时放弃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称,自秦朝在今滇东北开五尺道并置官守,“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8)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华阳国志》卷3《蜀志》说:“(汉高祖)虽王有巴蜀,南中(指今滇、黔和川西南地区)不宾也”(9)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14页。。后元三年(前141),刘彻继位。经文景之治,西汉的国力大为增强,武帝开始注意南方。西汉几次经营西南夷,均与开拓其地的交通线有关。西汉经营西南夷的主要原因,是武帝企望开通自僰道(治今四川宜宾)沿牂柯江(今贵州北盘江)达番禺(今广州)的用兵通道,以及自蜀地经西南夷、身毒(今印度)达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的道路。
西汉将始自僰道(治今四川宜宾)的五尺道,由今云南曲靖延至滇池地区,沿途经朱提(今云南昭通)、味县(治今曲靖)等地至益州(治今晋宁以东)。又复通由成都至邛都(今四川西昌)的灵关道,沿途经临邛(今四川邛崃)、严道(今四川荥经)、旄牛(今四川汉源)、邛都(今四川西昌)等地。继续南下,经会无(今四川会理)、弄栋(今云南姚安)、云南(在今祥云县)、巂唐(治今永平西北)至不韦(治今保山),前行可达今缅甸北部。由不韦南下的道路,即史籍所称之“博南山道”,因途径位今云南永平县西南的博南山而得名。(10)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7页。博南山道开通于西汉武帝时。有关考证参见方铁:《〈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辩》,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经博南山道入今缅甸辗转可达印度,博南山道及其延长路线又称“蜀身毒国道”。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沿途的城镇纷纷兴起,以下考述见于记载者。
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发地,通往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的五尺道、灵关道启程于此。成都也是汉朝管理南方丝绸之路的行政中枢。早在秦惠王二十七年(前278),张仪奉命修建成都城,城周回12里,城墙高7丈。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修成都城时距城十里取土,所挖池塘因以养鱼,时称“万岁池”(11)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96页。。《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说,成都为蜀郡治地,辖十五县,有七万余户,“有工官”(12)班固:《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8页。。成都辖12乡、五部尉,“州治太城,郡治少城”。成都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东接广汉,北接汶山,西接汉嘉,南接犍为”。成都城有四出大道,“道实二十里,有衢”。成都城西南两江上有七桥,(13)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54、235页。平日交通繁忙,行人摩肩接踵。
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笫八上》,西汉在四川盆地置巴、蜀、广汉、犍为四郡。以后武帝开通往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的道路,征调数万民工耗时数年,又“散币于卭僰”以安集之,浩大的费用主要来自四川盆地诸郡的租赋。西汉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其中的益州刺史(治今成都)管辖蜀地诸郡,以及今云南及附近地区的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以东)、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南)。东汉维持巴、蜀、广汉、犍为四郡,又在四郡与西南夷相接的地区,增设广汉、犍为、蜀三个属国,(14)范晔:《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14页,第3515页。可见两汉经营西南夷,确立以四川盆地诸郡为依托的方略。由于益州刺史部设于成都,成都乃成为经营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的行政中心。
成都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西汉成哀年间(前32~前1),成都人罗裒以钱数十万为资本,贸易、贩运于成都与京城,“数年间致千余万”(15)班固:《汉书》卷91《货殖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90页。。成都等地官府还以赋税所得,购买蜀地名产运销京城,“收采其利”,时称“均输法”(16)范晔:《后汉书》卷43《朱晖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60页。。两汉时期,成都地区的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商品的种类、质量与生产规模,均接近内地发达地区。
在文化方面。文帝末年,蜀郡(治今成都)太守文翁在成都立郡学,遣蜀士赴京向博士学习七经,学成后还乡里教授。在文翁的倡导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17)司马迁:《史记》卷89《循吏·文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25~3626页。。文翁倡学二三十年后,成都出现一批对汉文化有深厚造诣的蜀士,一些人成为全国有名的学者、文学家与科学家,如成都人张叔文与司马相如。武帝时张叔文应征为博士,司马相如官至中郎将,被尊为汉代的“辞宗”。《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笫八下》称:“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18)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笫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5页。。《华阳国志》卷3《蜀志》说,西汉时蜀地“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东汉建武后,成都“文化弥纯,道德弥臻”(19)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23页。。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后,四川盆地的经济、文化传入今云贵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成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除成都外当数僰道(治今四川宜宾)。僰道为犍为郡治所,犍为郡辖12县。《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引应劭语称僰道为“故僰侯国”(20)班固:《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注引应劭曰:“故僰侯国也。”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9页。,可见僰道原为僰人聚集地,开发的时间甚早。晋人以蜀郡、广汉、犍为为益州之“三蜀”,称僰道“旧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大姓吴、隗,又有楚、石、薛、相者”(21)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54页,第285页。。
自秦国统治四川盆地,官吏常頞开通五尺道,“诸此国(指今宜宾至滇东北)颇置吏焉”(22)司马迁:《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秦代的五尺道始于僰道(治今四川宜宾),经今滇东北至郎州(治今云南曲靖),西汉时延五尺道至滇池县(治今晋宁以东)。元光五年(前130),西汉修建南夷道,随后在南夷道设若干驿亭。南夷道始自僰道,经南广(治今云南盐津)、平夷(治今贵州毕节),接通牂柯江(今贵州北盘江)辗转至番禺(今广州)的水运路线。僰道为五尺道、南夷道的始发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在大夏目睹来自蜀地的蜀布与邛竹杖,回朝后建议汉武帝,开通由蜀地经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至身毒(今印度)、大夏的道路。为寻觅通往身毒、大夏的道路,武帝遣使自僰道(治今四川宜宾)四道并出,分别前往冉駹(今四川茂汶一带)、徙(今四川天全)、邛(今四川西昌)、僰(今四川宜宾一带)之地,被巂、昆明等所阻。(23)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6页。可见僰道为蜀郡等正式辖区与徼外之地的分界,统治者对僰道以外区域的情形茫然不知。元鼎五年(前112),南越(中心在今广州)反叛,西汉遣五路兵击之。其中一路由蜀地过犍为(今四川宜宾),经夜郎(在今贵州西部)沿牂柯江(今贵州北盘江)趋番禺(在今广州),西汉开拓的南夷道终于派上用场。
僰道(治今四川宜宾)是两汉自蜀地向西南夷移民的必经之地。由僰道南下的五尺道、南夷道所经的今滇东北一带,经济与文化较为兴盛,成为今云贵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汉晋时期沿五尺道、南夷道从蜀地迁来的移民甚多,以后形成不少重要的大姓。《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说,朱提郡(治今云南昭通),元封二年(前109)置,东汉建武后改犍为属国。当地官府“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24)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14页。,有朱、鲁、雷、兴、仇、递、髙、李等大姓,“亦有部曲。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25)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14页。。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南),汉代有大姓龙、傅、尹、董氏,蜀汉时大姓朱褒见于记载。味县(治今曲靖)亦为南中大姓的聚集之地。立于东晋义熙元年(405)的《爨宝子碑》,出土于曲靖扬旗田。立于刘宋大明二年(458)的《爨龙颜碑》,出土于距曲靖不远的陆良。“两爨碑”反映了宁州(治今曲靖)大姓醉心汉文化,奉内地习尚为圭臬的情形。
在今滇东北地区,两汉在五尺道所经之处建立不少城镇。《华阳国志》卷3《蜀志》称犍为郡土地沃美、人士杰出。(26)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三《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54页。犍为郡所辖朱提(治今昭通)、堂琅(治在今巧家以东)、存鄢(在今宣威县境)诸县均在今滇东北。(27)班固:《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99页。以上诸地最重要的城镇是朱提。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朱提郡置于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有属县四。东汉建武后改为犍为属国,领属县五,有8000户居民,城中有朱、鲁、雷、兴、仇、递、髙、李等大姓,各辖有部曲。又称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28)《永昌郡传》,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朱提废城至唐代仍存。《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说,自僰道(治今四川宜宾)行九日至鲁望(在今滇东北),其地称为蛮、汉地区的分界,为唐代前期曲州、靖州的所在地,曲州、靖州的“废城”与坟墓、碑阙等遗物,仍残存可见。(29)樊绰撰:《云南志补注》,向达校,木芹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唐代曲州治今昭通,即汉代朱提旧地。另据记载,“(僰人)多以荔枝为业,园植万株,收一百五十斛”(30)《郡国志》,载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九《剑南西道八·戎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92页。。据《广志》:“犍为僰道南,荔枝熟时百鸟肥”(31)郭义恭:《广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以朱提为中心的今滇东北地区,汉晋时期大面积种植荔枝,不可能都在当地消费,大部分当运销蜀地。
沿五尺道往南,较重要的城市还有建宁郡的郡治味县(治今曲靖)。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军征讨南中反叛大姓,关键之战即在味县打败大姓首领孟获所率叛军的战役。南中平定后,蜀汉改益州郡为建宁郡(治今晋宁以东),以李恢为太守,兼领交州刺史,移治味县。蜀汉在味县举办具有相当规模的屯田,南中人谓之“屯下”。建宁郡初辖17属县。以后蜀汉分其地一部分为平乐郡,改领13属县。味县是蜀汉镇守南中的军政机构庲降都督的所在地,驻扎了大量军队,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味县城内有重要的聚会场所明月社,夷、晋之民若不奉官,则官府与之共盟于明月社。汉代味县建有城池。《蛮书》卷6《云南城镇》称石城川为味县故地,贞观中为郎州,开元初改为南宁州(治今曲靖)。“州城即诸葛亮战处故城也”。足见唐代南宁州的州城,即为汉代味县“故城”。
在南方丝绸之路所经的今滇中一带,最重要的城市为益州郡的治所滇池县(治今晋宁以东)。滇池县原为滇国的统治中心,“滇池泽在西北”(32)班固:《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1页。。《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称,益州郡置于武帝元封二年(前109),领24县,有28万户居民,益州郡土地宽广,土质肥沃,滇池城紧邻周回210里的大池,因源泉深广,下流浅狭有如倒流,乃称“滇池”。其地“多长松,皋有鹦鹉、孔雀,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当地豪民奢豪,难以抚御,且不时反叛。(33)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94页。
元封二年(前109),西汉于滇国旧地置益州郡(治今晋宁以东)。据记载,“(其)后数年,(滇国)复并昆明地,皆与之属之此郡”(34)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6页。。西汉联合滇国打败巂、昆明后,将巂、昆明活动的地域划归益州郡,几乎包有今云南中部的大部分区域。五尺道、交趾道以滇池城为终点,今滇东、滇西间的行旅往来亦必经其地,滇池城乃成为西南夷的交通枢纽与政治经济的中心。因有滇国经营的基础,滇池城具有较大的规模,人烟亦较繁盛。唐代《蛮书》卷6《云南城镇》称晋宁州为汉代滇池县(治今晋宁以东)故地,“幅员广数百里,西爨王墓,累累相望”。《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言,从拓东节度城(在今昆明)至安宁馆一日,“安宁馆本是汉建宁郡城也”。可见汉代的滇池城建有城堡,唐代《蛮书》因此称为“汉建宁郡城”。
两汉时期,滇池流域尤其是滇池县(治今晋宁以东)的经济、文化有较快的发展。益州郡太守文齐,在滇池县一带“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史称其地“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忕,居官者皆富及累世”。王阜任益州郡太守,“政化尤异”,滇池县“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35)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6页。。滇池县还是大姓集中之地。《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称,自汉武帝开西南夷,“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其中一些人居住在滇池城。汉代益州郡有著名的大姓雍闓,其先辈是汉代名将雍齿,原居汁防(今四川什邡)。以后雍齿获罪,其家族被强迁至西南夷。东汉时雍闓逐渐发达,成为南中(今云南、贵州地区)有名的大姓。(36)陈寿:《三国志》卷43《蜀书·吕凯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7页。
灵关道上重要的城镇有邛都(治今四川西昌)。《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称元鼎六年(前111)置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西汉越嶲郡辖15县,东汉改为14县,有13万余户百姓。越巂郡包括今川西南与云南的楚雄北部、丽江等地。蜀汉延熙五年(242),越嶲郡太守张嶷重修郡城邛都,“夷人男女,莫不致力”。同时恢复周围的七县。(37)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09页。
不韦(治今保山),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路段的重要城市。永昌郡号称“古哀牢国”(38)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4页。,开发的时间很早。永平十二年(69),哀牢夷归降,东汉以前代所置之哀牢、博南二县为基础,添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置为永昌郡,郡治不韦。(39)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9页。永昌郡辖8县,“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40)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8页。,管辖今云南省的西部、西南部与相邻的今缅甸东北部。永昌郡号称有各族居民23万余户,是东汉著名的大郡。(41)范晔:《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13页。
不韦是中原王朝镇守西南边疆的重镇,历来受朝廷重视。蜀汉章武初,永昌郡无太守。时值南中诸郡叛乱,功曹吕凯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诸葛亮南征,盛赞其义,上表曰:“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乃以吕凯为云南郡太守,王伉为永昌郡太守,“皆封亭侯”(42)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5页。。“威恩内著,为郡中所服”的不韦大姓吕凯,为从蜀地迁至不韦之吕不韦宗族的后裔,不韦县名源于此,(43)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7页。可见不韦地区有不少大姓。不韦还是蜀身毒国道上重要的商贸市场。《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44)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1页。。《蛮书》卷6《云南城镇》称永昌(按:即汉代不韦)为“要镇”。南诏与唐朝决裂,重视经营云南地区的西南部,南诏的精锐之师共三万人,有1/3驻扎在永昌。事实上永昌在南方重镇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在汉代已基本确立。
两汉还积极拓建由蜀地前往中南半岛东部的道路。据《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汉武帝置交趾郡,郡治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交趾郡辖12城,龙编的地位以后愈显重要。西汉在全国设置十三刺史部,交趾刺史名列其中,治所在龙编。龙编城的修建乃受重视,其城壁至唐代犹存。《蛮书》卷1《云南界内途程》称,交趾城(按:即汉代龙编城),“汉时城壁尚存,碑铭并在”。
东汉建武十九年(43),伏波将军马援奉命镇压交趾(在今越南河内)的二征起义,他率军沿麋冷水道出进桑(治在今屏边县境),经贲古(治今蒙自东南)、西随(治在今金平县境)至交趾,沿途开通水陆道路,以方便运输军粮和辎重。对马援开通由今云南中部至越南北部的交通线,时称“交趾道”,因经由进桑关,这条道路又称“进桑关道”(45)郦道元:《水经注》卷三七《叶榆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4页。。道路的走向为由今云南中部南下蒙自,沿红河经今屏边地界达越南河内,沿途“崇山接险,水路三千里”。另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西汉于进桑县之红河河畔设进桑关,可见其时红河已有民间的水陆运输,西汉因此设关,马援正式开辟这条通道,以供军队利用。道路开通以后,“转输通利”(46)郦道元:《水经注》卷37《叶榆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4页。。这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另一条支线。
红河水流湍急,夏秋季水位落差甚大,逆水行舟不易,走交趾道自今云南中部沿红河而下,由交趾北上多为陆行。由历代记载观之,在五代时期交趾脱离中原王朝版图之前,中国内地与交趾的联系大都通过海路。在元朝沿邕州(治今广西南宁)至大罗城(在今越南河内)的道路置驿站之前,交趾道是中原王朝联系交趾陆运的主要通道。
建初八年(83),为减少风浪过大导致覆舟的海运事故,东汉朝廷接受大司农郑弘的建议,整修由零陵(今湖南永州)、桂阳(治今广东连县)进入岭南地区的道路。工程竣工后,“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47)范晔:《后汉书》卷33《郑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6页。。交趾(治今越南河内)、九真(治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在今越南平治天省)等郡,经常向朝廷进献龙眼、荔枝等水果,东汉于所经道路十里设一驿,五里置一堠,派使者乘驿马昼夜进献水果。进献使者劳累太甚,且常被野兽伤害。永元十五年(103),和帝乃颁诏停止进献。(48)范晔:《后汉书》卷4《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4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48《汉纪四十》永元十五年十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559页。以后由零陵、桂阳至岭南地区的道路较少见于记载。中原王朝联系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主要还是走行经今云南地区的道路。
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
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南边疆与内地、中南半岛的商贸、文化的交流得到较快的发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据研究,商周时期制造的青铜器含有云南地区出产的铜。考古学家对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测定,发现有91件青铜器的原料产自云南永善金沙地区。(49)李晓岑:《商周时期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据《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西汉时我国产锡的地点仅有3处,而且大都在云南地区。(50)班固:《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八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1页。先秦时中原造青铜器所用之锡,可能大部分来自云南地区。(51)童恩正、魏启鹏、范勇:《〈中原找锡记〉质疑》,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1984年第4期。
东汉时除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西南)未见著录外,西南夷的其他边郡均有开采金属的记载。所开采金属除铜以外,还有铁、银、金、锡、铅和白铜等。新开的金属矿源以永昌郡(治今保山)较为重要。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52)常璩:《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47页。。永昌郡还出黄金、光珠与铜锡。《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称,永昌郡“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53)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9页。。据王充《论衡》卷19《验符》:“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纤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采得日重五铢之金。一色正黄”(54)王充撰:《论衡》卷19《验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从永昌郡见于记载的情形,可窥知东汉时西南夷矿冶业较为兴盛。
西南夷诸郡的铜矿与银矿经开采提炼,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将成型的金属锭料运入内地供铸币之用。据《汉书》卷24下《食货志第四下》:“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颜师古注:“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55)班固:《汉书》卷24下《食货志第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78页。。可知朱提(治今昭通)所产银被大量用以铸币。1976年,在四川西昌发现新莽时期的一处窖藏,出土铜锭4个和铸造“货泉”用的钱范5块,(56)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编委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表明西汉末年邛都是优质铜的产地,出产的铜或供官府制造钱币。
经南方丝绸之路运入内地的金属还有银和铜。朱提(治今昭通)出产的银,邛都(在今四川西昌)所产之铜,被汉朝确定为铸币的原料,不仅是由于纯度较高,还有产量较大、质量稳定等方面的原因,汉朝对此类采矿工场进行专门管理。朱提、堂狼(在今云南巧家以东)出产的铜器,其铭文在产地下或有“工”字,可见东汉时云南制造的青铜器,来自官府经营的“工官”作坊。(57)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订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7页。
除锭料等初级产品外,朱提(治今昭通)等地生产的铜器也不断进入内地,被称为“朱提铜器”或“堂狼铜器”(58)孙太初:《朱提堂狼铜洗考》,见《云南青铜器论丛》编辑组:《云南青铜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对这一类铜器各地多有收藏,在著录或出土的汉代铜器中,朱提、堂狼的铜器占有较大的比例。东汉以后,朱提、堂狼的铜器较少见于记载,可能是因铜器不再流行铸著款识之故。从昭通地区晋墓出土的情形来看,朱提、堂狼铜器至晋代仍继续生产,但规模不如东汉之盛。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冶铁和制造铁器的技术从内地传入西南夷。先秦与西汉的前半期,西南夷诸族还不会冶铁,所使用的铁器来自蜀地。东汉时滇池、不韦、台登、会无等县始有产铁的记载。但应指出,汉代西南夷使用的一部分铁器仍来自蜀地。近年贵州出土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的铁器308件,较出土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铁器的数量增加近两倍,这些铁器大部分来自巴蜀地区。(59)宋世坤:《贵州早期铁器的研究》,载《考古》1992年第3期。
随着交通业的发展,内地的日常器物也不断传入西南夷。在西汉中期后西南夷的墓葬普遍出土汉式风格的各类器物,这些器物虽有一些为当地仿制,但大部分是从内地输入的,如铜镜中的草叶纹镜、昭明镜、日光镜、百乳镜,半两、五铢等秦汉时的货币,以及带钩、印章等类器物。
除锭块等金属产品外,西南夷(指今云贵、川西地区)出产的手工艺制品、珍宝与珍禽异兽,经南方丝绸之路不断输入内地,也是朝野人士喜爱之物。《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说,滇池地区多出鹦鹉、孔雀,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出产兰干细布与梧桐木华布,又有光珠(宝石)、虎魄(琥珀)、水精(水晶)、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与貊兽(大熊猫),传说蜻蛉县(在今大姚、姚安一带)有金马、碧鸡,汉武帝派专使赴云南觅求未获,使者在途中写下《碧鸡颂》。西南夷的物产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进入内地。桓宽《盐铁论》卷1《通有》说:“徙邛笮之货致于东海”(60)桓宽撰:《盐铁论·通有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班固称自西汉开拓四夷,“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61)班固:《汉书》卷96下《西域传 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8页。。范晔言:汉代有“沉沙栖陆玮宝”“賨幏火毳驯禽封兽”等物堆积于内府(62)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60页。,这些珍品异物,有不少来自西南夷。
南方丝绸之路沿途也出产一些名贵的地方产品。《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称,永昌郡(治今保山)有“蚕桑、绵绢、采帛、文绣”,“猩猩兽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续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有兰干细布,兰干,僚言纻也,织成文如绫锦。又有罽氎、帛叠”(63)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30页,第431页。。《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说,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夷相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64)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49页,第2851页。。
从上述记载来看,永昌郡(治今保山)能织造棉布(绵绢、帛叠)、丝绸(蚕桑)、纻麻布(兰干细布)与羊毛布(按:即朱罽、罽旄),生产者为永昌郡的鸠僚等本地民族,纺织品自用或出售,估计产量不会太少。
西南夷诸族向朝廷贡纳珍宝异物,主要是供统治者享用。而西南夷输出的各类药材,则是内地百姓可得的疗疾之物。汉代西南夷已开发出一些动植物类药材。《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称,笮都(在今四川汉源东北)“土出常年神药”,汶山郡“有灵羊,可疗毒”。当地有食药鹿,鹿麑有胎者,肠中粪可治疗毒疾,其地“特多杂药”。《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说,堂狼县(治在今巧家以东)“出杂药,有堂螂附子”。晋代《博物志》称,云南郡(治今云南祥云东南)有“两头鹿”,鹿胎“可治蛇虺毒”(65)张华撰:《博物志》,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称:“岷山特多药,其椒特多好者,绝异于天下之好者”(66)范晔:《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注引《蜀都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09页。。西南夷等地出产的药材,不仅行销内地,而且因药质优良、效用显著享有较佳的声誉。
劳作、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兵卒与商贾,大都来自蜀地以及西南夷的味县(治今曲靖)、永昌(治今保山)等郡县地区。史籍记载了他们的辛劳与呼声。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西汉遣丁卒披荆斩棘开通博南山道,饱受劳顿之苦的筑路丁卒或行旅乃作歌:“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67)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该道在汉武帝时已开通。《渡澜沧江歌》见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7页。。这首《渡澜沧江歌》是现存云贵地区最早的民谣,反映了底层百姓对统治者开疆拓土怀有复杂的感情。
西汉在秦代的基础上拓展五尺道。由僰道(治今四川宜宾)至朱提(治今昭通)的水陆道路,大都艰阻难行,行旅须经牛叩头、马搏颊等陡坡,渡过筠连河、横江、洒鱼河等湍急的河流,“故行人为语曰:‘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庲降贾子,左儋七里’。”(68)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4《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420~422页。歌谣描写行经僰道至朱提的道路,路途艰险、行人辛苦。行旅沿途跨越犹溪、赤水及盘蛇一般弯曲的七曲河,翻过高耸“气与天通”的盘羊、乌栊等山岭,行人挥汗如雨,不忘发声呼应。来自庲降(按:指味县)的商贩,途经狭路与危棧之时,须以左肩担物连行七里,至宽敞处始可换肩,而得稍事休息。
在南方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前,已存在自四川盆地经今云南通往缅甸、越南等地的民间小道。1949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滇国墓葬发现若干来自西亚或南亚的琉璃珠、蚀花石髄珠、有翼虎银带钩等物。(69)作铭:《我国出土的蚀花的肉红石髄珠》,载《考古》1974年第6期。在出土“滇王之印”的滇王墓与成都先秦时的墓葬,还发现不少产自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环纹货贝。在东周中睌期至西汉中期滇池周围的26座大墓,出土海贝26万余枚,数量超过我国其他地区出土同类海贝的总和。在发现“滇王之印”的末代滇王墓,出土海贝三万余枚。(70)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证明运输上述物品的小道先秦时已存在。据《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张骞出使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见到通过西南夷运来的蜀布与邛竹杖,推测蜀地、大夏间有行经西南夷的小道。
通过先秦时期的小道,云南地区、中南半岛建立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交流,两地的青铜文化也存在联系。通过对铜制的戈、剑、矛、靴形斧、犁、斧、鼓等器物的比较,可以看出云南的滇文化、越南的东山文化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两者地域相近,并通过水陆通道的联系所形成的。但这两支文化各有典型器物,因此是不同的青铜文化。滇文化与泰国的班清文化也有联系,两支文化的遗址均发现作为明器的小铜鼓,滇文化中常见的鼓形座杖头铜饰,亦见于班清文化的一些遗址。在以上3种文化中滇文化发展的水平最高,周边的文化或多或少受其影响。除滇文化外,云南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与中南半岛同期文化,也存在一定的联系。红河流域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的相同点较多,澜沧江中下游文化与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较密切。西汉在今云南地区、越南北部设郡县后,滇文化、东山文化明显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约在东汉中期,这两支文化逐渐被中原传来的汉文化取代,班清文化所受外来的影响则不甚明显。(71)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
在中南半岛有称为“掸”的古国。掸国在先秦时已存在,掸国与汉朝有多次交往。东汉时,掸国于永元九年(97)、永宁元年(120)、永建六年(131)3次遣使至汉。掸国第二次遣使,国王雍由调派来一个“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的杂技团,其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72)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1页。。袁宏《后汉记》卷15《殇帝纪》,亦记载安帝时掸国进献幻人之事,并说:“自交州塞外檀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73)袁宏:《后汉记》卷15《殇帝纪》,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页。。掸国的地望在今云南德宏、文山之间往南,即东汉永昌郡(治今保山)、日南郡(在今越南平治天省)的外围地带,约在今老挝、泰国、缅甸中部略为偏东的地区。
两汉开通至今越南北部的道路,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梁书》卷54《海南传》说:“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74)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83页。在广州与广西的贵县、合浦等地的西汉后期墓,近数十年出土不少以玛瑙、鸡血石、石榴石、煤精、水晶、琥珀、玻璃等为原料制成的串珠,以及迭嵌眼圈式玻璃珠和兰色玻璃碗。(75)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页。这些珠饰与工艺品的形制、材料与中国传统工艺品不同,可能是来自南亚次大陆及其以西地区。1957年,在合浦堂排西汉晚期的四座墓葬,出土琉璃珠1656粒,玛瑙珠12枚,肉红石髓珠99粒,还有6件琥珀和14件水晶。据鉴定这些珍宝均来自海外地区。(76)《广西合浦堂排汉墓发掘简报》,见《文物参考资料丛刊》第四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内地的人口与经济文化进入交趾地区。西汉时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西北)已种植稻谷,生产的粮食能自给,还可接济合浦郡(治今广西浦北县西南)、九真郡(治今越南清化西北)。至迟东汉时交趾郡种植双季稻,东汉《异物志》说:“稻,交趾一岁再植”(77)杨孚:《异物志》,钱谦益:《初学集》卷27《五谷》引,《四部丛刊》本。。西汉前半期,九真郡及附近地区处于渔猎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粮食常靠交趾郡接济,仍“每致困乏”。东汉初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他教民制作田器,授予垦辟、耕犁之法,开垦大面积荒地,收成逐年丰稔,“百姓充给”(78)范晔:《后汉书》卷76《任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62页。。九真郡的农业进一步发展,分季节种白谷、赤谷,“所谓两熟之稻也”。史称“米不外散,恒为丰国”(79)郦道元:《水经注》卷36《郁水》引《林邑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4页。。
凭借发达的交通,交趾地区的社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东汉初,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太守锡光与九真郡(治今越南清化西北)太守任延,在治地“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任延针对“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的情形,移书属县,令官吏劝说未婚男女各以年龄相配,对贫困无礼聘者,长史以下官吏省俸金赈助,“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九真郡百姓对任延十分感激,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所生子多取名“任”(80)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卷76《循吏·任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6页、第2462页。。任延、锡光积极发展生产、改革陋俗产生了良好影响,徼外部落内属屡见于记载。建武十二年(36),“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朝廷封为“归汉里君”。次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兎”。范晔称“岭南华风”始于锡光、任延两位太守。(81)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卷76《循吏·任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6页、第2462页。东汉时期,内地文化在今越南北部逐渐传播,王充《论衡》卷19《恢国》称,日南(在今越南平治天省)等地,“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82)王充:《论衡》卷19《恢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
交趾地区出产的水果等物,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也进入内地。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西汉时交趾郡(治今越南河内)设有羞官。据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三国时吴国孙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83)嵇含:《南方草木状》(考补本),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交趾太守士燮降吴,每逢遣使诣孙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84)陈寿:《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93页。
总之,汉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与运作,推动了道路沿线城镇的建设,促进了内地与西南边疆及徼外地区间的商业贸易活动,该方面的内容是把握南方丝绸之路全貌,以及中原王朝经营、开发西南边疆情形的一部分,重要意义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