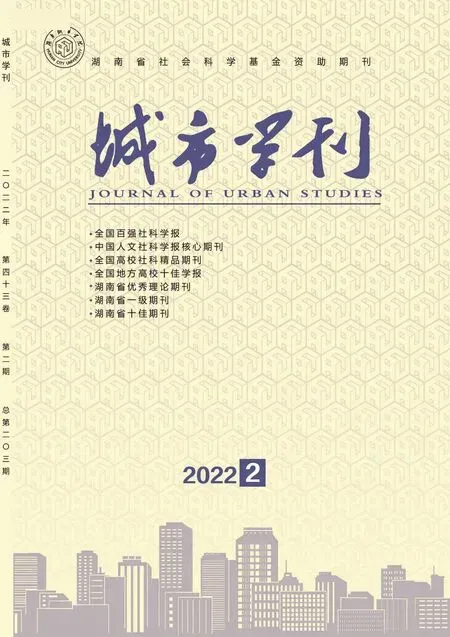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域下安徒生童话的科学想象
刘叶红
(湖南城市学院 人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现代儿童文学奠基者安徒生所处的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科学与技术突飞猛进。19世纪40年代,安徒生童话创作跳出童话传统思维中神秘魔法、巫婆和精灵等认知定势,开始以科技的想象书写童话的现代之音,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向儿童和成人呈现科技带来的世界巨变。
学者们对安徒生童话曾多层次解读,但这些研究多囿于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上。基于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安徒生童话中的科学想象,还未见深层次的阐释。然而,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生态、科技无疑成为后人文语境下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生态批评的定义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1]这一界定确定了生态批评对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内心世界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能脱离自然(环境)。安徒生聚焦科学想象的童话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识。科学技术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造成社会伦理秩序的改变,科技求真的道德准则不仅发挥了创造更加美好社会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功能,也带来了新的伦理困惑。因此,本文拟从生态批评视域聚焦安徒生童话作品中的科学想象,从科技文明的审视、科技异化中的自我认同和科技进步对儿童社会化的伦理关注三方面来阐述安徒生童话作品中的隐含作者建构。
一、浪漫与理性:意识形态争锋下对科技文明的审视
安徒生“是一个大自然独特的描绘者,是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欢欣鼓舞的人”。[2]对自然的书写、对环境的书写、利用科技的力量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由此对自然生态带来的影响都属于生态批评的范畴。首先,安徒生将生态自然观融入童话中。安徒生早期童话或植根于民间故事,或取材于现实生活,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文学崇尚自然,自然常常是作品的表现对象。安徒生童年时期和父亲闲暇时的树林游逛、游历不同国家的大自然体验、童年成长和游历经历中形成的荒野关注……这些体验都融入了安徒生童话的自然书写之中。[3]其次,安徒生将生态科技观融入童话中。安徒生中后期童话作品浓郁的浪漫主义想象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以科学想象为主体的冷峻现实主义。一方面,1779—1850年期间,以诗人厄楞士雷革为首的“浪漫主义”运动在丹麦盛行,但安徒生不同于其他浪漫主义者,对回到中世纪的生活毫无憧憬和兴趣。另一方面,安徒生所处的 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加快,科技迅猛发展,火车等公共交通得到普及,电报、发电机、无线电缆等通讯设施相继问世。在突飞猛进的科技推动下,时代潮流中的一切领域都在呼唤科学,科学进入文学也就水到渠成,人们争相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实,主体情感倾斜于客观现实,浪漫让位于理性。
安徒生把科学想象引入童话创作,自然科学技术创造下人类和自然界中非人类(动物、植物等)之间的关系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安徒生童话对自然(环境)和科技想象书写的主要表现有:第一,科学技术进步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的影响和改变。人类思想借助科技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但是对待自然生态的伦理态度却没有相应地提高。科技创造或破坏自然界生物的诗意栖居,或因欲望膨胀扼杀人类的美好灵魂,带来人的异化。在《海蟒》中,人类把发明的海底电缆放入海底,造成了海洋环境的破坏,引发海底生物的惊慌、骚动和好奇。在《树精》中,树精对大城市的繁华充满了强烈向往和渴望,不满乡下老家的生活,为了去巴黎看世界博览会,情愿以灭亡为代价来享受瞬间的绚丽。第二,自然审美和科技审美的对立。非人类生物在故事中并不是作为人类行为的活动背景或框架,而是和人类一起共生,是整个事件的共同参与者或独立建构者,他们一起以自然环境史或人类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呈现。人类与自然环境一起参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和历史文明的进步。但是,《夜莺》中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忽视大自然中夜莺的歌唱,夸大科技人造夜莺的价值和意义。《树精》中乡下新鲜空气中的自然美和城市里马尔斯广场开出的艺术和工业的璀璨的花处处充满了对人造景观的戏谑。第三,运用科技想象对未来世界生态环境的美好憧憬和歌颂,强调人的主体性。西方社会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安徒生多数童话都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在困难、悲苦的社会现实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力量时,就向“上帝”寻求出路。但“上帝为人立法”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和人的理性,正如康德所说“人为自己立法”。安徒生童话以科技代替传统魔法和神灵积极讴歌人类思想。《一千年之内》中,人类乘着蒸汽的翅膀观光,憧憬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理解,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紧密结合。《光荣的荆棘路》歌颂以科技造福人类、推动文明和历史前进的工程师。第四,科技发展既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也凸显人在自然生态前的渺小,只有从整体生态的视角审视天地万物,才能免受自然的惩罚和奴役。《恶毒的王子》中恶毒、傲慢、目空一切的王子乘着能在空中航行的船想要战胜上帝,却被小蚊虫征服了,弄得发了疯。
几乎所有童话都不同程度地再现社会意识形态。安徒生科学想象童话中的生态科技观体现浪漫与理性意识形态的争锋。社会的、历史的条件是影响和改变文学创作实践不可分割的方面,作者甚至读者先前的人生经历、知识储备、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都至关重要。安徒生童话创作的生成和接受也无法和社会、历史、心理等因素剥离开来。18世纪末法兰西革命演化为欧洲的一种“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氛围,人类开始从王权、神权和封建特权等绝对权威和未经检验的传统依赖中解放出来。[4]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生态文学勃兴,作家作品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素材,以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歌颂大自然,抒发个人情感。同期,欧洲工业革命对19世纪的科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达尔文进化论、优生学等思想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化选择过程提供了看似科学的虚假外衣。社会阶层由此借鉴了人类学、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实践”论证,在经济和政治上倡导自然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安徒生所在的西北欧边陲丹麦,是个君主立宪国家,有着严格的官僚封建结构,正在迅速地转变为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在19世纪初期的丹麦社会中,出身贫穷和卑微的安徒生,几乎不可能突破阶级障碍。因此,安徒生早期的童话总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替。在中后期的童话中,安徒生将19世纪丹麦浪漫主义文学的两个对立面——文学与科学想象结合起来,科学之花开在童话文学之树上。《乘邮车来的十二位旅客》指向人类的创造带来时代的日新月异,思想停滞不前就无法适应新时代,感觉生活在奇怪的时代。《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不断讴歌新时代的到来,呐喊擦掉过去的、野蛮的、黑暗的时代的故事,对怀古美化中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提出隐约的批评。由此可见,安徒生中后期童话把科学和技术想象融入创作,再现现实的经验世界,以前瞻性的笔触思考过去与现代、感性与理性,反映封建主义末期和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文明,投射浪漫与理性意识形态的争锋。
二、单声或复调:科技生态中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主体问题,是主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种关系定位和自我确认,一种有关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与追问”。[5]安徒生在已有科学技术和社会现实基础上发挥想象建构的乌托邦童话作品中,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工业文明的巨大发展,改变了现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由此而致的客观环境变化让童话中的主体(天地万物)出现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促使主体重新审视自己在社会、历史、群体和自然中的归属和位置,推动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来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或人与自我的角色关系。主体索求身份认同的共同关注都在于满足“我/他是谁”“我/他来自哪里”“我/他要到哪里去”这一意识需求。[5]55
身份认同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主体在熟悉的环境中,往往和所处社会群体中的成员一样具有一致的价值观,身份认同的焦虑常处于隐在的状态。当主体周围环境改变,身处陌生化的景观、思想之中,导致主体的不自由、不完善或不自信,这时身份认同危机产生,认同问题处于显在化位置,主体需要在异质文化和价值观中寻求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获取源自内心的信心和力量。安徒生童话创作所处的19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上新发明和新创造带来的奇异和陌生化、科技发展带来的城乡碰撞、科技进步带来的新旧时代思想观念的冲击不仅让主体生存的客观环境发生巨变,也让主体内心产生主动探寻自我在社会(群体)中位置和地位变化的认同需求和各种可能突围的途径。《曾祖父》中,新时代科学技术发明是促使曾祖父不断进行自我身份认同的外在推动因素。复古派曾祖父在怀疑—动摇—相信—欣赏的身份追认过程中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曾祖父从旧时代人们和现代人的对比开始发问,自嘲自己作为旧时代的人,在新时代里站不稳脚,表达对于自我身份的不自信。曾孙子以新时代的例证进行说服,曾祖父开始感叹科技的神奇是时代的一种恩赐,是人类的幸福。最后曾孙子和孙媳妇的海船遇难,火箭带着一根绳子越过汹涌的波涛解救了船上所有人,曾祖父彻底欣赏并祝福新的时代。可见,科技发明彻底颠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让新旧交替中的人类处于陌生化的社会环境之中,迷失了自我身份,但人类可以利用科技的力量和自然和谐共处。曾祖父就在来自科技力量的肯定性体验之下,重拾自信,获得新时代身份认同感。《树精》却是主体自我身份求证的一曲悲歌。科学技术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乡村和城市的剧烈碰撞带来自然美的祛魅和现代都市的复魅——这些都点燃了树精急剧膨胀的欲望,并使其渴望拥抱城市绚丽,获得身份认同。树精和乡下小女孩一样,不顾老牧师多次劝阻,在内心强烈的认同需求驱使下,挣脱现有乡村身份的桎梏,去迷人的城市寻找更加“美好”的全新自我。但脱离社会群体成员的共有认同框架,固执地追求个性化的自我身份认同,现实的主体性和理想的主体性终究无法达成一致和融合,造成身份认同的幻灭。
安徒生科学想象童话中的主体身份认同方式承载的是巴赫金的独白—复调思想。《干爸爸的画册》是一篇散文式作品,在这个独白式的语篇中,只有作者的声音在叙述丹麦的过去和现在,叙述不同时代不同主体的身份认同。画册的第一页是关于哥本哈根用瓦斯灯代替老油灯的故事。油灯执行职务的最后一晚,和瓦斯灯一起站在街上,瓦斯比老油灯亮得多,油灯感觉自己处于次等的地位,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通常来说,身份认同作为主体的一种心理和随之相应的行动,往往是在和其他主体的交往和相互“较量”的关系中获得。但作者以老油灯的单声调独白,没有和瓦斯灯之间的抗衡和相互制约,而是以积极乐观、不卑不亢的心理,既对自己已做的工作、已完成的历史使命表示认同,也对替代自己的瓦斯灯表示欢迎。油灯明确知道“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的存在身份,通过对自身意义的自我反思默默从历史场域中隐退,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但多数时候,童话文本更是不同声音不同世界观交汇的空间和场所。不仅作者的声音蕴含其中,也都给予童话中每个个体充分表达话语的权利,多声调是复调的核心。《海蟒》就是一篇异质化、狂欢化的多声部作品。人类思想和智慧发明的海底电缆伸入海底,所有海底的合法居民在惊慌失措的混乱之后,开始了多方参与的多声部叩问。海底鱼类众多独立而又不相融合的声音与意识相互交织,彼此以平等的姿态互相交流、争论,构成群体间的众声喧哗,[6]通过“它是谁”“它来自哪里”“它要到哪里去”的追问和辨认,从对他者的审视中获得心理安全感和归属感,获得自我身份认同。
三、认知与想象:科技进步对儿童社会化的生态伦理关注
安徒生童话虽表面上是为孩子们讲故事,但实际也适合成年人阅读,是作者借助文本语言传递其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媒介。童话、民间故事、神话对儿童社会化产生“润物无声”的影响,是实施儿童社会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儿童社会化是指“儿童在特定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习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以及掌握相应的社会行为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7]一方面,儿童小说、经典童话“会通过叙事宣扬或强加某种社会政治态度给读者,同时也会反映作者有意或无意的观念和信仰”,因为“文本需要影响儿童的生活,并引导儿童的社会化”。[8]另一方面,儿童在聆听或阅读童话时对隐含其中的意识形态加以内化,对故事人物等产生认同。安徒生聚焦科学想象的童话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识,儿童在阅读童话的过程中顺从或反抗隐含其中的道德伦理准则,在自我观念和社会角色上成长为“社会人”。
第一,科技与自然生态伦理。敬畏自然是人类生态的一种古老情感。但是,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给人类生存的物质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不仅改变了自然生态面貌,也逐渐改变了人与自然间的生态伦理准则,人对自然的敬畏感逐渐消退,自然美祛魅,取而代之的人类理性的力量。但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人类都无法成为自然的主宰,打破自然生态伦理准则的科技进步,只会被自然奴役。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是相互支配和统治,而是相互依赖,和谐共存,在自然的循环能量中找到和回归自己的处所。在《冰姑娘》中,有以冰河皇后为代表的自然和以人类为代表的洛狄的力量较量。冰河皇后为代表的自然威力无比,她是生命的谋害者和毁坏者,也是冰河的强大统治者,她在人类面前表现的狰狞面目正是工业文明出现之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伦理折射。洛狄的母亲坠落山谷冰罅丧命、洛狄的叔父因雪山崩塌而死,当自然的极端环境无情地吞噬人的生命时,人类在自然面前束手无策。冰河皇后的傲慢和目空一切正是人类身处残酷自然中渺小和无力的伦理想象。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人类开始在山谷炸毁石头、铺地基和炸山洞,准备建铁路,随后火车头在新建的铁路上像一支箭似的行驶。科技的力量让人类开始在自然面前变得强大。冰河皇后依旧嘲笑以主人自居的人类,认为大自然的威力仍然在统治着一切。尽管洛狄的野性、勇气和胆量在和冰河较量的过程中多次取胜,但故事结尾以洛狄在结婚前夕被冰河皇后的冰吻夺去生命,回归大自然的怀抱而告终。源于自然又融于自然的生态循环方式应该暗合生态整体观的伦理规范。
第二,科技与社会生态伦理。童话故事以奇异的乌托邦替换性想象来传播话语的同时,也以其批判性的手段让我们洞悉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历史、实现更加公正的社会的目标。[9]科技革命加快社会发展,拓展时空观念认知,满足人们延伸和探索宇宙时间和空间广度的愿景。但是,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必然会让旧的社会秩序展现不足,旧的社会伦理秩序被打破和瓦解之际,新的社会伦理建立,随之给人类带来种种价值和信任危机,出现新的伦理混乱。安徒生科学想象童话描述社会现实,又以超现实的手法表达无限,具有社会生态伦理意识。《曾祖父》中,在新时代的一个小城市里,工业文明前整个城市都按照市政厅上面那个走得并不太准的大钟上的时间生活。跨国铁路建成后,人们必须开始知道准确的时间,不然就会发生撞车事件。所以市民现在都依照车站里一个日光定时的走得非常准确的钟来办事。另外,电报的发明和使用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相距迢迢的曾祖父和曾孙子能够让日子变成钟点、分钟和秒钟,能跨越时空的限制获得对方的即时消息。可见,科技不仅能改变固有的时间秩序,也能跨越空间限制,为正确有序的社会生活提供便捷,构建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更加和谐的社会伦理。但是,旧的社会秩序的打破和新的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新旧社会秩序交替之际,会引起新的伦理困惑。正如《曾祖父》中所反驳的,新时代的弱点在于现在的国家机构就像一座玻璃钟,它虽然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但是科技创造带来的社会生活直观化、机械化、同质化却让人产生价值迷茫和极度不自信。
第三,科技与精神生态伦理。我们不仅有客观外部自然物质生态,也有人的内部自然精神生态,亦即人的内心。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社会变革、让人类受益的同时,不仅让人的内部自然的完整性呈分裂状态,信仰崩溃、精神失落、伦理道德沦丧等精神生态问题接踵而至,也疏离了人际间的正常关系,给人带来隔阂、冷漠和痛苦。[10]人类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危机在不知不觉中迅速向精神世界蔓延,造成人的精神异化。人的内部自然的异化反过来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11]安徒生科学想象的童话中,人类思想借助科技的力量开始征服大地、征服海洋、征服时空、征服愚昧,但是精神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引发新的道德伦理危机。在《演木偶戏的人》中,演木偶戏的人希望他的木偶成为有生命、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演员,由他担任真正演员的导演。但是,科技的魔法棒将他的愿望实现后,他却变得焦头烂额,非常可怜,因为所有的木偶在获得生命后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各自的利益需求,他们之间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相互争执。可见,科技改变了原有的精神生态秩序,让人的愿望更加容易实现的同时也加剧人的更多欲望的膨胀,如何调节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生态伦理是科技文明不断发展之下的共同关注。在《柳树下的梦》《依卜和小克丽斯汀》和《单身汉的睡帽》这三个故事中,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碰撞之下,女主人公都因进入城市的繁华而内部自然生态异化,身处乡村文明中的男主人公却都对异化的情感做出了善和爱的道德伦理回应。
布斯提出,文学文本中都有作者的存在,亦即从总体上控制诱导读者的“隐含作者”,但是伊瑟同样认为,文学文本阅读也是读者一种主动建构和认同的过程,它由外在的历史或作者现实而决定。[12]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切入分析了安徒生科技元素童话作品的意识形态、价值认同和对儿童社会化的生态伦理关注。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分析安徒生童话作品中蕴含的科技观和生态观对认识和理解当今科技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注释:
本文的作品均以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童话全集》(全套4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