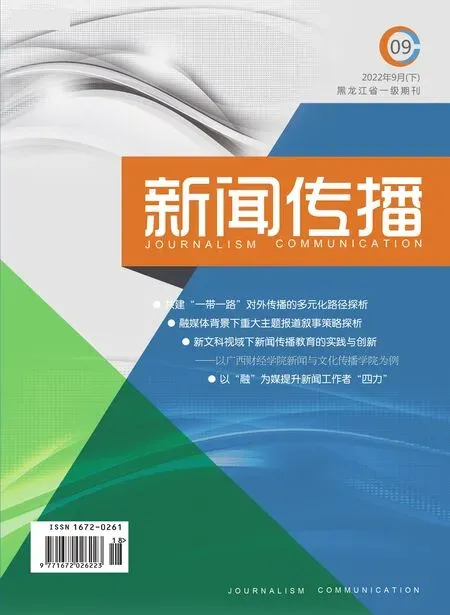“我和我的”系列主旋律电影的传播主题分析
徐维康
(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 730020)
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带有政治经济传播学属性的内容电影类型,在过往的10年间受到制作方和受众的双重聚焦。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就崭露头角,经过漫长的发展和革新,主旋律电影的表现方式和内容叙事也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迎合受众和现实题材。立足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和新冠疫情的侵扰,主旋律电影更要发挥鼓舞受众的作用,向受众传递中国精神、中国主题、中国力量,用本土内容作为创作出发点和驱动力源泉,采取积极有效的传播方式进行影响力推广和受众精神认知,扩大主旋律电影的主题教化作用和道德德育作用[1]。
一、《我和我的祖国》陈述群——爱国主义传播主题
《我和我的祖国》全影片一共包含七幕不同的人物剧情,通过在历史时间序列上的顺序讲述进行互相构建,完成对祖国叙事的表象。剧中第一幕《前夜》讲述的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负责国旗升降仪式的林治远对升旗的这一重大任务的呕心沥血付出。剧中的国旗形象就是国家形象的代表,升旗仪式是对国内人民期盼建国的回应,也是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上的重塑。传播主题的叙事上以群众的热爱贡献为驱动,同时在多种活动的人员参与上也形成了无形的耦合条件限制,以国旗顺利升旗为叙事目的,将对受众的爱国传播主题于升旗矛盾中得以解决,剧情对升旗仪式的顺利推进也拓展引发万千在建国活动中志愿付出的建设者的叙事共鸣场域,使得受众在传播被动层级上也能产生情感互动。
第二幕《相遇》的叙事对象是1963年10月一个名为高远的核研究员,为核事业牺牲自我和爱情。叙事情感传播上也是通过电影对受众传递现实事实来唤醒认知沉寂历史和现实映射,其中叙事视点对小人物的生命奉献、爱情取舍、声誉满损等角度和国家事业的贯穿表现来映照其中被隐姓埋名但甘之如饴的爱国主题。与上述叙事行为表达方式类似的第三幕《夺冠》,在这个叙事场景中导演将镜头对象对准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小学生,以小学生的行动讲述责任和对国家的支撑,从宣传主题的落脚点看就是在国家主题中宣传未来接班人的传承刚毅和对外的责任过渡。
第四幕《回归》将时间序列划归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时刻,通过对修表师傅对手表的修复和中英谈判的零和博弈来校准中国领土的时间回归,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为国家分裂历史的发展趋势进行校正回归,是国家形象的再度刷新和国民认同的现实支撑。其主题以香港回归为主线,以中英博弈和港民期盼为拓展,充分展示回归的现实必要性和民心所归。
第五幕《北京你好》的叙事焦点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出租车司机张北京在面临家庭信任和同年汶川地震造就的人际援助困境之时,果断选择对弱势群体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援助,爱国叙事传播主题聚焦在国人对国人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人际关系帮助中,展示国家内部强社会认同的深文奥义。第六幕《白昼流星》基层干部通过对神舟十一号传诵故事的解读实现对年轻藏民兄弟俩的人生信条重塑。一方面叙事方式上以道德信任来完成人性的救赎和国家基层工作人员形象的展现,另一方面人物构型上是加强爱国建设话语的陈述如“站起来说”等台词的多种意指:强国需立人、立人需自强、自强需自立,以对自我的积极重塑唤醒对爱国的自发共情。第七幕《护航》在叙事范畴上进行时间和空间限制,时间限制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式之时,空间限制在剧中女主人公吕潇然所在的空天飞行表演场地和人员圈定,双重时空限制让主人公退居幕后来做保障飞行任务的后勤,爱国主题的凸显以个人工作属性与国家形象任务之间的取舍得以托出,是一种利益小我性质的“强国报国有我”间接情怀。
七幕剧情在不同的领域各自展现小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潜在的叙事国家主题,主题倾向是小人物间的爱国主题的话语运作,多个叙事内容的话语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被累进主题渲染,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国家形象认同和政治认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内核注入新的驱动力,同时在西方解构主义文艺思潮和文化冲击下,爱国主题的电影宣发可以有效地抵御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占据等问题。
二、《我和我的家乡》陈述群——集体共性传播主题
第一幕《北京好人》的叙事对象延续前一部剧情中的张北京角色,叙事背景的矛头直指社保改革中农村医保认知与医疗体系庞杂之间的对立。在叙事特色上具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性批判,最终落脚于国家基层村民自治体系中的村委会得以普及国家的相关利民政策,从侧面验证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在该篇章中叙事策略就是从内聚焦视角出发以小人物的无奈来凸显集体(国家基层村委)的力量,迎合最广大的乡村受众集体,以一种更亲民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挖掘最符合群众利益的真实情感共鸣,与观众达到现实意义上的情感共通、文化共融[2]。
第二幕《天上掉下个UFO》叙事内容围绕一则关于贵州黔南州阿福村UFO新闻事件展开。该篇章的叙事线索为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当地村委通过制造网络热点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提振当地乡村的经济,映照出中国基层村集体设法推动乡村振兴、盘活乡村经济的各种方法的微缩样景。后面展现利用村民发明的无人机推进物流产业的发展也是昭明乡村振兴中科技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振兴的方法内涵。
第三幕《最后一课》是在国外大学教学的范教授因为记忆认知的问题回到国内自己支教过的乡村寻回记忆,但是原来的乡村已经变了模样,根据当地特色发展特色乡村——迎合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当地的年轻人为了回馈范老师当年的无私奉献通过房屋复古改造帮助范老师寻回记忆。突出当地受惠集体的集体责任和集体关怀。后面范老师重走乡村老路也唤醒了相关记忆,记忆回转过程中历史与现实重叠闪回,显示了现实乡村生活的历史发展历程与改变的对比,也验证了当年教授的乡村学生也已经成为现在乡村的改变者,老师改变了学生,学生成长后改变了家乡,叙事的主题明显化即为集体叙事中传承与发展的力量[3]。
乡村振兴战略在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建成小康社会从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推行乡村人才振兴,乡村人才是建设乡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4]。第四幕《回乡之路》和第五幕《神笔马亮》讲述的都是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对集体的自我奉献付出和对自我利益追求的省欲去奢。两个单元相同的叙事情节都趋于个人能力强效后回到乡村回报集体,引领集体意识的统一来重点解决乡村发展阻塞问题,运用防风固沙改善环境、因地制宜引入经济作物、撮要删繁主抓农产品宣传和乡村环境翻然改进等方法构建和谐发展的良性集体经济和乡村生态。这一叙事章节向受众传播的主题是对乡村振兴人才工作的肯定,还呼吁更多有志青年投身到基层集体中帮助广大村民改善乡村生态经济环境,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集体经济矛盾背景之下,着重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现集体经济发展的平衡和社会再分配的乡村改革。
《我和我的家乡》以家乡为叙事主题展开陈述,在视听话语的表象上专注为集体话语的叙事,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相价值赋予。在受众传播角度,导演对单元剧幕起承转合的转场之间更多表现普通人的群像,验证表达传播主题中的平民化的范式以及对人物范型在剧中文本叙事场中不断地被构建、丰富与完善。
三、《我和我的父辈》陈述群——道德传承传播主题
《我和我的父辈》陈述群中的前两个叙事单元的传播主题都是在牺牲奉献道德话语范畴中得以表现。前者《乘风》是抗战时期子辈继承父辈的道德意志为人民所牺牲但在人民的意志中存活,完成前中后剧情一以贯之“舍小我而利他者”和“身虽死,名可垂于竹帛也”是奉献道德的具体话语实践和陈述表象,是革命意志和传承奉献道德的意象融合;后者《诗》记录的是1969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三级发动机研制基地,一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和抚养父亲都为人造卫星事业而牺牲自我。但是他们的精神意志被孩子施天诺所继承发展并成为未来航天事业中的航天员。“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而你,我的孩子,是让平凡的我们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视听语言对叙事文本的旁白设置讲述了无数航天工作人员将自己的一生化作笔墨并书写在中国民族复兴史的纸张上,成就一篇篇为人民所乐道的“诗”的同时将他们的奋斗精神道德传承于下一代,使得航天精神代代相传。正如张红武学者所言:剧作在把个人追求、家庭情感、国家情怀、民族大义熔于一炉的叙事主题中,一直着眼于个体叙事,极力避免宏大叙事对个体情感和命运的“忽视”[5]。
法国著名史学家马克·费侯在其著作《电影与历史》中指出:“电影与历史两者间有许多产生交集的概率:例如,它们可以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交会;也可以在扭转未来局势,或造成社会变迁的那一瞬间彼此结合,在这类重要的时刻里,电影便介入历史[6]。第三幕《鸭先知》取自“春江水暖鸭先知”。叙事内容为1978年上海的一位父亲赵平洋改革开放这一春江水中的游鸭,身处其中并且迎合国家政策趋势,并不断向下一代传递对于国家政策的支持,这也就与国家形成共存互渗的关系。剧中旁白“神奇的不是他,而是每一个人”意指参与过改革开放的每一个人;2018年,赵平洋全家在上海中心大厦遥望当年的老房子,其下一代也继承了父辈对国家政策的认同与实践从而也实现人生的跃迁。在这个叙事段落中,影像形式上传递子辈对父辈的关于认知方法论经验的认可,价值趋向上是对国家政策实践和国家预判的认可,叙事主题上是改革开放经济提振背景下民生改善带来的对国家发展的“信”之道德内蕴。
第四幕《少年行》是科幻虚构形式的叙事内容,讲述的是来自2050年的机器人帮助小学生在儿童科技设计大赛上获得科技创新自信,并以父爱的补位去支撑孩子对未来科技探索的决心。剧情的台词独白“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很多次失败,五千次的失败才造就出伟大的产品”,明喻两个一百年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历经多次挫折与失败,才能实现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复兴产品”,同时借助剧情对孩子寄予的厚望也显现时代的接力棒需要一代代的传承,需要对物质的改造能力和对精神的道德承载能力的统御。本幕剧叙事后期机器人在面对本我和超我的道德困境矛盾时表现出超我的现实超脱选择,叙事表现为从人工智能到人性智能,赋予人与物的道德获取和传承,标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人文道德传承的辩证发展观,对道德传承回归爱国和国家认同的互文表现继往开来。
结论
“我和我的”系列主旋律电影以三部影片连续地将传播叙事主题从爱国主义的国家形象主题聚焦到家乡共性的集体意识再微缩至父子辈道德传承主题,整合成三级不同层次、不同范畴的爱国奉献主旋律。剧中对于普通人的具体主题行为刻画贴合现代主旋律电影叙事发展趋势的“去中心化”从而转向对“多点聚焦”的叙事主题传播探索。剧中以多个陈述群潜在重复主题的方式进行情绪渲染,以达到量变影响质变的辩证传播效果论,同时以多领域多方向的小人物困境刻画更能在叙事策略层级上展现国家之困境的微缩展映。该系列的传播主题在较高的叙事维度上实现了众多普通人物群像的思想展现和荧幕中所构建的人物形象的共鸣,将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放大到国家层面、家乡建设情感放大到集体层面、民族复兴情感放大到道德传承层面进行展示。其众多典型人物的呈现超越了简单的自我意志和国家、集体、道德意志的冲突的传统套路,而是融入了个人情感和大众情感,通过个人情感与大众情感的汇聚,影片最终实现人物本我形象的超脱[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