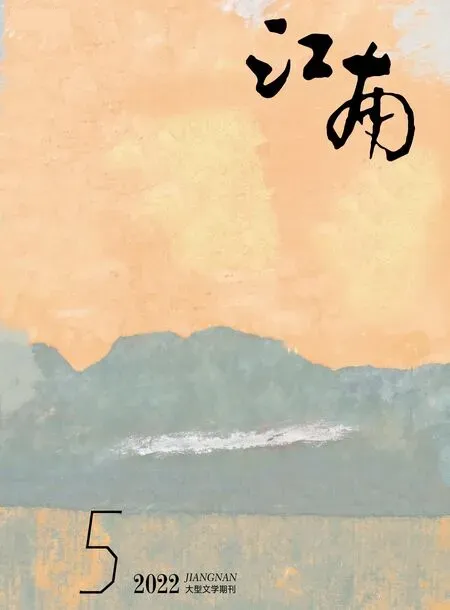石头记
□ 大 解
放生一块石头
2019年秋天,我们一家人在太行山的河滩里捡石头。那是河北邢台的一段河道,在乱石滚滚的河滩里,我们遇见了另外两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也在河滩里转悠,我就走了过去搭话,聊一阵才知道他们也是捡石头的,其中一个捡到了一块小石头,在手心里攥着,并且拍摄了视频发到网络上。我说我在停车的地方捡到了一块石头,大概有五六十斤重,是黑色的。我描述了那个石头的形状,其中一个人说,你捡到的那块石头是我放生的,是我以前捡的,现在我不喜欢了,就把它运回到它原来的地方,放生了。你若喜欢,就把它搬走吧。
听他说放生一块石头,我的心里忽悠一下,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立即对这个石友充满了敬意。在许多人看来,一块石头是没有生命的,喜欢的就捡回去,当做大自然的艺术品,摆放在家里,不喜欢的石头随便扔掉就是。而他,竟然把自己不喜欢的石头开车运回到原来的地方,完好地安放在地上,并且称之为放生,这就不同寻常了,他把石头视为了一个生命体,放了。
放生动物的,放生鱼鸟昆虫的,我都听说过,但是放生一块石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在河滩里捡石头,把需要带走的石头竖起来,或者放在高处便于发现的地方,以便临走时搬走。对于舍弃的石头,要好好地放在河滩里,轻拿轻放,绝不磕碰。一块石头,我不喜欢,说不定别人会喜欢,即使没有一个人喜欢,也没有毁坏它的理由。石头在河滩里,遵守着自然的秩序,你翻动它本来就是一种冒犯,扰乱了它的平静,如果再磕碰或暴力撞击,就不厚道了。石头本来在河滩里待得好好的,没有招谁惹谁,你没有理由扰乱或伤害它,即使你不喜欢它。
一块石头,不是为了你的喜欢而生长的,它们是山脉和岩壁的碎片,从山体上崩落下来后经过亿万年的滚动摩擦和河水冲刷,才变成现在的样子。在人类出现以前很久,石头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肯定的是,等到人类都灭绝了,石头还会存在,并且山脉和岩壁还会不断地隆起和崩塌,生出新的石头。在时间的长河里,大石头会变小,小石头会变成沙子和泥土,泥土也可能重新变成石头。人类选取石头,是按照人的审美原则在自然中挑选艺术品,而一只黑猩猩选取石头,可能仅仅是用石头砸开一个果核。石头的生死和循环,不是为了讨好人类,而是服从自然的秩序。
那天,我们与放生石头的人在河滩里偶遇,聊了多时,我们之间仿佛是前世的熟人,说话非常投机,随后各自散开,继续在河滩里捡石头,后来我们没有再见过面。那天临走时,我把他放生的石头搬到车里,运回了家,收藏至今。我在想,今后,如果我不喜欢的石头,我也要放生,把它们送回到河滩里,让它们回归大自然,重新接受风吹日晒,接受自然的塑造和进化。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个放生石头的人,一定是个善人,他的行为教育了我,让我认识到,一个人不但要尊重生命,也要敬畏天地万物,尊重昆虫走兽、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那么,一块被人放生的石头,又被我请到了家里,使它再次离开河滩,成为我的藏品,我是不是犯了一个错误呢?我觉得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命数,也许它必定辗转多次,来到我的家里。很久以后,说不定它还会辗转到谁的家里,或者又回到河滩,一切都看机缘,一切都是造化,这就是它的命。
那次捡石头,我不仅得到了一块石头,更重要的是得到了教育。从那以后,我把石头视为有生命的东西,甚至把捡石头看成是一种猎石的过程。我经常去河滩里捕猎石头,寻觅它,捉住它,抱走它,但绝不伤害它。我猎捕到手的石头,带回家里,洗净,养起来,摆放在适当的位置。我家里养了好多石头,它们不吃不喝,不用浇水施肥,也不逃跑或乱窜,比养花草和小动物都省心。在家里石头是老实安生的,但在河滩里却并非如此,有好几次,我在河滩里发现了好石头,由于没有及时竖起来放在高处,结果没走多远就找不到了,后来反复找都找不到,好像石头逃跑了一样。所以,捕猎到的石头,最好放在高处或者在旁边做一个明显的记号,否则它即使不逃跑也可能隐身,让你在茫茫大河滩里苦苦寻找却视而不见。
我善待每一块石头,即使不喜欢它,也不伤害它。养石头,是一种修行,无论是捕猎或放生石头,都给我带来了慈悲和快乐。
石头记
在讲述石头之前,我首先要说的是,玩石头是闲人的游戏。
写此文,我设定了两种潜在的读者,一是不喜欢石头的人,当他们硬着头皮读过此文之后,或许会喜欢上石头,从此关注石头的特征和价值;另一些读者,我假设他们原来就是石头迷,我愿意跟他们分享我收藏石头的快乐。
在我眼里,大自然中的石头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石头,是自然中普遍的存在,它们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从未被人类认识、使用或赏识,它们遵循着自然的秩序,坦然地待在它们的所在之处,从未被打扰;还有一种石头被人类发现,在人的眼中具有某种审美价值和经济价值,那么,这些石头就有可能被人捡走或者挖取,成为人们珍爱的藏品,不管它们是不是真的值钱。
有些石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一块石头,在一些人的眼里可能一文不值,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却视若宝贝。审美的差异,个人的情趣,都会决定一块石头的价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石头的特殊造型、图案、质地、硬度、表面纹理、完整度等等,决定了石头的总体价值。假如一块石头的图案、造型、完整度都好,而质地又是羊脂白玉,那么它的价值肯定比同样图案造型完整度都好的质地为粗粝砂岩的石头要贵重很多。
我收藏石头,尽管也很挑剔,但我深知一块石头的形成是多么漫长和不易,因此我从不埋怨大自然的造化,我理解石头。我经常与朋友们一起去河滩里捡石头,对于不想带走的石头,翻动时都非常小心,绝不损坏或磕碰。我爱石头,也尊重石头,从不伤害石头,如同我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我没有理由去伤害一个与我无关的人。
在我看来,每一块石头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有些宽阔的大河滩,一眼望不到边,其间卵石无数,总有一些被人选择并带走,成为收藏品。关于石头,我曾经写过一些相关的文章,这里引用其中的一篇,就算是偷懒吧:
“在自然艺术中,最能体现减法雕塑的东西莫过于石头。尤其是河滩里的那些卵石,经过上亿年的冲刷、摩擦和风化,表面上多余的东西都被淘汰掉了,剩下的部分仍然处在不断的减缩之中。自然法则具有消磨和耗散的性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摧毁。万物遵循着自然的规律,把生长性交给那些速朽的草木和生灵,而让石头来抵挡腐朽,体现生命的意志。但石头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万物最终都要化为泥土。因此也可以说,任何事物都处在临时聚合物的离散过程之中,好像一开始就是为了解体和粉碎。
“相对于人类,石头是持久的。一块石头的生成和死亡过程可能需要几亿年的时间,在这期间,自然作为塑造者对它们进行了不懈的削减,其创作过程既不刻意也不疏忽,每一块石头都获得了自己的形体。自然创作没有原意,只有过程和结果。人类所喜欢的石头,是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在自然中寻找对应物,并赋予其人文含量,并因此而体现出价值。这些,都是人类强加给它们的,作为石头本身,并不会因此而有结构和元素性质的改变。
“根据人类的艺术观和价值观,在石头中寻找艺术品,确实是一种审美行为。有些石头的质地和造型符合了我们的审美需求,给人以美的享受。当我们遇到那些简单到最佳状态的石头,你就无法不佩服自然的创造力。我相信石头是有生命的东西,并在人们的审视中获得了灵魂,与人进行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我把石头当作自然雕塑的艺术品,比之于人类的作品,更朴素、简洁、大胆,也更浑然天成,不可重复。因此,我尊重石头胜过尊重人类的制品。毕竟它们是天造之物,每一块石头都历时数百万年、数千万年甚至数十亿年,每一块都是唯一的、绝对的。大自然从不创造相同的作品。你所见到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孤品。
“在一个以标准化和机械化批量生产的时代,完全相同的东西已经成为商品市场的主角,而且正在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时间仿佛也是同谋,以适应这个疯狂运转的时代。在这种以复制为能事的人类活动中,石头依然保持着原始的惰性,以慢和沉来抵消人类的浮躁。它们慢慢地变化,慢慢地衰老,慢慢地成为泥土。石头有足够的耐力,等待下一次创造、凝固和循环。而在这变化过程中,上帝之手一再地雕塑它们,像减负一样卸掉它们多余的部分,成就自然的艺术。而那些从石头上脱落下来的尘土,将作为自然的元素沉淀下来,成为埋葬我们的东西。”
以上带引号的这些文字写于2006年11月7日,那时,我收藏石头已经有十年之久,应该说对石头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但是现在回头看,那时候讨论石头时还是带了很强的文气,像是一块玉石虽然经历了风化,但老气尚显不足。
说到老气,可以说每一块石头都是寿星,都有着漫长的进化史,但是并不是每一块石头都会露出老气。有些石头在河道里一直经历着滚动和摩擦,表皮被不断磨损,无法形成皮质,而有些石头处于稳定的河床里,也许几千年都不曾移动过,一直处于风吹日晒之中,渐渐地在石头表层形成了深厚光滑的石皮,看上去老气横秋,一身的沧桑感。由于处境不同,石头的皮色也不同,比如彩陶石、沙漠漆、戈壁石等等,都有一层老皮。还有一种石头,一直在深水里,被河水浸泡和冲刷,形成了一种水冲的老皮,比如大化石就是如此。大化石产自广西大化县境内的河道里,皮色厚重,富丽堂皇,形状大多沉稳大气,是雅石收藏的上品。
并不是所有的石头都有幸泡在水里,戈壁石就一直处于干燥少雨的戈壁滩,常年被风吹日晒,年深日久在石头表面形成了厚重的石皮。前些年,有人在新疆哈密的戈壁滩上发现了一种坚硬的泥石,多为片状和块状,见棱见角,浑身布满风沙吹出的波纹,表面光滑油润,仿佛上面涂抹了一层油漆。哈密泥石非常坚硬,硬度达到7度上下,两块薄片石头相互敲打,会发出清脆的金属音,宛如乐器。此外,彩陶石、黄蜡石中的细蜡石、三江彩卵、和田玉中的籽料和戈壁料,也都因质地细腻而呈现出不同的皮色。
我收藏的石头,有几块老皮石,但更多的是造型石和图案石。造型石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石头具备了某种象形,或者什么也不像,但是非常憨厚淳朴,具有禅意,看起来舒服,摸起来光滑,都可收藏。图案石主要以纹理取胜,质地、象形,都是参考要素。人们的审美情趣不同,对于石头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高下之分。有一种说法是:喜欢就好。
喜欢石头的人是幸福的。幸福到什么程度呢?石友们的体会是非常喜欢、达到痴迷的程度,看上去就像个傻子。对于捡石头疯狂的发烧友,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如果你问他明天是去捡石头呢还是结婚呢,他的回答很大可能是:去捡石头吧,要不结婚的日子往后再推迟几天?对于他来说,媳妇早娶几天晚娶几天都是媳妇,跑不了,而捡石头不同,去晚了好石头有可能被人捡走。他放不下石头,好像河滩里有好石头在等着他,不去不行,非去不可,去晚了心里都不踏实。喜欢石头的人,那种痴迷和狂热,很难让人理解。
有那么一些年,我得到了几块不错的石头,我的老婆非常羡慕,因为她比我还迷恋石头,但一直没有什么像样的收获,因此对我有点羡慕嫉妒恨。没想到过了几年她运气大发,一连捡到好几块得意的石头,她一下子骄傲起来了,话里话外都有点蔑视我的意思,但是由于我的收获确实不如她,也只好忍受她的傲慢和奚落。人世是公平的,运气不会只落在一个人身上,风水轮流转,过了几年,我的运气来了,一连得到了好几块好石头,用我老婆的话说,你终于开张了。确实是,开张以后,我的心情大好,整天处于欣赏藏品的快乐中。我家有几块石头,每年都要给它们过生日,大吃大喝一顿,回忆当时捡到他们时的情景。石头的生日就是捡到它们的那一天。如果因为忙,错过了给石头过生日,过后一定要补上。我有一块石头像是一个貔貅,一百三十斤左右,是我们全家人的最爱。每当我们全家人一起出远门的时候,我老婆都要拍几下它的屁股,说,我们出去几天,你在家里不要乱跑。在我们的心里,它真的有可能乱跑,因为它确实像是一个憨厚的神兽趴在地上。
有时候,因为对石头的看法不同,也会有争执。比如我在太行山里捡到的一块石头,大约三十斤左右,像是一个大头鱼,但是颠倒过来看,石头上面的纹理像是三条河流在交汇,我喜欢这种江河汇流的气势和旋流,就给它取名为三江汇流,而我的老婆坚持认为它是一个大胖鱼。她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把石头倒过来摆放,看她的大胖鱼,我回家后发现她动了石头,又重新摆放,看三江汇流。她看见我重新摆放石头也不反对,过几天我一看,她又给颠倒过来了,又成了大胖鱼。她喜欢这样,你说我能怎么办?她喜欢就好。
快乐是无价的,谁也不知道快乐多少钱一斤。石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石家庄有一个捡石头的小群体,都是好友,经常一起相约去捡石头。从1996年开始,我们利用节假日去山里,几乎走遍了八百里太行山的多数河道,即使捡不到石头,也锻炼了身体,得到了出行的快乐。走遍了太行山西部的河道以后,有那么一些年,我们都老实了,因为临近几百里内的河道都去过了,确实是无处可去了。这时,我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小石头上,迷恋上了玉石。玉也是石头,与其他石头一样,玉器也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我的枕头底下总有玉,睡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玉,醒来就赏玉,你说是什么心情?人,只要真心喜欢一样东西,这件东西就会给你带来快乐。我估计迷信就是如此吧,精神变成物质以后,就会给人带来愉悦和力量。
说到玉器,我有几块风化极好的和田玉黑青戈壁料,产地是新疆哈密雅满苏戈壁滩,也称老迪砍戈壁料,那里有铁矿,铁元素进入了玉质内部,形成了红色和黑色的沁皮。这种戈壁料裸露在地表,经过无数年的风吹日晒,被岁月风化的表皮波纹显得格外沧桑,同时也更加坚硬和光滑,由内而外透出一种熟透的老气,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压手感强,质感沉稳而厚重。这种戈壁料的硬度接近7度,比和田玉籽料的硬度大半度左右,仅低于翡翠。
既然说到了和田玉,我就先说说我对和田玉的粗浅认识。这里需要声明一下,我不是玉器专家,我只是从石头的角度说说和田玉,不妥之处接受明白人的指正和批评。
和田玉的主要成分为透闪石,产状有多种状态。一是山料,开采于矿脉,主要分布在昆仑山脉沿线,西起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向东一直延伸到喀什、叶城、泽普、和田、且末,甚至延伸到阿尔金山乃至哈密戈壁滩腹地,断断续续两千公里内,都有和田玉矿脉。昆仑山脉向东延伸到达祁连山脉,也有和田玉矿脉,产于青海的和田玉,人称青海玉,也叫昆仑玉,都属于和田玉。二是山流水,也叫坡积料,分布也非常广泛,是透闪石矿脉崩落后散落在河床或地表上的碎块,由于时间较短,玉石表面的棱角虽然弱化了,但与光滑圆润的籽料还有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距离。这种山流水料适合于雕刻,不适合把玩,人称做料,就是可以加工做活的材料。三是河床里的籽料,籽料指的是河床里滚动磨圆的玉石,是最好的和田玉,价值也最高。四是戈壁滩地表上散落的戈壁料,这里要说明一下,戈壁料是和田玉,是透闪石玉,还有一种叫做戈壁玉的石头,它的名字里虽然带有一个玉字,但戈壁玉不是玉,而是一种好看的石英石。透闪石的质地是透明的纤维交织状或毛毯状结构,往深了说,透闪石是酸性大理岩在一定的压强和温度下形成的岩石,而石英石的内部结构是颗粒状,虽然石英石也有颗粒极其细小甚至达到胶状体的质地,但它仍然是石英石,其温润感和抗压强度与透闪石有很大的差别。在石头家族里,和田玉的抗压强度最大,油性也最好,看上去温润,仿佛一块粘糕,咬一口都会粘牙,而实际上它的硬度达到6-6.5度,非常坚硬,比铁还硬。铁的硬度是5度。
和田玉不仅产于昆仑山脉,也不是说仅限于新疆和田地区出产的玉才叫和田玉,广义和田玉是透闪石玉的统称,辽宁岫岩、青海、贵州、广西、俄罗斯、韩国,都有和田玉产出。辽宁岫岩的岫玉(蛇纹石)矿脉中夹杂着一些和田玉(透闪石)矿脉,河道里产出的河磨玉和黄白老玉,比如析木河磨玉,颜色以绿色为主,细度可以超过新疆塔什库尔干的墨玉和黑青,比青海产的一级细的青玉还要老熟和细腻。由于产地不同,和田玉的质地也有明显区分。新疆的和田玉温润细糯,内蕴深厚,呈现油脂光泽;俄罗斯玉颜色略显干白(黑皮料例外);青海玉明显水透,且内部水线偏多(野牛沟料也有浑厚的);贵州罗甸玉普遍发闷,石性较强,透闪石含量不足;广西黑青也是石性较重,石质发脆,透光性弱;韩国玉颜色偏黄绿,内部结构常为粥样,看上去有塑料感。这里顺带说一句,新疆也产岫玉(蛇纹石玉),而且产量巨大。如今,人们把阳起石和直闪石也划入和田玉的范畴。还有一种和田玉的近亲,人们把它叫做艾德莱斯玉,其结构介于直闪石和透闪石之间,或者成分混杂。戈壁料中的艾德莱斯玉硬度达到7.5度,非常硬,但是棱角太锋利,不适合把玩也不适合雕刻。
从颜色上说,和田玉有白玉、青玉、墨玉、黄玉、碧玉、黄沁料等等,颜色细分可以达到几十种,其中白玉产量较少,因此白玉籽料(尤其是羊脂白玉)一直是人们喜爱的玉石。青玉偏多,青玉谱系较大,人们把直闪石结构的沙枣青也划归到和田玉的谱系中,由于直闪石的结构特征,玉石常有猫眼效应,因此也被人追捧。黄玉极少,新疆且末和若羌、辽宁岫岩、青海,都有黄色谱系的玉石产出,但由于这些玉石颜色普遍偏向黄绿,人们统称为黄口料,其中纯正的黄色非常少见,因而也极其珍贵。墨玉的产地有新疆塔什库尔干、和田墨玉河、辽宁岫岩、广西罗甸等地,从外表上说,人们有时把极度的黑青和黑碧玉也看成是墨玉,而纯正的墨玉,黑如凝脂,一点光也不透。还有一种黑色的玉,属于阳起石玉,硬度略低于透闪石,由于玉石中含铁超过2%而导致不透明,并且发脆,雕刻时容易崩口。
常言说,玉不琢不成器,有时我也雕玉,偶尔也雕石头。我的雕刻不讲雕工,只求神韵,常常是石头本身已经具备了某种形态的雏形,我在上面简单粗略地雕刻几刀,唤醒石头内部蕴藏的神韵,属于画龙点睛,雕多了就是伤害。
不是所有的石头都适合雕刻,石头还是天然的好。保留一块石头的原始状态,包括它的伤痕和缺陷,是对自然艺术品的尊重。大自然创造的石头,是自在之物,并不考虑人类的需求,但有时也恰好与人类文明相遇,仿佛是一种天然契合,体现出绝妙之处。比如汉江石中的金纹石,有时石头上出现的那些弯曲变幻的线条,竟然酷似汉语书法,形成传神的文字。我有一块汉江金纹石,上有“登聖”二字,颠倒过来看是“觀象”,石头背面也有几个字,读作“臨河洲”,颠倒过来读作“悲愁”。这些字都很准确,毫不牵强,就像是书法家写上去的。我把这些词组串起来,凑成一句诗:“登聖觀象臨河洲,悲愁。”有意思不?我还有一块文字石,上面形成的文字大约是:“江天顺水動”,颠倒过来看大约是:“顺水到天边”。我说的大约,是因为这一行字是书法中的狂草,非常潦草,只能猜个大概意思,而不能准确断定。我发给朋友们看,他们还有多种读法,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也许上帝创造这种石头,是供我们欣赏的,不是让我们辨认的,我们不必读懂,也不必有确切的读法。读不懂,或多种读法,其误读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石头的魅力和张力,让人玩味无穷,揣摩不已。
我收藏的石头主要来自于太行山区的河道里,卵石居多,山石很少。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石种:太行石,雪浪石,戈壁泥石,彩陶石,三江彩卵,唐河石,黄河石,汉江金纹石,藏瓷,乌江石,盘江石,大化石,沙漠漆,马牙石,毛绒石,金印石,黄蜡石,莱州竹叶石,戈壁料等等,石头大到三百斤,小到手心里,各有特色,我都喜欢。我家里没有灵璧石,凡是在盐酸中浸泡之后可以融化成泥的石头,我都不收藏,因为它们易于加工和速朽。
关于石头,我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有没有价值和意义,是我自己的选择,粗暴地说就是:我愿意。对此,我欢迎交流和指正,但不接受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