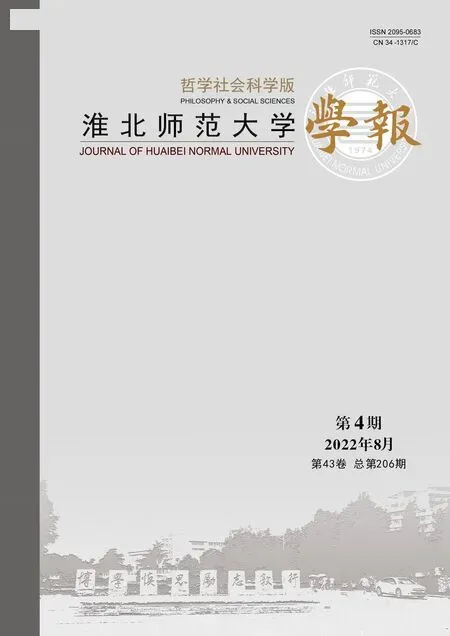新时代“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逻辑及其价值
——身体教育学的视角
秦立凯
(淮北师范大学 a.体育学院;b.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安徽 淮北 235000)
2018 年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9 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五育融合”成为新时代教育发展目标。劳动教育、体育教育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就劳动和体育的内在联系、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机制和路径等研究不足。已有研究揭示劳动和体育具有互补性质[1],劳动和体育是人类感性存在的两个基本面向[2],以五育融合为导向的体育课堂教学有必要融入劳动教育元素[3]。在身体理论成为多学科研究热点的背景下,从身体教育学的视角探索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理论基础和其价值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身体教育学的沦陷与劳动、体育教育之困
所谓身体教育学是指从身体的角度看,教育实践首先是一种身体的实践,是完成对身体的塑造和改变,将身体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并赋予更多可能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发的身体体验是知识之根、教育之根,而人的身体是体验和经验的源头和活水。相对于知识教育学而言,身体教育学更关注人整个身体的发展,强调使身体趋向强健,使人格趋向健全。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身体教育的必然取向[4]1。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身体教育学”一度沦陷,以致于有学者通过对脑科学等多学科分析后,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教育最大的失败是“身体的丢失”。①引自2019年4月22日,罗来武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座《人类行为的深层与表层结构:制度与文化分析的新理论——来自脑科学等多学科的一次大综合》。身体教育学的沉沦导致体育教育之困和劳动教育之困。
(一)体育教育之困
体育是身体教育的重要途径,著名教育哲学家雅斯贝斯说:“自我保存的冲动,作为生命力的一种形式,在体育运动中为自己找到了发挥场所;作为直接生命需要的一种遗迹,在训练中、在能力的全面性以及运动的灵巧性中得到满足。通过受意志控制的肉体活动,力量和勇气得到了保存,而且,追求同自然的接触的个人更接近了宇宙的基本力量。”[5]在雅斯贝斯看来,体育是按照游戏规则和人人必须服从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重要手段,它能从诸多生命元素中开发积极的健康生命,引发崇高的生命体验与生命冲动,保持身体力量和勇气,进而实现对自身的生命创造与人本逻辑的本位回归,更接近人的自由发展的本质。
但是当代社会崇文有余,尚武不足,体育教育面临困境。首先,教育实践中对体育教育的忽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课业负担重,体育氛围淡薄,体教分离,应试教育已经登峰造极,千军万马过高考独木桥的奇观没有随着大学扩招而转变;其次,受学科应试教育影响,提升体育中高考成绩、提高国家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等成为师生以及学校的“终极追求”,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体育锻炼习惯并未确立;最后,实践中“健康第一”作为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具有衍生性、同质化、自上而下导出和放大化的取向,同时,体育的文化本质及其人文价值在“健康第一”的优先考量下被弱化和抑制了[6]。体育教育之困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青少年身体素质持续下降,这一趋向至今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二)劳动教育之困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过程”[7]。新时代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凸显,劳动教育是培养青少年运用知识与技能获得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教育实践。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苏霍姆林斯基说:“劳动以外的教育和没有劳动的教育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8]但劳动教育却因种种原因而面临困境。
首先,表现为对劳动教育的忽视。刘良华指出中国教育对于“身体”的忽视与轻视不仅显示为“体育”的不发达,还体现在对“劳动教育”的不屑一顾[9]。据调查,高校开展劳动教育形式单一,占比不高,开展劳动教育的高校不足两成,其中进行系统化劳动教育设计的仅占11.5%,占全部高校的比例仅为1.9%[10]。中小学劳动教育也不容乐观,进入21世纪,由于劳动教育“被弱化、被软化、被淡化”,综合实践活动中的劳动与技术教育成为实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唯一途径[11]。其次,表现为对劳动价值观的忽视,劳动教育流于形式,当前大学毕业生中出现的“频繁跳槽”“随意毁约”“盲目追求高薪”等不良倾向,一定程度上和劳动价值观教育缺失有关。其三,对劳动教育的本质把握不准确,以致于劳动教育畸变为技艺学习,畸变为休闲娱乐,畸变为惩罚手段等[4]208。
二、身体教育学视域下的“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逻辑
从身体教育学的视角来看,“五育”中,劳动教育侧重于运用系统的科学知识与技能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品德和劳动价值观,解决“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看世界、改造世界”的问题;体育侧重身体发育和发展,解决“以怎样的身体状态看世界、改造世界”的问题。“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具有深厚的逻辑基础。
(一)身体理论:“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理论逻辑
身体是劳动和体育的载体,身体理论是当代哲学和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流派,是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理论基础。“劳动创造了人”论断揭示了劳动和身体的内在联系。劳动的逻辑起点是“身体”,这种身体并非一般意义的肉体存在,而是身心合一、与环境同构,有着自由体验的身体[12]。劳动是改造人的身体的重要手段,对于促进人的身心自由发展,实现人的本质具有决定性价值[13]。
体育是人类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的实践活动,著名体育学者胡小明、任海、张洪谭、程志理、方千华、马德浩等,对体育和身体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刻分析。他们一致认可体育的特征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以主客体同一为存在方式,以人文精神为价值导向的社会实践活动。近年来身体素养说成为体育学术研究热点,研究认为身体素养是统领当代体育改革和发展的理念[14],和青少年健全人格、学业成绩、运动习惯的养成等都有密切关系。
劳动和体育都以“身体”为逻辑起点,人的身体和本质力量是在劳动和历史的生成过程中创造的,身体理论构成劳动和体育协同育人的理论基础。
(二)游戏的人:“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本质逻辑
游戏活动是在固定时空下进行的、有规则的、自愿的、并且具有约束力的娱乐消遣,它属于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行为。劳动和体育都蕴含着人的游戏精神,是作为主体的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追求,是人的力量的本质体现。劳动具有解放人的本质力量,自由劳动本身就是最佳的自由教育,它并不仅仅是通过在教室接受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而获得的。体育则是由人类玩耍活动,逐步发展到游戏阶段,再经理性化发展而来的高级文化活动。体育运动是人类身体本能之中蕴涵的那些运动能力、行为方式、活动内容和能量发泄,是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体育运动就是游戏活动本身隐含的那些最为实在的、自然的文化和行为内容, 是游戏语境中的一个特殊概念,其中隐含着对于人类起源的解释[15]。换言之,体育科学的实质在于改善人体外在的形态结构、内在的道德和精神层面的价值范畴,在于通过体育实践的反思追问人格修养,洞察生存体验,感悟伦理教化,从历史实践和社会实践维度完成对身体的规训和改造,最终实现人自由充分之发展。
劳动和体育的本质皆有游戏属性,这是劳动和体育协同育人的本质逻辑。马克思曾对劳动异化进行深刻的批判,所谓劳动异化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不能享受劳动的乐趣,不能享受到应有的劳动成果,使得劳动作为具有超越性和本真性意蕴的游戏性质大大弱化[16]。当代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使得竞技体育异化现象也日趋严重,体育离游戏的属性越加遥远。
(三)社会转型:“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现实逻辑
当代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表现为全球化、城镇化、信息化等。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生产力变革促使人们劳动结构发生变革,进而对人身体形态产生深刻影响,最终可能会对人类身体素质产生一定消极影响。劳动、体育同为重要的身体教育范畴,在教育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二者的关系从未如此紧密。劳动本身具有一定健身效果,因为劳动者(体力劳动者)挥舞手臂、扬起铁锤、肩挑手提等劳动方式本身就包含了运动的基本形式。当代社会体力活动付出的主要形式是劳动和体育,劳动的形式日渐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化,体力劳动日益减少,那么,体育就成为体力付出的主要形式,体育在现代社会的刚需越来越大。所以,体力性劳动和体育活动就成为社会转型条件下保持身体健康,并发挥协同育人功能的重要手段和路径。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转型的另一表征,我国正践行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对标世界体育强国,不仅要重视体育教育,也要重视劳动教育。在奥运赛场,我们常见奥运冠军有着各异的职业背景,如2020 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飞碟多项冠军巴罗奇(澳大利亚)的职业是农业保护官员,柔道女子负78公斤级冠军阿武教子(日本)的职业是警官,赛艇女子单人双桨冠军斯托姆波罗斯基(德国)的职业是一名时装设计师,这种现象和西方国家重视劳动教育是分不开的。德国是公认的体育强国,但德国的“工匠精神”和完备的劳动教育也是卓有成效的。德国把劳动教育视为学生职业生活的重要准备和基础,早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就明确了以劳动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职业启蒙教育。德国的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实用性,以生活和职业需要为导向,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17]。美国在1898 年颁布《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对中小学生的职业能力做出具体要求,美国还通过具体的课程与活动实施职业启蒙教育。俄罗斯的劳动教育强调让学生掌握劳动知识、提升劳动能力,重视对学生劳动价值观的培养。2009年,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制定出台《俄罗斯公民精神道德发展与公民道德教育构想》,其中“基本国家价值观”就包括“劳动与创造”。
(四)劳卫制:“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历史逻辑
劳卫制是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历史逻辑。劳卫制是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制度的简称,1954年5月4日国家体委正式颁布《中国劳卫制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学校、部队和机关单位等掀起了持续接近6 年的劳卫制锻炼热潮。劳卫制对增强我国国民体质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学校体育产生巨大影响。
劳卫制反映了劳动和体育的基础地位,劳动不仅是重要的教育手段,也是重要的建设国家的重要途径,是体育锻炼的目的所在。劳动不仅是体育起源的关键因素,也对体育起到引导作用。俄罗斯2013 年重新实施新版劳卫制,对我国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防形势是复杂严峻的,重提劳卫制并借鉴其中好的做法,不仅有助于提升劳动和体育在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也有助于提升民族自信心,实现富国强兵。
三、身体教育学视域下“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的价值
从身体教学的视角审视,劳动和体育是身体教育学的重要内容,加强劳动和体育协同育人具有多元价值。
(一)助益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价值
当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体力活动不断减少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不仅包括体育锻炼时间少、体力活动不足,也包括日常生活中徒步行走等体力活动的减少和由于电器的广泛使用带来的家务劳动体力活动减少。据统计,1991-2009年的18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居民的体力活动量减少了45%,依照此趋势到2030 年时将下降51%。这种下降速度远超美国[18]。劳动转型是体力活动减少的根源,是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重要成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劳动匮乏带来的慵懒,影响到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加剧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劳动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劳而获的“主人”,一类是不得不劳动奔波的“奴隶”。历史的诡异在于“主人”往往走向堕落,“奴隶”却获得拯救,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奴隶”通过劳动增长了才干,强健了身体,主人却因慵懒身体衰败,失去“主人”地位。这正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它深刻揭示了人们在现代性社会进程中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未来的社会将出现两类城市人:第一类是城市末人,其基本特征是纵欲而慵懒;第二类是城市精英,其以持续的体育运动之激情保持对好逸恶劳的欲望之节制。体育运动乃是一种关乎勇气与激情的事业。城市精英自觉地将体育运动作为拯救身体的唯一方向,勇敢地将体育运动作为自己事业的一个基本项目。”[19]身体教育学视域下,重新强调劳动教育和体育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劳动与体育协同育人对遏制青少年体质下降具有积极意义。
(二)突破城乡学校体育发展瓶颈的价值
劳动教育的困境固然和应试教育环境下不被重视有关,但劳动教育形式单一,内容空洞等是重要原因所在。如一些学校将叠被铺床、刷碗刷筷、捡拾垃圾等作为劳动教育内容,其效果十分有限。但是把体育活动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中,效果就截然不同了。利用城乡融合国家战略推行之机,畅通城乡体育资源,创设城乡劳动教育融通课程,不仅能解决当前城市体育和农村体育发展的“死结”,还为劳动和体育协同发展提供新的形式和内容。
让数量众多的城市学生深入农村参加农业劳动,乡野环境能让孩子真切地感悟自然,感受到劳作的快乐。在劳动过程中,接触村民,了解民间疾苦,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培塑村民所具有的坚韧品格,学习包括传统体育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学校已经积累了劳动教育的良好形式,如2015 年10 月,北京市教委启动初中生学农教育实践活动,初中生走出教室,在田间地头体验劳动的艰辛与乐趣。至2018 年10 月,三个市级学农基地已开发了200多门接地气、接课本、接生活的学农课程,涉及农业与生产、生活、文化等多个领域。清华附中曾连续组织了八届高二年级学生到马连店、三堡、周口店、窦店村等参加农业劳动[20]。农业劳动是涉及全身的身体活动,具有较好的健身价值。劳动过程中,学生的体格得以锻炼、价值观得以培塑、人格得以完善,这正是劳动教育和体育教育的本质目的所在。任海指出:“正是在教育的意义上,农业劳动教育也可被视为体育在劳动教育语境中的应用,是身体素养和劳动素养教育的结合。”[21]
(三)实现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价值
体育生活化实质上是体育生活方式,是指体育活动行为融入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体育生活方式属于身体活动概念范畴,而身体活动是指:“任何由骨骼肌收缩引起的、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运动,日常的身体活动包括家务、体育运动、休闲活动。”[22]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主张“体育生活化”,即体育与劳动教育紧密联系。他认为体育的任务是激发潜藏在人身上的天赋的生理力量,没有各种体力的发展,劳动教育、劳动习惯、技能培养、训练就谈不上[23]。
体育自起源之日起,就和劳动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例如,原始的狩猎就是一种体育休闲和生产劳动的身体活动。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休闲社会,劳动和体育的交融互动仍然是休闲社会的重要内容,如寸土寸金的伦敦大都市,由市政府出面,在城市中心或市郊找一些荒废的公共空地,分割成一块块的土地,通过申请的方式交给那些没有自家院子,或自家院子很小的家庭耕种,每到周末,那些“都市农夫”都会在自家耕地劳作、聊天、休闲,小孩子可以参加劳动,或者在空地踢球、玩耍,一幅亦劳亦体的美好画卷。[24]
体育教育和劳动教育协同育人的最佳形式是体育生活化,体育激活人们积极参与生活中多种体力活动的动机,使其生活充满活力。体育本质上是一种高级的文化生活方式,现代社会发展的消极后果之一是现代性弊端凸显,人们身体遭遇健康危机,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提高人们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拓展生活空间,调节生活节奏,进而可以起到修复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功效。在此意义上说体育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对于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四)实现退役运动员人生理想的现实价值
竞技运动员退役安置困难和职业体育发展滞后是我国职业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截至2019 年,全国各级各类体校2037 所,在训青少年46 万余人。我国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 万人,每年退役人数约0.4万,如遇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年,退役运动员人数还会增加[25]。伴随高淘汰率,竞技运动员文化素质低,就业技能差,退役安置困难问题凸显,其中不乏优秀运动员,如体操冠军张尚武街头卖艺,马拉松冠军艾冬梅抛售奖牌,邹春兰做搓澡工等。
职业体育是重要的劳动门类,从社会角度看,职业是劳动者获得的社会角色,劳动者为社会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并获得相应的报酬。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75个中类、434个小类、1481个职业。职业体育发展能够为竞技体育人才提供广阔的创业就业空间,这将吸引大批优秀人才进入职业体育行业,从而有助于劳动和体育协同育人的实施。2018 年度体育产业统计数据显示,2016-2018 年全国体育产业法人单位数量由14.2 万个增长至23.8万个,2018年体育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为443.9万人[26]。就职业体育发展提供劳动就业岗位而言,我国和发达国家尚存在巨大差距。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职业体育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都较强,据统计,2011-2017年间,英国体育产业就业人数从49.2 万人增长到58.1 万人,增长18.3%,同期全国各经济部门就业人数平均增长9.3%;体育产业就业增长率在文化旅游和体育部门中仅次于创意产业、文化产业,远高于旅游业、电信业[27]。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不成熟和市场规模的制约直接影响到青少年及家长的劳动就业观,进而影响到后备竞技人才的培养,以及未来竞技人才进入体育市场就业。
所以,加强劳动和体育协同育人,大力发展职业体育和培育成熟完善的职业体育市场有助于解决退役运动员安置困难问题,有助于运动员人生理想的实现。
结语
生产劳动与体育活动是人类感性存在的两个基本面向,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活动方式,我国劳动教育和体育教育曾密切结合,对提升人民体质和建设国家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劳动教育和体育教育在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旁落,“身体”丢失,身体教育学沦陷。新时期哲学人文社科理论的“身体转向”,身体教育学复兴,为劳动和体育协同育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契机。以“身体”为逻辑起点的劳动教育和体育教育具有高度互补性,其本质皆是成长为自由充分发展的“游戏的人”。社会转型的现实和劳卫制的历史则昭示着二者协同育人的应然愿景。这启示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劳动和体育教育协同育人的力度,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解决的效果,培养更多的竞技后备人才;另一方面,以城乡体育资源畅通、体育生活化为契机,以职业体育充分发展促进劳动教育和体育协同育人的实效。新时代,“五育”中具有战略支撑地位的劳动教育和体育教育,是人类保持充沛的情感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必将是未来中国教育改革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