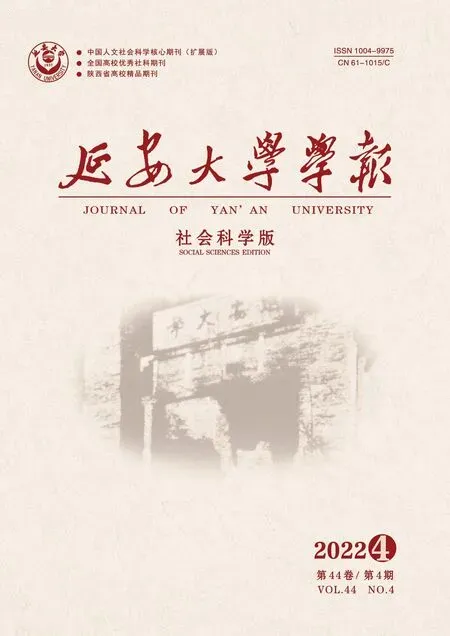时代体验与历史书写
——《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原因考析
白 玉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路遥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以下简称《惊》)刊载于《当代》1980年第3期,此前两年,他“接连投了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1]122路遥深感“年轻人发作品是很困难的”,《当代》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同意刊载《惊》,使路遥“第一次真正树立起信心”。[2]573-574现有资料对《惊》发表前后情况考察颇为简单,其背后隐藏的诸多文学话题被忽视。笔者以《惊》作写作缘起作为论述起点,考析秦兆阳同意刊发《惊》作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两个人在创作理念上高度契合,在呈现历史、认知历史、书写历史、思索历史的方式上有着共同的认知。
一、个人经历与历史认知
路遥的创作,无论是记录现实还是追忆过去,都带有鲜明的历史意识,他试图在讲述个人亲历的故事时,为历史寻找永恒的注解。秦兆阳在关于《惊》写作缘起的信件中,首先发现路遥创作中深沉的历史认知。
根据朱盛昌日记,1980年5月3日编辑刘茵收到路遥的一封信,信中主要阐释《惊》的创作缘由。路遥致信刘茵专谈写作缘起,是秦兆阳特意询问的。在刘茵推荐下,秦兆阳审阅《惊》,他“看后很赞赏”,认为“作品很独特”,“决定发表”,请刘茵同志“马上通知作者,并询问其创作缘由”。“创作缘由”是作者创作时的最初动因,也是编辑探究作家创作动机的最直接的方式,“首先弄清作者为何要写以及为何这样写,才能更准确把握作者的意图”,日后“提的修改意见也会更切合实际”。[3]140
路遥有着超越常人的领悟能力,同是《延河》编辑的闻频回忆,“1971年初,也就是路遥诗情正浓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歌词有什么特点、要求,我三言两语,作了最简明的回答。没过几天,他拿了几首歌词给我看,果然是歌词,而且都合乎要求,同时,构思和组词还不落俗套”。[4]可见,路遥创作善于“巧用功”“用巧功”,先了解创作原则,知晓创作标准,然后再勤思落笔,作品既合乎规范,又超拔脱俗。以此可以推想,路遥在阐释“创作缘起”时,也会格外谨慎,反复思量阐释的最佳途径,也会用到类似的“巧功”。
秦兆阳对文学的深沉思考多收录在《文学探路集》《集外集》《谈艺录》等文艺理论集中,其中有关于文学创作的宏观思考,比如现实主义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主观与客观、文学理想与现实问题、历史真实论等,另外还有一些微观的思考,他对细节描绘、主题凝练、情节结构、环境渲染、刻画人物、创作冲动等问题都有卓越别致的见解。虽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路遥曾深度剖析秦兆阳的创作理念,领悟其文学精神,经过吸收、转化、灵活运用到“写作缘起”书写中,但经过比较,笔者发现路遥在“写作缘起”中阐释的文学真实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家责任等与秦兆阳的文学创作观有某些相似之处。
秦兆阳阅读《惊》的“写作缘起”后,被路遥讲述的个人“真实”故事触动,认为“作者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来的”。[3]140一方面,他肯定路遥善从“真实”取材;另一方面,他看到路遥在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微妙关系上,所作出的突破。在小说中,马延雄是秦兆阳所钦佩的“经受过革命的锻炼、将先进的觉悟和思想意识,有机地融入理智、感情中,成为其生命中的第二天性”的英雄人物。[5]36马延雄的原型是时任延川县委书记张史杰。在路遥写给曹谷溪的信中,曾提及“文革”时自己与张史杰的历史渊源,并想请张史杰能够帮助办理弟弟王天乐招工之事。平时交往中,二人关系很微妙,“都掩饰自己,尽量都表现出一种在公众事务中应该高尚的面目”。[6]142在路遥闪烁的话语中,可以探视到张史杰“不纯粹”的一面,“他(张史杰)暗示我(路遥)要以他为模特儿塑造一个高大的县委书记形象”。[6]143路遥经过几番思量,最终决定创作这一命题之作。路遥塑造马延雄这一人物形象时,并未“把文学任务放置在狭窄而又简单的基点上”,“以自己的思想感情为唯一标准去衡量一切”,[5]7而是追求较长远的认识价值、道德意义、感情深度和美学价值,“从纵的发展和横的联系上摄取历史意义”。[5]17路遥提炼出蕴藏于人物原型(张史杰)现实生活中崇高的“真实”,洞察到其担任县委书记时处理日常政务时的睿智以及对当地人民朴素的情感。由此可见,路遥在处理“真实”事件时,所拥有的宽阔的眼界与深远的思想。
秦兆阳和路遥是两代人,年龄相差33岁,都经历过历史创伤。1958年,秦兆阳因提出“干预生活”“写真实”等文艺观点,遭受批判,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作家出版社出版专辑批判《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他的精神极度痛苦,真像五雷轰顶,又像堕入深渊,睁着眼睛看着黑夜,看着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一夜未眠。”1959年,他被下放到广西柳州机械厂劳动,此后多在广西生活,长达十五年之久。尤其在“文革”初期,“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被视为“文艺黑线”的“黑八论”之一,“秦兆阳遭遇苦难更深重,挨斗、关押、勒索,受尽折磨”。[7]422“文革”结束以后,秦兆阳多次递交“申辩”和“请求”,直到1979年3月才恢复党籍,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得以正名。路遥初中毕业后,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因“文革”爆发,只能继续留乡闹革命,希望凭借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被错失。后又因参加“武斗”被指控,成为他背负一生的“污点”,后来参军、高考、参加工作,都因此而影响到政审。正像厚夫《路遥传》中所写:“这是他的‘原罪’,一有风吹草动,他的小辫就被人牢牢揪住。”[1]135“文革”时期,秦兆阳已到不惑之年,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已经成熟,抗击打能力要比年轻人略强。路遥经历“文革”遭遇时,刚刚初中毕业,一切飘摇未定,他要经受更多的心灵磨难,才能一次次在苦难中崛起,不被沉重现实击垮。
一个作家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关系,其实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博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岁月里,认识、思想都有差别。”[1]125路遥“怀着天真而又庄严的感情参加革命”,进入时代风暴眼中,成为“红四野”的“王军长”“县革委会副主任”,后被县军官小组立案调查,最后,他果断地抽身而去,疏离狂热与暴力,转身学习创作,投向美与善的书写中。在秦兆阳看来,如何理解“文革”历史事件可以体现作家时代责任意识。在文革结束之际,文坛一片呻吟,他在“伤痕”诉说中看到危机,他没有明确指出危机是什么,但他渴望从危机中走出来。他试图寻找另外的视角,发掘讲述“文革”历史新的可能性。秦兆阳初读小说《惊》,给予他的阅读感受是“新鲜”“独特”,[8]176阅览“写作缘起”之后,他进一步确定,这是一位作家对“文革”历史的自觉主动地思考。路遥“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向自我,向他者,向生活,发出自己成熟而又理性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态度、愿望和主张”,[9]这位主动积极“发话人”的文学精神中蕴涵着独特的声音。所以秦兆阳认为其作品“基调是高昂的”,[3]140他感受到路遥处理复杂历史的能力,赞赏其超越个人生存环境的局限,努力挖掘历史恒常精神的广阔文学意识。
文学青年路遥在《惊》“写作缘起”中阐释的文学观,暗自流露其对秦兆阳文学精神的追随,这或多或少沾染个人功利意识,却激发了路遥对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思考。《当代》1982年第3期刊载“《当代》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并发表获奖作家的话,路遥坦然地道出作为当代作家的艰难,“面临一个更加复杂而又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要“深刻而有力地反映我们时代面貌”,“首先得和我们的浅薄作斗争”,[10]以免落入“平凡庸俗的实在主义或狭隘的实用主义”。[5]266《惊》是路遥第一次“试笔”,之后他对现实的思虑日益深切,《人生》叩问当时“青年出路”这一“公共问题”,[11]在《平凡的世界》里,他“捕捉‘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历史诗意”。[12]《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中,他依然坚持认为作家“要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在伟大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2]91陕西作家陈忠实洞察到路遥有着“深刻的历史理性”思维,“不在意个人的有幸与不幸,得了或失了”,而是“挤在同代人们中间又高瞻于他们之上”,“热切关注着整个民族摆脱沉疴复兴悲壮的历史性变迁”,“向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揭示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青春男女的心灵的期待”,其文学世界包孕着“开阔的历史视野,深沉睿智穿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这是作为深刻作家路遥与平庸文人的最本质区别”。[13]8-9这也正是秦兆阳所发现的“广阔的”路遥。
二、由“小历史”讲述“大历史”
秦兆阳对“一幕”进行过全面阐述,“一幕”是作者面对“惊心动魄”的“巨大的事件”,所择取的“一两点有代表性的片段”。具有碎片性的“一幕”是作者创造“具有最突出、最有特征性和代表性的典型”。[5]53“一幕”可能是“一个人物、一个家庭、一个比较单纯的情节或事件”,但其具有“容纳生活内容和思想的含量”。[5]66这涉及作家如何处理历史信息的“无限”与“有限”的问题。“我们需要写伟大事件的面貌,写重大问题,反映一些复杂情况”,“作品容量是有限度的,所反映的生活真实也是有限度的”,“作品不能作无限制的要求,也不必要做无限制的要求”,[5]107而是要集中表现“生动的、有说服性和代表性”的“一幕”,[5]36这一幕可能只是碎片性的生活瞬间,却可以由此“形成事件纠葛”,建构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进一步“表现社会内在意义的个性,和社会根本意义的矛盾”,[5]39路遥从“一幕”性的历史瞬间开启“展开”的旅行,书写“惊心动魄”故事,体现其讲述大历史的能力,“使作品的内容向宽度和深度扩展”。[5]66
《惊》的文题是不是在秦兆阳的启发下修改而成的,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证。需要提及的是,编辑会根据创作内容修改文题,比如莫应丰的《将军吟》最早文题是《将军梦》,秦兆阳认为“名字太灰”,韦君宜建议改为《将军的沉思》,后来,秦兆阳又提议直接改为《沉思》,刊载时才最后决定使用《将军吟》这一文题。陈国凯的《代价》“题目改了两次”,作者的原题是《活着和死去的灵魂》,后改为《被保护下来的》,最后才改定为《代价》。[3]135-136据晓雷回忆,《惊》最初“似乎叫作《牺牲》”,主要表达两层意思,“表面写一位县委书记牺牲了”,实际深意不仅表明这位县委书记不幸,而且所谓的另一派也经受同样不幸。在晓雷看来,《牺牲》的立意有别于同时代人,路遥“不仅关照自我牺牲,还关注双方牺牲”。[14]虽然《牺牲》体现路遥创作时难得的“他者”意识,但是依稀流露出某种“伤痕”言说,暗示路遥也曾陷入时代流行的个人话语中。值得庆幸与欣慰的是,路遥摆脱“牺牲”的创伤语调,“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路遥深感“不管写什么样的生活,人的高尚的道德、美好的情操以及为各种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应该是作家关注的主要问题”。[2]573可见路遥对历史的深层思考,力求发掘其中蕴涵的永恒精神,延伸扩展作品的意义空间和内在价值。秦兆阳在给路遥的公开信——《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中,“惊心动魄”是其分析《惊》时所紧扣的关键词,他前后四次使用“惊心动魄”一词形容现实社会复杂万端,除此之外,他还使用“惊人”“动人心魄”“惊叹”等近义词形容时代的大矛盾大波动对作者内心情感产生的大激荡。路遥正是通过对“惊心动魄一幕”的叙述与铺展,表现出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正义与良知。
根据《秦兆阳年谱》,秦兆阳亲身经历过“武斗”,时间大约在1967年冬至1968年4月,但他不是参与者,而是逃避者,“为躲避武斗,从广西到北京,又到河北、湖北等地辗转避难”。[7]422在某种程度上,《惊》对“作家秦兆阳”有“唤醒”作用,“一个有丰富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作家,时常是看到了一点就触发了一个主题,或形成一个人物,或构成一个故事”,“是根据某一事象来作有根据的推此及彼,产生联想,这‘一点’对于他来说不是一点,而是把他贮藏在记忆里的东西唤起来了”。[5]53《惊心动魄的一幕》唤醒“作家秦兆阳”对“文革”的记忆。从1979到1981年,秦兆阳创作多篇小说沉思“文革”的历史,比如《女儿的信》《苏醒》《纪念》《回答》《最后五分钟》《在十字广场上》等,其中《苏醒》《最后五分钟》《在十字广场上》小说背景是1967、1968年的武斗事件。
从创作时间上看,《苏醒》与《惊心动魄的一幕》较为接近,写于1979年12月25日,说明秦兆阳与路遥几乎在相同时间,以同样方式,思考着同一问题。《最后五分钟》《在十字广场上》分别写于1981年前后、1981年夏,也就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之后。这几篇作品与《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着相似的构思与表达,比如紧扣“惊心动魄的一幕”设计情节,矛盾双方都是由两派青年构成,最后有一位“牺牲者”勇敢站出来化解矛盾,避免更多的伤亡等。秦兆阳多次使用相似构思,并非是简单地“复制”自己或者路遥的创作经验,而是因为他对瞬间性阐释历史方式的肯定与赞赏。
三部作品中,除《苏醒》刊于《人民文学》1981年6月日外,《最后五分钟》《在十字广场上》皆是未刊手稿。两部未刊载的小说并非是“未完成”作品,相较《苏醒》,后两篇小说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故事叙述、矛盾冲突等方面显得更为成熟,更能突显秦兆阳书写时的文字张力。为何后两篇小说没有公开发表呢?笔者揣测,那是因为秦兆阳在规避模式化、公式化的创作方式。在《文学探路集》中,《概念化公式化剖析》《再谈概念化公式化》《形象与感受》等多篇文章皆论及“概念化种种方面”,在他看来,很多写婚姻问题、工人农民生产活动的小说,“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取材结构”,都犯了“公式化一般化”的毛病,都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创作上的表现,为帮助正在成长中的作家摆脱这种“狭窄而又简单”的文学创作方式,他还特意提出种种突围路径。[5]7秦兆阳尊重文学,崇尚文学创新精神,相同的创作模式、取材方式可以作为平时练笔,一旦公开发表便不可重复别人、更不能重复自己,否则便陷入“文学制造”的“邪路”上。[5]33
上述小说共同阐释忠诚与承担的故事。“牺牲者”并未穷途末路,完全可以依靠自身能力,演绎反抗者或复仇者的传奇故事。《惊》中马延雄可以在人民的保护下,辗转求生;《苏醒》小说中主人公苏醒,身材高大,拥有一套祖传的武艺功夫;《最后五分钟》尚世雄也有绝地反击的时机与可能;《在十字广场上》中的青年人,在射击比赛中得过奖,枪法精准。但是他们却主动选择牺牲,换取更多人的生存,朴素地认为“死我一个比死你们很多人要好”。苏醒主动请求将自己捆起来,《最后五分钟》尚世雄从未想过向对方复仇,《在十字广场上》中的青年人最终倒在枪口之下。文章结尾是作者特意设定的“有意义的结尾”,“牺牲者”作为“说话者”“发言人”“规劝者”,躺在中央,所有的武斗者围绕着他,他拼尽最后力量,规劝每一个青年,放下青春躁动,放下立场、放下对抗,做一个开阔的人,珍视国家、珍视集体、珍视生命。一切都沉静下来,只有“牺牲者”用生命呼唤而出的声音在升腾,人们的情绪倾于平和,思维回归于理智,难以缓和的冲突局面得以回转,“牺牲者”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实现对他人的拯救。至此,小说叙事推向高潮,“牺牲者”英雄形象得以呈现,格调得以升华,故事的现实意义得以升腾。
三、寻找中国精神的代言
《惊》能够在《当代》发表,除上述秦兆阳与路遥文学精神的深层对话外,还与《当代》刊物倡导的历史责任感紧密相关。《当代》创刊于1979年6月。1979年8月秦兆阳主持《当代》编辑工作,他多次提及《当代》,编辑选稿也要有比较强烈的责任意识,关注形势,关注文艺界的动向,真正触到生活深处,艺术上要有创新,还要有较强的道德感。只有如此,刊载的作品才能“对时代负责,对人民负责”,“在历史上才能站住”。[3]142对于反映“文革”的作品,秦兆阳始终坚持“写打成右派或“文革”中受苦的东西不用”,作品可以“写真实”“表现苦难”,但不可“发泄气愤”,“不能老是哀叹、牢骚、呻吟、哭泣”。1981年前后,有的刊物回避刊发相关作品,但是,秦兆阳、孟伟哉主张“要无愧于《当代》,要有自己的主见”,“可以发,但要把好关”,这个“关”,就是关注文学的“启蒙”意义,作品要“给人以自信心、民族的自信心”。同时,在题材上“要广、深、新”,要超脱现实,不要影射,从人类历史出发,真正写出某种国民精神。[3]146-147
秦兆阳成长于延安时期,延安文艺汲取俄苏建塑社会主义新人的意义,提出“新的人民文艺”思想,作品“应该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成长的过程”。[15]从20世纪文学叙事脉络来看,马建雄应当属于“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谱系中的代表人物。50年代到70年代的“新人叙事”,虽内容各有侧重,但都共同阐释牺牲、责任、奉献、忠诚等时代精神。进入新时期,社会语境迁变,如何延续“新人叙事”是秦兆阳这一代文艺工作者亟须应对的问题,秦兆阳发现马建雄“人物形象对于中国的意义与价值”,是路遥寻找的中国“精神的代言”。[13]9
《惊》发表之后,在《当代》的推荐下,路遥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9—1980年《当代》文学奖(荣誉奖)”两大奖项。从周扬在颁奖现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文艺批评界呼吁作家要成为中国精神的传播者,成为“人民意愿的表达者”,要“有充分信心和魄力创造出最先进的文化,克服一些庸俗的、低级的趣味拒绝平庸作品,提高文学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从而“提高我们读者的识别力和鉴赏力,培养和提高人们健康的欣赏趣味和欣赏水平”。[16]628-629巴金作为评奖委员会主任委员,赞赏许多作品都是从“人民中间汲取来得热和光去温暖、照亮、鼓舞别人的心”,“都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崇高的心灵”。[16]634因此,无论是周扬还是巴金,他们都深切认识到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具有切实的精神价值,有助于“将普通民众锻造为新的‘历史主体’,以承担民族自立、国家重建的历史使命”。[17]
秦兆阳作为全国中篇小说奖(1977—1980年)评奖委员会十五名委员之一,他中肯地评价“这两年多以来受欢迎的作品,还是现实主义深入的,带血带肉的真实”作品。[8]1761981年6月在文学讲习所讲课时,他以《大墙下的白玉兰》《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作品为典型案例,“漫谈现实主义的‘深化’”问题,把“深化”高度概括为“作品要与时代大真实紧密结合”“表现最深刻的生活逻辑”“作品已经达到和应该达到但又尚未完全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等诸多方面。[5]303谌容、张一弓、王蒙、从维熙、冯骥才、蒋子龙、路遥等作家,践行的正是秦兆阳“现实主义深化论”这一文学理想,他们“内心深处保持健康的文学趣味以及健康的灵魂气质”,塑造的人物形象诠释国民精神,促使人们“追求社会出路和人生意义,追求人生和社会的真善美,体现伟大的境界”。[5]62
《惊》发表以后,秦兆阳继续鼓励路遥,希望他找寻到更开阔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代》刊物甘当平台,继续刊载路遥作品;二是秦兆阳以公开方式致信路遥,希望他进一步增强《惊》的艺术含量,传达更深厚的历史认知。
秦兆阳在审阅《惊》时,便提议“我们应该发表这个作品,而且要把这个作者好好树一树”,[3]140路遥作为重点培养的青年作者,秦兆阳对其寄予厚望。在《当代》创刊号的卷首,韦君宜所提出的编辑思想中,其中就有一条是“希望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每期都要有新作家的名字出现”,她认为“这才是文艺兴旺的现象”。[18]有些青年作家,并非《当代》杂志所推选,秦兆阳也会给予长期关注。比如创作《小镇上的将军》的陈世旭,在《十月》(1979年第3期)发表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之后沉寂两年,秦兆阳了解到这位作家“深知创作艰难”,又不跟随“文坛轻率之风”,于是,亲写一封短信,激励他继续创作。[19]秦兆阳把“刊物”视为“阵地”,常将领兵作战思维运用到《当代》编辑工作中,办刊物要“有计划、有意图、有步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培养作家上,秦兆阳同样具有战略眼光,“有阵地没有部队就不能作战”,编辑孟伟哉也强调,“要有意识地组织一支作者队伍”,不仅要“发现新作者”,更要“培养新作者”。具体的实践策略是“发现”之后“连发几个作品,这个人就推出来了”。[3]141《惊》之后,《当代》继续发力,1982年第5期发表路遥另一作品《在困难的日子里》。作品中,马建强在饥饿的岁月里,小心翼翼地呵护脆弱的自尊心,他坚韧、正直、善良、不畏困难,成为中国青年的精神代言。《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得1982年“《当代》文学奖”(中长篇小说奖),这不仅是对路遥创作的肯定,还是对作品中坚守人的尊严、恪守人的风度精神的致意。
《惊》没有收到预期良好的社会效应,对此秦兆阳一直自责当时“没有认识这个题材的更深的意义”,“没有给他提出更好的修改意见”。[8]176在《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中,他对《惊》进行更宏阔更深远的创作设计,“这是一首长篇叙事诗的题材,如果能够深化、扩展、别具匠心、充满热情去写,可以写成一首传之长久的诗作——尽管是用小说的形式写的”。[5]316这正呼应路遥在“写作缘起”中提及的《惊》修改设想,“这篇作品目前这个样子并不理想,缺陷和不足今后如有机会和条件,我想用较大一点的作品来反映这一段生活”。[2]573秦兆阳鼓励路遥能够凝聚历史目力,进一步拓展讲述历史的路径,“开掘、深化、提炼、扩展”,以中篇小说为基础,扩展成一部“更深沉、更宏大、更美妙”[5]317的长篇小说书写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为中国精神找寻更多的代言。
综上,路遥创作《惊》时,不仅继承延安文艺创作传统,还对历史、时代进行积极思考,突破个人时代体验的局限,在创作中呈现出开阔的文学气象。《惊》作由小见大艺术地、真实地讲述历史的方法,唤醒“作家秦兆阳”书写历史的激情。秦兆阳捕捉到路遥作品中深沉而又高昂的叙述基调,肯定其具有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广阔的历史视野、深沉的历史情怀,并在路遥创作道路关键之处,给予他无私地鼓励与帮助。可以说,秦兆阳是路遥文学创作精神的发现者,路遥是秦兆阳文学创作理论的践行者,他们对中国文学创作精神有着共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