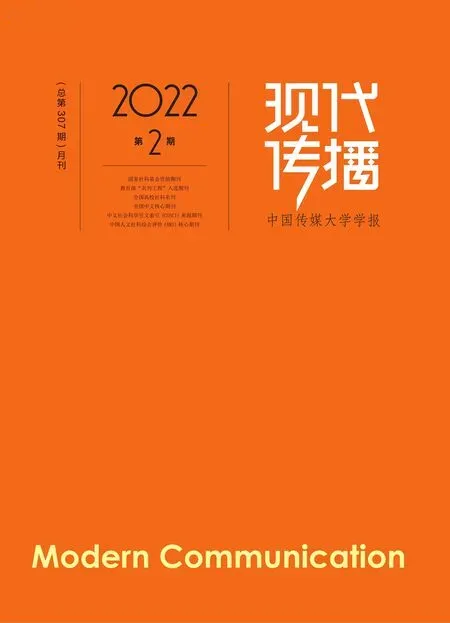作为“政治腹语”的社交机器人:角色的两面性及其超越
郭小安 赵海明
以大数据算法和深度学习技术为支撑的社交机器人,通过实施计算宣传战略,深度介入了政治选举、政治议题对话等政治过程,干预政治活动,影响政治决策。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已发现有数千个自动化的社交机器人账户发布了与选举有关的数百万条内容,其中内容大多涉及阴谋论和政治谣言,这证明社交机器人、跨党派媒体机构和阴谋论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关系,社交机器人在扭曲公共空间的政治对话中发挥了作用。①在智能传播的背景下,社交机器人不仅是媒介工具或传播渠道,其更因自动化和模仿人类的行动模式,具有有限人格主体之特征。可以预见,社交机器人或将重塑信息传播模式和媒介生态,引发政治权力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变革。本文以“政治腹语”概念为切入口,剖析社交机器人的运作机制及其功能的两面性,试图打破对社交机器人日渐固化的负面刻板印象,并对社交机器人的有限人格属性进行剖析,预测其对未来媒介生态的影响,以此摆脱传统工具论视角的束缚。
一、作为“政治腹语”的社交机器人:概念、性质及争议
社交机器人早期的表现形式是一个自动化的账户,活跃于商业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以机械重复地发送和收集信息为典型的活动模式。随着算法的复杂化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以及大量用户数据的公开表露或泄露,机器人能够更加轻易地通过机器学习和模仿能力,在语言表达等方面变得更像人类,社交媒体平台难以识别和封禁这些机器人程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社交机器人的外延从自动应答的程序逐渐拓展到人机交互的智能媒体层面。本文将社交机器人定义为:以社交平台大数据和算法为技术架构,由人类创建的自主行动的计算机程序,它能通过模仿人类用户的话语和行为习惯,在人机传播的模式中生产和传播信息,“智能”地与人类进行“互动”,并试图影响现实生活。
社交机器人的创建及运行均有后台的主体操纵,处于前台的社交机器人就如同腹语表演者手中的玩偶,给人们造成言说主体的虚假印象。所谓腹语最早指的是由肚子发出的声音。在西方中世纪宗教文化中,掌握腹语术的人利用迷信,声称能够唤醒亡者的灵魂,假装扮演预测未来的先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腹语具有不同的属性和意义,腹语者或是代表上帝的权威而传达神谕,或是掌握邪术的巫师,而腹语被视为藏在肚子中的魔鬼,这使得腹语术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阴谋论色彩。
早在17世纪霍布斯(Thomas Hobbes)就指出腹语者是由超凡魅力的权威者充当的虚假的先知,能够操纵和欺骗民众破坏国内政治秩序,他还声称第一个建立了社会的人只不过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社群,故霍布斯认为只有统治者或君主才具有传达神圣意志的权力,其将人类社会或国家的起源与政治腹语相联系起来。这种源自前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腹语形式,正在现代社会中得以重现。数字网络时代,社交机器人的出现成为“迷惑感官的力量”,为腹语者创造新的意义,并且作为媒介化技术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公共话语空间。政治腹语就表现为操控政治权力的暗箱,反对者通过歪曲或掩盖信息的真正来源,误导民众得出错误的结论来暗中争夺政治权力。②
社交机器人作为政治腹语的言说者,往往指涉背后操纵主体的权力角逐,在西方国家政治传播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网站中的链接中有66%是由自动机器人而非真实人类帐户发布的③,而这些运作社交机器人的组织则具有中心化协调的本质,目的是吸引毫无戒心和政治观点极端化的民众来关注特定的政治议题。④无独有偶,除美国外,欧洲、韩国、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社交机器人的身影。学者们将社交机器人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它传播虚假信息,干预政治选举活动,操纵公共舆论,制造虚假共识,宣扬极端右翼政治话语等。2016年,微软创建的聊天机器人Tay在创建后不到24小时内,就在社交媒体中发布了“希特勒是对的,我讨厌犹太人”等否认大屠杀、极端右翼分子支持的种族主义言论。总体上,学界对于社交机器人邪恶型作用方式的揭露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模仿和伪装来实现真实身份的窃取与再造。腹语术的本质就在于使人们听到的声音与看到的身体相脱节。⑤在前现代社会,由腹语者操纵的身体与声音分裂的意象中,这种没有实体的声音被当做来自上帝的权威的声音,是操纵民众感官的腹语。在网络社会,媒介化的社交机器人作为政治权力的化身,其身份隐匿是腹语隐喻的具体化表征。凯瑟琳·佛洛斯特(Catherine Forst)认为社交机器人引发了数字技术时代的政治腹语问题,将真实的声音腹语化,替代和利用真实的大众声音,同时又并非大众声音的真实来源,以扰乱政治秩序,塑造现实政治生活。⑥
社交机器人通过锁定有影响力的用户、盗取和伪装账户等方式使人们受到错误信息的操纵。2017年,特朗普在Twitter与一名名为Nicole Mincey的推特用户互动,后者有近15万粉丝,然而,这个账户实际上是由社交机器人运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Nicole Mincey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麻省理工学院高级虚拟中心通过机器深度学习技术、合成语音、视频对话替换技术等制作视频,展现了“月球灾难事件”的全新叙事角度:阿波罗11号宇航员没有能够返回地球,尼克松总统发表了与现实事实相反的演讲。⑦社交机器人还恶意制造虚假影片用于诽谤,著名的以色列女演员盖尔·加朵(Gal Gadot)就曾是深度伪造图像视频的性暴力受害者。这些人工智能深度假视频呈现了超真实的画面和叙事,使大众难以辨别其真实性。
二是社交机器人通过话题标签制造烟雾屏障效应,捏造虚假信息、扭曲事实。2016年美国大选中社交机器人开展了计算宣传等政治传播活动,即“社交媒体平台、自主机器人和大数据的集合,它们的任务是操纵舆论”⑧。社交机器人被视为社会控制的政治战略,在某些特定政治倾向的公共领域中传播特定的观点,是影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思想的工具。社交机器人通过在冲突性议题上对流行标签的快速识别、追踪,以趋势劫持影响公共话题讨论,加入误导性信息,制造烟雾屏障效应。例如,新冠疫情中的社交机器人被用于建构阴谋论和传播非科学的观点,利用#greatawakenin、 #coronavirustruth 、#5G等标签,污蔑该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传播病毒由5G传播等假新闻,将讨论话题从公共卫生转向政治阴谋论。
烟雾屏障效应还用于误导人们的态度和行动,其以海量而无价值的贴文湮没话题标签,来分散用户的注意力,引发民众的恐慌和愤怒情绪。例如,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分子组成的极端组织创建了机器人账户@antifa_us,推高#DCBlackout标签的热度,宣扬抗议活动和煽动暴力,引发民众的恐惧心理。2015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Twitter、Telegram等社交平台部署了大量社交机器人实施信息恐怖主义战略,转发招募人员的信息,试图获得舆论支持,说服人们加入伊斯兰国参战,并取得一定效果。
三是社交机器人利用民粹话语制造群体极化效应,屏蔽对立的声音,使政治对话变得更加两极分化。研究表明,机器人的数量仅需占特定议题讨论参与者的5%—10%,就可以改变意见气候,而它们所传播的观点最终会占主导地位⑨,这也意味着“相对少数的机器人足以朝着其所支持观点的方向左右舆论环境,引发沉默的螺旋效应,导致机器人操控的意见被接受为公认的多数意见”⑩。社交机器人甚至主动制造沉默的螺旋效果: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社交机器人发布话题标签#macronleaks,精心挑选选举静默期之前的时间点,传播不利于马克龙的邮件泄露信息,使网民对马克龙的政治阴谋论讨论喧嚣尘上。社交机器人利用媒体的沉默,反而制造了“沉默的螺旋”效应,使“边缘叙事成为这一事件期间塑造政治话语的最重要因素”。
社交机器人在舆论空间中还具有“导向”特质,旨在对特定观点施以程式化的宣传方式。由右翼民粹主义者个体或组织所扮演的腹语者操纵着成千上万的社交机器人,以“共鸣”和“遍在”的效果,制造虚假社会共识,创造了看似众声喧哗且活跃度高,但实则并不存在理性对话的舆论场域。在疫苗、禁枪等具有争议性的公共议题或是涉及种族等社会边缘群体的问题上,右翼分子利用社交机器人建构了以愤怒和恐慌情绪为主导的、观点极化的舆论空间,营造出充满分歧、撕裂和冲突的社会氛围。由此可见,数字化的虚假信息产生和运行的环境是一种更大的“公共传播危机”,社交机器人为了产生某种影响,刻意构建虚假信息秩序,破坏着民主政治决策过程。
虽然“腹语”一词具有阴谋论的意味,但事实上,政治腹语作为建构万物的元传播话语也有其积极意义。从中世纪神权政治到现代政治制度,腹语所指涉的权威也从神的启示转移到了对民主制度的信赖之上。政治腹语曾在西方宪政民主的产生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基于一个全能而不在场的声音,创造了全新的政治形式,例如代议制民主便是由腹语者代表“沉默的他者”的声音。在卢梭那里,立法者便是维系社会契约论的腹语者,代表民主的声音和权威,以便让公众适应由社会契约而建构的政治共同体。弗朗索瓦·库伦(Francois Cooren)认为,腹语是传播的关键要素,任何传播形式都可以是腹语化的,当政策、价值观、意识形态通过腹语者所操纵的玩偶传播之后,总会引发人们的言语或行动,组织、社会乃至国家都是腹语效应的外化表象,其发挥何种功能、产生何种影响,取决于政治行动主体的意图。因而政治腹语是以权威声音从原本空洞无物的政治空间中建构全新的话语和意义。
可见,社交机器人的角色和功能本应兼具多个面向,但当前学术界对社交机器人的研究多聚焦于其“阴暗面”,认为它作为“舆论操纵的机器”,将破坏现有的舆论生态,扭曲政治传播过程,而对其正面性功能的关注远远不够。尽管有部分研究关注了社交机器人的正面功能,但仍集中讨论技术本身,并囿于技术善恶论的二元划分剖析其具体的应用领域及作用机制,未能从学理层面深入探析社交机器人的智能化本质,忽视了社交机器人的人格主体性。某种意义上,智能媒体具有传播和行动的两面性,它既是具有社会嵌入性的独立传播主体,同时也是可控的“弱”行动主体。社交机器人既是作为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制度化媒介工具,也是具有“有限人格”的政治行动者,我们在充分认识其阴暗面的同时,也应挖掘其民主潜能,并预测其对未来媒介生态所产生的影响。
二、被忽视的另一面:社交机器人的民主潜能
社交机器人作为新兴物种,介入并建构着新型政治话语空间,已然成为现代政治传播中的主要参与工具。社交机器人改变了公民和政治家参与政治过程的方式,在推动公共议程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比如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政治议题和环保、健康等公益事业等议程中发挥宣传作用,帮助公民更好地理解专业领域的知识。同时,社交机器人在促进政治对话,扩大“电子民主”版图等方面有积极意义。奥伦·佩雷斯(Oran Perez)提出旨在促进公众参与协商的电子民主计划,设想通过开发和应用智能电子民主机器人,实现“增强民主”,后者可以提升人们的政治参与和信息决策能力。具体而言,社交机器人的民主潜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海量信息的智能把关者与虚拟对话者
政治腹语的重要功能是言说,而社交机器人言说的内容受到腹语者的控制和筛选。社交机器人可以充当技术“把关者”角色,协助媒体从业人员和政府自动检索网络中的信源并进行事实核查,常态化监测并打击假新闻和谣言。在国外谷歌、微软及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草根组织和志愿者用户开发反骚扰机器人,发起“假新闻挑战”,主动检索、识别和过滤那些人为操纵的虚假信息,评估文章的真实性。blocktogether.org和ggauto blocker也是用于谣言防控、政务信息发布等关乎公共事务的社交机器人,防范公共话语空间被侵蚀。
在社会公共事件中,由腹语者所操控的社交机器人在参与自动化生产和传播新闻的活动中充当了与公众对话的角色。2017年英国曼彻斯特爆炸事件后,社交机器人发布积极的同情性信息和实用的救助性信息,协助专业救助人员快速搜寻求救者。在气候变化议题上,@AI_AGW机器人作为一个积极主动的搜索者,追踪那些否认全球变暖的用户,向他们提供基于事实的信息,科学地解释全球变暖问题,且能够较为流畅地回答人们的问题。社交机器人还可协助政府进行风险意识宣传和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公众采取预防行为以减轻疫情,强调生存技能和健康风险意识,例如使用#Stayhome,#WashYourHands等标签向人们宣传和普及关于疫情的知识,提高大众风险认知和应对能力。
(二)民意的智能分析与预测者
政治腹语的重要功能还体现在预测方面,中世纪腹语者正是利用腹语技术,充当所谓“先知”,将编造的谣言和阴谋论改造为“预言”,使之在社会广泛流行。社交机器人的预测功能可以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提升信息透明度。
社交机器人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事件和竞选活动中,预测和分析网民的投票意向,间接参与政治活动。2015年的芬兰议会选举中,候选者在脸书(Facebook)页面中的点赞数与选民投票行为之间存在积极的相关性,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选举的成败结果;在2017年的印度旁遮普邦议会选举中,社交机器人成功预测了各政党赢得的席位数量,证明机器预测政治竞选结果的可信度。
在社会治理方面,社交机器人可通过大数据深度挖掘技术,实时监控网络舆论,快速感知舆情信息,预测社会抗议事件的未来走向。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收集、分析有关社会政治和武装冲突动态的信息与数据,由机器学习技术建立预警系统,用来防范社会冲突。社交机器人通过分析Twitter的主题标签和话题趋势,预测了2016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后的反特朗普抗议活动和2017年1月美国各大机场中发生的阻止难民入境法令的抗议活动。2018年3月发生的澳大利亚森林大火救灾过程中,社交机器人通过关键词分析、主题标签和地理位置信息等内容收集和分析数据,起到定位人员位置、传播现场信息、打击谣言、发出警告和提供行动建议等诸多作用。
(三)过滤气泡的破除器
算法具有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不仅将人们从信息大爆炸中解放出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而且有助于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效率,解放社会生产力。在某种程度上,由算法驱动的社交机器人具有代替大多数人做选择的能力,并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仲裁者和决策者。从技术“善用”的角度来看,算法驱动的社交机器人可以对信息或数据做出反馈,通过聚合、桥接的方式对信息进行二次编辑,建构积极的意义空间。
一方面,算法驱动的社交机器人可以向用户提供“反向”个性化信息,充当用户和政治隔离之间的“信息桥梁”,打破用户的信息茧房,弥合政治裂痕,缩小政治鸿沟。例如,社交机器人Bridgerbots和Popporbot通过计算出传播网络中的结构性位置,占据信息网络的重要传播节点,渗透Twitter用户的高度极端或同质性的子网络,监测网络用户的信息来源,如果信息总是来自同源的子网络,那么机器人会将多个其他子网络的多元和异质的信息流输送给用户。其通过人机协同的模式共同发布推文,反向利用社交机器人的算法分发技术,提供更温和的观点,或相对意识形态立场的信息,纠正算法偏见,破解过往的信息接收模式,甚至直接与用户互动,丰富用户所接触的信息内容,“戳破”给定子网络中用户所处的信息过滤泡沫。
另一方面,算法机器人可以在舆论空间中精准供给公共议题。虽然搭载算法的社交机器人是持有偏见的,但这种“偏见”也可以偏向于反映公共利益和输出主流价值观,构建“公共利益+个性化推荐”的信息传播模式,将公共性设置为算法的优先推荐机制,限制算法的应用边界,强化用户主动的信息决策过程,让算法得到善用,这要求算法技术的创建者具有包容性、公共性、客观中立的价值观念。
(四)协商对话平台的搭建者
社交机器人正在成为大众化的技术,在公众与政府之间、不同立场和政治倾向的人群之间,搭建协商互动平台,推动多元化的政治对话,使数字公民获得监督政府、表达观点、参与政治的权力,从而有助于以非对抗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促进公共辩论和政治参与,形成社会共识。
在构建民主话语和公共空间方面,社交机器人不是一个替代性的话语空间,而是发挥反霸权话语的作用,维护公共领域的公共性。GitHub中的开发者们在Twitter等社交平台部署开源代码的机器人,赋予了创作者和用户使用机器人的权力。WikiEdits作为自动化协助型机器人嵌入了社会政治实践过程,强化公众对政府如何参与编辑公共信息过程的认知。社交机器人在多方主体中重塑了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结构,标志着围绕技术参与者重新分配主体的新政治经济开始出现。巴西媒体集团主动使用机器人发起了#maisvocê(More Like You)等话题标签,在话题传播的早期由机器人放大新闻媒体链接,提高议题的热度,吸引线上用户和线下观众的注意力,以便发起公共的对话和讨论,构建了“制度化的受众”。
在促进公民社会参与方面,社交机器人在社会或政治议题中发挥动员作用,塑造集体感知。在墨西哥,已有公民利用社交网络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追求真相和问责政府,甚至揭露和对抗政府部署的社交机器人及其开展的计算宣传战略。2016年,由莎拉·尼伯格(Sarah Nyberg)创建的名为Liz的机器人(@arguetron)精通网络中各种形式的偏见,它持有左翼政治立场,引诱右翼极端主义者如特朗普的支持者、反女权主义者等用户参与辩论,典型言论包括:“为什么会有人听特朗普的话呢?”“白人特权是真实存在的。”等。当Liz声称“资本主义是垃圾”时,网民还鼓励它提出更好的替代性方案。
(五)公共服务的智能助力者
由技术逻辑建构的智能媒介深度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智能可穿戴设备、移动设备的普及,使社交机器人在数据收集与分析领域大显身手,并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
在公共政策方面,希腊政府部门利用搭载了知识数据库的人工智能社交机器人,为公民提供退休养老计划的指导和解决方案,创造更有效的数字沟通渠道。芝加哥大学数据科学与公共政策中心的Aequitas项目,IBM的AI Fairness 360开发了跟踪和纠正偏见的社交机器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通过训练智能机器,识别城市生活条件的街道图像,利用这些信息改善社区中存在的不平等状况。
在教育领域,由IBM公司开发的机器人程序Simpler Voice能够解析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各种复杂文本,提取并呈现简化的图像和简短的语音信息,以可视化方式达到扫盲的效果。智能机器人还能将情绪转化为声音,以帮助盲人“看到”与之交谈者的情绪。华为公司基于人工智能和增强技术创建StorySign虚拟社交机器人程序,帮助聋哑儿童将文本翻译成手语来学习阅读。
医疗领域中,德国西门子医疗集团开发机器人AI-Rad Companion,帮助医生更迅速和准确地诊断疾病,甚至加快药物研发速度。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小组使用人工智能预测癌症,准确率达94%。华为公司开发的Track.Ai智能医疗设备,能够识别儿童的视觉障碍,以便在疾病的早期就干预治疗。此外,在环境保护方面,南加州大学社会人工智能中心使用社交机器人分析数据,帮助预测偷猎者和动物活动轨迹;Wild Me和Microsoft还使用社交机器人识别、记录和跟踪鲸鲨等濒临灭绝的动物。社交机器人在气候变化、深空探索等诸多领域亦有诸多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社交机器人虽然仍是受后台腹语者操纵的前台言说者,但在其发挥积极面向作用时,却不必隐匿和伪装身份,而是将其账户信息标记为含有“bot”字样的昵称,主动声称它是机器人程序。例如,用于监测、追踪和识别政治机器人、僵尸工具和不可信账户的BotSentinel,其昵称(@botsentinel)和头像,都让人们直观看到该账户是发挥正面功能的社交机器人。可见,作为智能媒介技术的社交机器人本身并不涉及特定的价值偏向,它既有可能是操纵和诱导公众舆论的技术黑箱,也具有民主解放的积极潜能。社交机器人在本质上是人类、机器人和共在的环境之间相互转化和互动的产物,其行为方式依赖于人的意图,以人的需求和目的为导向。社交机器人究竟产生何种影响,不由技术本身决定,而是受到社会环境和技术水平、民族国家的制度结构及特定的政治背景、操控和使用社交机器人的行为动机、所要达到的行动目标等诸多因素共同制约。如果不能跳出这种非黑即白的技术善恶论和工具性的媒介技术视角,就无法全面客观认识社交机器人的属性与本质。
三、作为有限人格的社交机器人:工具性超越及深远影响
虽然社交机器人背后存在商业资本和政治主体等操纵者,但其自动化和智能化特征使之超越了“政治腹语”的典型表征:从工具化的视角出发,把媒介技术看作听从人摆布的傀儡,并以简单的善恶之分作为评判智能媒介的标准。如前所述,任何一项媒介技术都有两面性,如果囿于工具性的技术视角而对其抱以刻板偏见,就会陷入无休止和无意义的技术善恶论争辩中,使我们无法全面而客观地看待社交机器人的本质,遮蔽社交机器人的智能化属性。社交机器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现象,而是深度地介入了人类社会关系,建构着人机新型社交模式和社会关系的媒介化技术。
从现实应用领域来看,社交机器人能够创作新闻、音乐、文学等作品,被视为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的“第六媒介”。基于机器深度学习技术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预测能力的不断提升,智能技术正在获得一定的自主能动性,模仿和发展出人格化的情感和言行,甚至在未来会获得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目前,谷歌搭建的DeepMind神经网络正在使智能机器人朝着超人工智能的方向演进,它可以自主地通过学习建立联系并创造意义,甚至在迭代更新中不断增强它的各项能力。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将社交机器人看作传播的工具或中介化的媒介,更不是“政治腹语”的操纵对象,而是具有与人类对话和互动能力的传播主体。
在社交机器人出现之前,人类的即时性传播活动建立在“身体在场”或以互联网搭建的“虚拟在场”的基础上。社交机器人则超越了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平台媒介属性,使人与机器展开交流甚至协作等社会交往行为,并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生产过程重塑了公共话语空间,创造了全新的人机传播场域与情境。社交机器人的特殊性在于以虚拟的数字态身体与用户进行着无需身体在场的交流。例如,人们在对Siri说“谢谢”这一简单的传播行为中,就表现为人与机器共同创造着“社交在场”。机器正在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而具有意识的另一主体——人类,则(不得不)对这个智能技术存在物做出反应。社交机器人的人格化特征,使人们感受到高度的交流在场,并在与之交往中应用人类社会的规则、社会期望等,甚至做出情感反应,引发同情和保护的情感,从而产生了“无中介的幻觉”的心理效应,使原本中介化的社交机器人被转化为社会实体。
社交机器人是由平台或个体基于大数据、算法逻辑和自然语言生成等技术架构所创建的智能媒体,其存在形式是以数据态的方式存在,借助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空间,社交机器人跨越了时空、渠道等中间介质的种种障碍,与用户直接进行交互。因此,在数字网络时代,具身化将是社交机器人及智能媒介的关键特征。社交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也不再仅表现为唐·伊德(Don Ihde)所阐述的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他异关系”,即通过自主能动的行为介入环境并与之互动,而更像是透明化媒介形成的具身关系,是以交流主体的存在形式实现的人机传播模式,建构和营造人机传播情境并生产意义空间。因此,社交机器人正由中介化、工具性媒介属性,日益转化为去中介化和超越工具属性的言说主体的性质。
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具有交互性、对话性和社会性。智能媒介不仅是单纯机械式地联结人与人传播的中介,而是实现意义创造的传播者和参与者,深度改造着人类社会的实践,并引发所谓的“虚拟协同呈现”,从根本上改变人际传播范式、意义生产过程以及社会行动形式,导致社会关系从人类社会转向了人与社交机器人交流的合成互动社会。人机传播是指“人类与数字对话者的交流,后者包括在真实或虚拟环境中的具身化的机器传播者、智能代理以及技术增强的人”。与传统的工具化媒介的角色不同,社交机器人作为具有社会嵌入性的独立传播主体,聚焦于“人与机器之间的意义创造”,渗入了人类社会中的生产、传播、交往等指涉“传播”本身的社会活动。社交机器人建构的意义与传播情境则影响着人的认知与行动,反之亦然。社交机器人的自动化生产、处理和传播行为,使之在与人类的交流中构成了一个反馈性回路,并扮演着拟人化的传播者角色,故社交机器人正在被视为人机传播中的数字对话者。
另一方面,除了人机之间的“交流”外,社交机器人的去中介化和去工具性还体现在行为上与人类进行“互动”的过程。社交机器人的互动性和伪装性特点是建构人机传播关系的关键特征,使之演变为行动主体,能够影响人们对特定议题的认知及行动决策;同时,传播活动将日趋演化为由自主能动的且不限于同一个物种的传播主体之间进行的行为。戴宇辰指出,某物的物质性首先表现在其相对稳定的内在特质;其次是以数码或物理形态存在的行动者可以跨越时空界限而不受到社会建构影响;最后是超越对原有情境的主观阐释。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交机器人同样具有鲜明的物质性属性。首先它是一种媒介技术,这是由其自身的行为方式(生产和传播信息)与社会属性(交互性特点)决定的;社交机器人以数字态的形式存在,本质上是不可见的计算机代码,而外在形式是伪装而成的社交媒体账户。它可以24小时连续不断地传播信息和进行社会互动,其自动化的属性完全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极限,可以在接受指令后自主行动;社交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能够自主地实现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此前学者们探讨物质性时,往往从抽象的概念层面论证“物”在社会情境中所具有的能动性,尤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最具代表性,该理论把任何包括人类和非人类的行动者看作能动的转译者,例如静态的物在复杂社会关系和行动者网络中参与了建构的过程,亦或是被建构的结果。然而,社交机器人作为动态物介入行动者网络,则使这种停留在概念层面上的静态物的抽象能动性成为了现实。
传统媒介生态中,人类是唯一的舆论主体,但在智媒时代,社交机器人相当于一个未知的变量参与到行动者网络中时,它既是自动化的行动者,也是建构媒介生态的行动主体。道格拉斯·吉尔博特(Douglas Gilbert)直言,机器人主体是人类、机器人和共在的环境之间相互转化和互动的产物。当我们将视线聚焦于社交机器人及其行动时,便会发现在其活动覆盖范围内的媒介生态,是由社交机器人自主而能动地进行的社会建构过程。社交机器人的物质性表现为“关联网络稳定化的展演性效应”,网络生态内部的舆论生发、信息传播、网络公共事件的生成、乃至标签行动主义的线上社会动员等过程都由包括社交机器人在内的网民、意见领袖、主流媒体、监管者等多方主体参与联动,在这个过程中,社交机器人的意义再生产使网民投入到民主对话中来,或是在与其他主体的互动中,激活多方主体参与意义重构过程,或以技术赋权的方式成为“人民的声音”的传播者,挑战原有的话语权力关系结构。
当我们具体考察社交机器人发挥的作用机制时,可以将上述多方主体构建的关系网络简约化为“操纵者—社交机器人—受众”的行动者网络。在此,社交机器人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或命令的执行者,受到其背后操纵者意图的影响,但这只是一种单向的传播行为,尚不能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者。社交机器人“互动性”特征的重点在于,当这种隐匿了真实身份的社交机器人作为一种积极能动的行动者联结了操纵者和受众时,实现了操纵者的意愿,让部分网民受到操纵者意图的影响,而且由社交机器人转译了受众的意愿,使受众不得不考虑他们接收到的信息内容并作出相应的认知和行动。此时社交机器人才发挥了联结多方主体的作用,并在网络舆论生态中彰显能动性。从社交机器人及其操纵者的视角看到的传播模式是:用户—(社交机器人—机器人的创建者/操纵者)。而从用户的角度理解的传播模式是:(社交机器人伪装的)虚假用户—真实用户。社交机器人藉由伪装术和拟人化的特征,完成了由中介式的传播媒介到传播主体的身份转变,同时使用户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与“媒介”交互在场的具身式体验。
“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时代”。从后现象学的“延展的中介化理论”来看,媒介技术不是联结客观世界和人类认知的中介,而是重塑了我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媒介不仅反映了世界,而且塑造世界。约翰·杜翰姆·彼德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对空言说》中说道,虽然人类同时具有言语和交流,但“交流”并非人类独有的能力,人们也从未放弃对于无血肉之躯的计算机等存在物,在构想、研发及技术的更新中找到彼此交流的可能。作为智能化的媒介存在物,社交机器人是与人类进行直接交流的跨物种传播主体,这使得交流正在将人类社会推向由多元化的智能传播主体所搭建的后人类技术图景——人类与智能主体的交互打破了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交流模式。
四、结语与反思
总之,社交机器人既可能是舆论的操纵者和阴谋的实施者,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未来还可能摆脱和超越工具性媒介的束缚,成为具有一定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情绪表达能力等的有限人格主体。社交机器人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应用,而会极大地拓展和突破过往的媒介概念、传播模式以及原本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和交流方式,并在人类社会的关系与情境之中发挥其媒介化的作用,建构具身性的人机传播模式和社会关系。彼得斯说:“我们在漠视‘超自然现象’和‘非人存在物’时,使用的都是‘遏制’策略,这种策略只不过是一种道具,用来支撑我们脆弱而危险的身份。”正是这种策略的应用,使我们在面对社交媒体中日渐兴起的社交机器人时,更多地对其采用批判性的负面立场,而较少地以人与非人存在物共存、共在的态度对待新兴的物种。不知为何,近年来智能媒体的兴起使我们开始警惕技术,并聚焦于技术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却丢弃了人类最初对待技术的乐观主义精神——技术造福人类的积极面向。
社交机器人等智能媒介技术的角色多面性与功能多样性,正在引导我们跳出工具论的局限性,为我们提供一种重新认识和看待社交机器人等智能媒体的媒介学视野。作为有限人格的传播主体,社交机器人必将重塑媒介生态,人与社交机器人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操纵和利用关系,而是涉及两个不同物种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社交机器人和人类各自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存在,又因传播与交互而建立社会关系并创造新的意义。如果将社交机器人视为特殊的行动主体,将颠覆现有的理论,“人+社交机器人”的传播格局已成为一种可想象的社会图景,这将对未来的舆论生态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应在人机协同的媒介生态中,编织和塑造对未来社会的想象。
(本文系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人文社科专项“重大公共事件中的情绪传播及风险防控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8CDJSK07WK08〕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