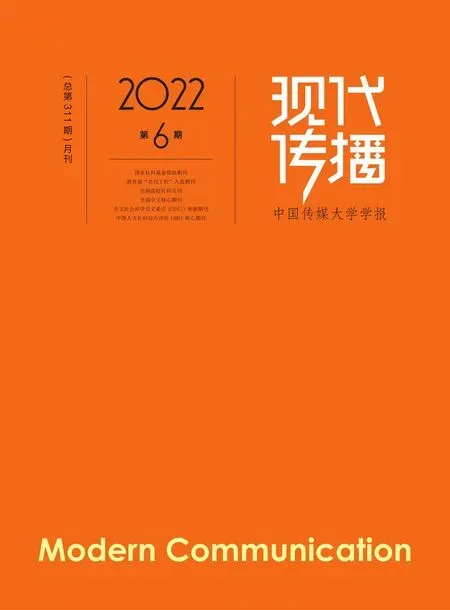社会表征视域下媒介污名的生产与抵抗*
——以网络流行语“X媛”为例
王 韵 魏书琮
网络流行语既是人们在网络中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也是大众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载体。从早年的“给力”“正能量”“屌丝”,到近年的“打call”“后浪”“打工人”等,网络流行语涵盖范围甚广、褒贬皆存,其传播度和影响力与不同主体的话语实践以及社会心理、商业逻辑、媒介技术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当前大众文化多样性的体现,网络流行语有助于提高网民的集体归属感和社会交往的愉悦感,然而,网民对其非理性的使用在传播过程中造成的语言污染、话语狂欢、群体污名化等问题也不容忽视。
2021年的“佛媛”“病媛”事件继2020年“拼单名媛”后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网红塑造“虚假人设”并由此“捞金”现象的关注。在这场媒体与大众的共谋论战中,部分专业媒体对“佛媛”“病媛”人设进行批判,继而引发网民对该群体的言语讨伐。伴随着“媛宇宙”“演媛的诞生”等戏谑、讽刺性言论,“X媛”作为话语模因被网民不断复制传播成为新兴的网络流行语,并标签化为网民用来指摘与自身价值观不符的女性的工具。而事件反转与舆论演化也推动“X媛”污名化问题成为网络社会议题的焦点。本文通过“媛”由褒至贬的污名化过程的梳理分析,引入社会表征视角扩展以往的媒介污名研究,探究网络流行语“X媛”如何经由媒介话语生产建构污名,并揭示网络时代网民在媒介污名社会表征再生产中的互动与抵抗作用。
一、理论视角与问题
(一)社会表征理论
表征(representation)又称为心理表征或者知识表征,是外部事物在人脑中的内部“再现”。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创立了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在其著作《社会表征》中论证了这一理论的起源、主要观点及研究取向等问题。该理论承继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对“个人表征”和“集体表征”加以区分的学术智慧,将个体主义取向的主流社会心理学推向了对群体的研究,强调社会共识的形成,倡导社会的发生,是国际社会心理学的新范式。莫斯科维奇将“社会表征”界定为“某一社群所共享的价值观、观念及实践系统”,其“兼有两种功能,其一是为个体在特定生活世界中的生存进行定向,另一则是提供可藉以进行社会交换及对生活世界与个体、群体历史进行明晰分类的符号,使人际沟通得以实现”①。社会表征研究具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国内有社会学者分别基于规范、认知和行为面向总结出三种社会表征研究路径——结构研究、过程研究和功能研究。②有研究指出,各社群社会表征的建构和重构愈来愈与宏大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动态的社会过程紧密相关,并从中或隐或显地折射出种种社会矛盾或冲突。③这体现了社会表征理论对社会转型期背景下的群体性“污名”意义建构的解释力。国内以社会表征为理论视角的研究大多源自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领域,遵循信息传播、话语建构和群体分化的过程研究路径较多。
(二)问题与研究方法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认为,污名是一种令人“丢脸”的特征,由虚拟的和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的一种特殊差距构成。④污名研究存在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路,研究范式虽不尽相同,但大多重点关注特定疾病、性别、种族、社会身份的越轨行为及其污名的社会建构性。媒介污名化是指在大众传播实践中造成的污名现象,在传统媒介时代,以新闻报道中的污名研究为重点。随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中出现了“泛污名化”现象,即污名现象不断增多、污名对象不断泛化、污名内容逐渐多样、污名关系愈加交错复杂。⑤国内早前研究主要围绕新闻报道中具有争议性的不同社会群体展开,如“农民工”“城管”“女司机”“剩女”“中国大妈”等群体的媒介形象及污名的生产机制、成因、影响及其对策。近年来也出现了针对网络流行语如“绿茶婊”“屌丝”等本身即有侮辱性与贬低性意涵且具有性别指向的媒介污名研究。
本文以“X媛”网络事件中的各类文本内容作为质性分析资料,对网络中与本事件相关的材料进行搜索、记录和保存,形成了新闻媒体、自媒体以及网民个人账号等主体发布的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在内的自建语料库。基于已有网络舆情生命周期的研究,将收集文本资料的时间段选定为2021年9月5日至2021年10月31日。选择这段时间主要基于以下原因:2021年9月5日,“深响”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别爱太满,别睡太晚:寺庙的流量密码与新媒体生意经》,文中提及泛佛、“佛媛”、引流等内容,之后文章被虎嗅网、凤凰网等专业媒体转载,“佛媛”一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21年9月21日《工人日报》刊发批判“佛媛”的评论文章成为“X媛”网络事件的导火索,而后《健康时报》发布有关“病媛”的新闻促使事件继续发酵;围绕“X媛”的讨论在网络空间不断发展演化,到2021年10月31日大致涵盖了舆情传播的潜伏期、延续期、暴发期和恢复期。语料库一部分为《工人日报》《中国妇女报》报纸媒体的评论文本,《健康时报》、澎湃新闻在新浪微博平台发表的网络新闻文本,以及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回应和处理事件的文本。还有一部分为新浪微博、抖音、小红书平台内网民发布或参与高热话题中的文字、图片或视频。研究团队对相关图片和视频内容进行了文字提取和声音转录。
二、基于“媛”字词义变迁的表征分析
(一)“媛”字的古代初义考
从古代“媛”字的词义考察出发。“媛”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诗经》,《国风·鄘风》中《君子偕老》一诗,其末句“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即是对主人公倾国倾城姿色的描摹与赞叹。收录了大量古汉语词汇的“辞书之祖”《尔雅》释训篇中“美女为媛,美士为彦”⑥,句中“媛”(yuàn)意为美女。《说文解字》中载:“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从女,从爰。爰,引也。”⑦即是说“媛”是人们想去牵引的美女。可以看出,在传统社会中的“媛”作为褒义词用于形容女子美好仪态与姣好容貌。
(二)从外貌到才品:“媛”的词义拓展
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媛”的意涵亦不断变迁。“名媛”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小说《两晋秘史》中,指“有名望的美女”⑧。明清女性文学的出版风尚推动“名媛”词义的转变和丰富。明代“名媛”多指出身名门、有才华的女子,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认可的江南“才媛”文化为代表。再到清朝,沈善宝编撰的《名媛诗话》共十五卷,主要收录从顺治到咸丰年间才女名媛的诗作,且包括从上层女性文人到农妇出身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女性。“名媛”没有相貌、家世背景的局限,主要彰显女性的才品。再到戊戌变法后,清政府于1907年3月8日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标志着中国女子第一次获得了享受学校教育的合法权利⑨,这为女性接受西式教育,继而参与社会交往、实现就业甚至参政奠定了基础。由此,“名媛”的含义在女性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并涌现出了如陆小曼、唐瑛、林徽因、张爱玲等具备思想学识的近代“名媛”代表。
(三)作为网络流行语的“X媛”
继上文对“X媛”事件的梳理,《工人日报》于2021年9月21日刊发评论后,网络中出现诸多批判“佛媛”的转载、报道或评论文章。9月28日,《健康时报》于官方微博发表题为《“佛媛”之后再现“病媛”: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妆》的文章,并被澎湃新闻、《南方日报》等诸多新闻媒体官方微博账号转发。然而次日,被展示出人像照片的新闻当事人以实名方式在微博上维权发声,抛出三甲医院诊断书,声明自己拍摄手术后的康复照片并非意在作秀和卖货,该行为使事件发生反转。但个体的网络维权行为并未终止“X媛”在互联网上的持续发酵,由拼单“名媛”衍生出“佛媛”“雪媛”“病媛”“菜媛”“饭媛”“艺媛”“幼儿媛”“支教媛”“公益媛”等污名化女性的网络流行语。
将这一现象置于具体社会语境中考察,发现其折射着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代网络社会中业已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一方面,商业逻辑下资本通过控制和塑造女性身体以迎合大众想象,并将其作为一种商品吸引消费者,消费文化对大众审美的全面渗透加深了女性身体的物化程度,也推动了网红经济的出现。部分女性在现存社会力量的支配下主动进行自我商品化,通过身体展演将他者的凝视转化为社会资本,令身体成为获取经济利益与权力的工具。另一方面,近年来性别事件愈发成为网络中的热门话题,促使更多性别议题进入公共领域。⑩在女性相关话题受到前所未有关注的社会环境中,“佛媛”“病媛”事件经由媒体主导的特定修辞格的话语生产再次激发了网友对部分网红虚假人设的不满情绪,而网民的评论互动等话语实践促进了“媛”字污名化表征的形成。
社会表征的形成受多方因素共同作用,其过程包括表征建构的社会背景、表征主体和表征对象(具体实体或抽象概念),它们彼此互为关联。在“佛媛”“病媛”事件中,媒体机构、网民等表征主体以话语为手段批判“X媛”的虚假人设,促使以“X媛”为修辞格的词语成为具备贬损意味的污名对象。表征对象“X媛”作为话语模因被不断挪用,又进一步加深了其污名化的影响。从语言学角度对“X媛”进行结构分析发现,其成为网络流行语的条件主要基于两种特定的修辞格。一种是呈现出“双音节名词/动词/形容词+媛”的结构特征,如程序媛、支教媛、幼儿媛、病媛等;另一种是位置不固定但含有“媛”字的其他组合词汇或短语,如“媛宇宙”“演媛的诞生”等话语。
综上,“媛”的多种语义作为表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及其背后的社会现实与文化思潮。
三、“X媛”媒介污名化:作为社会表征的生产与抵抗
(一)锚定与具化:“X媛”话语生产及表征形成
社会表征包括锚定(anchoring)和具化(objectifying)两种心理机制。锚定是将人们感兴趣的、异质的和不熟悉的事物通过解释和命名纳入既定的分类系统中,使其作为一种类别可以被解释和沟通。置身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既有心理结构,常对新事物存在具有差别甚至迥异的判断和认知。但大众媒体借锚定与具化机制,以话语作为工具,能够引导人们态度的改变。
第一,“X媛”意义的生产通过话语将其纳入大众熟悉的类别图式。如在《工人日报》针对“佛媛”事件的评论文本中,文章标题将“拼装名媛‘上新’”定义为一场“闹剧”,奠定评论文章的批判基调。而“拼装名媛”作为熟悉图式引导读者识别“佛媛”这一社交媒体中的新人设,将她们划归为一类。文章还将“佛媛”与《西游记》里的各色妖孽做类比,表达对其道德越轨却获经济收益的强烈谴责,实现了媒介话语对“佛媛”的宰制。由提出新异事物,到划归既有类别并对其做出解释,再予以演绎归纳赋予其负面评价,“X媛”的话语意义被建构并经由大众媒介迅速传播。
评论1:那条案、那香炉、那豪宅名车,都是老演员了,文案也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再定睛一看,这帮“佛媛”不就是上一波拼装名媛吗?……笔者不由地想到《西游记》里各色妖孽,狐狸的尾巴哪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
第二,有效的具化机制主要通过对“X媛”的符号化建构共识性的社会表征。具化是将各种元素组合形成社会框架,如规范、价值、行为等,在沟通压力下形成并组织在表征元素中,它使人们那些模糊和抽象的观念变得具体。新闻媒体或自媒体意见领袖拥有在网络社会中控制、筛选和再分配话语的权力,表现为以具化的心理机制构建有形的和可理解的“X媛”社会表征。从拼单“名媛”再到“佛媛”“病媛”,媒介话语将新异对象“X媛”与拼单“名媛”体现出的“虚假表演—形象展示—人设营销”行为模式相结合,将“媛”作为表征文字的符号意义具化至已有框架中。
评论2:一位碎花裙年轻女子,在拿着Prada包装的一捆芹菜凹完造型后,将芹菜扔进了垃圾桶。……奢侈品与烟火气原本就是个悖论,这是一个常识。而她们偏要纷纷出演类似的魔幻菜媛。
基于这种框架化的表征机制,事件原本面貌的重要性下降,大众逐步接受由掌握话语权的表征主体设定的认知框架。“X媛”也由抽象的话语表征具化为“利用美丽外貌和身体收割流量”以谋求商业利益的女性,构建出在资本驱使下供大众符号消费的违背公序良俗的群体形象。
与此同时,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媒介环境中,获取关注和流量成为部分媒体从业者的首要目标,挪用“X媛”修辞格进行话语再生产操作简便且易获得高关注度,导致“媛”从原始背景中逐渐分离出来,并在“媛媛”不断的框架化话语生产中获得了某种独立性。从实际影响来看,原始事件的框架化(议题化)传播对网络受众具有一种“认知赋能”的作用,即将认知焦点从“事件当事人的遭遇”向“事件社会含义”转移。在不间断的“X媛”话语生产和使用中,表征话语与被表征对象间的差异不断缩小,甚至直接将本与特定环境、特定行为等外在特征相联系的“X媛”,抽象成属于“媛”这一范畴的典型样例和表征框架,使“媛”成为具有侮辱和贬损意味的污名表征。
评论3:菜媛、病媛、离媛等等都一一粉墨登场,她们通过买菜、生病、离婚等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切身经历”,与凹出的名媛人设,达到一个戏剧化的冲突,满足普罗大众的猎奇心理,从而最终达到利用私域流量卖货变现的目的。
(二)二元编码:“X媛”符号边界的建构
社会(包括现实与网络)中的人类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框架下进行的。不同框架下的行动者被划分至不同的社会范畴,同时,社会范畴化也在形塑着主体的认知与行动框架。社会范畴化的基本策略是通过二元编码机制完成的。所谓二元编码机制是作为被驱动的社会行动者,在对人和物等进行分类的过程中,采用对立概念进行区分的方式或策略。在此基础上群体被赋予“我群”与“他群”的区分,并在社会表征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形成符号边界。符号边界作为行动者对人和物的共识性分类,具有概念性与想象性特征,如网络流行语中的“绿茶婊”“屌丝”“工具人”,以及本文中的“X媛”,都因其较强的机械复制性更易作为符号表征被继续强化并加深污名化。
“X媛”符号边界的二元编码建构性可在以下三个层面被识别。首先,“X媛”的媒介话语体现出“正确—错误”的二元编码。社会表征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规范着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动,此种力量是一种恒在的结构和符号的传统,而大众往往难以意识到此结构在自身思想和媒介话语中的隐蔽存在。部分群体面对官媒发文批评“佛媛”时,会自觉认同指斥“佛媛”的行为是对网络不良风气的纠偏和匡正。同时受我国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伦理观念影响,“X媛”被指以虚假人设骗取流量或实现商业变现违背了笃实诚信之道,豪宅、跑车、名包显露的奢靡之风悖离了朴素节俭的要求,在寺庙“佛欲”风的装扮也不符合“礼”之恰当不逾矩。大众在媒介话语“正确—错误”的二元编码下划清了“我群”与“他群”的界线。
评论4:虚荣心得到满足、流量变现更方便,搞不准还能找到富二代,管它是不是亵渎神灵的呢?反正信佛是假的,名牌也是假的啊,只有骗流量、挣快钱的想法是没有变的。
其次,从社会性别层面,大众媒体在将“X媛”作为符号言说的过程中建立起“男—女”的二元编码。长期以来大众媒介在男性文化控制和操纵女性身体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女性身体被认为是根据人们的感官和生理欲望与想象生产出的供人消费的商品。对具有鲜明性别指向的“X媛”加以批判实则凸显大众媒体话语仍囿于传统性别窠臼的狭隘性,体现了男性视角的凝视,女性自觉内化不同阶段的父权制价值观以及为符合社会主流观念中的“理想身体”从而实现自我规训。“媛”构字法上的“女”字偏旁表明其与女性的天然联系,而“X媛”的编码机制则将批判矛头对准了女性。实际上,互联网平台中利用虚假人设获取高流量的行为并不存在性别之分。如禅意内容制作者并非只有女性,一些寺院的主持、高僧也通过短视频平台获取高流量并实现带货,他们以“广结善缘”作为自己踏入自媒体领域的理由,吸引普通大众在其账号下进行云烧香、云信佛。因此,“X媛”在屏蔽了部分社会现实后,作为符号模因在“男—女”二元编码下产生了对女性群体的泛污名化。
再次,从群体身份层面体现的“生产—消费”二元对立的范畴看,泛化出的“X媛”呈现出作为互联网平台图文或视频内容的生产者,与作为消费者的普通大众的对立。媒介话语中,以生产内容为职业的“X媛”是兼具年龄与外貌优势,通过塑造虚假人设将符号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的“网红”群体。此表征迎合了已有社会共识中人们对女性与网红群体的刻板印象,引导大众有意识地识别“X媛”,并采取相应行动以防落入其背后的消费陷阱,将大众与“X媛”在社会认知与社会行动两个面向上相区隔。官方媒体虽意在批评滋生于网络的人设乱象以阻止失范的符号生产和网络消费,但部分媒体在眼球经济的逻辑下继续将“X媛”作为符号修辞吸引大众对网络热点现象(如拼单“名媛”)的衍生品进行消费,而此行动又造成网民们的新一轮符号狂欢,加剧了“X媛”的媒介污名化。
评论5:这媛那媛的,不过是背景板不一样,这个群体,想做的事都只有一件,就是炫耀。而炫耀则是一门生意,那些看似无意轻松的奢靡感,吸引一部分心态不成熟、价值观不正确的观众,要么为其买单,要么成为其中一“媛”。
以上三个层面的二元编码皆建立在大众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他者身份特征的识别和归类之上。这种经由二元编码机制强化后的符号边界通过群际间的社会比较和持续建构不断加剧了“X媛”的污名化。也能由此发现媒介话语逻辑中蕴含的对互联网平台发展中资本炒作乱象的谴责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秩序的运转。
(三)社会互动:共识强化与争议发生
现代社会中,信息在技术的驱动下得以快速流通,普通大众获得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沟通并卷入社会表征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莫斯科维奇强调表征在日趋异质化、权力去中心化的现代社会中表现出动态性与多样性。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表征,而不同类型的表征也会因社会现实的变化而转变为另一类型,其中尤为强调互动在表征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由此,对“X媛”污名建构除去考察生产过程外,也要把握大众的沟通与对话在表征建构中的能动性。
一方面,多方针对“X媛”事件的舆论互动及社会行动制造并强化了共识性的污名化表征。媒介话语生产污名表征的同时形塑了社会规范,大众基于对低声望的规避,在所属社群的互动中对已形成的符号边界进行内化,“我群”和“他群”的区隔通过互动中的群际比较被生产,这一过程令“媛”字代表负面意涵的社会观念被不断巩固。媒体话语对社会实践的介入也强化了“媛”字的污名表征。从互联网平台迅速关停“佛媛”相关违规账号等处罚行为的报道文本中可以看出,平台方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共识,通过“自律”机制实现了政府监管下的行业自我规制。
评论6:经过整治,用户如果搜索“佛媛”,在部分平台上会有温馨提示,“请对虚假人设、借机营销行为说不”。
另一方面,社会互动过程中的群际冲突与对抗性话语再生产形成了“X媛”争议性的社会表征。在有关“媛”产生媒介污名化的讨论不断发酵过程中,少数媒体及网络意见领袖从破除污名角度引导舆论,网民也对“X媛”的泛污名共识发出质疑。不同社会群体由于群体规范和所处环境的差异,对同一客体可能有不同的表征。这为“X媛”媒介污名的社会表征在媒介话语、传统性别秩序、商业逻辑以及大众舆论等多重力量的互动博弈下不断再生产提供了解释框架。以“病媛”事件反转为关键节点,网络空间中的争议声量渐强,促进“X媛”争议性社会表征的形成。如《中国妇女报》刊登的《警惕以“媛”为女性标签的污名化》一文指出:
评论7:把个案普遍化,将“媛”标签化,进而泛化甚至污名化,这是极不严肃、极不公正的,必须予以制止。特别是各类传播平台,要承担起推进男女平等的社会责任,对具有明显性别歧视意味的所谓流行语(词)进行把关甄别。
又如网民对新闻媒体专业主义的质疑,他们认为,部分颇具影响力的专业媒体并未以客观、真实、准确的原则报道事实真相,中伤了以乐观态度面对疾病的病人。而在“病媛”当事人发声维权后,持不同立场的社会群体针对“X媛”事件的观点冲突也愈加明显。网络社交平台中出现了针对污名如“我不是病媛”“当事人回应病媛事件”“是病人不是病媛”等吸引广大网民参与的话题,且截至完稿上述三个话题的讨论量已破36万条,总阅读量突破9亿。
评论8:“是病人不是病媛”话题主持人@丁香园微博评论区高赞评论节引:
媒体自己说这些所谓的病媛是为了“博关注、引流、涨粉、带货……”,那么不去求证直接扒人照片造谣的媒体是为了什么呢?
而且媒体干嘛非要取个什么什么媛的代称啊?非要把媛引申成贬义吗?
(四)抵抗实践:基于性别的身份认同与戏谑性符号应对
在互动中部分网民表现出一种主动应对的姿态,以性别身份认同的方式实施对“X媛”媒介污名化的抵抗。一方面,身份是个人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一种表现,以与他者的相似或相异构成身份认同。但由于在脱嵌的当代社会中性别、年龄、职业、血缘等结构性因素对身份认同的建构力量逐渐式微,通过自我的主动选择与主动建构的“自反性”身份认同逐渐成为网络中的主要方式。以“病媛”污名为例,作为污名客体的患者具有极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这些女性个体主观化地模糊病躯与正常身体的边界,借由图像身体的复魅,赎回患病身体的创造力。新闻当事人通过自我言说和自身“在场”争夺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在病房照片被误用间接导致群体污名风险后,她们主动地谋求名誉恢复和精神重建。一名维权当事人在个人平台发布的视频中如此表述:
评论9:首先,(使用)“病媛”这两个字就是非常的可耻的好吗?就是对女性的一种污名化……我胸腔镜手术前后做了两次,没有一个医生护士告诉我说你不能敷面膜,你不能用那些护肤品……必须要维权,今天你们是拿我们一些个人开涮,明天就是一个群体。
另一方面,戏谑性的符号应对也是网民抵抗媒介污名的表现手段。在当前我国现代化转型语境下,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性别观念的流变。越来越多的女性作为遭贬抑的“第二性”对社会生活中充斥的男性话语霸权具有更加敏锐的识别和反抗意识。社会表征动态形成过程进入了符号应对阶段,即个人或所属群体开始描绘和解释新事件,这为“X媛”媒介污名化的消解提供了一种新路径。以性别认同为基础,大众特别是青年女性对病人的感性支撑体现在“生病也要漂亮”“谁说在医院就不能化妆”等网络话语实践中。基于对“媛”字原为褒义词的认同,甚至出现了以自我“污名”以达到“去污名化”的网络话语再生产,在“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的觉悟中思考女性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境况。她们开始利用延续新造词语的方式应对新事件,如网友幽默地称自己是“呼吸媛”“走路媛”“活媛”等,以“我是X媛”句式进行污名消解的媒介实践。这种具有主体性的话语实践以戏谑性的方式对污名化的“X媛”进行解构,促进“媛”字社会表征的再生产,其作为抵抗实践不仅深化了女性的社会性别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性别污名的消解。
四、结语
新媒介平台的兴起重塑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为多元的文化思想提供了传播交流的场域。“X媛”的媒介污名化作为展现当前网络社会生态的窗口,为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与语言学等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样本。媒介污名的形成关涉宏观的社会背景、网络环境、性别秩序等,也与不同主体的传播实践密切相关。因此,对不同主体的社会责任进行反思为实现网络共治和污名消解提供了可能。
首先,新闻媒体应坚持客观、真实、公正、准确的原则,加强对新闻信息溯源核查的同时秉承平衡的报道准则,避免新闻失实对媒体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其次,网民作为参与建构表征的能动主体以及可能遭受污名的潜在主体,应提升媒介素养和社会性别意识,增强对信息的甄别与批判能力,避免传统观念中部分存续的集体无意识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在保持平等和谐的性别观念基础上以自身行动重塑社会性别文化,促进性别污名和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消解。再次,互联网平台应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完善平台社区规则、加强账号管理、健全内容审核机制,及时应对网络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和新现象,防范和抵制不良信息的传播。最后,互联网从业者需内外兼顾、加强自律,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以虚假人设等营销手段赚取短期流量不是职业发展的长久之道。由多方主体共同缔造的理性话语空间是媒介污名得以消解的土壤。新媒体语境下如何更有效地管控滋生于大众媒介的各类话语失范行为,避免出现以网络流行语为隐蔽载体的性别贬斥,仍需从多元视角对该社会表征的建构与消解进行更为长期、全面和经验性的观照。
注释:
① S.Moscovici.LaPsychanalyse,SonImageetSonPublic.Paris: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76.p.103.
② 赵蜜:《社会表征论:发展脉络及其启示》,《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228-241页。
④ [美]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页。
⑤ 张昱、杨彩云:《泛污名化:风险社会信任危机的一种表征》,《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第118页。
⑥ 〔晋〕郭璞注:《尔雅》,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⑦ 〔汉〕许慎:《说文解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16页。
⑧ 王莎莎:《“名媛”的词义及其流变》,《文教资料》,2016年第26期,第17页。
⑨ 王美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与女子教育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90页。
⑩ 董扣艳:《性别冲突与父权制意识形态批判——微博“热搜”话题的批评话语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