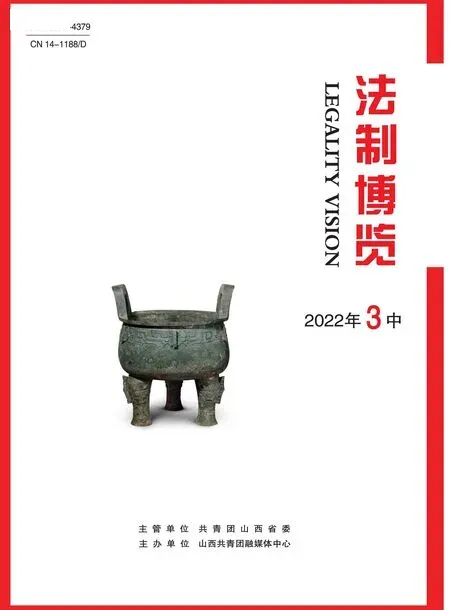《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的理解与适用
宋雨轩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一、责任的性质
关于第三人侵权行为,现行《侵权责任编》及其他法律中并无此概念,杨立新教授通过对《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进行解释,将其上升到独立的侵权行为形态类型的高度,并进一步将其归入到多数人侵权行为范畴,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为第三人责任的一种;[1]而张力教授在其理论基础上,对第三人侵权行为做了重新梳理和再造,其认为第三人侵权行为应当归入单独侵权行为范畴,其对应的侵权责任形态为包括第三人责任在内的多种责任形态,具有多样性。[2]笔者比较赞同张力教授的观点。
第三人侵权行为中,导致损害发生的全部原因力均来自第三人实施的过错行为,而处于第三人与受害人以外地位的那一方,我们称其为“关联人”,关联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仅仅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非能够作为构成要件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关联人要么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原因力,要么根本未实施任何行为,所存在的仅仅是第三人的行为,因此它本质上属于单独侵权行为的范畴。此外,在侵权行为形态与侵权责任形态的对接上,并非强制性的一对一,也可以是一对多。事实上,现行法律除了为第三人侵权行为配置第三人责任外,起码还有以下责任形态配置:直接规定的不真正连带责任、间接规定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先付责任、第三人责任和补偿责任等等。[3]反映到动物侵权中,便是因第三人过错导致的动物致害责任,属于第三人侵权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二、关于《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的解析
(一)责任的承担
根据《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的规定,受害人所受人身或财产损害来自动物这种危险源的爆发,且该爆发是由于第三人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情况下,受害人对此享有选择权,即既可以起诉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也可以起诉第三人。其中,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与第三人之间形成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前者在赔偿受害人后有权向后者追偿。该项规定不仅符合章节名“饲养动物侵权责任”下的动物致害责任基本原理,契合第三人侵权行为的理论构造,而且适应现代社会对受害人加强保护的需要,有助于其得到较为充分的救济。
从适用对象与范围的角度看,《侵权责任编》第九章项下所属的动物侵权责任类型均有适用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的空间,即一般动物、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动物园的动物以及流浪动物致人损害时,如果存在第三人异常介入的情形,便存在适用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的可能性。因此,在拆分因第三人过错导致动物致害责任时,要注意区分不同的动物类型,将一般要件与特殊要件相结合,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在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动物致害责任一般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还要同时适用第一千二百四十七条与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的构成要件(同时存在第三人的过错及其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如果缺乏这两项要件,就不能成立动物致害中的第三人责任。
(二)关于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的不合理主张
关于《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在因第三人过错导致的动物致害的情形下,简单地将侵权责任归咎于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既不严谨,又不符合立法精神。该主张的理由有二:1.通过考察域外相关立法,其均将第三人行为列入免责事由,包括部分免责和全部免责;2.面对“不相关”第三人的异常介入行为,不同主体对其预见和防范程度是不同的,“法不强人所难”,不同情形不可一概而论。
以上主张与理由虽然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但细细琢磨会发现其不能成立,反驳理由如下:
1.将第三人过错行为作为抗辩事由的依据,主要集中于《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其作为第三人侵权的一般性规定,在解释学上,按照杨立新教授和张力教授关于“第三人侵权行为”的观点,诸多学者对《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的解释均为“第三人过错”,即仅限于抗辩事由的讨论,而杨立新教授另辟蹊径,将其厘出并独立为一种侵权形态,张力教授对其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梳理和分类。“第三人的行为是减轻或免除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责任的事由”的主张也是仅仅局限于抗辩事由范畴,显然不够周延。对于因第三人导致的动物致害,尽管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没有过错,无过错责任仍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从人情角度看这或许有所不公,但在第三人责任中,由于相对人与危险源往往存在主体、客体或行为上的联系,即他们对动物拥有权利或利益,而不免除其责任便是享有这项“权利或利益”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况且,即便其被判决赔偿受害人,因该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其并非最终责任承担者,仍可通过向第三人追偿的途径来终局免责。
2.对于第二个主张,首先,在第三人导致动物致害情形下,损害结果全部是由第三人行为造成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按理说由第三人承担全部责任最为合理且公平。但在法律实践中,大量案例表明,案中是否存在第三人、该第三人具体是谁等问题,在取证上存在困难;即便确定了第三人,面对受害人的诸多损失,仅凭借其有限的财力物力根本无法弥补。此种情形下,如果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的责任仍旧被免除,受害人没有其他选择,这无疑是让受害人承担不能救济之风险,这对受害人非常不公平,有违民法公平原则与救济功能。其次,不免除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的责任,符合实质公平的要义,契合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设立初衷和精神。[4]“对第三人的不法行为进行区分对待”的做法无助于案件的解决,既不能按主体归责,也不能救济受害人。无过错责任的目的并不是归责,而是一种人文关怀,目的在于社会公平与和谐,而不是对过错行为的惩罚制裁。
(三)问题探讨
问题一,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在向受害人履行赔偿后,其向第三人追偿的理论支撑是什么?笔者认为,一方面,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其自身与损害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仅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即“动物这一客体属于其所有”。例如,甲拿乙的保温杯故意把丙打伤,仅仅因为保温杯属于乙所有就认定乙与丙受伤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显然不成立。同理,因饲养动物而获取了利益,该项“利益”所对应代价便是基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与第三人之间,基于第一千二百五十条之内容,因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可向第三人追偿,故在此项关系中,第三人才是处于责任链条上的最终端的那一方。
问题二,因“第三人的动物”而导致动物致害时,能否适用《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的适用前提被限定为“第三人过错行为”,而“第三人的动物”并不完全等同于“第三人过错行为”,由此在处理以上类似案件时该条文不能直接拿来适用。有学者认为此处规定存在法律漏洞,笔者认为,因法律规定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与案件情形一一匹配。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借鉴瑞士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通过类推适用的方式,①《瑞士债务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损害发生系由第三人挑动者,可得向其求偿。”;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二项:“动物系由第三人或他动物之挑动,致加损害于他人者,其占有人对于该第三人或该他动物之占有人,有求偿权。”将《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五十条中的“第三人过错行为”类推适用于“第三人的动物”。
例如以下案例:
甲牵着耕牛在田间劳作,乙的狗没有拴紧从家中跑出,看见耕牛便突然追咬上去,受惊吓的耕牛撞伤了路过的丙。那么,丙可以向谁请求损害赔偿?
1.《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第一千二百五十条之责任构成要件
具体到本案例,对照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各构成要件均已具备;且就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但书”而言,被侵权人丙并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损害之情节,甲无法依此主张“免责与减轻责任”。所以,受害人丙有权依据《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请求耕牛的饲养人甲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但是,在本案中,甲的耕牛之所以撞伤丙,是因为乙的狗追咬耕牛所致,亦即由甲之外因素所致,这就需要考察第一千二百五十条。在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动物致害责任一般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还要考虑第三人异常介入之因素,即第三人行为、因果关系。
2.丙如何行使请求权
在本案中,乙是动物致害责任当事人中的第三人。甲的耕牛之所以撞伤丙,是由于乙的狗追咬耕牛使其惊慌乱跑所致。换句话说,在本案中,动物危险的实现(即耕牛撞伤丙),并非直接因为第三人的行为,而是由于第三人的动物(即狗)所致。
在本案中,该“狗”是他人(即乙)所饲养之狗,且狗之追咬甲的耕牛,并非由于不可抗力等事由所致,乃是因乙疏忽所致,从而也就可以认定第三人乙存在过错状态。
基于上,丙在寻求救济时,由此既可对甲起诉,也可对乙起诉,请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是,丙能否对二人同时提出赔偿请求,亦即能否将甲、乙共同列为被告而予以起诉呢?
就其中的动物致害责任,即丙根据《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并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第一句来主张的情形,自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第一句之表述上看,丙在损害赔偿请求权之行使上,享有一定的选择权,既可以单独以甲为被告,也可以单独以乙为被告,而且均可要求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在甲与乙之间,则形成所谓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关系,且依《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五十条第二句之规定,甲作为“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乙追偿,而且是全部求偿权,亦即第三人乙处于终局责任人地位。且如果丙仅将其中一人诉至法院,虽然二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法院不能主动依职权追加被告。
至于丙是否享有进一步的选择权,即将甲与乙同时列为被告,学界意见不一。我们认为,比较务实的且有利于受害人丙的思路是,应允许丙如此来行使请求权,且在判决书中须指明乙须承担终局的赔偿责任,但同时又要说明在判决生效后,丙先向甲请求赔偿给付时,甲不得拒绝(可附带说明甲对乙的追偿权)。
三、《侵权责任编》中第一千二百五十条与其他条文的关系
(一)与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文论述,在第三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上,《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与第一千二百五十条之间的关系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即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构成第三人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第一千二百五十条构成第三人侵权行为的一项特殊条款。根据“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在此类案件中,第三人对受害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的同时,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也不得置身事外,而是应当按照第一千二百五十条与之并担不真正连带责任(享有最终追偿权),而不可援引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条进行抗辩,主张减轻或免除责任。
(二)与第一千二百四十五-一千二百四十九条之间的关系
根据《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四十五至一千二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可以从中归纳出:一般动物、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动物园动物、流浪动物致人损害的各自情形及其责任分配。可以看出,以上均有可能发生第三人因素介入之情形,此时,在法律适用上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综合判断其构成要件。
四、结语
在我国《侵权责任编》第九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中,第一千二百四十五至一千二百四十九条对一般动物、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动物园动物以及流浪动物致人损害的情形均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及至第一千二百五十条,随着“第三人过错行为”这一因素的介入,便产生了因第三人过错导致动物对他人造成损害的情形,使其既符合第三人侵权行为的理论构造,又能够与前面条文发生联动,其在法律适用时应当予以关注。进而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与观点均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