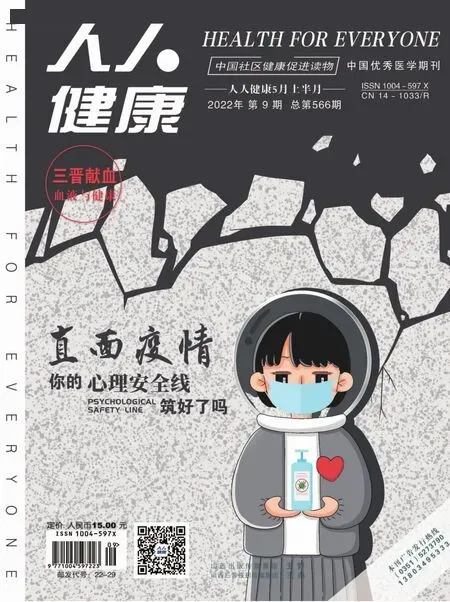D- 二聚体检测在静脉血栓栓塞症诊断中的价值研究进展
聂红娟
(贵港市人民医院 广西 贵港 537100)
VET 包括静脉血栓形成(DVT)、肺栓塞(PE)两种类型,作为临床常见疾病之一,及早诊断是治疗、改善预后效果关键[1]。纤溶系统是人体重要的抗凝系统之一,亦是维持正常血液流动必须的产物,以溶解血管中沉积的纤维蛋白为主要功能,亦可修复组织、去除纤维蛋白沉着引起的血管阻塞,D-二聚体(D-D)是交联纤维蛋白经纤溶酶作用后的终末产物,可准确反映血栓形成后溶栓的活性,为明确其诊断VET 价值,本文就相关知识进行论述。
1 D-D 的形成机制
D-D 是凝血酶及凝血因子XIII 作用的交联纤维蛋白在纤溶酶作用下产生的特异性降解物质,其可反映体内纤维蛋白的溶解能力。究其原因是当体内形成纤维蛋白凝块时,无活性的纤溶酶原会被激活成为有活性的纤溶酶,致使机体内纤维蛋白溶解过程被激活;其次将纤溶酶降解后形成纤维蛋白凝块时,会出现各种可溶性片段,随着病情的加重可出现纤维蛋白产物,研究发现可溶性片段包括:X-寡聚体、D-二聚体、片段E、中间片段等,前两种片段中含有D-D 单位,因此通过D-D 检查可明确机体内纤溶状态,亦可作为评估机体内是否形成血栓的关键原因[2]。
2 D-D 的检测方法
目前检测D-D 的方法较多,但不同检测方法使用的试剂、标准不同。查阅资料发现目前检测D-D 的方法有30 多种,但却使用20 种不同的单克隆抗体。D-D 检测方法包括抗体靶向的D-二聚体表位、捕获、检测方、仪器要求等几个方面。
2.1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过程中通过将在血浆中加入D- 二聚体抗体包被的微量滴定孔中,而后结合固定的D-D 分子并加入特异性的标记抗体,从而产生比色反应。该方案敏感度、特异度较高,因此被临床公认为测定D-D 的金标准,但实际检测过程中存在耗时、对操作要求高等缺陷。
2.2 酶联免疫荧光分析法
酶联免疫荧光分析法(ELFA)检测D-D 的设计原理与ELISA 相同,但该方案属于全自动方案,可直接检测特异性荧光抗体、D-D 结合后的荧光产物,在实际检查过程中存在周转时间快、可在单个样品上检测的优势。
2.3 乳胶测定法
血浆中D-D 与吸附D-D 单抗的乳胶颗粒结合,医师可根据形成的凝聚体进行检测,该检测方法与ELFA 操作特性相似。
2.4 全血试验法
在检测过程中将一滴全血滴在载玻片上,而后加入含有D-D、红细胞膜抗原混合双特异性抗体试剂进行检测。
从医师的角度出发,D-D 的检测方法意味着其操作特征不同,部分关于阳性D-D 诊断VTE 的方案被应用于临床,通过分析发现诊断D-D 的多种方案敏感度在69%~97%,特异性在40%~47%。因此在检测过程中需用相应的目标人群进行独立、前瞻性验证,以明确最有效诊断方案。
3 D-D 检测的意义
查阅资料发现[3],D-D 主要应用在排除诊断上,常规的D-D 临界值设定为0.5mg/L,低于临界值提示VET 发生率较低或不太可能出现VET;其次,D-D 检查阴性可安全、有效地排除约33%的疑似患者。
4 D-D 在VET 诊断中应用价值
4.1 D- D 结合临床症状在VET 诊断中的价值
研究发现[4],D-D 诊断VET 的敏感度在97%左右,但特异性不足50%(40%左右),较高的敏感性虽仅可减少VET 漏诊率,但会增加假阳性发生率。因此经相关检查发现疑似VET 患者D-D 阳性需展开进一步检查,旨在通过采血多普勒超声、CTPA 等影像学检查进一步确诊,但假阳性的出现不仅会增加不必要的超声、CT 检查,亦可增加患者经济压力,导致医院医疗资源形成浪费[5]。
临床评估VET 的方法包括VET 相关症状、体征、危险因素等,在评估过程中可按照VET 可能性大小将其分为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目前评估VET 的主要方案为Wells 评分、Geneva 评分。
针对评估结果显示VET 可能性较低的患者,若D-D 检查结果显示为阴性,则3 个月内VET 发生率在0.5%,无需进行进一步检查便可排除VET 的可能;针对评估结果显示VET 可能性较低的患者,若D-D 检查结果显示为阳性需进行下一步研究,旨在明确其是否存在VET;若评估结果显示VET 可能性为中等或较高,则不建议进行D-D 检查,可通过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直接检查。针对中危、高危患者即使不存在VET、D-D 检查结果也不会显示为阴性,究其原因是癌症、近期手术等均可增加D-D 在体内水平,尽管目前对于其他升高因素尚不明确,但其在提示有VET 可能性中具有一定意义[6]。
查阅资料发现[7],临床研究人员通过联合临床评估调整D-D 阳性临界值,提高该检查方案在临床的实用性,国外研究中将疑似VET 患者随机分为2 组,其中一组选择统一D-D 阈值组,另外一组根据临床可能调整D-D 阈值,通过对比发现3 个月内两组VET 发生率对比无统计学差异,但第二组使用D-D 检测的人数减少22%,需要影像学检查的人数减少8%。由此可见,在VET 诊断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D-D 阈值,既可减少不必要的D-D 及影像学检查,亦可节约医疗资源。但该方案不一定可安全、有效地应用在其他疾病诊断过程中,因此临床需谨慎选择,避免诊断失误影响治疗及预后效果。
4.2 PE
PE 作为各种内源性或外源性物质,在堵塞肺动脉后可引起肺循环障碍、呼吸功能障碍等问题。且该病患者临床表现复杂多样且缺乏特异性,常规检查无法获得有效、直接的证据,导致该项检查准确率较低,在临床极易出现漏诊、误诊等情况,对预后效果有严重影响,因此临床医师需注重对PE 的早期诊断[8]。
多年来国内外在PE 诊断研究中,均认为D-D检测可被应用在PE 风险评估中,且被认为在PE 诊断中极具优势。有学者认为D-D 诊断PE 敏感度在95%左右,阳性预测值在99%,经对比发现D-D 筛查PE 是合理的,其可较计算机肺血管造影优先应用PE 筛查中。目前该方案无法单一诊断PE,但对于疑似急性肺栓塞者可通过D-D 检查首先进行筛查[9]。
4.3 随年龄调整D- D 临界值在VET 诊断中的价值
研究发现,机体内D-D 水平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但随着年龄的增加D-D 的检测特异性下降。有学者指出[10],50 岁以上患者D-D 阈值可增加至年龄的10 倍,而D-D 水平高于500μg/L 但低于其他年龄调整阈值的排除PE 的可能性,此类患者3个月内VET 发生率在0.3%[11-13]。
高龄是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2014 版欧洲心脏病学会在急性肺栓塞诊断指南中明确提出根据年龄矫正D-D 临界值[14-15],年龄≥50 岁患者以“年龄×10μg/L”作为筛查VET 的标准,并指出可将D-D检查结果联合临床症状作为初步筛查VET 的方案。
4.4 概率调整的D- D 临界值在VTE 诊断中的价值
临床研究人员通过联合临床概率调整D-D 临界值,即在评估结果显示VET 可能性较低,可将D-D 标准设置为1000μg/L,在评估结果显示VET可能性为中度时,可将D-D 标准设置为500μg/L。为进一步提高评估结果特异性,可指导VET 可能性较高者实施影像学检查。
5 小结及展望
在VET 诊断中结合D-D 检查结果及临床症状有极高应用价值,且该指标可应用在VET 复发风险预测及评估过程中,为医师制定或调整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但实际应用过程中检测D-D 的方法较多,一种方案得出的结论不能简单推翻另一种检测方法,因此后期临床需对D-D 检测的操作方法、结果的标准化进行解读,为临床诊断VET 等血液系统疾病提供高质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