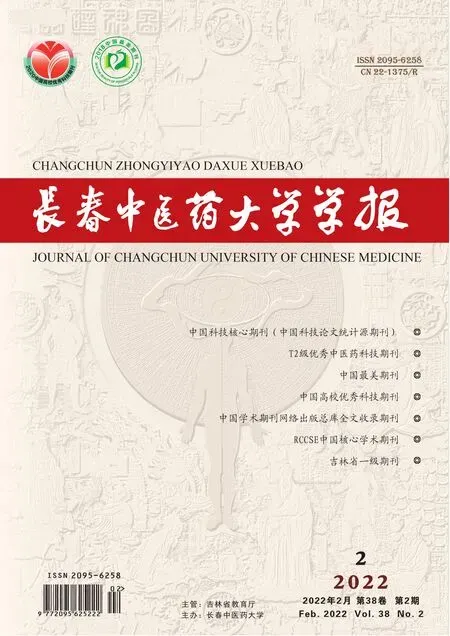仝小林院士“顶焦髓系”疾病辨治经验
陈科宇,高泽正,杨映映,宋珏娴
(1.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 100053;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3.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 100053)
《灵枢·营卫生会篇》根据脏腑的部位和功能将人体分为上、中、下三焦。仝小林院士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解剖学知识,提出颅腔(容纳脑和延髓)和脊髓腔(容纳脊髓)也应单作一“焦”,命为“顶焦”,进而将人之四腔(颅腔和脊髓腔、胸腔、腹腔、盆腔)与人之四焦(顶焦、上焦、中焦、下焦)一一对应。又根据每一“焦”脏腑经络功能之差异,提出了“四焦八系”理论体系:“顶焦”包括“神系”“髓系”,上焦包括“心系”“肺系”,中焦包括“肝胆系”“脾胃系”,下焦包括“溲系”“衍系”,将现代解剖学与古代藏象学合二为一[1]。本文所阐述的“髓系”即为“顶焦”颅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病变主要与现代医学中的中枢神经系统与周围神经系统疾病有较大的重合(病位在脑髓、骨髓、脊髓等),并可包含中医所讲的脑髓病、痹病、痿证、中风等[2]。
1 髓系的生理特征
“顶焦”包括颅腔和脊髓腔,颅腔为脑所居之处,向下与脊髓腔中的脊髓相连,两者共同组成了指挥、调节人体各种生理活动的中枢。人的精神、情志、感觉、运动都与神经系统密切相关,其物质基础就是脑和髓。仝小林院士认为脑主神,主要控制人的精神、情志;髓主经,主要支配身体的感觉和运动,并将“顶焦”分为“神系”与“髓系”。髓根据其分布不同,名称各异。肾为作强之官,主骨生髓,肾精化生,藏于骨中者为骨髓,藏于脊椎管内者为脊髓,上行入脑者为脑髓。其主要生理功能包括:
1.1 充养脑
“脑为髓之海”“诸髓者,皆属于脑”“灵机记性在脑”“所以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髓为奇恒之腑,藏而不泄,以先天之精为主要的物质基础,赖后天水谷精微的补充,由肾中精气化生后,沿督脉上行入颅聚于脑,与脑相连,起着充养脑的重要功能。脑得髓充养则脑力充盛,思维活跃,博闻强识。
1.2 主经,司运动
仝小林院士认为,髓为周围神经系统之主,亦为中枢神经系统之用,主要调控肢体的感觉与运动,与经络、肌肉、骨骼等密切相关[3]。髓海充盈,则感觉灵敏,肌肉丰盈,活动自如。
2 髓系病理特征
2.1 易受外邪侵袭
髓系支配着机体的感觉和运动,与皮肤、肌肉、五官等感觉和运动器官直接相连,故外邪易通过官窍、玄府侵袭髓系。六淫邪气可通过人体官窍侵袭髓系。头为诸阳之会,风为百病之长,风邪常夹杂他邪,侵袭头部,伤及髓系。
2.2 多虚亦有实
髓由肾精化生,由五谷精微滋养,容易产生不足的情况。先天肾精不足,后天调养失当,年老体弱,疾病损耗等均可造成髓海空虚。饮食不节,起居失常,劳役失当,情志内伤都会导致髓精暗耗,髓海空虚。髓系病性属实者多由外邪侵袭、病理产物入络引起,主要由风、寒、湿、痰、火、毒、瘀、外伤导致,从而产生异常亢奋的状态,如肢体的痉挛、抽搐[2]。
2.3 以不足和亢奋为两种病理状态为主
髓海不足,则思维迟钝,记忆力下降,肢体瘫痪、痿软无力;髓海有余,则肢体痉挛抽搐,强直僵硬。
总之,髓系疾病,邪气侵袭是外因,脏腑内虚是内因;病性多寒多虚,但亦有实性病变;临床表现以不足(迟钝、瘫痪、痿弱)和亢奋(痉挛、强直)为两种主要病理状态。
3 髓系病证辨治概要
髓系疾病涵盖范围较广,髓充养脑,主司运动,既包括了中医学与脑相关的病证,也包括了和运动相关的病证,与西医学中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脑卒中、头痛、脊髓损伤、脊髓空洞症、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等)和周围神经系统疾病(如格林-巴利综合征、多发性肌炎、重症肌无力、运动神经元病等)有较大重叠。髓系疾病以不足和亢奋为两种主要的病理状态,所以“刚柔”辨证为髓系疾病的辨治总纲[4]。“刚”指亢奋的病理状态,包括痉挛、强直、躁狂等亢奋性的病证;“柔”指不足的病理状态,包括迟钝、瘫痪、无力等亏虚性的病证。在临床用药上,仝小林院士常用三黄躁狂煎、四逆散、四逆汤、葛根汤、大小续命汤、补阳还五汤等治疗髓系疾病,如用葛根汤治疗外邪客于经络之刚痉,瓜蒌桂枝汤治疗外邪客于经络之柔痉,大小续命汤、补阳还五汤治疗瘫痪病、痿病等[4]。髓系不同病种各有不同的病理特点,病因病机及辨治方法不尽相同,且大多均已形成完善的辨治体系。
3.1 明辨病性,补虚泻实
仝小林院士认为,脑髓病当先辨虚实。水谷进入人体后,化生为气血,浓缩成精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变为脑髓。脑为髓海,脑髓起着充养脑的作用,故脑髓病变是髓系疾病的重要组成部分。虚者或先天肾精不足、脾胃虚弱,生化无源,髓海不充;或年老体衰,肾精亏耗,髓海渐空;或后天饮食不节、劳倦思虑过度、久病消耗,生化乏源,暗耗精髓。以虚为主要病理状态的脑髓病,填补脑髓为主要治则。地黄饮子是填补脑髓的专方,原用于治疗喑痱,具有阴阳双补、添精补髓的功效,故仝小林院士将其广泛用于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病等。配合龟鹿二仙胶,疗效更佳。若阴虚甚,方中生地黄可用至60 g。仝小林院士常用自拟方仝氏通脊益髓丹:鹿茸片60 g,龟板胶120 g,金毛狗脊、骨碎补、补骨脂、干地黄各90 g,三七、肉桂各60 g,黄芪180 g,牛脊髓120 g(焙干研粉)制水丸,黄酒送服,治疗脊髓空洞症、肌萎缩侧索硬化、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脊髓损伤等“髓系”虚证[4]。
髓系疾病多虚亦有实。风、寒、湿等外邪侵犯人体,或久病体虚,体内气机失常,湿、痰、瘀等有形病理产物蓄积,导致实证或虚实夹杂。治疗上,实证以祛邪为要,因势利导,散邪外出;虚实夹杂以祛邪扶正为主要治则,在补精填髓的基础上,加以利湿、清热、祛痰、化瘀等治法,标本兼治。如治疗湿热成痿(腰以下痿软,行走不正,或瘫软不能动,两足欹侧),可用清燥汤清热燥湿。此方源于《脾胃论》,对空泡性脊髓病疗效显著[4]。
另外,仝小林院士总结诸多治疗髓系病证的“三味小方”,如治疗小儿五迟、五软,妇女产后精血亏虚,老年脑髓空虚等,常用鹿胎膏3 g,阿胶9~ 30 g,紫河车 3~6 g,制膏服用[5]。治疗老年痴呆症,常用鹿茸片3 g,龟板15 g,牛脊髓 1 条煮汤服[6]。治疗脊髓空洞症,常用仝氏益髓起痿汤:鹿茸粉3 g,鲜牛脊髓粉(冷冻干燥)6 g,黄芪粉9 g,混匀冲服,同时服用金匮肾气丸或地黄饮子,疗效更佳[7]。
3.2 明辨病位,透邪外出
髓有脑髓、骨髓、脊髓之分,髓藏于骨、椎管中,与肌肉、骨骼的运动密切相关,与西医学中的周围神经和肌肉病变相类似。痹病是指外邪在机体正气不足、卫外不固的基础上乘虚而入,以致脏腑经络气血痹阻而产生一系列疾病[8]。
仝小林院士认为,风寒湿邪气在伏邪致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结合痹症理论,提出“脏腑风湿”学说,即人体感受风寒湿邪,或通过五体而内传,或通过官窍而直中,使得风寒湿邪留而不去,伏于脏腑而成痼疾,每于复感、伏邪引动造成疾病的加重或反复[9]。而髓系易受外邪侵袭,当风寒湿邪气侵袭机体,伏于肌肉,进而深入经络,传及脏腑,这类神经系统疾病即为“髓系风湿病”,接近于西医学中慢性格林巴利综合征、运动神经元病、脊髓胶质瘤、小舞蹈病等。仝小林院士认为,痹为痿之渐,痿为痹之极,痹病在表,由风寒湿外感而来,病位在经络血脉,虽有内伤但仍以外感为重;痿证在里,多由素体虚弱、髓海空虚加之外邪侵袭所致,以内伤为主。在治疗上,“髓系风湿病”以复感为透邪之机,运用温阳、补中、除湿、散寒等方法,适时以透邪为要。若髓系疾病患者初期应用激素治疗,病机则转为本虚标实,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此时须用三黄泻心汤、二陈汤等药物涤痰驱邪,先治标实,此法驱邪不伤正;后期治疗多选用独活寄生汤、大小续命汤等加减以祛风散寒,扶正祛邪[10]。
痹病又可分为五体痹与五脏痹[8]。五体痹病位较浅,正虚不固,风寒湿邪侵袭肌表,致人体经络闭塞、营卫失和,由浅至深形成皮痹、肌痹、筋痹、脉痹、骨痹。痹病治疗时需分在经在络。在经者病位较浅,治疗上以透散邪气、驱邪外出为要,同时固护脏腑,防止邪气内客脏腑。如因外感寒湿急性起病的风湿性关节炎,可以汗法驱邪外出,方用麻黄加术汤[11]。若久病入络,风寒湿与痰瘀互结,则在透邪基础上兼以化痰消瘀,活血通络;对于脏腑功能虚损,年老体弱,气血阴阳不足者,则应在透邪基础上兼以扶正,内外并治,攻补兼施,托邪外出。如由外感寒邪所致的肩周炎,治疗时常用黄芪补气,配伍桂枝、当归、鸡血藤、羌活、片姜黄等温阳活血、祛风通络。
若五体痹治疗不当,或病邪直中脏腑,形成五脏痹,仍然要以透邪为要。邪气进一步深入,便可致痿。痿病的病因较为复杂,除正气亏虚,精髓不充,外邪侵袭外,饮食劳倦、情志内伤均可致痿。若邪气伏留督脉脊髓,闭阻气血,致肢体瘫痪、痿弱不用,常用葛根汤加乌头、鹿茸壮阳通督。若痹、痿病在颈臂,常用葛根汤加减,发汗解肌;病在腰膝,常用三痹汤加减(独活寄生汤去桑寄生,加黄芪、续断、生姜等),补益肝肾,补养气血。
仝小林院士喜用九分散化裁治疗痛痹,不论其寒热,在原有辨证方的基础上,一般加生麻黄6~9 g,制乳香、制没药各6 g,制马钱子粉0.6 g(研末分冲),将其作为止痛药使用。若疼痛剧烈,还可加川乌15~60 g,及芍药甘草汤。仝小林院士认为,芍药甘草汤是缓急止痛的专方、效方,常用其配伍葛根、松节治疗肩凝症;配伍桂枝、鸡血藤治疗不安腿综合征;配伍川乌、乳香、没药治疗关节痛;配伍吴茱萸、黄芪治疗虚寒性胃痛(为痉挛性剧痛);配伍川楝子、青皮治疗胁肋胀痛。在用量上,治疗脏腑痛时,白芍用量30~45 g,甘草15 g;治疗经络痛时,白芍30~120 g,甘草15~30 g。仝小林院士自拟仝氏益气通络汤:炙黄芪30 g,川桂枝15 g,鸡血藤30 g益气温经活络治疗以疼痛、麻木、肢凉为主要表现的肢体麻木,若疼痛、肢凉明显,加制川乌;若麻木明显,加川芎[4]。对于各种外伤、内伤引起的瘀血疼痛或痹病疼痛,则用化瘀定痛散止痛,或配以辨证汤药使用,方药组成:制马钱子、生麻黄各3 g,生大黄6 g,三七、血竭、制乳香、制没药、苏木、梅片各9 g。
仝小林院士对于藤药亦有应用心法,认为藤蔓是经络药,治疗经络病。常用鸡血藤、首乌藤之类温通经络,治疗经络受寒;用忍冬藤、络石藤之类凉经散络,治疗经络郁热;用雷公藤、天仙藤之类治疗以红肿热痛为表现的关节风湿。凡是经络关节不通者,用麻黄、桂枝;疼痛者用乌头;气虚者,用黄芪。
3.3 分期论治,先辨阴阳
仝小林院士认为,脑卒中以内伤积损为基础,以外邪侵袭、饮食失度、劳倦不调、情志不遂等为诱因,以风、火、痰、气、瘀为主要病理因素,导致阴阳失调,气血逆乱,上冲犯脑,神窍闭阻[12]。并根据解剖部位和临床表现,将脑卒中归为“四焦八系”中的“顶焦髓系”病范畴[1]。
中风首先应分阴阳。阴性起病,治以温通补气疏络,予大、小续命汤,加以黄芪、地龙之类;阳性起病,治以通腑化痰祛瘀,予承气汤、导痰丸、抵挡汤类。如患者体型肥胖,脉来洪大者,予小续命汤宣肺利水;痰邪厥逆而上,腑气不通者,予桃核承气汤合三生饮化痰通腑。若患者脉压差大,脉弦细而数,为阴虚阳亢之象,予镇肝熄风汤滋阴潜阳;阳闭患者,予安宫牛黄丸、紫雪、至宝丹开窍醒神;脱证患者,予参附汤回阳救逆。在方药运用方面,大、小续命汤是六经中风的通用方剂,尤其适合由寒冷诱发中风的老年动脉硬化患者。仝小林院士自拟“起颓汤”以起颓补气,治疗中风后遗症期患肢瘫软无力,肌肉萎缩之气虚络瘀证,药物组成:黄芪30~120 g,川桂枝9 g,陈皮9 g,三七6 g,天麻9 g,川芎30 g,鸡血藤30 g,地龙粉、全蝎粉、水蛭粉各1 g(分冲)[4]。
此外,仝小林院士还提出以“态靶因果”理论作为中风病的辨治方略。在把握中风病各阶段的基础上,分期分类分证,宏观“调态”,微观“定靶”,筛选靶方靶药,态靶同调以期提高临床治疗的精准性。根据疾病的发展过程,将脑卒中分为中风前期(一级预防),急性期,中风后期(二级预防),每一期下又可分为实态和虚态,态之下再分证,最后根据证选择靶方、靶药,提高治疗的精准性。如急性期实态中,桃核承气汤是痰热腑实证的靶方;急性期虚态中,镇肝息风汤是阴虚风动证的靶方;中风后期虚态为本,实态为标时,补阳还五汤、起痿汤合黄芪、地龙是气虚络瘀证的靶方靶药。同时在治疗时兼顾前因、后果,审因论治,既病防变,共奏态靶同调之效[12]。
4 小结
“顶焦髓系”功能主要在于充养脑,调控人体的感觉和运动。髓系之病,正气内虚是发病基础,邪气侵袭是外在条件;病性多寒多虚,但亦有实性病变;临床表现以不足和亢奋为两种主要病理状态。临床诊疗皆以刚柔为济,补虚泻实,适时以透邪为要,先别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