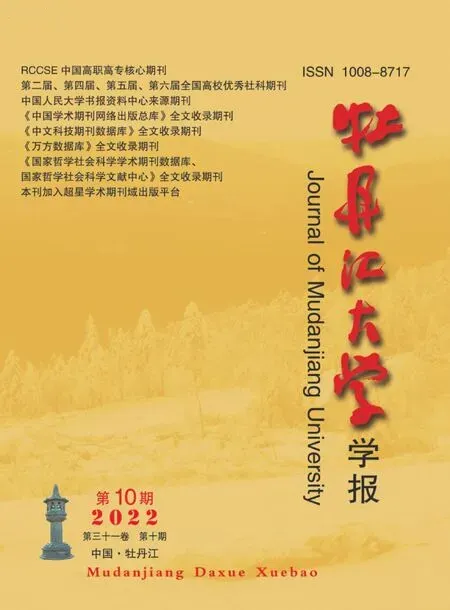《苹果树》中的女性符号
陈 晨
(伊犁师范大学,新疆 伊宁 835000)
一、引言
曾于1932年荣获诺奖的约翰·高尔斯华绥,至今依然保有着其显而易见的文学影响力,众多作品之一的《苹果树》(又称《仲夏之恋》)就是其中之一。文本叙述的爱情故事外表简单但意境极为丰富,而这一点又是通过作家在隐喻和象征之间的不断切换而达到的。可以说,这是一部透过表层阅读进入深层阅读的文学作品。通过其独具一格的艺术手法,高尔斯华绥的作品道出了爱情的本质性难题。同时,也通过这样的难题,作品为我们揭示了爱情为何只有在与社会机制联接在一起时,才能显示自身的复杂性。这样的问题也将读者最终带向了不脱离社会政治语境下的爱情对女性具有的哲学意义。
二、在隐喻与象征之间的“苹果树、歌声和金子”
隐喻和象征是文学作品中重要的表现手法,整个文本的意义构筑以及创造性联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张力。“苹果树、歌声和金子”在文本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开头,一次是结尾。在开端和结尾处安排这样的隐喻和象征确实有着作者独具匠心的创造性,同时这样的安排也是文本之所以如此具有思想魅力的原因之一。隐喻和象征是和意象交融在一起的,“意象是一个既属于心理学,又属于文学研究的题目,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或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而这种重现和回忆未必一定是视觉上的。”[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开端的“苹果树、歌声和金子”作为文本的意象是主人公爱舍斯特对于过去的心理回应,这种心理回应同时也是对于他现在美满生活的一种滑稽而又合情合理的讽刺。
这样的意象隐喻了他现在处于上层社会的安逸而又丰实的生活状况,象征了这样的生活总是缺少着什么。缺乏的心理特征是欠缺安全的心理反映,在结尾处当爱舍斯特看过妻子斯苔拉的速写,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时才觉悟到自己忧虑和无助,这样忧虑和无助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终究不能获得“苹果树、歌声和金子”的赏赐,因为他的心灵不能平静。“我们的‘隐喻’整个概念中的四个基本因素似乎可能是类比、双重视野、揭示无法理解却可诉诸感官的意象、泛灵观的投射。”[1]文本中主人公爱舍斯特脑海中所出现的这三个隐喻和象征可以分别对应这里的“无法理解却可诉诸感官的意象”和“泛灵观的投射”“苹果树”隐喻了苹果树下的约定,然而这个约定最终只能是可怜梅根一个人的信条,“歌声”象征了在大自然下纯真爱情的甜美,这样的甜美只有梅根一个人独享,“金子”象征了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梅根自己或者是她善良双眸里对纯真爱情渴望的泪水。
这一切流淌在年轻爱舍斯特的体内,现在却已经枯竭。由于梅根自杀,爱舍斯特在重新来到这片土地上看到那徜徉在大自然怀抱里的坟地时已经难以自制内心的情感,他苦痛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物是人非,唯有梅根即“苹果树、歌声和金子”始终未变。梅根躺在这片纯洁的土地上,爱舍斯特还活着,一生一死之间存在着多少的苦痛,梅根已经远离了痛苦,而爱舍斯特本人将继续活着。文本里的《希波吕托斯》在爱舍斯特想来是绝对真实的,爱神终究让一切变得公平,死的人还活着,而活的人就快要死去。“苹果树、歌声和金子”属于梅根本人,梅根就是“苹果树、歌声和金子”。
隐喻和象征之所以能产生如此的张力以及由此而生的意义就在于隐喻和象征不像一般的文学表现手法那样语义界限明确。隐喻和象征和心理特征联系密切,外在的感官世界通过隐喻和象征内化为心理的解读,中间的介质含混不清从而使得隐喻和象征突破了表面意义的约束,产生了有力的思想多源性。在文本中“苹果树、歌声和金子”还可以和自然联系起来,梅根住的地方是自然的净土,当爱舍斯特来到这里时心灵也为之一振,这样的净土使得爱舍斯特所向往的爱情出现在这里。除此之外,“苹果树、歌声和金子”可以预示一切美好的东西,含义可以扩大,意义可以丰富。文本中有很多处描写这样的美景,如“他躺在草地上。从田野里金凤花的绚丽灿烂和橡树的金光闪烁,到这灰色山岗下的虚无缥缈的空灵之美,这一切使他充满了一种惊异之感;什么都不一样了,只有潺潺的流水声和布谷鸟的歌声没有变。”又如“月亮刚刚升起,十足的金黄色,挂在山上,从灰树半裸的枝干所构成的栅栏后面窥视着,像一个明亮有力的精灵注意着周围的动静。”[2]“苹果树、歌声和金子”分别代表了实物、声音和颜色,这三个概念各具美感,仿佛能涵盖世间一切美丽的东西。同时在“苹果树、歌声和金子”隐喻和象征时也存在着深刻的对比,因为最美的梅根离开了这个世界,一方面“苹果树、歌声和金子”在梅根离去之后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梅根离去之后“苹果树、歌声和金子”已经没有梅根在的时候美丽动人了。
“苹果树、歌声和金子”具有丰富的隐喻空间,如苹果树可以象征大自然,歌声可以象征自然界一切美丽的声音,金子则可以象征月亮,也可以象征自然界的太阳。这种亦幻亦真的画面让爱舍斯特留恋忘返,他的理想主义情怀,他的骑士精神确实在当时出现在他的内心,在那时他还是试图打破一切陈腐观念的青年,他爱好文学,他对世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只是因为他可以在“苹果树、歌声和金子”里找到他真实的自己。甚至在他遇到美丽纯真的梅根时他也在内心中起誓梅根就是他要找的天使。那时的他看到了苹果树,听到了歌声,生活的色彩是金色的。大自然里的农庄没有都市的龌龊和肮脏,农庄里的梅根没有都市女人的娇媚和肤浅,爱舍斯特爱上了这里,爱上了这里的梅根,因为梅根让他切实地感受到都市没有的“苹果树、歌声和金子”。他的朋友加顿没有驻足停留,也许加顿早已明白自己不属于这里,只是爱舍斯特抛开一切陈腐观念的想法之后,大胆地爱上了梅根,这样的爱属于自然的爱。
当自然的爱再一次遇到都市的爱之后,爱舍斯特发觉自己对梅根的爱只是幻象里的爱,那种真真实实的爱只能从斯苔拉那里获得。爱舍斯特心中对于梅根和斯苔拉的对比已经将自己和梅根划清界限,他的理智让他失去了他真正渴求的纯洁之爱。在这里,并不能说明爱舍斯特对于斯苔拉的爱是虚假的,但是这种对比本身就含混着利益的交换,只是爱舍斯特并不愿真实地表现出来。也许他对斯苔拉的爱是真爱,但是这样的真爱是否能够像对梅根那样来得轻松而又真实,舒服而又愉悦?这是一个他内心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许他从和斯苔拉在一起的那一天起就把这样的问题搁置了起来,但是爱神的报复,梅根的离去,这一切又让他从新审视了自己。他的妻子斯苔拉生活在都市里,她没有“苹果树、歌声和金子”的色彩,爱舍斯特明白这一切,对妻子的一吻也许只能算作妥协的安慰,只是斯苔拉并不知情。文本最后斯苔拉问道爱舍斯特她的素描好像缺少什么时,爱舍斯特的回答真实地说出了答案,缺少了“苹果树、歌声和金子”,也缺少了爱舍斯特曾经的爱情,缺少了很多,只是这时的爱舍斯特已不是曾经的爱舍斯特。梅根虽然离去,她却依旧在这“苹果树、歌声和金子”的世界里体会着自然之神对她的爱意。
三、爱情:走向一种理智的疯癫?
文本中梅根对于爱舍斯特的爱情是理智的,然而在爱舍斯特抛弃梅根之后,梅根的表现又确实是疯癫的。由于梅根对于爱情的激情造成了她自己的疯癫。“激情使疯癫成为可能,但疯癫却以一种特有的运动威胁着使激情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疯癫属于这样一类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规律受到损害、歪曲和破坏,从而表明这种统一体既是明显的和确定的,又是脆弱的和已注定要毁灭的。”[3]
文本中老夫对爱舍斯特描述梅根死去的样子时说道:“那姑娘躺在水里。有一棵从石缝里长出来的金钟花正好落在她的头上。我看着她的脸,十分可爱,十分美丽,像孩子的脸那么平静——真是美极了。”“那时候已经是六月份了,可是不知道那姑娘在什么地方找来一些苹果花,插在自己的头发里。所以,我认为她肯定是着了迷,才会被淹死。一定是这样的!水还不到一英尺半深呢。”[2]梅根是这样安静却又以一种理性般的姿态讽刺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带一点的挣扎,然而她对于爱舍斯特的爱,这样的激情,却毁了她美好的人生。“在疯癫中,灵与肉的整体被分割了:不是根据在形而上学上该整体的构成因素,而是根据各种心象来加以分割,这些心象支配着肉体的某些部分和灵魂的某些观念的荒诞的统一体。这种片段使人脱离自身,尤其脱离现实。这种片段因本身的游离状态而形成某种非现实的幻觉,并且凭借着这种幻觉的独立性把幻觉强加给真实。”[3]梅根确实变的疯癫了,当爱舍斯特离她而去,她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将幻觉变成真实,想象着自己的婚礼,也许她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想象着她在柔软而又安全的水域中经历的一切和爱舍斯特的美好,只是她真的不能分清楚这里面的真假和虚幻。她的疯癫只因为激情在爱情里占据了主导地位。
爱情所具有的能量可以撼动一个人健全的理智,毁灭理智的同时也就毁灭了她自己。梅根的疯癫是个人无法解脱爱情苦痛时的症状,当梅根将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份爱情上已经预示了她的疯癫。疯癫是病理性的还是心理性的在这里不能做过多的阐述,只是梅根这个可怜的姑娘最终难以逃过爱情的纠缠。感性和理性这个纵观古今的话题再一次在爱情里被提了出来。感性孕育着非理性,而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个人面对世界时的一种自救的态度。人只有在非理性中才能寻找到波涛汹涌的存在之流。正是因为梅根无法诉诸于理性,因为在爱情面前理性有着天生的软弱性,当梅根诉诸于感性却被一直以来的理性牵的东倒西歪,找不到方向,这样一种对于爱情的不适症状在每一个人心中都存在着。我们再次审视这样的爱情时又遇到我们面对的问题:疯癫是爱情的合理反映吗?
《哈姆雷特》里的奥菲莉亚离开世界时确实和梅根有几分相像,但是奥菲莉亚的疯癫却和梅根不一样,奥菲莉亚的疯癫是对生活中许多她难以解释的爱恨情仇的焦虑之后的抉择,梅根则是爱情缺失症的受害者,奥菲利亚的疯癫不仅仅是哈姆雷特造成的。疯癫的梅根不是精神病人,她只是一个理性世界之外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对于梅根来说是真实的也是可信的。精神的涌动已经突破了意识流的界限,深藏在心底的渴望从新为自己创造爱的国度。在这样的过程中,梅根化作了爱神自己。疯癫只是理性规约下的言语,当剥除言语的污秽,真相就更进了一步。任何试图去进行再创造的努力只会在死亡面前停下脚步,梅根停下了脚步,她拥抱了死亡。她的疯癫成为了她对于爱情的幻想。
四、女性-符号:从诱惑到控制的资产阶级
“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艺术不仅重现生活,而且也造就生活。”[1]如果从社会性质的角度来看女性地位的话,《苹果树》这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下女性卑微的地位。在伍尔芙评价小说的论文中,她曾戏谑道:“高尔斯华绥先生一定会拼命算计女人所处的阶级,以及她和社会乃至整个时代的关系。”[2]从这点看来,《苹果树》确实将女性在资产阶级下的从属地位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处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最常见的办法是把文学作品当作社会文献,当作社会现实的写照来研究。”[1]
主人公爱舍斯特作为资产阶级的化身,原本在和朋友加顿徒步旅行结束后回到伦敦这个充满着资产阶级气味的都市,然而因受伤不得不在一个农庄停下来疗养几日。在这里,爱舍斯特的理想主义和骑士精神被美丽的大自然焕发了出来,似乎从那时起,爱舍斯特就有意疏远他的资产阶级身份。这时的爱舍斯特心中充满了人道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怜悯之心相悖。爱舍斯特后来对梅根的抛弃也说明梅根不再存在可利用的价值。在文本中当爱舍斯特离开梅根准备帮她买衣服遇到哈利德一家人,在车上看见远处梅根跳下车时,他进行了一番资产阶级的自我安慰“这次看见梅根,这能有什么变化呢?自己离开她,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要怎样做才能显得不那么丑恶呢?毫无疑问,自从遇见哈利德一家人之后,他已经渐渐地确定他不会跟梅根结婚。如果他们结合的话,那不过是一段荒唐的恋爱生活,一段不安的、懊悔的、艰难的生活—件接着—件。他就会感到厌倦,只是因为梅根给了他一切,梅根是那么单纯、那么值得信任,那么像朝露一般温柔。而朝露是会渐渐消失的!”[2]
哈利德一家人是资产阶级家庭,如果与之结缘的话想必对他以后的生活不会造成困难。然而梅根作为农庄的一个质朴漂亮的女孩,是没有办法理解所处的社会性质给个人造成的压力这一实质问题的,就像爱舍斯特自我宽慰时说她像朝露一般温柔,而朝露是会渐渐消失的!梅根无法解决资产阶级为她部下的重重阻碍,一旦她做不到资产阶级要求她做的,那么她就会消失。作为女性的梅根没有权力获取自身与外界社会的平衡,这种平衡的代价是价值交换。试想如果真的爱舍斯特将梅根带到伦敦,那么她的结局是否会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一样,或者是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我们看到爱舍斯特身上有着《红与黑》中于连的潜质,但是他却更像《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认清了社会现实,有着对这个社会不抱有任何幻想的理智态度。梅根的自杀宣布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胜利,宣布了爱舍斯特的胜利。
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存在着很多约束人性的性质。人的心理情节不愿在享受的过程中度过,过程必须有着创伤一般的刺激才可以使人获得愉悦感。这种创伤可以是人自我创造的,也可以是社会添加的。在这里梅根的创伤来自于社会,通过社会所制造的创伤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世界里。作为男性的爱舍斯特在梅根和斯苔拉两个女性间选择了斯苔拉,对于选择主导权为爱舍斯特带去了愉悦,虽然他知道离开梅根会很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抵不过选择斯苔拉的愉悦。福柯认为欧洲近代认识发展中经历了三种类型的文化(认识型)。第三个认识型是19世纪以后,着重于历史性的根源分析,追求事物的本质。认识型决定了知识,知识决定了人;认识型决定了社会的形式,社会形式又决定了人。在认识与社会发展上,人都不起作用了,所以人就消失了,人的时代结束了。梅根被社会决定了,真正的梅根,真正的“苹果树、歌声和金子”消失了。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妇女交换也是社会的一种符号运作,因此男人必须把自己的姐妹嫁出,同时要娶异族的女子为妻,这样,他们就容易与其他的氏族结为联盟。婚姻成为了巩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涉及到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直系的亲属和父母。男女则成为整个社会符号体系之内的被游戏者,成为符号链的一部分。从这里看出,不管是梅根还是斯苔拉,他们都成为男权时代统治下的社会符号,只是起到了巩固社会关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爱舍斯特或许没有这么深刻的觉悟,但是由男权时代建立的社会已经将女性的命运放在了游戏规则里,作为符号的女性在游戏规则里被牢牢掌控。梅根和斯苔拉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她们的命运已经注定。生活在大自然里的梅根遇到了一个来自城市的青年爱舍斯特,两个阶级的矛盾必然会在两个人的爱情里加剧,只是梅根没有意识到。她的善良,纯真自在和自然的美相得益彰,只是爱舍斯特不属于这里。爱舍斯特曾以为他可以越过阶级阻碍,但是当他遇到出生于同一阶级的斯苔拉时,他内心里已经明白他的灵魂已被腐蚀,他不属于那个大自然的农庄,他不属于梅根。这些内化为性格层面的意识状态已经被改造的不能适应天然的原始心灵,爱舍斯特离开了梅根,离开了那个真正的自己。梅根的纯真心灵遭遇了来自资产阶级社会爱舍斯特的压制。
爱舍斯特由于阶级性的原因很难将自我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梅根,梅根没有受过资本主义的教育,在她心中没有阶级属性所烙下的性格特征。电影《一只安达鲁的狗》就曾经形象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教育的扭曲和变形,爱舍斯特是经过这样教育的毕业一年的大学生,而梅根是“苹果树、歌声和金子”的化身,她没有收到异化教育的影响。当这两位出身不同阶级的人走到一块时,爱情一时间剔除了阶级的顽固成分,他们欣喜地在苹果树下约定。然而当爱舍斯特看到哈利德一家人时,他服从于阶级教育的控制,认为他对梅根的爱情靠不住。这样的自我意识不得不说是阶级教育的胜利。作为女性的梅根当性别上收到压制的同时阶级属性也受到压制。梅根相对于爱舍斯特来说是自由的,因为梅根没有受到异化,没有经历强制改造,然而她的不幸就是因为她遇见了爱舍斯特这样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青年。爱舍斯特离开梅根后与斯苔拉的生活里是否能想到梅根,恐怕很难想到,虽然在文本的开端他不同意他的朋友加顿的话,但是他确实就是像加顿所说的那样在过着他的生活,他的朋友加顿说:“老朋友,咱们现代的一切不幸都是来自怜悯。看看动物,还有印第安人,他们只是感觉到自己偶然的不幸;再看看我们自己,总是免不了要为别人的不幸担心。让我们别再为别人的不幸担心了,这样的日子会过得快乐些。”[2]
五、结语
相比较爱舍斯特,梅根对于爱舍斯特的爱是真真实实的付出,然而这个“苹果树、歌声和金子”一般的姑娘却遭遇了资产阶级的冲击。梅根没有易卜生笔下的女性人物娜拉那样勇敢,她所居住的童真世界受到重创,她没有能力恢复过来,这一切却只和她的阶级出身有关。当然,可以设想另一种可能,就是梅根从重创中恢复过来,依然可以满怀信心地等待属于自己的爱情。如果真是如此,作为“苹果树、歌声和金子”的梅根等待的就是一种社会的变革。
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首先在隐喻和象征的层面揭示了女性人物的生命维度,其次,在从理智向疯癫的过渡中突显了女性爱情在面对现实社会处境时的复杂性,最后,借助剧中人物阶级属性的划定,指明了女性自身从原始自然的隐喻角色向资产阶级价值符号的转变过程。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将小说诗学与阶级批评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得作品面对女性身份的问题,并没有走向意识形态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