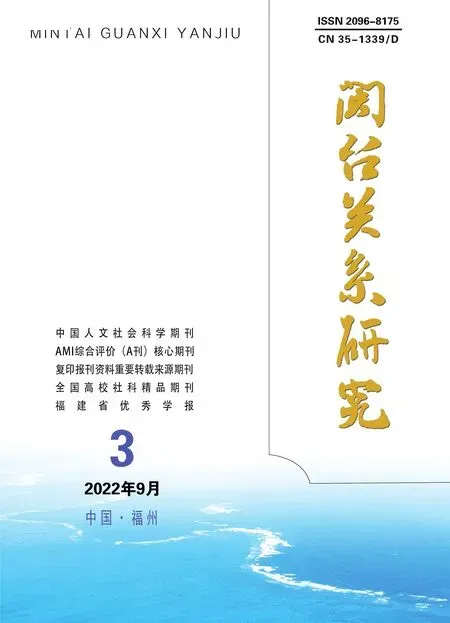中美竞争下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构”与美台关系走向
俞婧婷,何达薷
(1.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2.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实行“双轨政策”,在两岸之间维持“战略平衡”。一方面,中美签订三个联合公报(即1972年“上海公报”、1978年“建交公报”和1982年“八一七公报”,以下部分简称“三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无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另一方面,在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美国于1979年出台“与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以国内法的形式同台湾地区保持并发展“实质关系”。[1]这就是美国长期以来遵循的以“三报一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2017年以来,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由“合作”转向“竞争”,其对台政策亦随之出现重要变化。在保持基本政策层面“一个中国政策”不变的同时,美国不断提升台湾在对华竞争中的战略地位,通过对台“六项保证”(Six Assurances)的“公开化”和“政策化”及出台一系列重要“友台法案”,不断侵蚀“一个中国”内涵,其对台政策呈现“重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构”不是解构原有政策框架后的“重新建构”,而是在原有框架基础上的“扩容”和“重组”。6年来,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构”大大降低了原来“三报一法”政策框架对美台关系发展的限制,也使美国获得了利用“台湾牌”的政策便利。这不仅直接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还造成台海局势的日益紧张。
一、中美竞争下美国对台政策“重构”的战略考量
美国对华战略是影响美国对台政策考量的决定性因素,2017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重构”主要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需要。特朗普(Donald Trump)任期内,随着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竞争,美国在重视台湾“工具性”价值的同时逐渐重视台湾的“战略性”价值;随着对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拜登(Joseph Biden)上台后美国则更强调台湾的“战略性”价值。
(一)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战略考量
以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报告发布为标志,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出现重要战略转向,由原先的“战略接触”转向更具遏制性意味的“战略竞争”,并以实际行动展开一系列竞争攻势。部分学者从地缘政治视角阐释了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原因,认为驱动美国对华战略转变的根本性动因在于21世纪以来中美实力差距缩小引致的美国“霸权担忧”与“地位焦虑”。[2-4]出于维持“全球霸主”地位的战略考量,2017年以来美国在对外战略上聚焦大国政治,在全球层面实行“有策略的战略收缩”,同时加大对中国的“战略进攻”。继特朗普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战略竞争者”(strategic competitor),相继出台的《美国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ure Review)、《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等文件不断补充,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在特朗普时期逐渐明晰。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框架逐渐成型,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断提升台湾作为对华“讨价还价”筹码的交易性价值。特朗普执政期间,不管是在中美贸易争端“如火如荼”之时签订史上金额最高的对台军售案,还是在叫嚣中美“脱钩”时频繁发表有关台湾问题的激进言论,抑或是在即将卸任之际取消所谓“美国对台湾所有的交往限制”,都体现了特朗普政府对“台湾牌”的运用。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逐渐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美国重要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就在年度报告中专门设置“特朗普如何提升美台关系”章节[5],声称“台湾是亚太地区的‘民主源泉’(democratic kindred spirit)”,与中国大陆有着“根本不同”,特朗普政府应当从“提高台湾政治地位”“扩大美台经贸关系”等方面加强美台关系,确保“从富有进攻性的‘威权中国’(authoritarian China)手中夺回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则多次公开表示,相较于冲绳或关岛,台湾的地理位置更接近东亚大陆和南海,可以为美军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以便需要时在整个地区快速部署,特朗普政府需要重新审视“一个中国政策”,并通过打“台湾牌”谋取战略利益。[6]出于以上考量,特朗普政府逐渐将台湾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有利抓手”,并从实际行动上将台湾纳入旨在遏制中国发展的“印太战略”。例如,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就将“与台湾保持牢固关系”写入“印太”章节,并且强调会“根据‘与台湾关系法’所作出的承诺,向台湾提供防务需求,满足台湾的战略防御需要和威慑力”。[7]因此,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兼具了“工具性”与“战略性”的双重特征。
(二)拜登政府的对台战略考量
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后,拜登政府大致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在上任后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拜登声称要加大投入以确保美国在中美竞争中取得胜利。同时,拜登在《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中指出:“世界的权力分配正在发生变化并且产生新的威胁,尤其是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坚定且自信,是唯一有能力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构成对稳固、开放的国际秩序持久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8]8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拜登政府不仅进一步深化特朗普时期的“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对华竞争战略,而且加强与欧亚地区盟友和伙伴在对华竞争上的“战略合作”,以期构建更为有效的“综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即使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遏制也没有丝毫放松。2022年3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机密版《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同时发布的2页版情况说明(fact sheet)中指出,美国将“优先考虑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挑战,然后是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9]2022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发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演讲时也明确指出,即使俄乌冲突仍在继续,美国仍将专注于中国对国际秩序所造成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most serious long-term challenge)。[10]可见,美国对华竞争将呈现深化和长期化趋势。
当前,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持续调整及中美战略竞争深化背景下,美国已将台湾视为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主导地位的重要“战略资产”。2021年10月,布林肯在公开发表所谓“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声明时,宣称台湾是一个“成功的民主故事”,是“全球高科技经济的关键(critical)”以及“旅行、文化和教育的枢纽(hub)”,并声称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联合国成员将台湾视为“重要的伙伴”(valued partner)和“值得信赖的朋友”(trusted friend)。[11]2022年布林肯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再次表示,“美国与台湾有着牢固的非官方关系,台湾不仅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vibrant democracy),也是该地区领先的经济体(leading economy)”,并声称“美国将继续坚持在‘与台湾关系法’下的承诺,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10]在此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更加重视台湾所谓“第一岛链战略支点”的“战略价值”,加强台湾所谓“不对称战力”(asymmetric capability)的构建,并且将“台湾牌”与“同盟牌”结合起来,增强“以台制华”的战略威慑力。
综上所述,为延缓亚太地区权力转移进程并维持现有国际权力格局,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从特朗普时期兼具“工具性”与“战略性”,发展为拜登时期更加突出的“战略性”。而台湾问题“战略性”的凸显则需要美国扩大“政策空间”,提升美台“实质关系”。为此,在过去6年时间里,美国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干预与渗透力度,通过不断深化美台“实质关系”、出台一系列“友台法案”来适应对华战略竞争下美台关系的发展需要,这使美国的对台政策呈现“重构”特征。
二、中美竞争下美国对台政策“重构”的表现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目标,2017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与“重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不断明晰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和作用、推动对台“六项保证”的“公开化”和“政策化”,以及扩充美国对台政策的法律基础。
(一)明晰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角色与作用
2017年对华战略出现重大转向后,美国开始提升台湾的“战略地位”。特朗普政府相继通过《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等政策文件,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United State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将台湾视为美国在“印太战略”中的“桥头堡”,强调台湾在中美竞争中的地缘战略地位。该文件称,要有效提升台湾的非对称防御战略和能力,“以确保其自身安全,避免遭受胁迫,保有战略韧性以及有能力以自主的方式与中国大陆接触”,并称要“协防包括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国家和地区”。[12]5在论述“中国”的部分,该文件还提出要让包括台湾在内的“民主伙伴”广泛参与,展示自身获得的“民主成就和好处”,以达到“推广美国在该地区的价值观并平衡中国政府模式影响”的目的。[12]7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亦将“战略竞争”作为对华战略的核心内容,在沿袭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基本概念和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对华“战略包围圈”。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不仅重视台湾的地缘战略地位,继续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而且强调与台湾在“民主”和科技供应链方面的合作,进一步明晰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角色和作用。在2022年2月11日发布的拜登版《美国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报告中,台湾被直接定位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合作的主要区域伙伴(regional partner)”[13]9。该报告还指责大陆对台湾所谓“日益增长的压力”(growing pressure),称要在“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下维持对台湾的“长期承诺”(longstanding commitments)。[13]13可见,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向后,台湾已从“交易筹码”转变为美国的“战略资产”,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二)推动对台“六项保证”的“公开化”和“政策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除了“三报一法”,对台“六项保证”也是历届美国政府制定对台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就“六项保证”的实质而言,其与“八一七公报”的精神背道而驰,令中美在对台军售问题上龃龉不断。[14]在中美关系缓和时期,美国对“六项保证”的态度大体是“低调”与“保守”的;随着中美关系逐渐转向竞争,美国对于“六项保证”的解释也进入“强化”时期。[15]因此,2017年以后美国不断推动“六项保证”的“公开化”和“政策化”。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相继签署了“2018亚洲再保证倡议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2019财年约翰·S.麦凯恩国防授权法”(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0)、“2021财年威廉·M.索恩伯里国防授权法”(William Mac Thornberry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21),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六项保证”在美国对台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美国还通过公开1982年对台“六项保证”的原始电报,使“六项保证”正式“公开化”。
2021年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在涉台政策声明中频频将“六项保证”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与台湾关系法”并提。2021年4月9日,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新版“对台交往准则”中强调,要有效实施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16]2022年5月,美国国务院官网更改后的美台关系情况说明也显示,美国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以“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17]可见,经由特朗普时期发展到拜登时期成型,随着中美大国竞争的深化,“六项保证”逐渐与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中的“与台湾关系法”并列,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依据。其中,“美国不会设定对台军售的终止日期”“美国不会在对台军售前向大陆磋商”[18]等条文公诸于世,不仅使“六项保证”从一份缺乏文字依据的“口头表述”成为白纸黑字的“官方文件”,更给美国对台军售提供了更多所谓“法律依据”和“政策来源”,使其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更加“游刃有余”。
(三)扩充美国对台政策的法律基础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美方渐次提出的包含一系列政策和原则的框架,这一框架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19]其中,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对美国国内涉台立法有着决定性作用,其他涉台法案皆由前者延伸而来,是前者的补充,而这些涉台立法共同构成美国对台政策的法律基础。随着中美博弈的加剧,美国开启“全政府”对华竞争模式,不仅由行政机构牵头形成对华竞争态势,还积极寻求与国会等部门的协调一致。在“全政府”对华竞争下,2017年至2022年6月,有11项“友台法案”被总统签署成法(表1)。

表1 2017年至2022年6月美国总统签署完成的涉台立法
具体而言,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签署的涉台立法主要包括“军事安全”“高层交流”“国际活动空间”三个议题。一是“军事安全”方面,相关法律旨在加强美台之间“防务和安全合作”,增进双方“防务伙伴关系”。例如,“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2019财年约翰·S.麦凯恩国防授权法”“2018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2021财年威廉·M.索恩伯里国防授权法”“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均提到提升“美台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对台军售、定期向台湾提供防务物品和服务、促进美台高级军官交流等内容,要履行所谓美国对台的“现有承诺”,支持台湾发展所谓“不对称战力”。二是“高层交流”方面,相关法律旨在突破既有对台政策框架下的美台“官方互访”政治禁忌,试图在法理上颠覆美台关系的“非官方”属性。例如,“2021综合拨款法”中的“2020台湾保证法”要求国务卿必须在法律颁布的180天内将对台指导方针进行回顾并颁布新版对台准则,以进一步突破所谓“美国在高层互访上保持的自我限制”导致的美台高层沟通不足。[20]三是“国际活动空间”方面,相关法律旨在依靠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助力台湾拓展所谓“国际活动空间”。例如,2020年出台的“台北法”试图从法律层面赋予台湾地区同等于“国家”(nation)的经济、政治、“外交”待遇[21];在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来临之际,出台“指示国务卿制定政策为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和其他目的法”,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战略以帮助台湾恢复其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地位[22];等等。通过立法方式,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中以“与台湾关系法”为统领的法律基础不断扩大,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空间则被进一步挤压。
三、中美竞争下美国对台政策“重构”的逻辑
美国涉台政策的调整呈现“重构”的特征,这种“重构”的逻辑体现为“变化”和“不变”两个方面。虽然美国对台政策出现变化,但其背后仍有不变的内核。
(一)美国对台政策“重构”中的变化
首先,正式将“六项保证”纳入对台政策框架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邦交正常化以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除了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与台湾关系法”并列,还在暗中加入对台“六项保证”。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之前,“六项保证”虽是美国制定对台政策的内部指导原则,但并未公开纳入美国台海政策的官方表述,因此一直是美国对台政策框架中的“半隐性存在”。然而在2017年以来对华竞争战略态势下,“六项保证”已逐渐“公开化”和“政策化”,并落实为美国制定对台政策的“显性”依据。因此,美国对台政策框架已在原有“三报一法”的基础上增添了“六保证”。
其次,追求对台政策框架中“三报”与“一法”的力量平衡。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的对台政策一直从属于对华政策,在这一政策属性下,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中“三报”的重要性远高于“一法”。2017年以后,为了争取更大的对台政策独立空间以更好地服务于对华战略竞争需要,美国开始追求“三报”与“一法”的力量平衡。一方面,美国将“六项保证”正式纳入对台政策框架基础,直接损害“八一七公报”中的中美共识,侵蚀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中“三报”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签署“与台湾交往法”“2020台湾保证法”等系列“友台法案”,美国进一步夯实对台政策的法律基础,加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中“一法”的地位。6年来,由于美国不断削弱“一个中国政策”中的“三报”比重,同时提升“一法”的分量,两者力量此消彼长,最终“一法”的力量将与“三报”相抗衡。
最后,完成对台政策框架基础中各要素顺序的调换。在将“六项保证”纳入对台政策框架,以及将“一法”的地位提升到与“三报”同等之际,美国通过“一法三报六保证”的官方公开表述,做出中美竞争下更符合美国利益的“一个中国政策”解读。通过对台政策基础各要素的位置互换,美国将“与台湾关系法”置于美国对台政策的第一位阶,摆脱了原来“三报一法”框架下其制定对台政策的“自我限制”,实现了对华政策和对台政策的“并行发展”和部分“脱钩”。于是,美国对台政策模式由原先单一的“美→陆→台”一元政策模式转变为“美→陆→台”和“美→台”交互的二元模式。此时,美国对台政策的独立性及“以台制华”的便利性都得以大幅提升。
(二)美国对台政策“重构”中不变的内核
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需要获得更多政策空间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实现“以台制华”,但避免同中国发生冲突也是其追求的战略目标。因此,即便美台关系不断深化,这种深化也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下进行的,维持两岸“战略平衡”仍是美国对台政策不变的内核。
事实上,中美邦交正常化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三报一法”政策框架下维持着台海问题中动态的“战略平衡”,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虽然当前美国对台政策框架出现变化,但美国在台海问题上仍保持着“战略平衡”策略,即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防止两岸中任何一方改变现状。因此其在不断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内涵的同时,仍将保留“一个中国政策”的政策表述,即在“以台制华”的同时向大陆表明美国“一个中国政策”这一底线未变,以此缓和美台“实质关系”提升带来的台海局势紧张。正如拜登上台后的公开发言,虽然多次表示“协防”台湾,但每次发言后美国国务院和白宫都发表声明及时“矫正”,强调美国对台政策并未发生改变。2022年5月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对台湾情况说明更新后,发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在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本质没有改变,策略未改变”。[23]可见,尽管在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加大了“以台制华”的力度,但依旧沿用了过去40多年来“遏制+保证”的“双重威慑”方法。
由此可知,2017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构”是服从于中美大国战略竞争需要的,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构”路径不是解构既有框架后的“重新建构”,而是在原来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扩容”和“重组”。在两岸经济、军事等方面差距逐渐扩大的情况下,美国试图增加台湾方面的砝码,以恢复符合其期望的“两岸平衡”态势。换言之,美国对台政策“重构”的“变”,恰恰是在两岸经济、军事实力日益悬殊的背景下,美国继续维持两岸“现状”保持“不变”的政策选择。也正是如此,美国在中美竞争下利用台湾这一“战略棋子”对华进行“战略威慑”的同时,不会放任岛内“台独”势力的过激行为。2022年5月5日美国国务院官网大幅更改美台关系情况说明后,于同月28日再度改版,再添“美国不支持台独”内容;2022年6月11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在香格里拉峰会演讲时也明确表态美国不支持“台独”。[24]实际上,美国往届政府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两岸“动态平衡”的政策目标,是基于“两岸共同坚持一个中国”这一特定基础的。[25]如果“台独”势力不断挑战“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美国继续“玩弄两面手法”维持台海现状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四、中美竞争下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发展走向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为了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国将加紧利用台湾这一重要“战略资产”制衡中国的发展。2017年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构”赋予其更大的便捷性和灵活度,今后美国与台湾地区关系的发展将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展开。
(一)经济关系:以供应链合作为重点,打造美台经济“战略伙伴关系”
在中美大国关系逐步滑向“全面竞争”时期,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不仅着眼于地缘政治层面,也聚焦于经济与科技领域。拜登政府《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指出,美国必须重新投入资金以保持科学技术优势,并再次发挥领导作用,与美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建立新的规划,使美国能够抓住技术的机遇。[8]92021年2月,拜登签署行政令,就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做出说明,强调要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保护美国免受关键产品短缺的威胁。[26]2022年8月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将拨款542亿美元用于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研发等项目。白宫就此发布的情况说明称,该法案将用于降低成本、创造就业、增强供应链以及“对抗中国”(counter China)。[27]当前美国延续并加强了2017年以来的对华科技竞争,试图构建广泛的“去中排华”供应链和经济体系。作为全球半导体等技术产品的重要供应者,台湾也被美国纳入遏制中国的“供应链安全联盟”。2021年12月签署成法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就明确指出,“台湾是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对芯片短缺带来的挑战,升级与台湾的‘伙伴关系’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28]
基于美国在供应链安全上的战略考量,美国将发展美台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经济关系视为优先级。早在2021年3月,时任“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郦英杰(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在出席台积电铜锣厂动土典礼时就表示:“美国与台湾地区在整个价值链上有着大量的公司,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最天然的合作伙伴,支持美台在供应链领域的合作将继续是AIT的工作优先事项。”[29]2022年3月,“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Sandra Springer Oudkirk)在阐述年度工作目标时也指出,当前工作目标之一就是透过一系列新的政策倡议,与台湾共同强化全球供应链韧性。[30]目前美台已经举办了两次“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EPPD),也重启了时隔5年之久的“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双方会谈除了讨论包括供应链、半导体、数字贸易在内的经济议题,还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尽管美国并没有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IPEF)首轮名单,但几乎在同一时期启动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U.S.-Taiwan Initiative on 21st Century Trade),并将于2022年秋季举行首次谈判。随着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供应链安全等议题将会成为美台经济关系发展新的增长点。未来其可能推动经贸谈判的常态化与机制化,通过局部性架构协议加大洽签更具全面性的“美台贸易协定”(BTA)的可能性,打造美台经济上的“战略伙伴关系”。
(二)政治关系:构建所谓“民主价值同盟”,加强多边议题的“台湾连结”
2021年拜登上台后,美国积极构建对华竞争“新战略同盟”,强调结合盟友与价值观的力量,以所谓的“民主价值同盟”遏制中国这一“最严峻的竞争者”的发展。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直言:“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中国运作(operate)的战略环境,在世界上建立最大程度上有利于美国、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以及我们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力平衡。”[13]5台湾也被纳入所谓的“民主价值同盟”。2021年1月23日,拜登政府对台湾问题首发声明中表示,会“与朋友和盟友一起促进印太地区的繁荣、安全和价值观”,其中就包括继续深化与“民主台湾”(democratic Taiwan)的关系。[31]《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也指出,“支持台湾这个主要的民主社会和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符合美国的长期承诺”。[8]21
除了构建美台“民主价值同盟”,拜登政府还将台湾问题与美国的多边外交相联系,加强美国与其盟国在多边议题上的“台湾连结”。与特朗普政府提倡单边主义不同,拜登政府强调回归多边主义、强化联盟体系,并在修复西方同盟体系内部团结的同时联合盟友在台湾问题上“造势”。当前,美国涉台议题的“同盟联动”现象正在形成,其涉台政策开始由传统的“美国-台湾当局”单边输出互动模式转变为“美国+盟友-台湾当局”的多边互动模式。[32]例如2021年4月以来的美日峰会、美欧峰会、G7峰会等大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或声明,均提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2021年9月澳美部长级磋商(AUSMIN)结束后,其联合声明表示,“美澳再次强调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作用。双方都表示有意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是一个领先的民主社会,也是两国的重要合作伙伴,……,美澳重申继续支持在不诉诸威胁或胁迫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共同承诺加强与台湾在太平洋的援助协调(donor coordination)”[33]。同年10月7日,在中美“苏黎世会谈”隔天的例行发布会上,普莱斯在谈到台海问题时再一次援引此份声明中的对台表述,并表示“这与我们对印太地区的更广泛的态度一致,与我们对中国的更广泛的态度一致,我们已经与欧洲、印太地区及世界各地的盟友、伙伴通力合作,并以此明确这不仅仅是美国的立场,也是我们盟友和伙伴的共同立场”。[34]2022年6月,美日韩防长在三方会谈上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在会后联合声明中首度提及台湾议题。[35]在实际行动上,2021年12月美国举行的所谓首届全球“民主峰会”邀请了台湾地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宣布将于2022年10月在台北举办首届所谓的“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36]。可以预见,拜登政府将继续联合盟国共同应对台湾问题,以增强“台湾牌”的效力。
(三)军事关系:加强“安全防务伙伴关系”,深化“美台战略安全合作”
当前美国对台防务态度和政策逐渐“清晰化”,美台军事关系朝向“准同盟化”发展。拜登上任后,其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对台“协防”的明确指向。尽管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均立即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未变,但是各发言人在表述上却愈发强调“与台湾关系法”的作用。2021年10月,拜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有承诺协防台湾”,随后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在发布会上4次提到将以“与台湾关系法”为指导,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37]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隔天的发布会上也多次重申,“美国与台湾的‘防务关系’是以‘与台湾关系法’为指导的”。[38]而就在拜登发表“协防”言论的前几天,时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John Kirby)也强调,美国将致力于帮助台湾“在符合法律的情况下行使自卫能力”。[39]从中可以看出,在对台‘防务安全’方面,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中“与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在加强。
“与台湾关系法”第三节规定,“总统和国会应完全根据其对台湾需要的判断(judgment of the needs of Taiwan),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决定此种防御物品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40]根据长期以来美台军事关系发展情况,这里的“对台湾需要的判断”其实是美国对两岸军事实力差距的判断,也是美国对两岸军事冲突可能性的判断。正如“2018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第209节b条款“对台售武”指出的,“总统应当‘依据台湾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现有和未来可能的威胁’,定期向台湾移交防务物品,包括支持台湾努力发展和整合‘不对称战力’”。[41]当下,在中美战略竞争走向深化、两岸军事实力差距扩大的背景下,美国认为大陆对台湾构成的“安全威胁”在加大,而出于维持台海现状的目标,美国需要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对其第三节内容中“台湾的需要”(the needs of Taiwan)重新作出解释。
可以预见,美国将打着维护“台海稳定”和履行“对台安全承诺”的旗号,在助力台湾发展“不对称战力”、增加防务物资转移等领域深化与台湾的“战略合作”,为台湾的军事安全“加码”。例如,“2021财年威廉·M.索恩伯里国防授权法”第1260节A条款要求,国务卿或其指定人员此后必须每年出台一份对台军售的年度简报,该报告要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介绍美国在支持台湾保持足够“自卫”能力上的承诺。[42]这加强了美国对台军售的“例行化”和“常规化”态势。此外,2021年以来提出并正在审议中的多项涉台议案亦对美台“防务”关系有所指向。例如,2021年2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的“防止台湾遭受入侵法案”(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就表示“支持协防台湾”,并授权总统使用武装部队保卫台湾“以抵御中国军队的直接攻击、中国大陆对台湾领土的夺取、台湾平民或台湾军队成员的生命受到威胁”。[43]5该法案还强调,美国的政策是“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以实现统一台湾的任何企图”。[43]62021年6月16日,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分别提交了名为“台湾防卫法案”(2021 Taiwan Defense Act)的法案,虽然两份法案具体内容各有侧重,但都表示要“维持美国武装部队以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能力”[44-45],要求美国国防部确保美军有能力阻止武力夺取台湾的控制权。2022年5月3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安东尼奥·鲁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提出“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Taiwan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要求修改“与台湾关系法”,不再将售台武器限制为防卫性质。[46]虽然这些法案并没有通过,但其体现了美国国会增加美台“军事关系”的强烈意图。在实践层面,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通过持续的对台军售、成立“美台海巡小组”、频繁的军舰“护台”等行动提升美台“防务关系”。
然而美台“战略安全合作”并非无限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出席智库新美国国家安全中心(CNAS)主办的2022年国家安全会议时一再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根本目标在于“确保是否需要捍卫台湾问题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47]因此,美国不仅强调与台湾的“安全防务伙伴关系”,也将加强同中方的沟通,避免各方误判导致武力冲突意外发生。2022年6月中美国防部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会面,奥斯汀讨论了负责任地管理竞争和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必要性,并强调中美就改善危机沟通(improve crisis communication)和减少战略风险(reduce strategic risk)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48]
五、结 语
基于全球权力格局加速演变的现实,2017年以来美国对外战略重回“大国政治”,其对华战略也由原先的“接触”转向“竞争”。在此背景下,美国将台湾视为在亚太地区围堵中国的“战略前哨”,表面上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基本面不变,同时进行对台政策的“重构”。实际上,美国对台政策“变化”背后遵循着维持两岸“战略平衡”的“不变”内核。目前看来,6年来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构”为其提升美台关系提供了极大便利,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美台迈向“准军事同盟”的可能性不断加大。在中美战略竞争走向深化的当下,美台关系的发展趋势将继续冲撞中美关系,使台海地区陷于紧张的氛围之中。因此,要准确把握美国对台政策动向,防范台湾当局“倚美谋独”的企图,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进而推动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