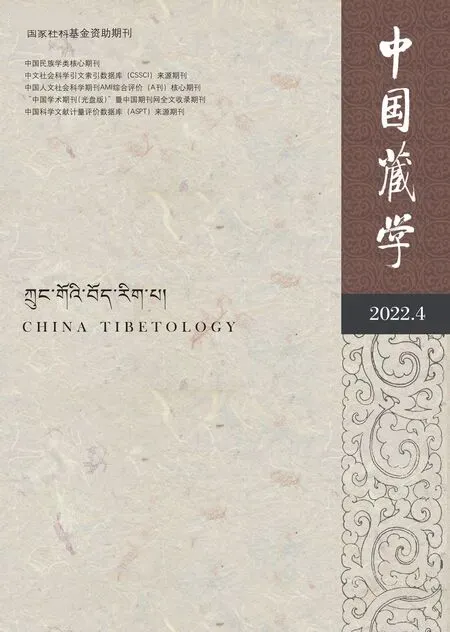《金刚三昧经》藏译之敦煌本与传世本对勘研究①
落桑东知
一、作为疑伪经的 《金刚三昧经》
直到近代,《金刚三昧经》一直被视为是从印度等域外翻译来的经典,②传统经录记为,《金刚三昧经》是北凉时期 (397—439)所译佛经,但未列出译者等历史信息。最早的记载见于公元374年道安 (312—385)编纂的 《综理众经目录》之 “凉土异经录”中。参见 《出三藏记集》卷3,CBETA,T55,no.2145,p.18c6.然而自20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水野弘元质疑其 “佛经”地位以降,①水野弘元主要从4个方面进行了质疑:一是有些翻译用语,只在玄奘 (602—664)以后才出现;二是出现了玄奘译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句子;三是出现了 “江河淮河”等汉语固有名称;四是参照了菩提达摩 “二入四行论”。参见释达和译:《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说与金刚三昧经》,《佛光学报》1979年第4期;敖英对水野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见 《关于 〈金刚三昧经〉的两个问题》,《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愈来愈多的学者将其归入 “疑伪经”之列,包括印顺②印顺说 “一般都论断为后代的伪作”,尤其是谈到 《金刚三昧经》中的 “二入”说时,他明确指出 “完全从达摩的 ‘二入’脱化出来”,显然应将此经归入 “疑伪经”。参见 《中国禅宗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页。、戴密微③据笔者所知,戴密微最早在其1952年出版的专著中,就表达了对 《金刚三昧经》的质疑。参见耿昇译:《吐蕃僧诤记》(上),台北:中国书店,1999年,第94—102页。、杜继文④杜继文:《新罗僧与唐佛教》,《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徐文明⑤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5—137页。和Robert Buswell⑥Robert Buswell, 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The Vajrasamadhi-Sū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 New Jersey: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等。其中,Robert Buswell是对这个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然而汉语佛教学术界对他的著作了解较少,笔者认为他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相关成果,现将他的相关观点介绍如下。
与以往学者对 《金刚三昧经》中土撰述之质疑有所区别的是,Robert Buswell推断此经是公元7世纪下半叶新罗国禅宗学僧编制的 “疑伪经”。新罗禅宗学僧为何要造此 “疑伪经”?他通过剖析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是当时的禅宗学僧借 “经”之名,宣扬禅宗初祖菩提达摩 “二入四行论”和东山法门 “守一/守心”等教义,尤以后者为其要旨。具体而言,公元6世纪随着新罗中央集权制的不断巩固,佛教作为意识形态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功能得到认可,因此在法兴王时期 (514—539年在位)将佛教作为国教而奉行。这种 “政教联盟”的统治模式,一直被其继任者所推崇。至公元669年新罗征服高句丽和百济,实现三国统一,华严宗在国家宗教权力网络中占据绝对优势。禅宗学人面对这种窘况,尤其是当时禅宗作为对教义诠释较为激进的新兴宗派,《金刚三昧经》的撰述者意图通过 “疑伪经”的编制,以达到宣扬自身独特教义、在宗派竞争中占得一席的目的。⑦同上,pp.6-24.
既然是新罗禅僧编制的 “疑伪经”,那么是何时由何人伪造的?Robert Buswell从 《金刚三昧经》最早的注疏者元晓 (617—686)入手,认为 《宋高僧传·元晓传》和 《三国遗事》中的相关历史叙事,为我们解密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 《元晓传》中透露, 《金刚三昧经》是新罗王为治愈其妃子,派遣使者从龙宫中以神奇的方式获得,此后大安对其进行了编辑、校订等事宜,并委派元晓对其作注疏,谓 《金刚三昧经论》。⑧同上,pp.41-73.对这些历史材料进行结构分析之后,Robert Buswell认为《金刚三昧经》可能是新罗禅僧法朗于公元685年左右撰述,之后传到中土流行。⑨同上,pp.170-177.
如前所述,在中土的经录记载中,以 《金刚三昧经》为名的经典,最早出现在道安于公元374年编纂完成的 《综理众经目录》中,由此可知4世纪后半叶,已有一卷名为 《金刚三昧经》的文本。然而,其后相继出现的经录,即公元494—497年僧祐编纂的 《出三藏记集》、594年法经编纂的《众经目录》、597年费长房编纂的 《历代三宝记》、602年彦琮编纂的 《众经目录》和695年编纂的《大周录》等,均不支持有存本传世。因此,Robert Buswell推断道安所录 《金刚三昧经》,在公元4世纪后半叶就已佚失不传。然而,佚失近3个世纪的 《金刚三昧经》,却在公元730年智昇编纂的《开元释教录》中首次作为 “拾遗编入”经典出现,并明确记载在中土已有其传世本。在此之后的各种经录,均记载有此本。由此,Robert Buswell认为智昇所录 《金刚三昧经》即我们现存版本,与道安所录 《金刚三昧经》并非同一版本,是新罗禅僧编制的那本 “疑伪经”。①Robert Buswell, 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The Vajrasamadhi-Sū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 New Jersey: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33-40.
《金刚三昧经》在东亚佛教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影响,自7世纪问世以来,不仅有中原汉地高僧大德对其进行注疏解说,而且也受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学者的关注,纷纷对其作疏阐发其奥义。如前所述之 《金刚三昧经》最早的注疏 《金刚三昧经论》,即由新罗国著名佛学大师元晓所作,亦是所有注疏系统中最负盛名、流通最广的一本。高丽僧义天 (1055—1101)在其所撰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中,列有唐朝时期新罗僧遁伦 (生卒年不详)所作的一本注疏,名曰 《金刚三昧经疏》,现已佚失。此外,1094年日本学问僧永超,在其编撰的 《东域传灯目录》中记载了4部匿名的注疏。②同上,p.6,n5.从中日韩佛学大师对此经所作的各种注疏中,我们能够发现此经具有明显的跨文化、跨民族交流的特征,在中古东亚文化交流交往场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金刚三昧经》在西藏的传播及经录之记载
发生在公元792—794年的那场关乎西藏佛教发展走向的、被学界称为 “吐蕃僧诤”的辩论事件,是汉地禅宗在吐蕃传播达到顶峰的标志。关于这场诤论中汉地禅师摩诃衍的相关观点,得益于由其口授弟子王锡笔录所成的 《顿悟大乘正理诀》在敦煌汉藏文献中的发现 (S.2672、P.4646、P.T.817、P.T.821、P.T.822、P.T.823等),我们已经对其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④《顿悟大乘正理诀》的研究,自戴密微以降成为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议题,相关研究成果亦颇丰。周拉教授此前将 《顿悟大乘正理诀》整本译成藏文,并对摩诃衍禅师的观点旁考藏文史料进行了研究,他的藏文全译本无疑为藏族学者了解摩诃衍禅师的观点提供了便利。参见周拉:《〈顿悟大乘正理诀〉研究及翻译 (一、二、三)》,连载于 《中国藏学》(藏文)2013年第4期,2014年第1、2期。我们在摩诃衍禅师的这本著作中,发现他曾3次引用 《金刚三昧经》,很显然他将此 “疑伪经”作为自己重要的经典依据之一。第一处的引文为:“又 《金刚三昧经》云,佛言:‘一念心动,五蕴俱生,令彼众生安坐?心神住金刚地,即无一念。此如如之理具一切法。’”《顿悟大乘正理诀》由3个部分组成,即序言、问答和表疏等,敦煌藏文文献属于残本,内容不全。这个引文部分属于问答部分,藏文写本中阙如。第二、三个引文分别出现在 “摩诃衍第一道表疏”和 “摩诃衍第二道表疏”中,两则引文内容相同,是第一则引文的最后一句:“如如之理具一切法。”①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上),引文分别在第94、232、237页。戴密微在强调 《金刚三昧经》中的相关概念和术语在禅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之后,作出评论说:“所以,摩诃衍和尚把这一经文当作为他的教宗辩护的权威论据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他的印度对手们反驳他说经卷只不过是一部受道教影响的汉文疑经,这也是颇有道理的。”②同上,第94—102页。笔者未能找到戴密微此处所说印度论师对 《金刚三昧经》的这种质疑,若他的论述有据,我们就可以相信当时印度论师已经对 《金刚三昧经》的经典性质,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定。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反映,吐蕃僧诤发生之际此经就已藏译,摩诃衍禅师的对手对其亦有相当的了解。从 《金刚三昧经》作为摩诃衍禅师所引用的重要经典依据这个事实,加上印度论师对此经性质的判断,笔者大胆推测此经流传到吐蕃,或可能是摩诃衍禅师及其吐蕃追随者,为了这次辩论的需要将该经进行了藏译。
在藏文最早史料之一的 《巴协》中,我们发现了一段历史记载,涉及吐蕃人对汉地禅宗最早的接触,也与 《金刚三昧经》在吐蕃的流传有密切的关系。据载,吐蕃曾派遣巴·赛囊等众使者前往汉地取经,途径四川益州一带时,遇到了名为金和尚的汉地禅师。金和尚为他们预言了未来佛教在吐蕃的命运,并授予他们相关的修法和经卷。③相关日本学者对这段史料剖析所得结论,参见Daishun Ueyama,The Study of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A Review of the Field and its Prospects, in Early Ch'an in China and Tibet, Edited by Whalen Lai and Lewis R.Lancaster, Berkeley: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83, pp.327-349; 亦可参阅 Matthew Kapste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Conversion, Contestation and Mem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75-78.随着四川禅宗保唐派 《历代法宝记》在敦煌文献中的发现,为我们揭示相关历史信息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此处的金和尚 (684—762)是四川禅宗净众派的祖师,俗姓金,新罗王之族,法号无相,后被尊称为 “东海大师”。④有关金和尚的传记、教法和师承等信息,参见冉云华:《东海大师无相传研究》,《敦煌学》(第四辑),1979年,第47—60页;Wendi Adamek,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然据西方学者Jeffrey Broughton推断,巴·赛囊遇到的不是金和尚,而更有可能是其后继者——禅宗保唐派的祖师无住和尚,因为巴·赛囊前去内地的时间为公元763年之后,而根据 《历代法宝记》,金和尚殁于公元762年。⑤Jeffrey Broughton, Early Ch'an School in Tibet, in Studies in Ch'an and Hua-Yun, Edited by Robert Gimello and Peter Gregor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pp.5-8.《历代法宝记》(约成书于774—780年间)作为金和尚、无住和尚一系体现其正统禅史观的重要著作,其中频繁地引用 《金刚三昧经》,进而可表明此经在保唐派所具有的显赫地位。⑥Wendi Adamek教授,以柳田圣山等日本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对 《历代法宝记》进行了迄今最深入的研究,并首次完整地进行了英译。 Wendi Adamek, 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On a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因此,笔者认为小畠宏云的论断具有一定合理性,他认为 《金刚三昧经》与保唐派的密切关系,使得其被藏译并流传至吐蕃。⑦转引自 Robert Buswell, The Formation of Ch'an Ideology in China and Korea:The Vajrasamadhi-Sūtra, a Buddhist Apocryphon,New Jersey:Pri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 n7.若真如此,《金刚三昧经》的藏译为我们揭示了禅宗在吐蕃传播的流变系谱。在禅宗进入吐蕃的最初,像 《金刚三昧经》这种重要的经典,就已开始传播到吐蕃,至摩诃衍禅师在吐蕃与印度论师辩论之际,禅宗在吐蕃大有可能形成了一个流派,或可称呼其为 “藏地禅”。当然,限于可资利用的材料之欠缺,我们无法较为准确、完整地呈现 “藏地禅”的历史脉络和整体轮廓。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从此经藏译至摩诃衍禅师登台,众多未留姓名的内地禅师远赴吐蕃,为弘扬禅宗教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说将其藏译是 《金刚三昧经》在吐蕃流传的第一步,那么吐蕃人对它的接受与否,可算作是第二步。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笔者认为经录中的记载是判断的重要标准。经录是区隔 “真经”和 “疑伪经”的依据,随着佛教典籍源源不断地引进,汉藏两地在不同时期都产生了多种版本的经录,这也成为历代敕修 《大藏经》刻写本的依据所在。基于经录的这种性质,我们能够窥探特定传统对某种经籍的认可度。吐蕃自藏传佛教前弘期,就意识到编纂经录的重要性。我们在被誉为吐蕃时期三大佛经目录之两大目录中,均发现录有其题名。《旁塘目录》专辟一栏 “从汉地所译大乘经典”,录有11部佛经之题名,其中就有 《金刚三昧经》。①西藏博物馆编:《旁塘目录、声明要领二卷》(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9页。在 《丹噶尔目录》中,我们同样发现编纂者设有 “从汉地所译大乘经典”一节,此下汉译佛经增至23部, 《金刚三昧经》在此称有6卷,1800颂。②Shuki Yoshimura, The Denkar-Ma:An Oldest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Kyoto:Ryukoku University Pubilcasher,1950,p.140.按照藏文经籍编排规制,每300颂为1卷,按诗歌体每4句为1颂,每句有长有短难以统计,按散文体每颂计为32个字符,从而粗略统计将近有57000余字。笔者对现存 《甘珠尔》收录传世本之部头大小,旁考汉文 《金刚三昧经》进行估量之后发现只有1万余字,因此 《丹噶尔目录》所载信息可能是有误的。
现存藏文 《甘珠尔》刻写本最早的雏形,是基于1312—1320年在纳塘寺整理发布的 “《甘珠尔》纳塘古写本”,但遗憾已佚不存。然而,此次 《甘珠尔》写本所依经录,主要是根据纳塘寺堪布觉丹热饶 (1227—1305)编纂的 《教法兴盛·庄严之光》。从中我们发现,编纂者在第十一章“译自汉地和于阗”部分,录有 《金刚三昧经》之题名。③百慈藏文古籍研究室编:《噶当文集第二部·第51卷》(藏文),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3—156页。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认为,《金刚三昧经》在最早的 《甘珠尔》写本中就已得到收录了,因为觉丹热饶既是此经录的编纂者,也是主持刊印写本的负责人。此后的历代 《甘珠尔》刻写本,譬如纳塘新版、北京版、德格版、卓尼版、拉萨版和蒙古库伦版等,均刊行有 《金刚三昧经》。④在这些 《大藏经·甘珠尔》刻写本中的刊印,以及其他经录和高僧 “闻法录”中对此经的征用情况,可参阅Tarthang Tulku ed., The Nyingma Edition of the Sde-dge bka'’ gyur/bstan ‘gyur:Research Catalogue and Bibliography, Volume 1, Berkeley:Dharma Publishing, 1982, p.331.《甘珠尔》刊行是一项非常浩大的文化工程,此经能列入其中而流通,说明藏地已全然接受了其佛经之地位。
三、敦煌藏译本P.T.623结构分析
敦煌文献P.T.623为 《金刚三昧经》藏译残本,在P.T.116、P.T.118、P.T.818等藏文写本中亦有引用。P.T.623首题录有藏译名称 “”,篇幅较大,共有28叶,每叶7行共计196行。⑤敦煌文献印影版,参见 “国际敦煌项目 (IDP)”网站。
P.T.623作为残本,兹先参照 《中华大藏经·甘珠尔 (对勘本)》(以下简称 《中华藏》本)收录的传世本,与P.T.623对应情况进行梳理。通过这样的结构分析,可知晓敦煌本是藏译原本多处,段落之抄写①《金刚三昧经》两个藏译本与 《大正藏》汉文母本全文对校,能够发现两个藏译本在严格意义上均非足本,由此本人设想最初从汉文母本藏译时,在很大程度上会有藏译足本,但在文本传承过程中出现了脱漏的情况。此处所说藏译原本,就是指可能的藏译足本。,而非是某个部分之连续而完整的抄录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中华大藏经·甘珠尔 (对勘本)》(藏文)第56卷,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329—382页。:

《金刚三昧经》藏译之敦煌本与 《中华藏》本对勘表
四、敦煌文献对传世本的贡献
笔者依据 《中华藏》本收录传世本与P.T.623残本对校之后发现,两个译本出自同一个藏译原本。然而,《中华藏》本与 《大正藏》收录汉文原本进行对勘,发现传世本有脱漏、错讹和章节编排出错等现象,致使尚有多处不堪卒读、辞不达意的情况。聊以欣慰的是,敦煌文献P.T.623等对其有补阙、校正之用处,希冀将来有学者能在文本精校基础上,刊行藏译仿正版 (diplomatic ed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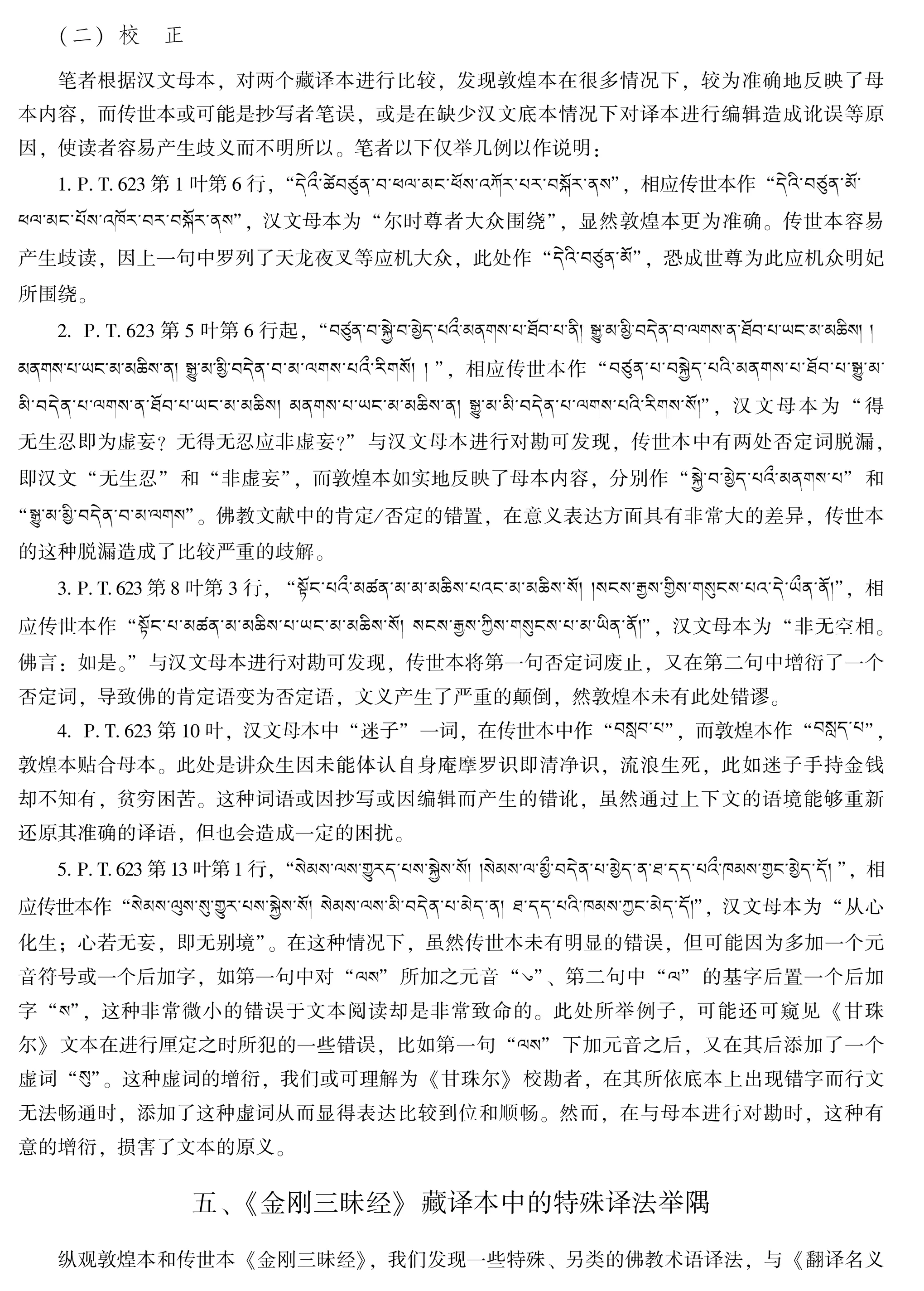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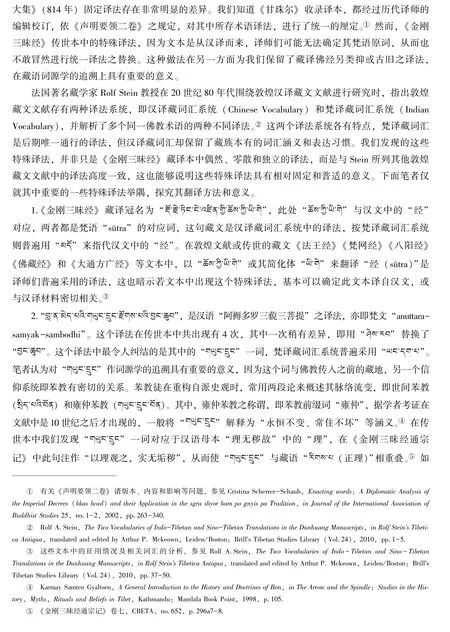

六、结 语
《金刚三昧经》作为朝鲜半岛编制的 “疑伪经”,漂洋过海流传到中土后被赋予了佛经之地位,之后又通过相应的渠道进入藏传佛教。这不仅是书籍作为特定文化之载体,在中古东亚文明内部一次深度交流的缩影,而且也反映了佛教初传吐蕃之时藏传佛教界博采众长的眼光,从各方吸取养分,壮大了佛教这种新的文化。
《金刚三昧经》能够收录在藏文 《甘珠尔》文本系统中,是禅宗在藏传佛教文化中留下的一条重要痕迹,但对后来的藏传佛教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其中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从译经质量而言,在缺失汉文母本的情况下,该经藏译本几乎无法卒读;二是藏传佛教重视文本的师徒传承,禅宗在藏地销声匿迹之后,这个译本所依的传承也就不复存在了。
关于该经藏文译本中夹杂的特殊译法,在缺失汉文母本、《甘珠尔》编纂者又不谙汉语的情况下,使得后弘期历代在编修 《甘珠尔》中的文本时,对其中陌生的译法未作固定术语的替换,从而为我们保留了这种古旧的译法,这对藏语词源学的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言之,若该经是从梵本所译,编纂者们肯定会作校正,但是因其原本为汉文,这已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所及。最后,鉴于现存该经藏译本质量堪忧,笔者呼吁学界能够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希望一部顺畅完整的译本能够早日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