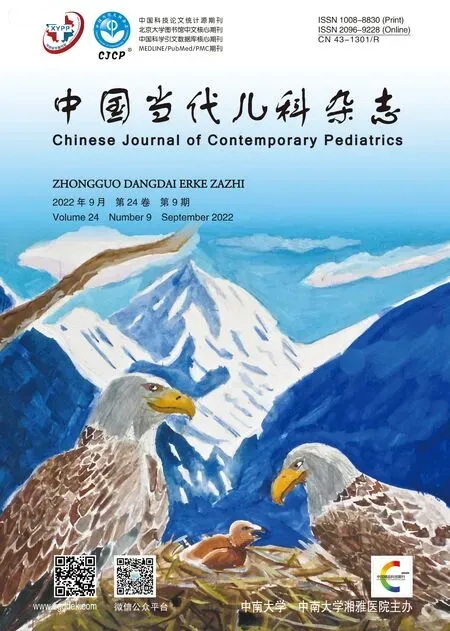婴儿百日咳的流行病学意义及其临床特点
姚开虎 胡亚红 袁林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北京市儿科研究所微生物研究室/儿科学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儿科重大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45)
百日咳全国病例数(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自2010年报告的1 764例后逐渐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2019 年达到30 027 例[1]。临床疑诊和实验室确诊百日咳儿童病例的年龄分布显示,小于1 岁的婴儿病例明显居多,达到79.2%和77.3%[2]。2004~2019 年全国监测数据显示婴儿占比达到53.43%;婴儿占比随年份明显上升,2010 年超过50%,2013 年后均超过60%[1]。同时,因为婴儿社会接触范围有限,婴儿百日咳病例常可追问出接触咳嗽患者的流行病学史。黄辉等[3]报道198 例儿童百日咳中,明确有咳嗽患者密切接触史者113例(57.1%)。但是,因为缺少实验室检测条件等客观原因,常有漏诊、误诊婴儿百日咳的现象,关注其密切接触者感染状况并进行管理的研究更少。因此,临床还需提高对婴儿百日咳流行病学意义及其临床特征的认识。
1 婴儿百日咳的流行病学意义
1.1 婴儿病例是百日咳存在持续社区传播的明确证据
分析婴儿百日咳病例的时间、空间特征,发现婴儿百日咳确诊病例呈现明显的散发状态,婴儿病例之间极少有直接流行病学关联。对于人类唯一宿主的百日咳鲍特菌来说,单纯基于婴儿病例很难实现持久的社区传播。当前婴儿百日咳的传染源主要是家庭生活中密切接触的年长儿和成人病例[4]。张喆等[5]研究了211 例百日咳儿童病例,其中187 例为婴儿,132 例发病前有咳嗽患者接触史,其中127 例(96.2%)为家庭成员。不过这一结论只解释了婴儿百日咳感染的可能来源,并不能反映百日咳持续社区传播的状况。散发的婴儿百日咳实际上只是百日咳社区传播过程中受到关注并诊断出的“显性”病例,其他在维持百日咳社区传播中发挥作用的病例,大多因为无明显症状或轻症而未就诊,或因漏诊和误诊等原因而未能识别和上报,是百日咳社区传播过程中的“隐性”病例。
1.2 婴儿病例也是百日咳社区传播的重要传染源
既往婴儿百日咳传染源研究中,几乎都隐藏着“婴儿接触的阳性年长儿或成人就是其传染源”的认识。传染源的判断,或者传染链条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不能由年龄或活动范围等单一因素决定。一个传染源即可导致婴儿发生感染。但是,开展婴儿百日咳密切接触者主动检测,往往会有很多阳性结果。深圳市儿童医院的一项研究中检查了270例儿童百日咳病例的617 名家庭密切接触者,其中173 例百日咳病原学阳性(28.0%),涉及父母亲、(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包括叔、婶、姑姑、舅舅、舅妈、姨、姑婆、保姆)接触者[6]。虽然,婴儿病例和这些阳性接触者有可能源于同一个患者。但是,因为婴儿病例有更多与其他人亲密接触的机会,最大可能性是婴儿传染了更多密切接触者。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常常是首当其冲的感染者。因此,笔者认为判断母亲是否是婴儿的传染源最为困难,对尚在哺乳阶段的婴儿病例尤其如此。
婴儿百日咳传染密切接触的家属或看护人员,他们又将病原带回社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临床诊断和上报的婴儿百日咳还可能是多条社区传播链的开端。不难推测,婴儿百日咳病例一定是百日咳社区传播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1.3 婴儿百日咳给疫苗免疫提出了更高和更急迫的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将预防百日咳的核心目标确定为预防婴幼儿,尤其是婴儿的重症百日咳[7]。为确保核心目标的实现,必须改进疫苗和疫苗免疫策略。对广泛使用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的局限性已有总结[8],研制出更为安全有效的疫苗势在必行。相对来说,优化免疫策略可能是当前更为切实可行的选择。首先,婴儿尤其是3 月龄以下的小婴儿常患百日咳,提示母传抗体不能提供保护。北京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母亲和新生儿的百日咳毒素IgG 抗体(PT-IgG) 水平在检测线以下分别占70.0% 和74.7%,<40 IU/mL 者更是高达96.4%和97.4%[9]。其次,全国百日咳报告病例,以及几项单中心确诊百日咳婴儿病例的月龄分布数据均有以下相似特点[2,6,10]:<3 月龄(未到疫苗接种月龄)、3~<6月龄(基础免疫阶段)和6~<12 月龄各约占1/3。说明基础免疫阶段及其以后的婴儿仍可感染百日咳,现用疫苗及免疫接种程序通过主动免疫策略无法完全保护婴儿,整个婴儿期都要警惕百日咳。虽然基础免疫不能完全预防婴儿患百日咳,但疫苗接种可明显减少重症百日咳和死亡[11]。
为了针对性保护婴儿百日咳,欧美已经开始实施孕期接种,可有效预防尚未到接种月龄的小婴儿患百日咳[4]。若孕期未接种,则对产后母亲及其家庭成员和新生儿密切接触者进行接种,给婴儿以严密保护,即采用“茧策略”(cocoon strategy)保护婴儿,但此措施实施起来依从性较差[4]。此外,很多国家将百日咳疫苗免疫接种起始年龄提前至6 周龄,WHO 也推荐6 周龄接种,6月龄内完成基础免疫[7]。上述预防措施,仍然不能完全阻断百日咳的社区传播,婴儿百日咳仍无法完全避免。针对这一客观事实,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展从出生到老年的全生命周期百日咳疫苗接种程序[12],这可视为在全社会层面上对婴儿人群实施的“茧策略”。
2 婴儿百日咳的临床特点
2.1 疫苗时代的婴儿百日咳病例常有典型临床表现
疫苗时代,母亲通过儿童期疫苗接种所获百日咳抗体到孕龄时已几乎消失殆尽,大部分新生儿母传抗体水平都很低[9],这和疫苗前时代明显不同。现阶段临床病例的总结报道显示,婴儿百日咳常有典型咳嗽表现。吴少珍等[13]研究显示,虽然≥3月龄百日咳患者超过90%有阵发性连声咳,明显高于<3 月龄患者,但后者也达到了70.73%。唐琦钦等[14]研究表明,未接种疫苗的婴幼儿百日咳(67.5%<3 月龄)中,高达85.1%的患儿有痉挛性咳嗽。张喆等[5]报道211 例百日咳患儿(婴儿占88.6%),75.4%有夜间阵发性剧烈咳嗽,41.7%阵发性咳嗽伴青紫,28.9%有鸡鸣样回声。黄辉等[3]报道百日咳确诊病例198例(婴儿158例,占79.8%),痉挛性咳嗽发生率73.7%,咳嗽后发绀31.3%,咳嗽伴呕吐17.7%,吸气性吼声12.1%。朱慧慧等[15]报道≤3月龄百日咳入院时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比例(90.32%) 高于>3 月龄患儿(72.56%),且其痉挛样咳嗽(52.42%)、鸡鸣样回声(33.87%)、咳嗽后呕吐(35.48%)、发绀(53.23%)的比例也更高。婴儿百日咳在咳嗽发作时,一个呼气相内的咳嗽次数通常不及年长儿和成人典型病例那么多或密集成串,可能仅表现为只有连续2~4次咳嗽,而间之以憋气。婴儿百日咳无咳嗽或无明显咳嗽,而只有阵发性呼吸暂停、青紫或窒息的患儿较少,但这种患儿容易被忽略而贻误诊治时机,尤需警惕。
2.2 婴儿百日咳重症多,死亡风险高
婴儿百日咳可出现频繁呼吸暂停、重症肺炎、高白细胞血症、肺动脉高压等并发症,有致死风险[16]。需要重症监护干预的百日咳明显集中于婴儿病例,其中又以尚未到疫苗接种月龄的小婴儿为主,有研究直接将<6 月龄作为重症百日咳的诊断依据之一[11]。朱慧慧等[15]报道≤3月龄的124例患儿中,重症百日咳12 例(9.68%),明显高于>3 月龄组(4/164,2.44%)。在101 例百日咳合并重症肺炎患儿中,未接种疫苗者占79.2%(80例)[14]。
婴儿重症百日咳病死风险很高,报道的病死率为4.8%~50.0%[16]。疫苗前时代,美国百日咳死亡病例中,婴儿百日咳约70%,另外30%是1~5岁的百日咳患儿;疫苗广泛使用后,百日咳死亡者均为婴儿,≤3 月龄者占比超过90%[17]。我国2010~2020 年全国上报百日咳死亡病例数为13 例,每年上报0~3例。但婴儿百日咳实际死亡数远比上报情况严重。重庆儿童医院2015~2019年百日咳死亡25 例,其中24 例为婴儿[18];2016~2019 年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百日咳死亡13 例,其中3 月龄以下12例,另1例小于6月龄[19];2016~2017年北京地坛医院百日咳死亡4 例,均小于6 月龄[20];2016~2017 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百日咳死亡2 例[21];2019~2020 年湖南省儿童医院百日咳死亡1例,<6月龄[22]。
2.3 混合感染多
各种感染在婴儿期都容易发生,百日咳病程长,更容易出现混合感染。有研究显示百日咳患儿混合感染比例可高达67%[11]。混合感染也是婴儿百日咳易发生重症的原因之一。刘娟等[22]报道4 例换血治疗的重症百日咳患儿,气管导管内痰液、肺泡灌洗液及气管导管末端培养,除1例阴性外,其他均发现2~3种致病菌。混合感染也是百日咳病程长、病情反复的重要原因。当患儿百日咳尚未完全康复,又继发其他病原感染时,百日咳症状可以再度出现,从而导致病情反复,病程延长[23]。
研究报道的混合感染病原与当时、当地流行的感染病原种类、病原学检测条件、临床送检情况及结果判读等因素有关,因此不同研究报道的混合感染状况及病原种类存在很大差异。张喆等[5]报道的211 例百日咳中,鼻咽拭子分离到致病菌30 例(14.2%),其他病原20 例(9.5%)。广州报道的144 例儿童百日咳(婴儿140 例),混合病毒感染43例,混合其他细菌感染38例,且发现死亡病例混合感染其他细菌的比例比存活组更高,而混合感染病毒的情况则相反[19]。黄辉等[3]检测了66 例百日咳确诊儿童的病毒感染情况,发现9 例混合病毒感染,其中7 例合并副流感病毒Ⅲ型感染,这些患儿临床表现更重。吴少珍等[13]报道190 例百日咳患儿中共有115 例(115/190,60.53%)合并感染其他病原体,以合并感染病毒(73/115,63.48%)、细菌(58/115,50.43%)、支原体或衣原体(21/115,18.26%)为主。当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措施,不但可减少包括百日咳在内的呼吸道感染,而且能有效预防新型冠状病毒与百日咳发生混合感染[24]。临床实践中,应当注意混合感染可能掩盖百日咳的特征性表现。常见病原阳性仍需警惕百日咳混合感染。
2.4 血常规可有白细胞计数及淋巴细胞比例明显升高
婴儿,尤其小婴儿百日咳通常为初次感染,因此,血常规常可见白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占比明显升高。朱慧慧等[15]报道≤3月龄百日咳患儿入院时符合外周血白细胞计数≥20×109/L,且淋巴细胞比例≥60%的比例为41.94%。近来,有研究报道外周血裂隙淋巴细胞可辅助诊断百日咳[25]。伍金倩等[26]报道,若将裂隙淋巴细胞比率(在100 个成熟淋巴细胞中所占比例)≥4%作为诊断依据,则百日咳组阳性率为59.5%,高于非百日咳组5.8%。但是,裂隙淋巴细胞还可见于淋巴瘤和白血病。其实,在EB病毒等感染时,血涂片也可以查看到典型形态的裂隙细胞,甚至在正常体检血涂片也可偶见。因此,裂隙淋巴细胞仅可作为百日咳疑诊线索,不能作为特异性诊断依据。在百日咳流行时,观察评估裂隙淋巴细胞及其比率可能具有辅助诊断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疫苗免疫后再感染百日咳,绝大多数患者血常规不会出现上述变化或变化不明显。一项研究显示,同是≥3 月龄的百日咳患儿,未接种疫苗患儿外周血白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都明显高于接种过疫苗的患儿[14]。
2.5 实验室诊断婴儿百日咳,病原学检查优于抗体检测
婴儿百日咳通常就诊较早,适合开展病原学检测,包括特异核酸检测和细菌分离培养。因就诊早,在疑诊百日咳或有条件开展检测时,往往已经使用过抗生素,这样又会影响病原学检测。WHO 推荐百日咳病程1 个月内采用病原学检测,1个月后采用抗体检测[27]。由于免疫系统功能尚未成熟,小婴儿百日咳的抗体产生可能较慢。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数例小婴儿,百日咳病程已经超过1 个月,甚至已有2 个月病程,细菌培养仍阳性,而抗体水平依然很低。婴儿期是百日咳疫苗基础免疫阶段,这也给抗体检测结果解释带来影响。同时,已经接种过疫苗的婴儿,因为有免疫背景,感染百日咳后抗体有可能较早升高。总之,解读婴儿单份血清PT-IgG检测结果时,影响因素较多,临床意义不及病原学检测结果可靠。
2.6 抗菌药物选择有限
长期起来,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是百日咳清除细菌的首选抗菌药物,出生后即可选用,尤其适用于婴儿百日咳治疗。根据患儿情况,可以选用红霉素、阿奇霉素或克拉霉素[28]。对于敏感菌感染,一般推荐红霉素14 d 疗程,绝大多数7 d 就可显示明显效果,但少部分病例可能并不能清除细菌[29]。目前,国内临床分离的百日咳鲍特菌大环内酯类耐药常见[4],已经明显影响临床治疗效果。百日咳抗菌治疗的二线推荐药物通常是磺胺类抗菌药物,但应慎用于2月龄以下的婴儿。因有致命风险,如遇重症表现的小婴儿百日咳,临床可参照说明书注意用药的相关规定和原则[30],尽早使用有效药物。早期临床研究已经证明,β内酰胺类抗生素对百日咳的除菌效果明显不如大环内酯类[29]。体外实验也显示β 内酰胺类抗生素对百日咳鲍特菌的最低抑菌浓度已接近其他敏感菌(如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等)的中介水平[31]。因此,如要选用β内酰胺类,应在允许范围内使用较大剂量,且应14 d 足疗程治疗。近期,国内研究者也对β内酰胺类开展了清除百日咳鲍特菌感染的临床评估,发现对于大环内酯类耐药菌的清除效果明显优于红霉素,但对大环内酯类敏感菌来说,仍不如红霉素[32]。
综上所述,婴儿百日咳的出现是社区内百日咳持续传播的明确证据,婴儿是百日咳健康威胁最严重的群体,也是百日咳社区传播的重要节点,预防婴儿百日咳是疫苗免疫等百日咳防控措施的核心目标。国内目前报道百日咳明显以婴儿百日咳病例为主,但实际发生的婴儿百日咳病例更多,临床上还需提高警惕和认识,普及相关实验室检测。在重视识别婴儿百日咳的基础上,及时诊治、随访观察和规范管理其密切接触者,才能减少和阻断百日咳的社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