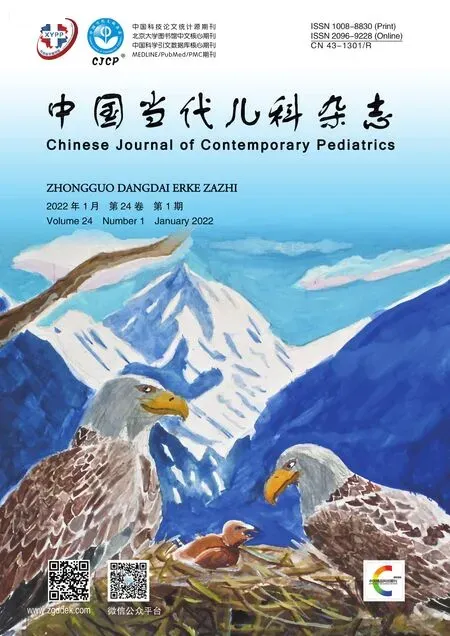子痫前期对母婴肠道菌群影响的研究进展
杨玥 综述 袁天明 审校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浙江杭州 310052)
子痫前期是妊娠期特有的并发症,影响着全球3%~5%的孕妇,是导致孕产妇及其子代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子痫前期对孕妇的近期、远期健康有不利影响,包括中风、高血压和代谢综合征等,其子代易出现早产、胎儿窘迫、胎儿生长受限(fetal growth restriction,FGR)、新生儿低血糖甚至死亡等不良结局[2-3]。子痫前期的病因是多因素的,有母体因素如子痫前期家族史、多胎妊娠、慢性肾病及肥胖等,还有胎盘因素如子宫-胎盘功能不全和胎盘体积/质量比增加等[4]。然而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近年来,随着对肠道菌群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肠道菌群的变化可能与子痫前期的发病相关,并影响子代的肠道菌群。故本文就子痫前期与母婴肠道菌群的相关性研究进行综述。
1 肠道菌群的功能
人体肠道微生物群由大约1×1014种微生物组成,包括细菌、真核生物、病毒和古生菌,其中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占80%~90%;其次是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和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参与机体代谢、营养、免疫等多种生理功能,影响多个系统疾病的发生与发展[5]。肠道免疫结构如肠道相关淋巴组织(gut 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GALT)、肠系膜淋巴结等的发育和成熟受肠道菌群信号通路的调节[5]。肠道菌群产生的活性物质有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胆汁酸、细胞因子、5-羟色胺等,其中SCFA是结肠上皮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对维持结肠上皮细胞形态和肠道正常功能具有重要作用,也能促进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的功能[6]。肠道菌群可通过刺激抗菌肽、黏蛋白和特异性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的产生,促使肠道上皮细胞对病原微生物和毒素进行防御[7]。其次,肠道菌群是“脑-肠轴”和“肠-肝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神经系统及肝脏功能形成双向联结通路[8-9]。
2 妊娠期母亲肠道菌群的变化
在妊娠期间,母体肠道菌群每3个月发生相应的适应性重构来维持正常妊娠[10]。与妊娠早期相比,妊娠晚期母体可能出现肥胖、血糖升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等,肠道菌群亦与母体生理状态的改变相适应,表现为菌群多样性降低,有益菌丰度降低,而促炎菌如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富集[11]。Aatsinki等[12]研究表明,妊娠中期孕妇的肠道菌群构成与孕期的体重增加密切相关,体重增长过度孕妇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丰度与高密度脂蛋白水平呈正相关。然而,也有研究显示,孕早期至孕晚期孕妇的阴道、末端直肠、唾液、牙齿/牙龈菌群种类组成方面均保持稳定[13]。
3 子痫前期与母亲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
3.1 子痫前期母亲肠道菌群的变化
子痫前期具有与代谢综合征相似的特征,可导致糖脂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和血管内皮损伤,从而引起母亲肠道菌群的相应改变[14]。Liu等[15]评估了妊娠晚期子痫前期母亲的肠道微生物变化后发现,致病菌如产气荚膜梭菌(Clostridium perfringens)和布雷德菌(Bulleidia moorei)的丰度增加,而有益菌如灵巧粪球菌(Coprococcus catus)的丰度降低,其中产气荚膜梭菌产生的α毒素可导致血压升高,灵巧粪球菌下降可能导致丙酸生成减少,增加胆固醇合成,最终增加子痫前期发病的风险。Lv等[16]对子痫前期母亲产前及产后的肠道菌群进行分析,并与血压正常、无妊娠期并发症母亲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布劳特氏菌属(Blautia)、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嗜胆菌属(Bilophila)和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在子痫前期母亲肠道中显著富集,与血压和肝酶水平呈正相关,上述细菌的富集与子代出生时Apgar评分和出生体重呈负相关;另一方面,粪杆菌(Faecalibacterium)、甲烷短杆菌属(Methanobrevibacter)、阿克曼氏菌属(Akkermansia)等在子痫前期母亲肠道菌群中显著减少,其中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水平与阿克曼氏菌属呈负相关。以上结论与Chen等[17]研究结果相符,其通过比较子痫前期母亲和血压正常母亲的肠道菌群发现,前者肠道菌群多样性减少,菌群失调明显,表现为机会致病菌如梭杆菌和细肠杆菌(Veillonella)富集,与母体血压、蛋白尿、肝酶和肌酐水平相关,而有益菌包括粪杆菌和阿克曼氏菌属明显减少。Gomez-Arango等[18]研究发现,产生SCFA如产生丁酸的臭杆菌(Odoribacter)丰度与孕16周时的母体收缩压呈负相关。以上妊娠期微生物群丰度的变化亦可能与子痫前期的发生和发展有关。
3.2 肠道菌群在子痫前期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肠道菌群失调已被证实可引起代谢性疾病,但肠道菌群在子痫前期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尚不清楚。目前关于子痫前期的发病机制有不同学说,包括胎盘重塑、抗血管生成反应、免疫应答的改变和氧化应激等,而肠道菌群也可能参与其中[19]。肠道菌群可通过多种机制潜在影响子痫前期的发病与发展,包括:(1)肠道中存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肠道菌群可产生相应的神经递质,进而改变血管张力和血管内皮功能;(2)调控宿主免疫功能;(3)影响宿主全身的炎症反应;(4)肠道菌群代谢产物调节血管功能。有报道称,肠道菌群在黏蛋白消化过程中会产生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肾素抑制剂及醛固酮,可引起全身血管收缩及血管内皮功能受损,从而诱发子痫前期[20]。肠道菌群失调时,革兰氏阴性菌繁殖增加,分泌更多LPS,通过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信号的传导和细胞因子的释放来激活炎症反应,参与子痫前期的发病[21]。子痫前期母亲肠道中梭杆菌的增加可导致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进而诱发免疫反应,影响细胞凋亡、增殖和DNA修复,破坏肠道上皮细胞,导致肠道渗漏,其后果可能是肠道细菌的易位[17]。Eghbal-Fard等[22]研究发现,接受子痫前期粪菌移植的孕鼠表现出Treg/Th17的失衡,从而加剧了胎盘的炎症反应,炎症因子的增多引起胎盘氧化应激和血管功能障碍,导致了母体对胎儿的排斥反应和高血压的发展。子痫前期与肠道菌群代谢产物氧化三甲胺水平升高有关[23],SCFA如乙酸、丙酸、丁酸的水平与高血压的发生呈负相关[24]。
3.3 子痫前期的微生态治疗
多年来,针对子痫前期的治疗一直局限于对症治疗或终止妊娠,近期研究[25-27]发现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紊乱可能对子痫前期的预防有一定作用。益生菌如双歧杆菌、乳酸杆菌(Lactobacillus)可通过蛋白水解和发酵作用,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活性,有效降低血压;益生菌的干预使肠球菌(Enterococcus)等致病菌减少,提升肠道屏障功能,并调节Th1/Th2水平,从而减轻炎症反应[25]。两项对挪威初产妇的调查研究发现,长期摄入含乳酸杆菌乳制品的母亲子痫前期发生率明显下降[26];与孕早期相比,在孕晚期摄入更可显著降低子痫前期的风险[27]。Sun等[25]发现经益生菌治疗的子痫前期大鼠肠道菌群定植能力明显增加,内皮素-1水平降低,一氧化氮水平增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血管通透性及炎症反应,使收缩压、舒张压处于正常范围。上述关于子痫前期微生态治疗的研究结果亦从侧面证实肠道菌群与子痫前期的发生有一定关系。
4 子痫前期对婴儿肠道菌群的影响
4.1 婴儿生后肠道菌群定植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既往认为新生儿的肠道菌群定植是从出生时开始的,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胎盘、脐带和羊水中存在细菌,表明胎儿在分娩前就已经暴露于微生物环境中[28-29]。母亲肠道、阴道、皮肤等部位及乳汁中的微生物菌群是新生儿生命早期肠道菌群定植的重要来源,受分娩方式、胎龄和喂养方式等因素影响[30]。分娩方式被认为是影响婴儿早期肠道菌群组成的重要因素,经阴道分娩婴儿的肠道被母亲阴道微生物定植,如乳酸杆菌和普氏菌(Prevotella);剖宫产的婴儿拥有与周围环境和母亲皮肤表面定植相似的菌群,主要为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棒 状 杆 菌(Corynebacterium)等[31]。胎龄是新生儿建立肠道菌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胎龄小于37周的早产儿通常存在肠道发育不成熟,母婴分离、抗生素治疗、侵入性操作和胃肠外营养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肠道菌群的定植、分布与发展,导致肠道微生物的异常建立。与足月儿相比,早产儿的肠道菌群多样性较低,有益菌如双歧杆菌、拟杆菌的定植延迟,而肠杆菌(Enterobateriaceae)、肠球菌和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a)等机会致病菌的含量显著增高,早产儿粪便的SCFA水平低于足月儿[32-33]。喂养方式与婴儿早期肠道菌群定植密切相关,母乳微生物群是婴儿肠道菌群的重要来源。研究表明,与配方奶喂养婴儿相比,纯母乳喂养婴儿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较低,其中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含量高于配方奶喂养婴儿[34-35]。母亲孕期肥胖、妊娠糖尿病等产前因素也可影响婴儿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发展[36]。Collado等[37]观察到婴儿粪便微生物组成受母亲孕期体重增加的影响。研究显示,与健康母亲所生子代相比,妊娠糖尿病母亲子代肠道菌群多样性显著减少,其中放线菌和变形菌增加,而普氏菌和乳酸杆菌的相对丰度明显降低[38]。
4.2 子痫前期对婴儿肠道菌群的影响
关于子痫前期母亲子代肠道菌群变化的研究鲜有报道。子痫前期会导致婴儿不良结局,如早产、低出生体重等,研究发现子痫前期母亲肠道菌群的改变会影响子代出生时Apgar评分和出生体重[16],推测子痫前期母亲所生子代肠道菌群变化可能与早产儿或小于胎龄儿相似,表现为多样性降低,机会性病原微生物增多等。母乳是婴儿肠道微生态组成的重要来源,妊娠期血压升高母亲的乳汁微生物多样性和乳酸杆菌相对丰度较低,促炎因子水平增高[39],推测子痫前期母亲母乳喂养的子代亦可能出现肠道菌群多样性及乳酸杆菌含量的降低,对婴儿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与妊娠糖尿病相似,子痫前期可能由母体妊娠期代谢异常所致,通过现有的对妊娠糖尿病母婴肠道菌群的研究可以推测,子痫前期母亲所生子代的肠道菌群变化可能与其母亲具有一致性,即菌群多样性降低,致病菌如布劳特氏菌属增加,有益菌如粪杆菌减少[40]。
4.3 肠道菌群影响子痫前期母亲子代预后的机制推测
Jiménez等[41]在胎鼠粪便中发现移植至孕鼠肠道中的被标记的大肠杆菌,而没有接受移植的孕鼠后代胎便中则未检测到该菌;Wang等[40]研究发现妊娠糖尿病母亲及其子代微生物菌群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以上研究证实了肠道菌群的母婴传递。子痫前期母亲的子代有不良预后,可能发生早产、FGR,甚至出现脑损伤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本文对子痫前期母亲和患有以上疾病的新生儿肠道菌群变化的相似之处进行分析,推测其中的可能机制:子痫前期母亲与早产儿肠道菌群中均观察到梭杆菌的富集[42],梭杆菌通过黏附素破坏肠道屏障功能后扩散到羊水、胎膜和胎儿中,使胎膜发生与绒毛膜羊膜炎类似的病理变化,最终导致早产[43];并可通过刺激孕鼠胎盘中TLR-4介导的炎症反应,导致胎儿死亡[44]。Seki等[45]观察到克雷伯氏菌在脑损伤早产儿肠道中过度生长,该菌被发现定植于子痫前期母亲胎盘中[46],亦可引起母亲尿路感染,从而导致子痫前期的发生[47],增加的克雷伯氏菌可能驱动免疫细胞的促炎极化,使外周血中的γδT细胞向中枢神经系统迁移,导致大脑皮质电位抑制及神经保护物质分泌不足,影响神经生理发育[45]。变形菌门的丰度在子痫前期母亲和NEC新生儿肠道中均增加[48],变形菌门通过激活TLR-4导致肠细胞凋亡增加、黏膜愈合受损和促炎因子释放增加,并减少肠系膜的血流量,形成肠缺血和坏死,从而引发NEC[49]。此外,在FGR的幼猪肠道中也发现变形菌门丰度增加,其可能通过参与炎症反应导致FGR的发生[50]。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许多研究提示子痫前期母亲存在肠道菌群的改变,而肠道菌群与代谢综合征、妊娠糖尿病、血压调节等相关,菌群失调可通过打破免疫耐受、增强炎症反应及代谢紊乱等参与子痫前期的发病,并推测可能影响子代肠道菌群的结构形成。但目前子痫前期与母婴肠道菌群的相关性及具体机制的研究仍较少,期待未来进行更多研究进一步阐明,从肠道微生态角度为子痫前期相关母婴并发症的预防及治疗提供新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