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钱”捐赠,收还是不收?
贺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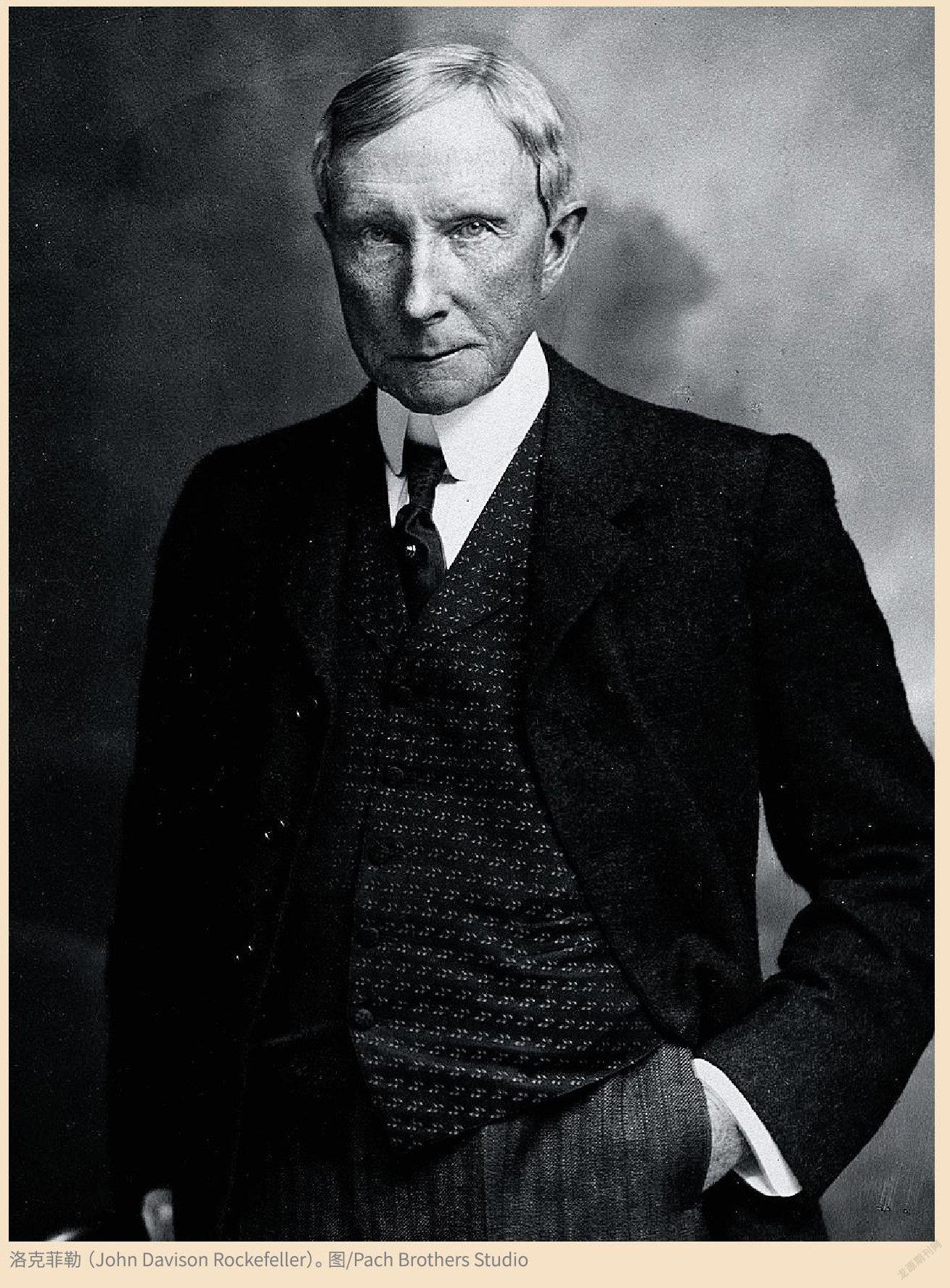
在“脏钱”捐赠背后,更应警惕的是非营利组织和捐赠者的利益交换
登基成为英国国王后,查尔斯担任王子和威尔士亲王期间所创立的二十多家基金会和慈善机构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
除了更为繁忙的日程安排,难以再对慈善事业亲力亲为外,基金会的名称或许也会面临变动。而更不确定的是来自外界的评价——就在一个多月前,威尔士亲王慈善基金会(PWCF)2013年接受的一笔100万英镑捐赠被爆出,捐赠人来自本·拉登家族。
这不是查尔斯名下的慈善机构第一次被爆出涉嫌“脏钱”捐赠。去年9月,苏格兰慈善监管机构曾就王子基金会接受俄罗斯银行家德米特里·雷乌斯50万英镑捐款展开内部调查。
今年2月初,因一名沙特商人在向查尔斯王子基金会捐赠150万英镑后,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和爵位,英国警方对王子基金会发起调查。
尽管时隔多年,这些捐赠被曝光后依然会引发强烈关注,这也反映了人们对“脏钱”用于慈善公益的担忧和不安。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依然是慈善领域的两难问题。
脏钱背后,
人们在担忧什么?
“脏钱”一词本身是委婉的说法,暗示着有不当行为或有争议的捐赠者,其资金存在着天然的不道德性。
关于“脏钱”的讨论由来已久,后来以大慈善家形象出现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钢铁大王卡内基,在其进入慈善领域的早期,因财富积累过程中的垄断性和非正当性,都曾被指谪为“脏钱”而受到民众和慈善机构的抵制。
而生前广受赞誉的特蕾莎修女,在其捐助者中,也能列出一长串“恶棍”名单,比如挥霍公司员工养老金并欺诈银行的出版商罗伯特·麦克斯韦;利用银行贷款欺骗投资者和贿赂政客的林肯储贷社主席查尔斯·基廷,当后者于1992年被判10年监禁时,特蕾莎修女甚至写信向法官求情。
有人认为,对于慈善组织而言,脏钱与否很难判断。在查尔斯被诟病的几笔捐赠中,雷乌斯因洗钱入刑,其捐赠动机或有“洗钱”之嫌。据称王子基金会的道德委员会在发现雷乌斯于2004年因洗钱被定罪后,拒绝了这笔捐款。
而本·拉登本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其家族资金是否也属“脏钱”却难以定论。威尔士亲王基金会宣称,在接受捐款前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尽职调查,这笔捐赠也经过了当时5位受托人同意。从流程上似乎并无不妥,但在一些公众眼中,这笔来自9年前的捐款,依然不可接受。
这也反映出非营利组织管理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大多数非营利组织依靠捐赠资源创造社会价值,而在“脏钱”的标尺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对于捐赠者的选择受到了诸多限制。
如果捐赠者已经被认定违法,或是声名狼籍,出于对自身羽毛的爱惜,很多非营利组织都会小心避开。
但是,除了避开那些有明显违法行为的捐赠者之外,如果捐赠者有着道德瑕疵,接受他们的捐赠也会受到来自批评者的关注和质疑,从而影响非营利组织的形象,之后的募款会变得更加困难。
由于很多捐赠者都来自于企业,在企业运营过程中,一些商业操作、避税行径,以及代际传递带来的财富积累,往往毁誉参半。如果对捐赠者的道德要求无限放大,我们似乎很难找到符合标准的捐赠者。
如果捐赠者和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和价值观相悖,在当下也会受到批评。比如当一个环保组织接受一家污染企业的捐赠,一家救助肺病患者的机构接受一家烟草企业的捐赠等等。
这就提出了一个命题,“脏钱”的背后,人们究竟在担忧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要从捐赠动机上来分析。以洛克菲勒为例,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浸会教徒,早在年轻时,做小职员每月收入仅6美元,也会定期捐赠收入的6%给教会学校。成为石油大亨后,由于暴揽财富的方式在当时引起公愤,美国外国传教士委员会甚至不愿意接受他的“脏钱”,但洛克菲勒和他的顾问从没停止过用慈善买回他们的名声。如果说洛克菲勒把慈善捐赠当成他改善公共形象的工具,也无可厚非。
而在王子基金会那场以捐赠换荣誉的丑闻中,查尔斯的助手迈克尔·福塞特曾给沙特亿万富翁马赫福兹去信,表示“鉴于……阁下的慷慨解囊,我很高兴私下向你确认,我们愿意支持和帮助你申请公民身份。我们愿意提出申请,将阁下的荣誉从名誉CBE(司令勋章)提高到KBE(爵级司令勋章)”。去年,福塞特在接受内部调查后辞职。
可见,在“脏钱”捐赠背后,更应警惕的是非营利组织和捐赠者的利益交换,或是获得干涉非营利组织业务的权利,或是获得足以“洗白”的公众认可和影响力,或是用于洗钱,或是被授予某项荣誉等等,当慈善捐赠的目的不再纯粹,非营利组织则难以保持独立性,其公信力和社会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进退两难的脏钱捐赠
然而,非营利组织如何判断捐赠资金来源的正当合法性?何况,现实往往是,在接受捐赠时,或许“钱是干净的”,捐赠人并未爆出道德和违法行为,但当问题发生后,如何对待这笔捐赠则更为棘手。
在公众的普遍认知中,“退还”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但事实上,由于非营利组织普遍依赖捐赠资金,待数年后事发,捐赠资金早已使用,无钱可退。
2019年夏天,因性侵未成年人入狱、随后又在狱中离奇死亡的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引发了学术圈的“大地震”。
由于爱泼斯坦生前曾向多所高校捐赠,和学术圈关系密切,在他死后,这些高校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在过去20年间,麻省理工学院从爱泼斯坦基金会获得了约80万美元的資金,大部分已经花掉,学院表示,将把同等数额的钱捐给惠及性侵受害者的慈善机构。哈佛大学也声称已经用掉了爱泼斯坦2003年捐赠的650万美元,剩余的捐款共计18.6万美元,将捐给援助人口贩卖和性侵受害者的团体。
而对于一些受赠金额较少的大学而言,似乎背负的道德压力也相对较小。亚利桑那大学声明不打算退还2017年收到的5万美元;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表示不打算退还2011年从爱泼斯坦慈善机构那里获得的2.5万美元。
除了“退还”或“转赠”,斩断与捐赠人未来的联系,也不失为一种平息舆论的方式。
2018年,因普渡制药公司故意隐瞒关于其明星产品奥施康定可导致药物上瘾的信息,助长了全国范围内阿片类药物的流行。在法庭指控之外,愤怒的民众将怒火转向了公司所有者萨克勒家族的慈善捐赠上,抗议者聚集在40年前捐建的萨克勒侧翼内,要求大都会博物馆停止接受其捐赠。
在持续的抗议之下,2019年,大都会博物馆不得不发布公开信,表明将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赠。但它也声明,“博物馆并非政治机构,不会对捐赠者进行正式的政治倾向或道德水平检验”;同时还表示,“我们觉得有必要远离那些不符合公众利益或我们机构利益的捐赠。”之后,大都会博物馆决定将萨克勒家族的名字从其资助的博物馆侧翼上抹除。
随后,接受过萨克勒家族捐赠的其他博物馆也紛纷发表公开声明,表示不再接受萨克勒家族的捐赠。尽管萨克勒家族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财富,但各博物馆都认为与萨克勒家族的慈善合作弊大于利。
如何避坑?
是否“脏钱”难以判断,那么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说,如何避开“脏钱”的坑?
尽管查尔斯名下的慈善机构屡屡被爆出捐赠来源问题,但在流程上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在王子信托的网站上,有一项道德筹款政策,针对被视为重大风险的捐赠和合作机会,王子信托制定了稳健的决策流程。受托人将有关道德筹款和声誉风险的捐赠接受决策的日常责任委托给道德筹款和声誉风险委员会(EFRR)和筹款领导小组。
王子信托还制定了许多道德筹款和声誉风险指标,通过这些指标来评估捐赠或筹资机会。其中,风险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与非法活动的关联、可能对年轻人成功机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活动,以及对王子信托声誉的潜在负面影响。如果捐赠被认为具有重大风险,王子信托基金的道德筹款和声誉风险委员会(EFRR)将通过评估,决定是否应接受捐赠。
目前,王子基金会和威尔士亲王基金的网站都暂时处于关闭状况,无法得知是否有类似的一套筹款政策,但从媒体报道出来的组织结构来看,也都具有一套完备的受托人制度和相关审查委员会,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摆脱脏钱捐赠的泥沼。流程规范的大慈善机构如此,小规模的慈善机构更是无从规避。
那么,在实现公益价值和接受脏钱捐赠之间,非营利组织应如何取舍?一方面,洁身自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另一方面,在不存在利益交换的条件下,钱的来源是否依然那么重要?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选择将同样规模的钱捐赠给其他慈善机构,而不是退还给爱泼斯坦,恰恰说明钱本身不存在干净或肮脏,而是可被替代的,从这个角度看,不存在道德问题。
只要保持机构和项目的独立性,不承诺捐赠人相关的认可和影响力,任何捐赠都是合法的。钱本身没有错,关键还在人心。
我们常在电影中看到这样的结局,侠盗在卧底与犯罪集团进行一笔非法交易后,款项最终匿名转入某个慈善组织的账户。镜头一转,修女装扮的慈善组织负责人对从天而降的巨额捐赠欣喜若狂,侠盗则深藏功与名。
没有人会去质问这笔钱是否是“脏钱”,毕竟,它大概率会被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
这才是捐赠最好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