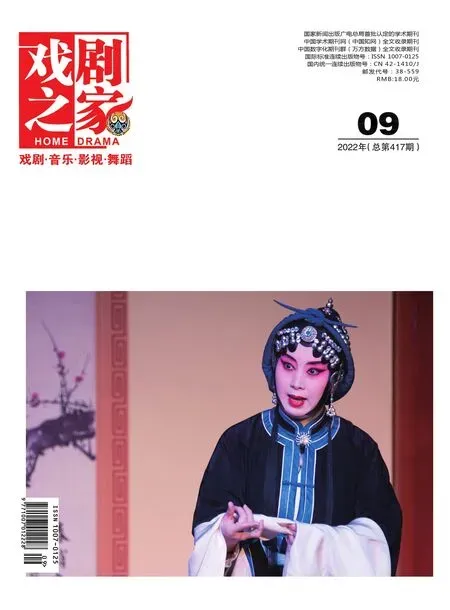以悲剧精神确立民族性的瓦格纳歌剧
——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漂泊的荷兰人》为例
孙 辉
(青岛科技大学 传媒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
十九世纪初期,受意大利和法国歌剧的影响,德国歌剧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德国剧作家瓦格纳通过自己一生的实践对德意志歌剧进行改革,逐渐确立了一种本民族的歌剧传统及风格。本文从瓦格纳作品中体现的悲剧美学入手,并将这种美学风格与同时期流行于德国的意大利和法国歌剧进行对比,从尼采的悲剧理论、瓦格纳歌剧的悲剧精神、以悲剧精神来确立的民族性三方面逐步阐述瓦格纳歌剧是如何区别于意大利和法国歌剧,通过悲剧精神来确立德国歌剧民族性的。
一、尼采的悲剧理论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是面对无法掌控的命运捉弄而引起人们的怜悯与恐惧,在一种命运不可对抗中引发人们的共情。黑格尔认为,悲剧是两种对立理想的冲突与和解,一种理想的实现需要另一种理想的毁灭。代表片面理想的个人虽遭受毁灭,却使代表整个世界秩序的正义理想得以伸张,这种毁灭是一种“永恒正义”的胜利。笔者认为,尼采的悲剧理论是对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理论的扬弃,他所认为的悲剧是一种在个体命运无常的痛苦和毁灭之下产生不朽的精神,既是一种恐惧和怜悯,也是一种精神的振奋。
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哲学领域,与瓦格纳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尼采,瓦格纳通过自己的歌剧改革实践在作品中创造出具有史诗性和古希腊悲剧意识的作品,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深深吸引着尼采。尼采在受到瓦格纳作品启发后创作出《悲剧的诞生》一书,他认为瓦格纳的歌剧就是古希腊悲剧消亡之后的复活。尼采一生都在关注痛苦与文化的关系,“其立足点不是回避或消除文化,而是为了肯定人生而肯定人生必有之痛苦,并寻找一种真正能够肯定痛苦的内在力量的文化”,尼采在瓦格纳的歌剧中找到了他所寻求的答案,认为艺术是一种能够为生命创造意义的文化,并由此提出了他的悲剧哲学理论。尼采认为,悲剧诞生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结合,在本质上是一种酒神精神。日神阿波罗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象征一种宁静的美好外观。而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代表着生命的热情和一种“醉”的迷狂状态,是一种从天性中涌现出来的狂喜与痛苦,代表着一切非理性的力量。尼采认为悲剧消融了两种精神之间的冲突对立,使得二者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最终产生了悲剧——这种既具有美的外观,又在精神上充满着“醉”的激情和力量的艺术品。
二、瓦格纳歌剧的悲剧精神
瓦格纳歌剧中的悲剧精神首先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个体在命运无常下的痛苦和毁灭。在《漂泊的荷兰人》中,荷兰船长个人就处在命运的诅咒之下,每七年才能上岸一次,其余时间只能永远在大海上漂泊,只有找到真心爱他的女子才能得到解脱。挪威船长德兰达的女儿森塔在命运的感召之下认定自己会成为解救荷兰船长的女子,二人也在互相了解之后一见钟情,互相宣告了自己永恒的忠贞与爱情。但在第三幕中,荷兰船长在看到森塔与其追求者艾里克对话之后误认为森塔背叛了二人的承诺,在心灰意冷之际回到大海,继续漂泊。而森塔为了证明自己忠贞的爱情纵身跳入大海,以毁灭的方式表达对命运的反抗。在《漂泊的荷兰人》中,我们能看到一种个体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和痛苦,而个体在命运无常之下往往走向毁灭。
其次,瓦格纳歌剧的悲剧精神在内核中表现为永恒生命的不朽,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下显现艺术的本源力量,也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在《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第一幕中,命运使得现实之中不能在一起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以另一种方式坠入爱河,将心连在一起。这种隐秘的爱情随着第二幕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二人的幽会进入了高潮,在激情昂扬的曲调和表演之下呈现出一种高昂的热情与迷狂,在狂喜之中沉浸于他们忠贞的爱情。而这种短暂的狂喜却被国王马克发现,特里斯坦被国王侍臣刺成重伤,喜悦成为命运使然的痛苦,这种狂喜与痛苦交织正是酒神精神的表现,呈现了悲剧的本质。这种本质在第三幕中继续升华推进,国王知道事情真相之后想要成全他们,但特里斯坦却死在了伊索尔德的怀里。伊索尔德在失去爱人的痛苦和回忆的狂喜之下随特里斯坦一同进入极乐世界。她最后的一人独唱使整部戏的主题得到升华:“在这浪涛汹涌的声音中,在这响亮的声音中,在世人呼吸的巨大气浪中——淹死。不知不觉地,使极大的欢乐,沉没。”在这场悲剧中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两个个体毁灭了,而个体的毁灭却显现出二人爱情的永恒不朽,显现出永恒生命的不朽。瓦格纳戏剧的悲剧性也正是通过这种形式表现给观众,在永无休止的痛苦和狂热的交响下,个体犹如生命狂流下的一粒沙,个体的毁灭犹如沙土归于大地,而正是这一粒沙在命运无常中与大地永存,个体在生命无常下显现出永恒生命的不朽。
三、以悲剧精神来确立的民族性
十九世纪,欧洲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国家建立,这是对传统宗教和封建王权的反抗。“民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了。推翻王权、教权,建立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意识在十九世纪欧洲人民心中逐渐形成自觉,艺术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歌剧艺术1597 年诞生于意大利,这样一种戏剧形式迅速在意大利流行并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18 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意大利歌剧走出宫廷和教堂,逐渐市民化,形成了喜歌剧,并在德国开始流行起来。1805年拿破仑占领德国,一方面由公国给予资助的剧团失去了经济来源,另一方面法国歌剧迅速在德国流行使得当时许多作曲家都根据法国歌剧的样式进行创作和布景。1815 年拿破仑离开德国后,剧团的资助虽然恢复,但剧团却变成由政府官员控制,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逐渐磨灭了剧团的创新意识。拿破仑战争虽然令德国政治、文化受到重创,却促进了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但是,剧团创新性的缺失以及意大利和法国的歌剧在德国的普遍流行使德意志歌剧传统和风格的建立困难重重,民族歌剧处于夹缝中生存的尴尬境地,德国剧作家开始有意识寻求德国歌剧的自我独立风格。
痛苦与狂喜的交织、个体的毁灭显现永恒的不朽,瓦格纳在悲剧精神和严肃性下进行歌剧改革,逐步确立了德国歌剧的民族性。瓦格纳在《歌剧与戏剧》一书中,经常提到“严肃”一词,他反对戏剧创作中存在的轻浮态度,如随意插入的歌唱、毫无意义的炫技表演以及生硬的芭蕾舞等。而瓦格纳这种对于歌剧的“严肃”的态度正是对流行于德国的意大利歌剧的批判。实际上,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中世纪时期单一严肃的意大利宗教戏剧逐渐市民化、大众化,而歌剧在诞生之初本就是意大利宫廷贵族消遣娱乐之物,所以意大利的歌剧尤其是喜歌剧自然具有娱乐和轻松的特点。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已经历了多年革命和战乱,公民对太平盛世的渴望使法国形成一种追求声乐享受的风气,轻歌剧开始盛行。将意大利多尼采蒂的《爱的甘醇》和法国奥芬巴赫的《天国与地狱》与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和《漂泊的荷兰人》进行对比,就能够看到其风格完全不同。《爱的甘醇》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意大利的小村庄,故事荒诞曲折,充满着世俗化和诙谐幽默等特点;《天国与地狱》则将奥菲欧与尤丽迪茜的悲剧故事处理为喜剧,对原古希腊神话故事进行改编,使其具有轻松愉快的风格。《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与《爱的甘醇》都歌颂爱情,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以一种悲剧形式通过主人公的毁灭表现爱情的永恒,让观众在震撼与怜悯之中获得净化。《天国与地狱》和《漂泊的荷兰人》都是对神话故事的改编,后者却没有前者的轻松愉快与幽默诙谐,而是通过森塔的死和幽灵船的沉没营造出以死亡完成救赎的崇高之感,在森塔与幽灵船共同沉入大海之后,荷兰人与森塔的形象在光辉处共同出现,以毁灭实现了永恒。通过对比这四部歌剧,我们能够看到瓦格纳在悲剧精神下表现出来的与当时其他歌剧所不同的民族性与严肃感,这种严肃性和崇高感是一种对流行于德国的意大利和法国歌剧模式的反叛,这种“深思与严肃”的民族性是德国歌剧实现自己国家歌剧艺术独立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瓦格纳的歌剧是辉煌的古希腊悲剧的复活与重生,他的歌剧以一种痛苦和狂喜交织的酒神精神来找寻生命之意义,以个体生命的无常来呈现永恒生命的不朽。这种悲剧精神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洗礼,让人在找寻自我存在与感受生命永恒的同时也为瓦格纳的歌剧营造出一种严肃感,这种严肃感为意大利和法国歌剧模式盛行的德国创造了一种“深思与严肃”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具有一种有别于意大利喜歌剧和法国轻歌剧的独特风格,这种独特风格将德国歌剧推向了辉煌的顶点。
注释:
①迈克尔·坦纳.牛津通识读本:尼采[M].于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②瓦格纳.瓦格纳戏剧全集[M].高中甫,张黎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