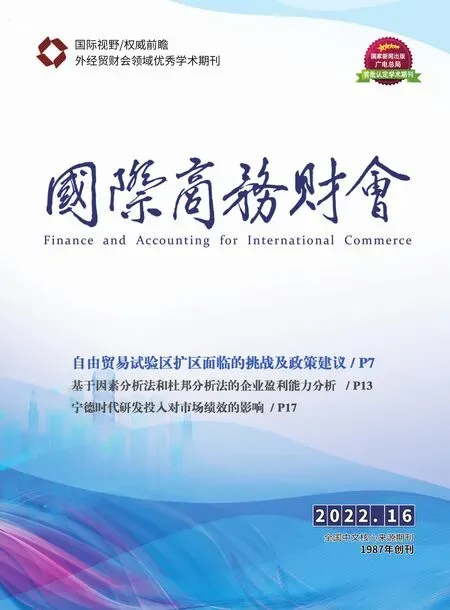疫情暴发对全球化及区域整合的反思
齐冠钧 尹政平 刘 娅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过去30 年来的全球化不断深化,导致先进国家高度仰赖外包(off-shore),丧失了工作机会及对基本物资的生产能力,也使各国暴露在供应链断链的风险中。引发对经济全球化及全球供应链结构的质疑。尤有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正是“疫情全球化”的主因。这样的反思引发的后果,就是开始出现生产回流(re-shoring)、经济“自给自足”等去全球化的主张。
全球化发展在疫情前就已经在趋缓中。各国或因内部的贫富差距、治理失灵,或有感于南海、朝鲜及中美等大国及地缘冲突风险,乃至于看到新科技带来的机会,都出现某种程度的去全球化作为。固然因新冠疫情引发的去全球化主张,有很多属于缺乏佐证的政治性论点,但对于“后新冠”世界秩序的讨论,国际上已有二种见解:一派认为原本已经脆弱的全球化会更加式微;一派则指出新冠疫情正好凸显国际合作的意义,全球化的定义及运作模式将从此改写。
一、公共卫生及经济安全受各国重视,不利于区域整合
新冠疫情扩散如此迅速,使得“公卫安全”(以及其他关键物资)及更广泛的经济安全议题受到各国广泛的重视,对全球贸易及投资的冲击难以避免。如同能源及粮食安全,现阶段关于公卫安全的讨论,也强调“自给率、战略存量”等概念的讨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于2020 年5 月14 日发布声明,指出疫情反映出美国过度仰赖进口造成的冲击,因此将重建美国对于医卫产品之下世代战略国家库存(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SNS)机制,并将以在地化产能作为SNS 的支柱,以降低对进口商品的仰赖。在配套的行政命令中,特朗普总统授权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DFC)采取包含提供贷款在内的必要措施,建议能处理类似新冠事件所需战略资源的国内生产能量,包括加强美国及其领土内的相关供应链的建立。以建立、维护,保护,扩展和恢复美国相关工业基础能力,降低对进口产品的依赖。对此,美国将投入高达250 亿美元作为本计划的预算。除此之外,澳洲、日本及欧盟国家均出现类似检讨、重建医卫供应链,降低进口依赖以确保公卫安全的供应链从外包(off-shore)再回流(re-shore)思维。
过去粮食及能源安全的自给率制度相对清楚,但公共卫生安全自给率的定义、范围、对象及方式则还在酝酿阶段。目前这种降低对进口依赖的自给率思维,已有延伸扩大到所谓战略性产业的趋势;近期台积电赴美投资的决定,便可谓属于这种思维的结果。未来亦可能出现保护主义藉“国产化”为由扩大对国际贸易及区域整合进一步造成影响。总之,不管未来各国如何定义任何自给率机制,都是一种排斥外国货、外国人,与全球供应链背道而驰的制度,性质上不利于区域整合及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二、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整,彰显区域整合的意义
虽然新冠疫情导致许多国家重视供应链安全,不利于区域整合,但另一个基于强化供应链韧性的思维,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却有助于彰显区域整合机制在后疫情时代的价值。
过去30 年来全球供应链架构越来越深化,分工(分包)网络日趋复杂、卫星工厂及国家越来越多,供应链管理本身就已成为一种“营业秘密”,然而专业分工越细,脆弱度也越高,致使一个环节出错,整个链条就会停摆。
在疫情暴发前,World Bank 及WTO 等国际组织联合出版的《2017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便指出2011—2015年间全球生产网络及制程开始萎缩,出现“在地生产、短链调整”现象。新冠疫情导致中国制造业接近停摆,再度凸现出供应链脆弱度及韧性的问题。基本上,这次危机彰显出三个供应链脆弱的老问题,一是“投资地集中”问题,二是“区域集中”问题,第三是低库存。以台湾为例,80%的外资通讯产能在大陆,LED 生产也近五成,疫情导致停工造成的伤害便无法规避。区域集中问题可以本田(Honda)汽车为例,其在中国5 座工厂中的3 座位于湖北,占总产能近五成,便成为这次冲击最大的外资汽车厂。最后,低库存与实时制造(Just-in-Time manufacturing)为丰田生产模式(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TPS)的特色,优点为降低生产成本(或是成本移转给供应商),缺点则为面对新冠疫情时,便可能因下游无法供货而导致整个生产线停摆。
有集中度问题或采用TPS 生产的厂商并非不了解集中度的风险及脆弱度问题,而是在传统制造科技中,集中度及TPS 往往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包含规模经济、采购效益等。面对陆续来到的在地生产、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前述结构的缺陷也不断被凸显,因而强化供应链风险管控能力及供应链韧性已成为企业甚至一国经济的关键改革重点。OECD 将此称之为处理经济挑战新方向。
供应链韧性可简要定义为特定系统面对无预期破坏干扰事件的调适及恢复能力。其中关键因素包含恢复速度及恢复程度。因而在后新冠时代调整关键,并非完全放弃规模经济及生产效率,而是调整寻求规模及韧性之间的平衡点。对此,OECD 建议企业必须开始有以下的布局调整以强化韧性:
加速数字科技转型导入及对新生产科技的接受及了解,提升藉由大数据、AI 及物联网等科技对供应链管理、弱点及风险评估能力,以数据建立集中度及强化韧性及最适库存的评估架构,以便客观了解差异并支持做出决定。通过加速“去中心化、分散式”供应链的布局规划,以便在重要环节建立“防火墙”及其他“阻断机制”,以避免一个环节的问题导致整个供应链瘫痪。加速自动化生产速度,提升因天灾疾病等导致的干扰的恢复力。加速导入能够支持分散式供应链的管理架构、信息系统及管理人才。
新冠疫情带动供应链加速“去中心化、分散式”调整,当然不等同于去中国化,但是因受到贸易战及科技战影响的产品已经开始自中国调整供应链布局,加上过去各国企业高度集中在中国,导致当生产线及供应链均有搬迁、分散布局的改变时,虽然赴中国投资的外资仍然为数不少,但因为规模很大,于是看起来就呈现出“去中国化”的趋势。以办公室及电信设备为例,2018 年中国含香港占全球出口值的47%,而在纺织业中国更成为全球最大的供应链核心,当这些供应链开始导入去中心化分散供应调整时,很自然给外界“去中国化”的印象。
供应链的移转分散在疫情前便已经出现,特别是自2018 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进口商为了规避关税,开始积极寻找中国以外的供应来源(亦即俗称的转单效应)便是一例。以机械设备为例,因贸易战转单的受益者以欧盟最高,2019 年对美增加出口为2.43 个百分点,其次即为属于CPTPP 成员国的墨西哥(增加1.23 个百分点)及日本(增加0.86 个百分点)。由以上趋势可知,CPTPP 成员国中的日本、越南、马来西亚及墨西哥等国,在过去两年中逐渐与美国的供应链关系深化、扩大。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因前述供应链韧性的考量开始推动的去中心化、分散化所采取的变革,亦会继续降低各国对传统经贸伙伴的依赖关系,增加开发新供应链伙伴及网络的需求,将可能加速供应链变革的速度。
在此趋势下,对亚太区域内甚至区外的新供应链网络的变化。同时基于分散式供应结构的布局需要,如RCEP、CPTPP 等多国参与的大型区域整合协定的价值反而会更加受到重视。
三、后疫情时代区域整合及合作新契机
另一个彰显区域整合价值的发展,则为许多亚太国家发起的供应链安全倡议。为应对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全球及区域经济封锁及其冲击,已有许多国家开始推动区域性合作机制,作为降低影响,加快恢复速度的基础。例如由加拿大发起的因应新冠疫情部长及协调小组(Ministerial Coordination Group on COVID-19,MCGC)便于2020 年4 月中旬由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尼、意大利、墨西哥、摩洛哥、秘鲁、韩国、新加坡、土耳其及英国贸易或经济部长联名发布维持必要全球连结共同声明,宣布将推动在医疗、疫苗、物流运输、贸易及其他领域的全球合作,并将持续推动自由贸易,并确保疫情管理措施满足“合比例、透明性及暂时性”等要件,以符合WTO 规范并降低对全球贸易的干扰。此外,新加坡亦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CPTPP 成员国加上韩国贸易部长,另外针对加速恢复双边及区域人流及物流,确保供应链恢复运作的共同合作达成共识。
APEC 亦于2020 年5 月发表贸易部长宣言,共同宣示各国同意将致力于促进必需产品的流通,并尽力减少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维护贸易的连结及畅通。APEC 国家亦将此宣言表达维护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对促进经济增长、加强亚太区域连结性有重要意义的认知。
前述的区域整合新方向有几个重点。第一,各国防疫措施主要靠本身的公共卫生防护网,但疫情过后的经济复原却必须仰赖各国相互合作。第二,重建被疫情打乱的全球经济网络要恢复运作,如何重建经贸伙伴间的互信基础为关键的起步。以上方向,反映出如CPTPP、APEC 等现有区域整合机制,原本即为“有志一同”(like-minded)国家的组合,很可能在后疫情时代作为提升各国在维护经贸秩序及建立经贸互动信心的平台,未来若借此平台持续推动公共卫生安全区域合作(而非各国以单边措施进行)、供应链重整信息交流等发展合作,进而成为后疫情时代之“信任联盟”的基础,其价值反而更为突显。
对中国而言,在后疫情时代更需争取成为本区域可信赖伙伴的认同,而通过如RCEP 等区域整合机制,将是最直接争取建立此一信任伙伴关系的方式。此外,通过RCEP 的参与,对于协助我国企业觅得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市场及供应链伙伴找寻潜在的“出海口”,也至为关键。特别是我国企业长期习惯于现有架构(例如美欧东盟三角关系),对于拓展新兴贸易市场的资源与信息相对不足,但在中美贸易战及科技战越演越烈,各国都担心且不愿选边的情况下,开发“美国队、欧洲队、东盟队”以外的新合作架构,其意义可能已经超越寻找新商机,甚至是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新动力所在。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及供应链架构确实造成冲击,但也凸显出后疫情时代区域整合的价值及新意义。我国在巩固落实RCEP 协定的各项条款之外,还应持续以加入CPTPP 作为努力方向,并在争取加入的过程中做出相应的改革和承诺,尽管由此带来的冲击和阵痛会存在,但正因如此才是展现我国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心,才是协助全球经济复原,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应有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