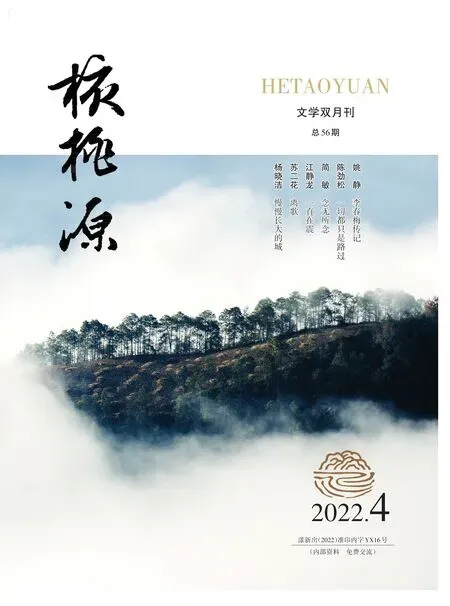一切都只是路过(组章)
陈劲松
格尔木
一切都只是路过:
流水、风,那些被大风搬动的石头,那些野花寂寞的红,还有那些被生活搬动的身影……
远处的雪山,它们的秘密正被黑色的鹰们一点点翻动。
格尔木。
我栖身的西部小城,在那个叫康泰花园的小区里,我脆薄的心事正一次次被梦境和诗歌翻动。
面前的书桌上,亿万年前的那尾红鱼仍在石头里飞翔……
格尔木:一切都只是路过。
在天峻
大雨泼下浓重的夜色,
最纯粹的宁静滴落下来……
小城伏在草原的膝下,恬美地睡去。
谁也无法叫醒一株被雨水抱紧的小草。呓语般的风走走停停,它轻手轻脚地穿过那个牧人的梦。
停电了,恍惚的烛光把小城摇成另一株雨中的小草。
隐隐传来的几声狗叫,加深了这个雨夜里俗世的苍凉。
此刻,在天峻,小城的宁静就是整个草原的宁静,而那个失眠的旅人,他的孤独就是整个草原的孤独。
如果他在薄薄的睡梦中回到了故乡,那么,他的幸福就是整个人类的幸福!
察尔汗
盐!
白色的岩流从冰冷的泥土中喷薄而出!
大地袒露内心的洁白!
忧郁的白色覆盖大地。
把火焰和光芒深藏。沉默的盐呵,你让我的文字隐忍,让我的诗歌一点点收起锋芒。
寂寞大地上盛开的花朵呀,它的芬芳深藏体内,就如夜晚的体内深藏月光。
察尔汗。
一大群白色的盐栖落,它们带着察尔汗在黑夜的梦境里起飞。
身体里布满盐的察尔汗,
你的疼痛被谁留下?
你的幸福被谁带走?
一辆辆满载着白色盐的卡车从察尔汗出发,它们正把天堂里的白,一点点送往人间。
昆仑山口
夏天突然被一片雪折断。
海拔4767米。
白色的羊群安静地从山坡上下来。
雪大起来时,它们就是大朵大朵的雪花了。
几头白色的牦牛停止走动。在雪停下来时,它们会不会和背上的雪花一起化掉?
昆仑山口,鹰是穿着黑礼服在天空踱步的绅士。
这些坚硬的石头,只有它们,永远在我的诗歌里飞翔,不会融化!
7月21日。
一场雪在海拔4767米的天空出现,我却无法把任何一朵干净的雪花,带回我低海拔的生活。
德令哈
把粗砺的风还给戈壁。
把寂静还给寂静。
把细小的涛声还给巴音河。
把一场适当的雨还给一座高原小城。
在今夜,把一首诗歌的中心位置还给十年前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
比夜色还凉,这些赤足的孩子,把高原的天空一点点踩低。
细小的风吹过,它要用多大的力气,才能帮睡梦中的小城翻个身?
车灯幽暗,有老旧的邮车安静地驶过。
恍惚中,谁恍如一位老邮差,正把自己寄往那逝去的时光……
镜像:梨花·白马
白驹过隙。
它微凉的蹄音一朵朵绽放,又旋即飘零。
淡淡的香成为那匹白马薄薄的背影。
梨花梨花,白色的蹄音如水,从四月的枝头滴落。
谁在低低地叹息:
在生命短暂的花期中,如何才能像一朵梨花那样开放?又如何才能像一朵梨花那样,守住生命最初的白?!
一匹比雪还要白的白马从四月闪过。
一场白色的花事从四月撤退。
一场白色的风暴,在时光中具有瓷器的性质。
悄然开放,悄然凋落。
梨花已从春天里抽身而退——
“流水淙淙,我已用透骨的香,把自己和流水区分开来”。
做一株麦子
做一株麦子,幸福地挺直腰身。在温和的大地上,面对冰冷风雨,面对劳作的农人,学会对谁昂首,对谁低头!
做一株麦子,站在温和的大地上,和另外的那些麦子,用绿色的叶子握手,用清香的花粉交谈。
做一株麦子,阳光中,向天空亮出自己小小的、绿色的誓言。
做一株麦子,清风为袖,露珠为眼。
做一株醒着的麦子,在冬雪下,叫醒最早的春天!
做一株扬花的麦子,在阳光中灌浆,让颂词乳汁般饱满,让麦穗般的诗歌向大地低下头颅!
做一株麦子,如果无法躲过那些偷袭的雨,也要在风中努力去挺直脊梁!
做一株麦子——
如果不能,就让我做那束闪亮的麦芒吧,用我小小的锋芒,守护着那些梦想的谷粒!
一棵树
我写到的那棵树:
它有鲜花的头饰,清风的披肩。它有露珠的项链,鸟鸣的耳环。
我写到的那棵树,它在春天跌倒。
还没来得及喊痛,它绿色的梦
便被一把斧子惊醒。
一根春天的肋骨被抽走!
(而更多春天的肋骨正被抽走)
那棵树咬紧牙关,面对着疼痛的闪电。
伤口呈现:
年轮旋转的切面,依然旋荡着绿色的风。
第一圈至第一百圈,岁月在悄然流转。
斧子落下,飞溅起时间疼痛的涛声。
那棵树烈士般在春天倒下。
它再也无法捧住一粒粒青色的鸟鸣,它再也无法像挽住一匹受惊的马匹般,挽住狂奔的风。
那棵树已经倒下。
在这个春天之外,我们应该,代替那棵树
喊出它的疼痛!
纸灰之冷
身份已然模糊:
一首诗歌的草稿?一封炽热的情书?一张充满苦味的中药方?
或是一张无辜的、洁身自爱的白纸?
灰烬的黑蝴蝶,比夜色更冷。
已慢慢变凉:无法被回放的真相,炽热的唇和玫瑰,那苦味的中药。
谁也不能从灰烬中取回:承诺、誓言,或浓或淡的墨迹,还有
那些白纸上曾经的风景。
一页纸纵身大火。
(一只投火的飞蛾!)
灰烬沉默。
而那个沉默的诗人,他只想从灰烬里取回那首诗歌中,词语的白骨!
梨子
我要叫它:兄弟。
在那根叫做乡下的枝头上,同一片冷风吹拂过我们。我感知过一滴雨水的凉,它也同样感受过。
我要叫它兄弟,它果核里藏起的那丝酸涩,也同样藏在我内心的深处。
我要叫它兄弟。
身份卑微,我们都有着黄色的皮肤。
在尘世里穿行,我们都坚持保有自己黄皮肤下
那雪白的干净的肉身。
星空的穹顶
这华美的穹顶,在穷尽想象的渺远的深处。
圣殿里洒下星辰吟诵的福音,这整齐的圣咏,让狮群般的雪山肃立。
多么静美!满布鞭痕的天空垂落下的光芒细小而又浩荡,像静静遍布大地的露珠和晨雾,像微风送来的柏叶的香气。
干净的桑烟与经幡是人间的布道者。
我承受这星空的恩泽,欣喜不已,又莫名悲伤。
荒原上空的月亮
被无边的苍茫一遍遍锻打过的银币,它的光芒被斟入十万雪山的灯盏。
草木褴褛,安于宿命。
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是打开的月光宝盒?这些银质的、冰凉的月光正从雪山的杯盏中流出。
如果没有人看到,这逝水般的月光就将白白流淌。
星辰寂寥,是疲惫的霜粒,又冰冷,又温暖。
风吹月光,是一种轻抚摸了另一种轻。
是一种苍茫抚摸了另一种苍茫。
星河低垂,荒原静默,万物颌首低眉。
天空中那枚密纹唱片,
正兀自空转……
夜行火车
当我写下:凌晨3点45分!
一列夜行的火车多像一只小小的拉链头,它飞快地把浑圆的夜色拉开,随即又拉上了。
当我写下:车窗边空虚的空酒瓶!
列车轻轻摇晃,摇着满车歪歪扭扭的远行者,摇着这睡姿各异的瓷器。
当我写下:一杯慢慢变凉的苦茶!
梦中人的舌根犹在发苦,睡着了,那梦仍泡在冰凉的苦茶里么?
这杯茶水的温度是否比窗外的夜色还要略凉一些?这满车拥挤的梦有谁的比这杯茶水的温度略高一些?!
当我写下:行李架上流浪的行李!
这些破旧的粗布被褥,在远方城市冰冷的工棚中,它将为那么多小小的梦想,铺开一个两平方米的床。
当我写下:失眠的劣质烟头!
车厢的连接处,它那么清晰地加深了一个男人的孤独与忧伤。
当我写下:座位下那个蜷缩着睡去的孩子!
当我写下:这严重超员的硬座车厢——
劣质的白酒与烟卷。发硬的面包。
蓬乱的头发,塞满泥土的指甲,崭新的布鞋。
细微的咳嗽与呓语。发酵的气息……
座位下,过道中,洗脸池上,谁能把身子与梦想一起放平?
在这个夜晚,谁能拿走火车“咔嚓咔嚓”的脚步声,然后让它怀里的人都能安然入眠。
在夜行火车上仰望星空
星群在夜空奔跑。
这群提着灯盏的孩子,他们用小小的光亮推开了一点点的夜色。
那个失眠的旅人,他用什么才能推开心里的黑?
列车行进。
这孤独的马匹,它与静默的雪山,满腹心事的湖水以及那些褴褛的草木擦肩而过。
它奔跑于荒原,也沉闷无息地奔跑于一个男人的内心。
哦,苍老的夜色里,那个在列车上仰望星空的失眠的旅人,他的孤独大于整个荒原的孤独,而小于天际那颗小如尘埃的星辰,暗蓝色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