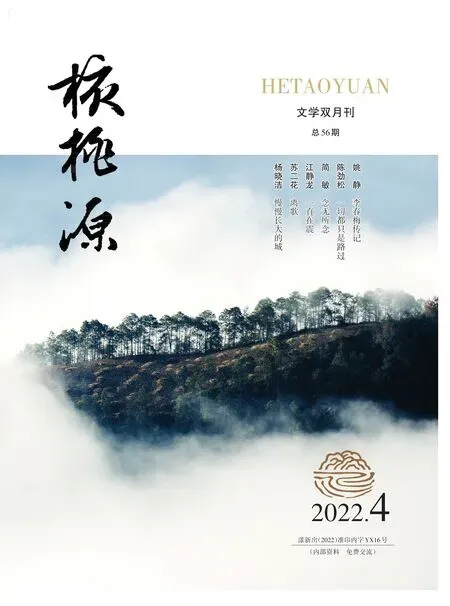母亲的长布衣
吴荣会
母亲今年八十二岁,自十八岁那年穿上那身长布衣,就再没脱下过。
旧时日月艰辛。据母亲回忆,也许是长个能吃,又缺乏肉类蛋白质,感觉从未吃过一顿饱饭,未穿过一身整齐的衣服。若做一条完整的长裤,衣袖就得省了。常常大冬天也只有单衣加身,草鞋蔽踝。而出嫁当天,母亲还是穿上了一身崭新的长布衣,虽然裤子是半旧的,鞋子也被大拇指顶破了。外婆有四个女儿,在那个凭票买粮购布的年代,外婆是如何节俭的攒下那些大块小头的布片,以凑成四套完整的长布衣。而母亲用手指宽的漂蓝布条把长衣领口、褂子领口均细致地滚上边,既美观,又牢固。
实际上,母亲那辈人择定婚姻,简单而僚草,或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或仅凭邻村旁寨有这么个人。而嫁错嫁对,都嫁了终身。无论嫁给谁,为着这个仪式,把一点点的碎布头都攒下做这身长衣。
做一身长衣需要布匹三丈多。头帕最短也得八尺,长的一丈一。一匹长布,无任何配饰,常用一般黑布做成,若用半毛布则算面料好的。自一匹新布成为头帕裹在头上,不断地出现好多褶子,这些褶子随着每天晚上摘下头帕,每天早起再缠上,不断地变换位置,变换形状。久之,随着布匹的软化,又渐渐形成固定的位置,固定的褶子。头帕将旧未旧时,褶子竟那么整齐划一,整条头帕像是折叠整齐的折扇,皱处稍有损迹。而整条头帕不再是发亮的黑色,微微泛黄。就像是母亲嫁来新组建的家庭,每个拧巴的日子,母亲都用她愚善的性情、温良的耐性慢慢捋顺,渐渐也平凡如一,平静如水。而青丝在千百道褶皱间呢喃絮语,也逐渐念叨成白发。母亲常把一根针别在头帕上,做活被刺扎时,取下挑刺,若是衣物破损,可简单缝补。
作为主体的长衣多用涤卡布做成,面料触肤感觉板结冰凉,但这种布结实牢固。母亲自己剪裁、缝制。衣裳整体呈前襟短、后襟长,后襟长至膝弯处,前襟的短板由围裙补齐,与衣裳呈一整体。衣袖与衣身为连体剪裁,腋处剪刀稍稍圆个弯,穿着舒服且不易在劳作抬手或穿脱时炸线。整件衣服的接口在脊背正中,若有零碎布片拼接,母亲总把接口安排在最恰当的位置。衣上共有四组纽扣,领口搭接处一组,稍向下横过半拃处一组,向下倾斜呈一个小弯大概至腋下一组,再往下一组。纽子与纽绊都用小布条纽成,一根小布条中间部分作纽子和纽绊,两边并拢寸许,而后分开盘成花样,小巧精致,美观且牢固。这几组纽扣是这件素净长衣唯一一个点饰。记得母亲还挂着一件配饰,就挂在纽扣上方肩下位置,一个精致的黑底漆花针筒。是奶奶生前许下传给母亲的。奶奶亡于远方,时隔三年之久,父亲凭着此漆花针筒为证,才捡其尸骨回家安葬,此后,总耿耿猜想奶奶近死前两年的经历,长嗟短叹。无论奶奶那个年代还是母亲那个年代,生活就如那一块块珍贵的布匹,尽管她们小心翼翼守护,还是支离,还是破碎。然而,她们仍用一根尖针、一股细线,一再用心缝补起生活。
围裙是整套长衣素服的门面。一块黑布剪裁成半围A字裙的模样,下围稍摆。两角的两个三角形部分及整个下围用白线匝上细密的花瓣图案,看上去竟有了繁花似锦的感觉。乡间有一句俗语“我给你系把围裙”,是用来戏谑说话不算数的男人。而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甩开手脚像男人那样干活,薅玉米、砍柴、挑水、拉磨……长长的围裙成为她劳作时的束缚,于是母亲围裙的一角总往上别进裙带里,几乎从不见解下。
系腰则仅是一匹漂蓝布,在整套衣服中好像也没太多实用意义,反而把纤腰裹得粗壮。然而自结婚当天穿上这一整套服饰,好像就混淆了年龄阶段,老孺少妇皆成为矮粗实壮的模样。这身长服的“兜”特别多,长衣短襟塞在围裙带中,里面可放东西。系腰布里可放钱、物,天冷时还可把双手捂进其中。围裙则是更大的“兜”,可放一捧瓜豆、一把野菜,连接生时,都把婴孩裹进围裙,贴近心尖。自穿上这套长衣,就成为一个家的顶梁柱,一兜一围皆揣满生活。
与其说不经选择的婚姻,一套特定的长服是母亲的桎梏,倒不如说生活的艰辛与母性的纯良才是拴住母亲的枷锁。母亲生育了九个儿女,年过半百还在哺育雏幼。
作为母亲最小的孩子,等我记事时,母亲已是花甲之年。那时,母亲开始拥有一两件她自己喜欢的衣服,一件金绒布褂子和一条漂亮的围裙。那条围裙的两角,母亲用白牙布镶起,里边用漂蓝布条叠成乘法口诀表状,先用手缝订其形状,再拿缝纫机匝牢。双层布围裙带的尾端,母亲把它留做三角形状,内里衬了两片三指大小的花布,像是草棵间冒着一朵小小的月见草花儿,别致极了。母亲还自己做了一对甩须。两条掌宽白布做底子,上面用辫线隔开成三段,上、下两段饰以纽成叉状的黑布条,中间一段饰以方形绣片,底上钉上母亲手制的极其别致的须子。那对绣了花的甩须啊,搭配在母亲素净的长衣上,拴在母亲左腰后,随着人群中母亲的彝族打歌步伐,艳丽飘摇,仿佛母亲竟在尘埃间盛开出花来。
时光流去,九个儿女都先后成了家。儿女们给母亲买各式各样的衣服。母亲也开始穿短衣、皮鞋。长衣多半折叠整齐放在柜子里。直到近些年,随着民族文化渐渐复苏,乡间又流行起了长衣装扮。母亲自然是喜欢长衣的,于是又做了一套。姨妈会剪花样,三姐绣花手法好,给母亲做的花样是“凤啄牡丹”。
这种改良过的彝族长衫可谓浓墨重彩,彝族姑娘穿上这套服饰真真是一朵盛放的玫瑰。母亲的长服帽子和围裙花样大致是两只凤凰啄一朵牡丹,花样圆润别致。三姐更是用心刺绣,把四只凤凰绣活,两朵牡丹绣得水灵。帽子花边和围裙边沿同样都用串芝领,一枝到头,没有哪一针针法稀了致使断枝,母亲甚是喜欢。除花样绣得艳丽外,配饰亦艳丽张扬。漂蓝布系腰也改成一条三指宽的腰带,同样绣着花,串着小珠小铃。长衣倒是一袭纯白,为搭配艳丽的围裙、帽子、腰带、甩须,三姐给绣了一小条指宽的衣领,几朵素净的蓝色小梅花。母亲自己给衣袖处、领口下围用蓝布条做了几道纹饰。整套衣服色彩、声响(围裙下摆、腰带都串着细小铃铛)都奢华极了。母亲虽然已躬了腰、驼了背,可母亲个子高,穿上这套长衣,还显出纤腰了呢。缝好试衣服时,母亲松垂的上眼皮更睁不利索,艳丽的色彩晃花了眼睛,但母亲很高兴,揉一揉努力睁开。
母亲还亲自剪裁缝制了几件长衣,一件白色、一件藏蓝、两件铜钱花绸一黑一蓝。那是母亲的老装,每次弄之前,母亲都先洗净双手,一剪一针,弄得极其细致。母亲还是选用的蓝系腰、黑头帕,黑底白线的围裙。母亲心底深处,还是认同最初那套素净的长衣。母亲还用着漆花针筒,头帕上却不再插着针,母亲人老眼花了,现在用的是大针,插在头帕上危险。如今流行的民族服饰那么精致,鞋子肯定也得讲究。三姐花绣得好,绣好鞋帮,母亲便给她做鞋底。母亲做的鞋底三层或四层,一层包一次边,一层比一层稍稍缩进。折一个个瓜子壳大的白布牙子,密密镶嵌进底层与二层之间。牙尖边缘切齐底层,望之美观,触之整齐。
而今母亲八十二岁,有阳光照的地方,母亲才看得见做针线活。坐在独凳上,母亲抱着鞋底插针、抽线,样子温暖、恬静而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