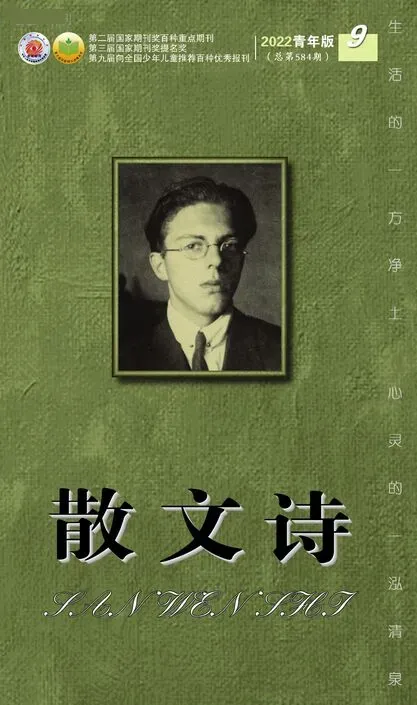创作手记:春天的野人
2022-11-11 02:46傅苏
散文诗 2022年18期
最早,我有两本日记,起笔于学生时代的初二,大概快毕业的时候,我把它们烧成了灰烬。
一页页撕下,点燃一根火柴,经过记忆的通道,减去一笔一划的文字所承载的一段少年心事的重量,带它们飞向虚空。
这个过程里,我望着那些热烈腾起而又渐渐喑哑的火苗只留下残存的碎片,再被风吹跑到远处,翻越院墙,飞过树梢,最后消失。我站在一只熏黑的火盆边,愣愣地呆了许久。
关于烧掉的两本日记,会是每个人都曾拥有过的梦境,或者现实,用文字的方式挽留自己,再以另一种方式道别。
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留下任何一本完整的日记,任何连贯的人物、时间、地点、故事和情节。伴随那些飞散的文字,记忆也溃败成性,许多生命日常的细节也都消逝得了无影踪。
只有吝啬的人才会把一生都打扮得像个储物罐,把时间的毛发梳理得贼光油亮,分毫毕现。只有滑稽的人才念念不忘荣耀,时刻去照照小镜子,希望把美好永铸成记忆的铜鉴。
我也有吝啬的时刻和滑稽的样子,但还来不及关照那枚尊贵的铜镜,人生已过数十载。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一面普通的镜子,名曰“匆匆”。
当时间被人们读成水滴的声音,秒针的火柴还在永无止境地奔跑和摩擦。
我忽然回想起那座北方小城以及她的春天,欲再返回,做一个放火的野人。
猜你喜欢
家教世界·创新阅读(2016年12期)2017-01-09
家教世界·创新阅读(2016年10期)2016-11-29
小学生作文(低年级适用)(2016年6期)2016-11-11
红蜻蜓·低年级(2014年3期)2014-07-09
小朋友·快乐手工(2014年2期)2014-02-25
小朋友·快乐手工(2014年1期)2014-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