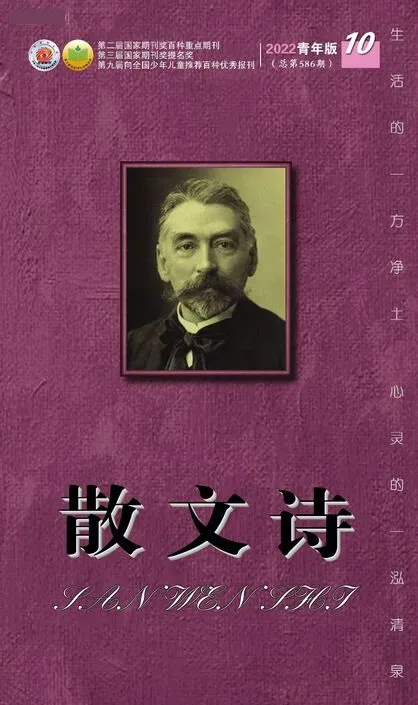致L(节选)
◎苏建平
辅音
我把你简约成一个辅音:L。你走过来,L便自动存在了。这辅音,它仍是装饰性的,一如你的脸粉、眉彩、唇膏。装饰之物还有:衫与裙,长袖与无袖,眼镜与耳环,手镯与项链。这如此繁盛的点缀和搭配。但我仍把它称作单个的你:L。你走过来,在词语中向我走过来,一如我借助词语走向你。我们用词语交谈,但我们却用辅音相称呼。你看,一个辅音,在它必然存在的时候,在舌尖某一个时刻脱口而出的时候,借助无形的身躯,是可以变得多么的私密。私密而唯一。
事件:夜行
你在哪里,L?我们去往乡村。傍晚,雨刮器不停地抹去挡风玻璃上的雨水。那熟悉的路,那陌生的路。它们交替出现,相互交织。天气好,或有夏天的蝴蝶缭绕着飞。现在,这不存在的蝴蝶成为一个想象和修辞。雨代替我们说话。有时候,雨水从车窗飘进嘴里。归程漫漫。雨水洗着车子,轮子在乡间小路沾上泥。像一个夜行的人。归程啊,L,你把着方向盘,错过了一个个转弯的十字路口,将终点一次次往后推。这更加漫漫的归程啊,在雨雾中变得越来越L。在越来越L的路途中,我抵达你,L。
此刻
我愿意你在另一个我不知晓的地方。你无所事事,靠在一棵南方的樟树上,摘叶,凝望?你走在去向你暂时寄身之处的路上,路过的人脸如落叶?你走进了某一个站台?你在一节车厢中,从玻璃上获得了对自己的短暂一瞥?你在车外事物的加速奔驰中,感觉到自己同时既奔跑又静止?你打开车窗为自己输入了一些暗香和浮动?你闭着眼或睁着眼?这一刻你最先忘记的是谁?一路上你说过几句话?你曾想说几句话?下车时,站口乘客的身影叠在地面上,你如何去踩这些影子?
类似于抒情
我往澄澈里想象你:透过窗外一路拔高的栎树和香樟树。经过春天,这亚热带植物体内引信启动,才是初夏,便亭亭如盖,仿佛一夜形成。它们的叶子,无所顾忌地张扬着自己的绿色。这些不可阻挡的个人主义者!它们绿,一路绿,往深里绿,疯狂地绿,透支来世地绿,仿佛只绿一次那样地绿。看到它们,我想起你。看到它们塞满空间的绿,我想起你骨骼般的影子和果肉般的身体。你白天和黑夜均一样地收缩自己、放开自己,遵循着你自己的节律:一块石头与一条河流,时时刻刻相互转化着。
感叹词
L,你这辅音,感叹词终于让你走进了元音的世界。你这反义词词典!啊,那不一定是抒情。哦,那不一定是惊讶。呃,那不一定是矜持。嗯,那不一定是同意。但感叹词环绕着你,像无边之物从有限的视界里长了出来:那是多么稀有的无中生有。亲爱的L,请高亢,请喟叹,请抒情,但其实你生活在叙事无边的生活里。叙事,一江春水向东流,会遇到上下错落、假意真情的石头。L,请相信,这正是元音与辅音相叠加的时刻。L,请你走过来,你所看到的一切狭窄和路途不平,全是它早于你的存在。它所说的一句话是:人生丰盛。但你却说:呔!
刺猬之歌一
我们相互监督着:保持那仅有的一根刺。我们的肉身多么容易屈服于这些物事:一碟好菜,一杯酒。它们仍然每时每刻都会来。不拒绝,我们在它们之中。拒绝,我们仍无法突围。但要知道,这仍是好东西,仿若山野间无处不在的落叶。你呀,L,如果这些围绕我们,反而是一种幸运。事实上,真正围绕着我们的东西是:上班要打的卡号,中午食堂吃饭刷的饭卡,一纸会议通知,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涌到嘴边又退回去的一句话。亲爱的L,我们需要重新学习生物学,那不仅仅是中学生考试的试卷,最重要但又唯一需要的是:我们命名着自己的自身一生的命题,却需要自己一生去回答。就像蛇咬蛇。就像土盖土。
一天的行踪
早晨,我们告别。你的车轮载着你驶在你的路上。这迷宫般的城市。你被堵在某一段路上等红灯跳跃。然后,经过房地产商楼盘售楼部,银行,大酒店,肯德基,网游吧。你继续被堵在另一段路上等红灯跳跃。然后,百货商场,菜市场,早餐店,银行,24小时夜店。你继续被堵。在车阵之中。奔驰,大众,奥迪,帕萨特,别克,本田。一条红底白字的大幅标语一晃而过。小街上,衣冠楚楚的人和蓬头垢面的人同时走来。你停在某处。上午。午餐。下午。电话和电话。L,那时你是不叫L的L。万花筒向你旋转过来。你只有将自己从万花筒中旋转出来,跃入夜晚,你才重新回到L。
有约
最亲爱的L,大风大雨刚歇。书房里纸片乱飞,灰尘吹出了房间,而雨趁势侵入到室内。这内外交织的风雨世界,它在阻隔我们,或在象征我们。它就这样横在我们的路上。我继续走向你。一个时刻可以放大成一个世界,但如果一个世界简约成某一个时刻,就会显得更美。然而,对美的定义,其实来自于我们自身:我定义你,以及你定义我。这简朴的公式,几乎像斐波那契数列:一种前后相续的加法,才产生了妙不可言的未来。在无穷无尽的序列中,你像一颗种子,将自己再生幻化成独一无二的果实。那是多么令人向往!为此,我祈祷着,只是为了成为这一颗果实。由你形成。
刺猬之歌二
我们相互离散着。我亲爱的L,我们携带着各自的刺,为了随时可以刺痛自己。在古老的灰尘中,我们练习刺自己,痛一点,深一点,用力一点,无情一点。这无望的课程,事实上,它仅仅是:一根刺晚于长出盔甲,一种爱晚于对它的否定。而我不能接受的是,走过如此长路,我走向你,却刚好走向反面。这是多么诡异的训练:我们满身带刺,并且获得对刺最感性的认识,但我们却全都走向一条分辨不清东西南北的道路上!即便如此,亲爱的L,也唯有你来,不断地来,一直来,就是来,走来,到来,来到我身边,同时,我来到你身边,我们方可贴近,用刺说话。
电子时代
最亲爱的L,当我如此称呼你,在电子时代几乎是一个老派的行为。何为?为何?哲学的发问和解释在电子圆周轨道上迷失了方向。L,电子一颗颗地在我们体内,那刚好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理由:必有规律,未必规章。所以,我盲目地沿着城市大街寻找你不可捉摸的频率。你深居在时间的暗处,在某一条道路的拐弯又纵深之处,我看不见你却看到你圆周的轨迹。无尽之路在无尽延展:你每天离开自己又回到自己,一如我回到自己却又离开自己;当我离开自己的时候,我却回到了你的身边。但更大的可能是:其实,我们在奇异的圆周运动中,刚好完成了一次轨迹的交叉,交叉并且融合,融合并且遗忘。
在一条河流上漂流
当我打开《霍乱时期的爱情》,我不得不遇到这样两个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费尔明娜·达萨。两个普通的小镇居民,仅仅在最年轻的时候秘密地交叉了一下。历经青春的无尽梦想和无尽动荡,他们终于来到了老年的河流上,并把自己所剩无几的老年放逐在一条河流上漂流。他们竖起了一面霍乱时期才挂起的黄色旗子。这让他们最后的旅程变成了一条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道路:永远在一条大河上来回航行,永远不在大河两端的港口靠岸。这航行中的两个老年人,其固执的脾气与青春期的冲动完全等同:拒绝解释,也拒绝复制。当马贡多一般的小镇毁灭又重生时,最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凭借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和所度过的独一无二的人生,依然在时间中来回航行。他们构成了破解人生秘密的钥匙:爱于此处,当是所有地方;爱于此时,必是所有时代。最亲爱的L,此刻我念着你,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念想:我要把他们同样称作L·萨和L·萨,因为,他们本质上其实是同一个人。
脸谱
神的脸谱:那是一种密码:用于内在的信念。人的脸谱:那是伪造的密码:用于存活于世间。有时候,我对“脸谱”一词存疑,一如对“密码”一词。我如此痴迷于有生命力的事物。于是,我说,树的脸谱:干与枝的目录学谱系,以及树叶的空间点染法,构成了我们每天存在的图象。但有时,我说,虽然千变万化,云的脸谱,变化仍然不够多。在不确定的意义上,地面上的一个人在一天里的变化,超过经过他头顶的某一朵云。但如此之多的星系和星辰,将一切变化幻化成无法理解的超级复数。亲爱的L,我们正处在某一种变化之中,但我们穷尽一生都无法找到这变化本身。复数固然美丽,但是,这如此繁复的宇宙,不管有多少脸谱,L,我只愿给你一种:花的脸谱。
一朵花
从无可穷尽的花的脸谱中,我仅仅只献给你一朵花,L。我甚至都不能叫出它的具体名字。此世间,花无数,但未有哪一朵花刚好在我想念你的时刻来到世上。它们的到来总是神秘莫测。但它到来时,我们如此不可控制地深陷于物质生活中,我们根本来不及腾空自己,也来不及更新自己。你看:我呼唤你,等于呼唤世界,而事实上,世界正好在否定我们。我们同时、彼此、反复、绝对、没有回头路地走上了曲折的路。从无可穷尽的花的脸谱中,我仅仅只献给你一朵花,L。我甚至都不能叫出它的具体名字。此世间,花无数,但未有哪一朵花刚好在我想念你的时刻来到世上。它们的到来总是神秘莫测。由此,我欣喜地将它称为无名之花。我不需要它有什么形状,也不需要它有什么颜色,我仅仅需要它是一种奇异的花。当它成花,你便在了。
大约的事物
从小区出发,我们每天走上不一样的路。这直线的城市道路,或南北,或东西。然而,我们都在东西南北中拐进了有一个奇异斜角的地方:大楼,小座,那是刚好等待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融进彼处与此处,一如我们互称为此与彼。但谁是彼处?谁是此处?这卡座上的时光虽然由同一座时钟在走,我们却走向了一个必然相互秘存的分叉的人生:每个人都营造出一个小宇宙。多么好啊!亲爱的L,这奇异的安排,事实上,正好是在先教会我们彼此遗忘的课程,然后,才赋予我们彼此记忆的一刻。在孤独无以排解的时刻,遗忘才给了我们的记忆一把真正的钥匙:莫失,莫忘。
0们和1们
从日常生活中走出来,我最亲爱的L,我们一起走向某种象征。抒情令人厌倦。于是开始播放《OK Computer》(你好,电脑),来自于伟大的摇滚乐团Radiohead(电台司令),遥远又神秘的电台司令。但他们仿佛就在我们身边。他们歌唱0,他们也歌唱1。他们同时歌唱0和1。这意味着,他们在歌唱我们。现在,在歌声中,我攻击你,用1攻击0。但这似乎是一个错觉,你是如此强大,你以一个0,反过来攻击1,并且消化如树、如柱、如雾的1。亲爱的L,我们在二进制的神秘演算中,同时获得了死与生,或生与死。但在最高意义上,我们正好超越某种奇怪的演算,仅仅任凭自身,彼此交融和演化。那正是人间任何一棵树生长的轨迹。它在长,而又不知在长。它是如此的饱满。
你和我
亲爱的L,我最爱的L。你长在了人间,一如一棵植物在这空间里寄存。然而,我们一起厌倦了这调子。我们拒绝抒情。我们站在物的立场。我们像树与树一样相互交缠碰撞。有时候,我们是两块石头。如果有空气,可以裹住我们。你将自己的美,种在虚空里。刚好我知道虚空这个词。那并不构成我们交叉的路径。如果有路径,那是我们厌倦自身的时刻,但同时,我们却又沿着自身走向不可复制的时间。亲爱的L,你如瀑布一样直流而下,充满能量,你走过了人间的沙漠。在这么偶然的时刻,你竟获得自己的名字,并且我赞诵你的名字。我赞诵你,等于在一路上,光赞诵光,树赞诵树,水滴赞诵水滴,沙子赞诵沙子,路赞诵路,梦赞诵梦。而一切最简约的表达是:你赞诵你。
刺猬之歌三
我怀念你的刺。亲爱的L,你如此尖锐的刺,恰从你的柔中长出。你刚好在这个充满了欲望的空间。你刚好在此地,不带任何目的地自我存在。那正好构成我怀念你的理由。现在,我唯一怀念的是:你一身毛茸茸的刺,野性生长,无所顾忌,不可解释,却又不看自己,自由自在,无限动人。亲爱的L,此世界,彼世界,如此繁复,你的世界却是简单美好,一根刺,自世界。我们满身无数的刺仅仅是一个字:刺。如此,我们才可凭一种简约获得一个世界。那正是我们书写刺的诗篇的理由。
就是你
我最后要说的话,亲爱的L,就是你。一生做的菜只有两个,只叫你和我。一生两次欢宴,只有你和我。一起被时间遗忘的人,肯定是我和你。但是,我最亲爱的L,你是多么不可思议:那么多肉竟长成了你,那么多奇思异想环绕着你,那么多时光经过你才成为时光,那么多梦被你记起又说起,那么多路你用自己的脚一步步走过,那么多树叶在你经过时落下又长出,那么多星星你数过后忘掉却又重新想起,那么多谈话有时变石头有时变棉花,那么多欲望落空又重新贮满,那么多的这人间的鸟和兽,那么多的与鸟兽的合唱,那么多次的我们走进鸟兽之中。最亲爱的L,你的肉身短暂,在宇宙中,在,又如不在,如此,我才能在不在中寻找必在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