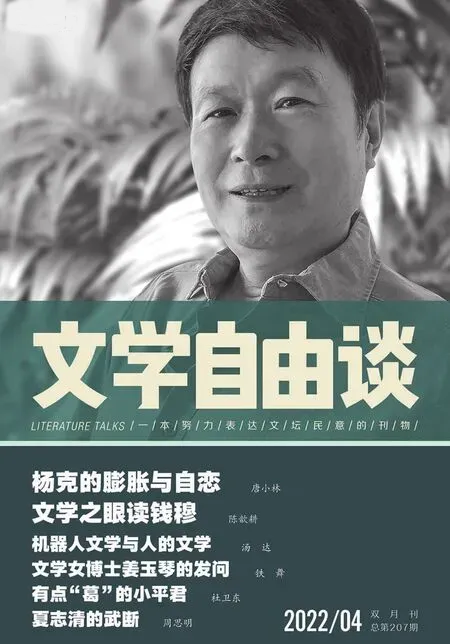文人年谱编修的三种疏误
□刘 阳
已不知几回,每逢新生导学场合,我推荐给学子们的第一种入门读物,总是文人学者的年谱。因为这等于起先就拿金针度人,趁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满怀理想朝气时,树起高大上旌旗,引导其少走弯路。我自己就是这么摸索过来的。记得昔年读《夏承焘年谱》,不但领略了一代词宗既博且专、又不立崖岸的治学心路,而且从年谱中不少有意思的细节,比如徐朔方、吴战垒等晚一辈杰出学者劝夏公“专力为学,勿写小文章”、“作提高科研,勿分心于普及工作”中,蓦然有所悟,慢慢开始明白了“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的道理,从此提醒自己小心别掉进“多歧亡羊”的窠臼。这种经验想必很多读书人也都有过。
当然,以上感受的前提,是须面对一部除了基本史实不出错,还能做到不留白、不简化和不滞闷的年谱。这做起来非一日之寒,可遇不可求。《夏承焘年谱》之所以一上手便让人不忍释卷,毕竟是由于有先生数十年寸累铢积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为底本依据,整理铺排成年谱,相对容易措手。饶是如此,倚重现成的文献,不意味着毕其功于一役。近读到雪克《湖山感旧录》,当中以亲历者身份栩栩载录夏翁未入儒林传之逸事,举凡“撰作这类普及性读物的事,心叔(任铭善)先生并不认同,数次进言劝止,云从(蒋礼鸿)先生也不以为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夏公自有主张,以普及词学为己任,一直不为所动”云云,便又开我眼。在看到了谱主的鲜活反应之余,也悟到年谱永远有可补的材料遗珍,不能不九蒸九酿,火候越久才越上佳。果真要臻于不简化、不滞闷之境,难矣哉。
但不简化和不滞闷,都立足于作为前提的一个“有”字,取决于放长线钓大鱼的时间或者说机遇,花功夫深耕细作,总能一遍遍完善。它们是年谱成败的充分条件。比起充分条件来,不留白则是必要条件。假如做年谱避难就易,遇到某些年份时忽略不计一溜而过,骎骎然以“无”出之,则难免失之于粗疏。同样是评上面的书,卢敦基《雪克老师侧记》记有次询问《辞源》如何,师答:“《辞源》嘛,我懂的它都有;我不懂的,它都没有。”——我每每感到遗憾的,是目下行世的文人年谱,懂得这个类似于注书的道理者似乎不多。表现为,在读者能推知究竟、可凭一己之力寻检到相关脉络、也不乏文献支撑处洋洋洒洒极尽铺陈,而对历来难注、缺注而读者迫切盼注处,乃至被公认为悬念与难点的空白地带,却概付阙如。这恐怕多多少少是此类年谱行而难远之故?
归结起来有三点:应叙之处从众回避而留白;所叙尚需明显补充而简化;叙中本可穿插细节而滞闷。促使我油然产生这些想法的,是年来又读到的一种渴慕已极的文人——恰好是夏翁传人——年谱:《吴熊和学术年谱》。对于吴先生,虽曾有幸就学于他多年设帐的学府,却生也晚而未有亲炙之机,只能仰之弥高。焚香沐手急急拜读之下,便感到了上述三种疏误。
先谈回避应注之处而造成的留白问题。吴先生身为“30后”文人,在三四十岁时遭逢各种运动,固然属于时代风会,然而若仅满足于将《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所载的活动反过来载入吴氏年谱,却在许多年份下以“在杭州大学任教”七个字笼统打发,是否便解决了问题?余期期以为不够。深入的勾稽表明,这时的谱主不辍读写,并没有闲散,否则又如何解释他“文革”甫一结束便蓄势冲顶,很快享誉于学林?像下面这些故实,我觉得因而就不该被跳过:
(1)从《杭州日报》1957年4月26日三版钩沉出吴先生弱冠诗作《迎》:“仁爱胸怀百战身,和平勋业创基人。……今朝试上湖船看,西子新妆百态生。”不仅应补入年谱,而且让人看到了年未及而立的精神状态以及早期诗艺。
(2)周育德《戏外寻梦》载,“1957年冬天,中共中央发出了知识分子劳动化,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动员。这是‘反右派’以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大措施。各个大学里都有下放农村劳动的指标,由校而落实到系,动员教职员报名。徐朔方先生和吕漠野、蒋风、吴熊和、蔡义江等先生都报了名,而且都得到批准,成了第一批下放的劳动者。留校的先生作诗送行,下放的先生也作诗唱和,搞得有声有色。”并附吴先生诗作,可谓洋溢现场感的珍贵史料,应径录而未著录,或也可补入1958年纪事。
(3)陆昭徽、陆昭怀合著的《书如其人:回忆父亲陆维钊》,和白砥编的《陆维钊文献集》,都指出1959年陆先生“与邵海清、吴熊和、平慧善合编教材《晚清诗文专题纲要》,供中文系进修生使用”。这又是条堪称珍贵的翔实材料,提供了任青年助教时编撰教材的情况。年谱若不载,知情恐难再。
(4)方厚枢《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详细介绍了1962年吴先生与夏翁合著(实以吴为主执笔)的《读词常识》作为“知识丛书”之一种,如何受中华书局约请而出版的背景情况,作为稀缺史料,当在年谱1962年部分作必要的补充交代。
(5)徐元《味耕园诗话·诗文集续》叙及1963—1964年间吴先生曾参加浙江古籍出版社策划、供知识青年自学参考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讲”(共五册)的编写工作,本已写好编好,却因《关于当前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骤至而不得不终止。立此存照,慨乎一代国运民瘼。
(6)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初版“后记”说,“一九七四年杭州大学中文系编了一本《〈红楼梦〉研究问题资料续编》,……当时中国古代文学教研组吴熊和、陆坚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这项工作。”以旁证形式坐实了“文革”期间谱主的重要行迹,拈出后有益于展示谱主学养的构成。
(7)1999年出版的《吴熊和词学论集》,“后记”称“然明刻陈子龙、李雯、宋微舆三人合集《幽兰草》,于国内各大图书馆访求殆遍,皆无藏本,意谓不复尚存于天壤间。不久前几经辗转,从沪上一位前辈藏书家处得到原刻本的复印本,不禁惊喜不已”。此处提及的“沪上一位前辈藏书家”,疑为词学大纛施蛰存先生。黄裳《忆施蛰存》有“记得有清初刻《幽兰草》,康熙刻《罗裙草》,都是精本。第二天跑去看时,三书已为蛰存买去,懊悔无已”的叙描。云间词派的重要文献《幽兰草》如何历艰辛而访得,是颇不妨从细部上详考一番的。
仅据上面七例可以看出,它们中有本证,更多则来自鲜活的旁证,汇聚在一起后,首度勾勒出了谱主前四十余年人生中的不少事况。运用这样的方法,当还可陆续复原出一幕幕更丰沛的历史场景,而避免取材过于单一而造成的年谱叙述上的逼仄。似这般努力填空,才能从各个角度满足读者之所需。
再谈所注尚需补充而造成的简化问题。人们希望看到的文人年谱,究竟是微言大义还是收罗详细?答案总该是后者。信息量越准确详尽,越会有意想不到的参考价值,保不准会在研究者习焉不察之处,提供火花和帮助。事实上,一位学人的著(特别是佚文)、编、译、序跋和访谈、学术与社会活动、成就反响、教书育人乃至生平轶闻,都应为编者悉心采择,左抽右取,一一安置于恰切的人生部位。以此来观照,眼前这部年谱能提供何种经验教训呢?
不得不说有遗珠之憾。这又包括著述叙录之全璧、参编成果之搜讨、零散文字之打捞、治学影响之述评、学术活动之检阅和培桃栽李之剪影等不一而足。
(1)对于吴先生丰入吝出的著述情况的叙录,存在着缺口。比如1977—1982年陆续发表于《语文战线》上的《杜甫的〈石壕吏〉》《韩愈七古三首》《杜牧为什么写〈阿房宫赋〉》《豪放派和婉约派的来由》《〈菩萨蛮〉、〈水调歌头〉等词调的调名有什么意义》《〈永遇乐〉的“否”字》这六篇早期论文,便都被漏了。至于1986年为《人民政协报》所撰《悼念夏承焘老师》,作为不可或缺的集外文,补入可窥吴承夏学的具体轨迹。而收入2003年《文史新澜》中的《〈石湖词〉编年》,不见于公开梓行的著作而弥足珍贵。像这些,便都属于有价值的补笔。
(2)参编文字亦复不少,若有心将分散八方的它们串联成珍珠船,自可发挥余热。如1989年担任副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辞典》中,那特色鲜明的“集评”,实出吴先生倡议。证据是《杭州日报》1988年6月6日第四版《既博且精 深中肯綮》报道的吴氏原话:“还有一个特色是集评,搜集前人有关评论,分条列在鉴赏文字之后。……搜辑这部分资料需要化费大量精力,要有多年积累才能汇辑成编。但这也是读者和研究者久所企盼的。”言者无心而听者应有意,这足以启示后学在编篡看似通俗的鉴赏辞典时,如何匠心独运而使之生命长青。
(3)还有大量散布于各出版物的鉴赏文字,它们能为今天的读者提供门径指示。如为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和《宋词鉴赏辞典》,精心执笔赵鼎、刘克庄等词人词作,又在《唐宋元小令鉴赏辞典》中对刘禹锡的《潇湘神》、在《元曲鉴赏辞典》中就朱庭玉的《行香子》《天净沙》等的一一指授,使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词学专家对曲学的同样熟稔,而深深服膺其“要打通视野,才能取其一点”的治学咳唾。余如1984年为《大学语文选讲》赏解《明妃曲》,以及为《电大教学》缕述《〈诗经〉与音乐》《李煜词的抒情特色》《关于初唐诗与初唐四杰》、1993年为《毛泽东诗词画意》评析《贺新郎·读史》、1999年为《吴文英词欣赏》导读《莺啼序》等,珠玑遍地,例不胜举而指不胜屈,皆之前闻所未闻,而复失收于年谱。还要提及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推出的一套六册《高中古代诗文助读》。那绝非一般教辅读物,以学术的高质量广受青睐。吴先生是其中多种的署名作者,不但不应漏略,录之于年谱,正可让今人瞧瞧一流教辅书该是何等风貌。
或曰:做年谱得拿谱主已系统行世的成果为依据。这不能说完全没道理。只是著作也好,论文集也罢,都是学者带上了价值评判色彩的、去取之后的产物,年谱则应如实交代事实,以全面还原著述为本色,不宜轻言“有选择”,尝鼎一脔反倒不好看了。在大数据技术深入人心的当今,要求年谱编者尽可能竭泽而渔,乃至不放过一副出自谱主之手的挽联(如傅杰《前辈写真》记吴先生1989年挽郭在贻教授联:“母老家贫子幼,空有才名惊耆宿;雨冷灯昏梦断,又为斯民哭健儿。”吴敢《吴溪流泽长》记吴先生2005年挽吴战垒先生联:“百身莫赎,天其丧予!八表同昏,吾将与谁?”),看起来就不是过分的期待。
(4)有关治学影响的述评,也需辟出空间来详加观照,因为这具有学术史定位的深远意义。其中既需要充分体现1990年入载张高宽等主编的《宋词大辞典》这样的肯定,以及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对吴氏领衔的杭州词学群体成就的大篇幅论述,还有《宋代文学研究年鉴》等大量评价,包括在《浙江通志》和《浙江年鉴》中也能找到的相关评议。也应适当容纳进一步的申论或商榷意见,如黄世中《中国古典诗词:考证与解读》嘉许吴先生有关《钗头凤》非陆游、唐琬本事的著名考证之余,也追问“如果沈园题壁不是《钗头风》词,那么陈鹄关于唐琬和词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又当属什么词牌呢”,不失时机地一并附入,让文人年谱产生“学记”的索引和参考价值,有什么不好?
(5)至于对学术、社会活动与育人情况关注的不够,也留下填充空间。譬如1990年3月主讲海峡两岸苏杭诗词研修会,授“唐宋杭州的城市与诗人”课等等不烦枚举。这方面的情况,总以做到齐全为宜。特别是1991年以来,吴先生应邀以主要专家身份开展“唐诗之路”论证,着古代文学地理学之先鞭,在年谱中着墨欠丰。又《杭州日报》1982年2月25日第三版《青年女工汪维尔考上研究生》说,“她还到杭州大学中文系向吴熊和副教授求教。吴老师开始对这个姑娘攻读古典文学有否前途持怀疑态度。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吴老师发现在小汪身上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深深感动,从而悉心辅导。”这样有教无类的育人事迹,踏破铁鞋难觅,岂有闲置之理?
最后谈叙中匮缺细节穿插而造成的滞闷问题。缝合以上缺憾之余,如何让谱主血肉丰满?尤其是对吴先生这样精气内敛、自觉远离媒体采访等浮世喧嚣的纯粹文人,更需要留心辑录。我的经验和建议是,用繁而密的注释形式,充分调动谱主各种生活细节,包括富于灵气的、事件化的例外状态,来支持正文中的事项排列,恍似交响乐中主音和复调相得益彰,又仿佛编年体与纪传体互补。可别小看一条生活化材料在年谱中的作用。比如胡可先访谈《甘愿坐冷板凳的人》记吴先生尊尊教诲:“搞学术研究,文献功底及考据都极为重要,但往往识见难高。一定要以考据为基础上升到理论研究,必须要有异端思想和独立精神。决不许随便滥发文章。”张仲谋《忏悔与自赎:贰臣人格》的“后记”,以吴先生1997年一次谈话点睛:“现在有些年轻人,一天到晚忙着写书,却没有时间看书,那怎么行。”寥寥数语而一针见血,足可为后学诫。由于是在注释中处理这类内容,尽可放开手脚,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随物赋形而一任大珠小珠落玉盘。
聊举一隅以三反:
(1)不乏能于小细节中看出大境界的珍闻。《浙江日报》1988年3月22日第四版配照片刊发何燕芬的特写《学无涯,思亦无涯》,当入年谱而未入。其中的重要材料,如引吴先生语“写文章是件苦差事,我这辈子还没与人板过一次面孔,却也老是高兴不起来”,以及“他说:‘晚上是必看电视的。这几天在播放的《假若明天来临》等电视剧,我看不错。呶,基本上就是根据这书改编的。’他拿起桌上放着的已阅了一半的谢尔顿著的《有朝一日》。又讲到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的两个译本,还有《文汇报》上新近发表的谢晋导演关于电影发展问题的探讨文章”,诙谐还原文人多面手的生活原色,再度让人领略卓荦之士在攻书为学上的博通。这于今似已成空谷传响,实值得移为年谱之注。
(2)论其性情气质,陈白夜、徐琰合著的《天使阳光行》郑重拾捡出“大学时期词学大家吴熊和先生让自命不凡的我们这一代警醒的惊世名言‘一代不如一代’”的史实。《杭州日报》1991年12月7日第三版《送礼》一文,娓娓道出了“有好多同学欣赏吴熊和先生的板书,便上门求字。吴先生生就菩萨心肠,一一满足,大家的心里好像树林里下来的阳光,好美。先生题的最多的是那句‘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的实事。蔚然而深秀,大抵是读到年谱中这两节注的人会有的感受。仍以页下注形式和正文叙述并辔,整部年谱是否顿然立体起来了呢?
出色的文人年谱,常常带给编修者一种侦探般的快感。从纷繁的枝叶鳞爪里,经由思维的缜密劳动而爬梳、排比、推演,渐渐理出头绪,甚至妙手有偶得,那一刻的快慰真是不足为外人道。这在我自己出于某种机缘而有幸编修某种文人年谱的过程中,确乎得到了共鸣。查考比勘之际,情不自禁地写出上面的真实阅读观感,或许有在博学君子面前班门弄斧之嫌?但我执著地以为,随着观念的解放,过去被认为逝者才享有的年谱编修资格,俨然正把许多健在的名人也涵容进来,对象的扩展会不会带来门槛的下降,是出版界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为此提出的问题,对有兴趣的同道来说想必不至于全然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