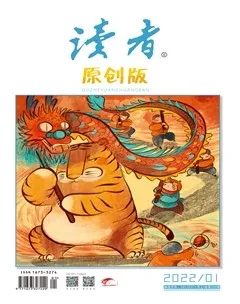房顶上的鲷子鱼
文|枨不戒
一
早些年间,镇上吃的水并不是自来水厂处理过的水,是水库的水。水用鹅卵石简单过滤,肉眼看起来是清澈的,也没有泥沙等杂物,只是喝到嘴里,会有一股水生植物特有的土腥味儿。自来水没通的时候,镇上有几口水井,老人都喜欢去水井打水,说是水质清冽,喝到嘴里甘甜。后来河边造纸厂建多了,水井的水就渐渐变涩了。再后来,自来水管从街边的商户延伸到土路边的农户,终于流进了所有人家。自来水虽然不好喝,但煮熟后是闻不到土腥味儿的,只是味道滞重。
和并非来自自来水厂的水一样,镇上的大部分东西都只具有形式上的作用。街边商户为了攀比,盖楼房时一律都是三层,财大气粗的也会建四层,只有远离集市的乡下才能见到两层的。可是不管房子是三层还是四层,进到房子里面,才发现地上的瓷砖只会贴到二楼;墙上的泥子也只会刷到二楼楼梯的尽头,三楼只有光秃秃的水泥;因为不住人,窗帘也省了,窗棂和房间里堆放的杂物都让太阳晒裂了。
我家也是这样。请泥瓦匠来建房子的时候,父亲煞有介事地画了张设计图,让师傅照图纸施工,但他一不懂建筑,二不懂艺术,只是为了省钱。于是,造出来的房子内部结构极其怪异,每层楼300多平方米的空间却只有四个房间,两个是卧室,长得令人发指,而横在两个卧室中间的客厅兼有走廊的功能。父亲为了赶时髦,在二楼卫生间装上浴缸和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安在三楼的房顶,黑色瓦片中间放着银色的太阳能板,白色管道一头接着面板,一头接着蓄水池。热水器质量不好,只有在室外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的三伏天,水龙头才能放出热水。但是在那样的温度下,其实水管里流出来的水已经是温的,加不加热意义不大。但是因为有了热水器,蓄水池被利用起来了,父亲还是满意的。
镇上所有的楼房,都会在楼顶砌一个蓄水池,这似乎成了镇上泥瓦匠独特的“签名”,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想出来的。蓄水池的主要功能是预防停水—把自来水管里的水抽到蓄水池里,停水时再注入管道中。有时夏天发洪水,管道进了污水,又或是管道维修,自来水公司停水一两天,根本不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蓄水池的次要功能是过滤杂质。有人嫌水不够清洁,就单接一根管道到蓄水池,把明矾撒在池水里沉淀杂质,做饭、烧水就用蓄水池里的水。那会儿好像也没有做专业防水,但水池里的水竟然从来没漏过,令如今的我感到惊奇。一楼卫生间的管道上有个水阀,可以向蓄水池上水,上水的时候管道嗡嗡作响,上满后管道就缄默不语。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爬到顶楼上去,看蓄水池有没有干,如果发现水少了,他就会叫我和弟弟上水。我们很喜欢干这个活儿,把红色的把手用力向下一扳,管道就沉重地唱起歌来,仿佛有千军万马在冲锋一般,充满激情。我家的蓄水池既不撒明矾,也没人做清洁,天长日久,水泥池子里长满了厚厚的青苔,池子边的缝隙里都是黑色菌斑,根本没人想喝里面的水。但因为父亲的坚持,蓄水池里永远都有半池水。碰上六月的雨季,大雨连着小雨淅淅沥沥下个把月的时候,蓄水池里的水涨满,水就沿着水泥墙面涓涓外溢,所以蓄水池旁边的外墙上也爬了几条粗粗的绿斑。
二
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弟弟正在打游戏,父亲从楼上下来,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蓄水池里长了鲷子鱼。我们一开始不信,但父亲信誓旦旦,不像是骗人,于是我们扔下游戏机手柄,从草席上爬起来,穿上拖鞋,跑上楼梯,嚷嚷着要看鱼。一口气爬到楼顶,太阳晒得人头晕,阳光是明晃晃的银色,像金属的光泽一般,刺得人眼睛酸痛,睁都睁不开。好不容易缓过来,我们盯着黑绿色的池底寻找,除了青苔和沉淀的杂质,什么也看不到。我疑心父亲骗人,消遣我们。他却煞有介事地指着一处让我们看。我眼睛都快瞪出眼眶了,还是什么都看不到,弟弟也一样。父亲弯腰捡了一小块水泥,朝蓄水池丢去,那个暗绿色的水中世界被惊醒,随着涟漪荡开,一道黑灰色的影子闪电般游窜,在浅水处,阳光照在它的肚皮上,我们这才看到一闪而过的银色鳞光。那瘦长的体形、敏捷的速度、银白的鳞片,果然是鲷子鱼!我们惊叫起来,围在池边,那条被惊起的鲷子鱼已经安静下来,匍匐在水底,和死寂的黑绿苔藓融为一体,只有它背鳍上的那一点点灰,提醒着我们这里有个活物。很快,我们发现水池里一共有三条鲷子鱼,手掌大小,是成年的鱼。它们潜伏不动,完美地融合在环境中,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太阳的炙烤让我们没了耐心,等了一会儿就下楼了,但心底的兴奋感一点儿也没减弱。整整两天,我们逢人就说房顶上长了鱼。堂妹和表弟过来玩儿,我也会热情地把他们拉到房顶上看鱼。
虽然家家都有蓄水池,但长了鱼的蓄水池只有我家有。我的心里充满疑问—它们是怎么来到蓄水池的?在那儿住了多久?它们吃什么?有没有鸟儿要抓它们?但它们不会说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沉浸在幻想中,想象它们奇幻的旅途—如何从水库游进管道,又怎么从管道来到我家,再从狭窄的水管里抽上房顶,最后在那个浅浅的蓄水池中安家。鲷子鱼是最灵巧的鱼,是水中的闪电,水中的精灵。江湖中有那么多种鱼,只有鲷子鱼不上鱼钩的当。我从未见过有人能钓到鲷子鱼,它太聪明,速度又太快,也不贪婪,经常是轻轻一掠,衔住一小块鱼食,等人发现时已经在一丈开外。用装了饲料的鱼篓也抓不住它,它们似乎没有钻洞的爱好,警惕心特别强。要抓鲷子鱼,只能用渔网将整面池塘围起来,从另一边驱赶鱼群,然后举着渔网向池塘中心推动,用拉网的方式才能网到这些精灵。
父亲最喜欢吃的河鲜就是鲷子鱼。新捕上来的鲷子鱼要马上清理干净,抹上一层薄盐,放在筲箕里铺开,然后放在太阳下暴晒一天,把鱼晒得半干后,放在油锅里用小火煎,加上豆瓣酱和姜丝,配上青椒片。这样煎出来的鲷子鱼两面金黄,香味儿浓郁。“门前一堰鱼,多吃几碗饭”,只要桌上有煎鲷子鱼,父亲就会高兴地念叨这句话,不仅会多吃两碗饭,还会小酌一杯。外婆知道父亲好这一口,经常和外公在门前的池塘拉网,夏季每隔十来天,就会送来一小筐晒得半干的鲷子鱼。我本来对煎鲷子鱼的兴趣一般,但架不住父亲日常的赞美,吃得多了,倒真的发现了鲷子鱼的好处:首先是香,这鱼晒的时候闻着臭,煎出来却喷香;其次是酥,这鱼的肚皮薄,用油轻轻一煎,皮肉和刺都煎酥了,入口即化;最后是嫩,鱼背上的厚肉纹理分明,又细又嫩。黄昏时分,父亲经常爬上房顶看鱼,但一次也没说过要吃了它们的话,明明他是那么爱吃鲷子鱼。他不提,我们也就忘了它们原本是一种食物。
三
童年的暑假,我最喜欢在正午时分跑出去玩,因为这个时候父母都在睡午觉,无人干涉。大部分时候我都会跑到路边去捡垃圾,去废弃工厂撬玻璃、铜丝,换了钱买一两根冰棍解馋。不去外面游荡时,我就爬上房顶,去看蓄水池里的鲷子鱼。夏天的太阳把水晒得滚烫,而水底除了苔藓就是霉斑,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正经食物。我总是害怕鲷子鱼热死、饿死,又或者是被鸟或猫掠走。但那个暑假,它们安安稳稳待在水池里,就像这里本就是它们的家一般。我不知道作为鱼生活在半空中是什么感觉,那三条鲷子鱼以一种荒谬而梦幻的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带来的除了惊喜,更多的是疑问,似乎一切都可以发生,一切又都无法解释。
那个夏天过后,我对鲷子鱼的热情退散了,就连父亲上去看鱼的时间也在变少。很快就是秋天,接着是冬天,当第一场雪给房顶铺上白色绒毯时,我们已经彻底忘了房顶上的鱼。蓄水池有没有结冰?鱼还活着吗?我们的思绪一点儿也没飘到这些问题上面。冬天的乐趣是火带来的,有了火,关于水的记忆就消失了。
我再也没有去看过那三条鲷子鱼,甚至再也没上过房顶,太阳把阁楼出口的松木小门晒裂了,楼梯上长满蛛网,那道封闭的小门将秘密永远封锁在门后。后来,我和弟弟求学,离开老家,去的地方一个比一个远;外婆和外公年迈,再也不能下水拉网;父亲生病,去世,餐桌上已经很少出现鲷子鱼。很多时候,我怀着某种信念热烈地期盼奇迹到来,但它始终没来,可是每当我想起那三条鱼的时候,又会恍然—原来奇迹是出现过的,只是它往往以一种意外的方式,一种与功利毫不相关的姿态,骤然出现在你面前。因为毫不相关,所以没人会在乎它。我不知道现在老家房顶的蓄水池里还有没有鲷子鱼,或许它们一直都在,也许它们已经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