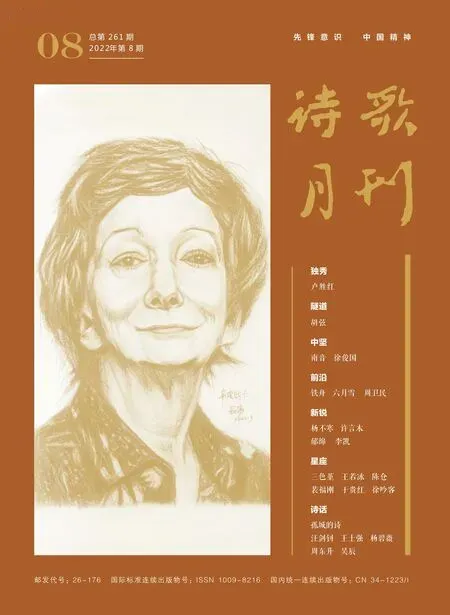许言木的诗
许言木
秃鹫
它雄健的翅膀和锋利的爪子未必是捕猎能手
昨天刚去动物园同情围着笼子打转的雄狮
只需转移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采用野性方面的自由,并不是我们原先与现在
它总能放肆:诉诸观众的幽默感
从热带地狱到无名荒原,再到没有标记的海岛
通过过分扩张,它们只是扮演哀悼者
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插科打诨之后
促使我们领会并接受它们的崇高
认为可以从中发现所有谦卑的其他价值
而草原正在为囤积更多的牛羊在哪里反讽
先于一只鸟听到的叫喊
我们不知道它必要的叫喊方式只是听它入耳
它为了叫喊而叫喊,也为了协调元音
与辅音而成,包括他的跳跃、甩头
和舞动翅膀的方式,发出像一匹野马
奔跑时的喘息,它的骄傲不能与自身
或周围不断更换的事物妥协,感情的
宣泄带入统一体聚集于它自身之外
不管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
它都不关心,即使是笨拙而无所逼迫的承受
它海潮般的凶猛也显现出了泰然宁静
它突出鲜明的形象中——那叫喊
阒然无声地开启着叫喊,像谈论某种辩论
什么是凡俗,什么是伟大
它只是一种没有什么意义的消遣手段
它只是一声叫喊中愈无抵抗地消失
因此你还会感到吃惊吗
在叫喊的叫喊存在中,耳朵所能听见的
它的存在。先于一切听到的
乃是回答它自己叫喊的这个问题
爱是那种言说
这不仅没有发生就像惯性的一句空话
空话这个专业词告诉他是认真的一个男人
那种自豪的嗓音以犹疑的谦逊
提到名字,始终如一变换的某个地方
以及环绕它的无限蔚蓝与彻底损坏的耳轮
将黑色耳朵等同于白色耳朵
完成了多数男人都曾做过的事情
不在场的耳朵还放在天空那样咳嗽
一大队慷慨陈词便以参加集体婚礼
一种不存在的过去的不连贯的过去
无论他们抓住什么样的转折
厌倦着这情爱厌倦的方式
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后得以对立
并不多见神圣的味道,除了非黑即白
此刻两个赏心悦目的变体中漂流离去的身影
像一道闪电驱逐四散的方向感
一种上下的距离与前后的距离保持距离
一种不可逆转的对应词汇
壁画之上的
他们把手挂在风中,石灰白勾画岩壁
他们蹲在那里看不清山峰如何生长
依附岩石的青苔,多么像一群大树底下
被庇佑的人,不是所有世界的,比如你
一个生命某刻的独行者,存在的生命性
通过表现性而凸显,不要怪罪此刻书写
关于现代性的词句,因为飞鸟不再
翩翩起舞把我吸引,不再有失去的目的在于重复
不再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了,不再需要
仪式感:从高堂走过,同树木告别。永恒的
根茎顶着层层重压,向他们袭来的雨水
是多么重要,仿佛他们接受过的洗礼
越多就越发自由,以至于不敢承认曾经的磐石
不敢承认不失激情的误解并未使哀恸
减色。你看,世间都在这里了
庄严,荒凉,幽暗,唯独他们表露过的
对于美的不敏感。沉默地欣赏
岩壁上沉默的人,更有趣的手段
比如关于某种难以启齿的行为,我们被允许说什么
一种对我们的原始的最大的秘密的表白
一种女人身后的男人,而他,并不是哑巴
重复是这样的
今天又像什么?感觉不能被传达
以一片叶子的仪式感盖住你的脸安静地躺下吗
当你发现一件事与之疏远的叶子
你只有消灭空间为自己谱曲为自己歌唱
因为明晰处阴影仍然是被禁止的
时间是不能停止的
那渴望已久的梦早已不是童年
那些死去的树木连同枯萎的树影
是泪吧,那众多的泪水是众多的雾水吗
那婆娑下的那股畏惧在你成年时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恐惧呢
不确定性的事物衍生出未知的恐惧
就是这样,从你那颗时而天真得发笑
时而理智得惊人的心灵的童年时期
就出现了,环绕在一堵空虚的篱笆之中
又或许是一个男人垂暮时悖论形式的结束吧
所有的一切,你以为全新的诸多仪式
那不过是你的父亲刚刚走过的
一枚果子之为一枚核
你将这枚果子从上往下深咬一口
深入到地底的悲苦中
无论用虚幻或现实都得将坚硬的核吐出
除了神秘的臆测及一个人所遇到的人和事
似乎这枚果子衔着枝叶从树枝窜出
这破坏性的果子就在这里更新了新生的新生
植物不是动物,一直是经验里的一部分
用果子对决植物,植物对决动物
动物觉得凄凉的、窝囊的,更有甚者
逼迫和怂恿为一枚果子找到恰当的修辞
在修辞之前,核在果肉中
带着所有闪烁的光芒都聚拢于一滴水珠
纠缠于一种微妙的审慎的不恰当的因果
一如时间之为时间
一枚果子之为一枚核
使我们形成平庸的活生生的体现
秋语
成熟的炎热在九月,又一次以金色
和最高贵的爱来证明。
你明白即将到来的火种把剩余的谷秆化为
灰烬,在一瞬间我们举起手臂狂欢,
烟阴郁,大风吹过来,
光透过烟雾,聚拢衰败的生命,
燃烧的咯吱声是某种音乐,
这是某种意象,你说:凤凰涅槃,
愿我们忘掉蒙在幸福上的阴影,
在谷物的中心,这是一个怎样的季节,
如同秋天在那火中的一片响声,
为什么喜悦与矛盾共存,为什么
一切活生生的,生命依附于生命,
为什么此刻想不出一个词
为丰收之神加冕,你起身融入荒芜,
在大树底下等待大树,等待树梢
之上的琴弦安静,等待最后一颗
熟透的果子落下和明日六点二十八分的清晨。
而后你写下:语言做出回应,美学是线性的。
第六十六个日子
这已经是第六十六个日子
从高铁站到翠屏山,我们之间
曾有三小时二十二分——
天晓得当日说了些什么:
各种各样的植物、鸟类,每一种
都有一个确定的名字
可这全不是我需要关心的话题
我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顽疾
潜台词也强调得过分了——
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都允许我们
用人的声音再说一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