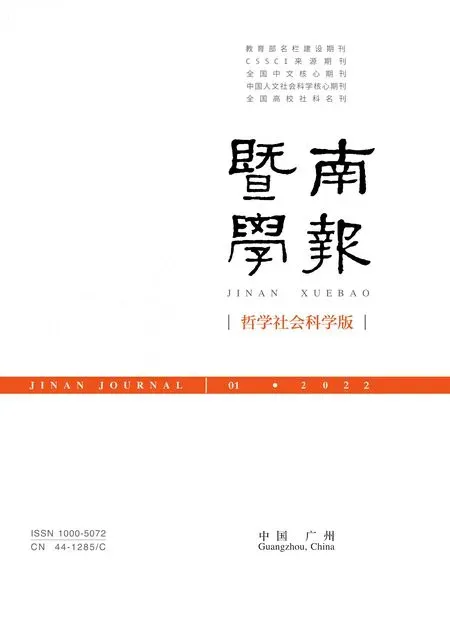疾病史视角下的云南与世界体系
——以现代鼠疫防治制度在云南的确立为例
李玉尚
1894年鼠疫在香港流行,并经由该地传播至世界各地,形成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香港和广东的鼠疫的来源,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本尼迪克特认为,由于云南—岭南间商路的开辟和形成、鸦片贸易的兴盛以及19世纪五六十年代广西的社会动荡,为云南—岭南间的鼠疫流行创造了条件。曹树基和李玉尚则认为,1867年北海的鼠疫疫情,很可能是当地动物间鼠疫波及人间之结果。对于广东省而言,鼠疫是本土的,不是外来的,云南与广东的鼠疫流行区是相互独立的。
当1894年之后世界不少地区因为不断攀升的鼠疫疫情苦恼不已时,中国东北、东蒙和其他地区也成为新的重灾区,已严重肆虐云南122年的鼠疫,却在1891年一场罕见的大雪之后,流行区域大为缩减,到1911 年仅见于蒙自与个旧,1940—1955年间又在滇西地区散在发生,1955年之后全省处于停歇状态,直到1982年再度复燃。吊诡的是,在1891年之后云南鼠疫疫情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之下,现代鼠疫病因学说迅速传入并广泛传播,较为完整的现代防治制度和体系得以建立,并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其背后的原因,则是清末之后云南已经突破和华南、南亚、东南亚地区间传统的商贸往来模式,不可避免地纳入到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了。
一、从熟视无睹到鼠疫宿主:鼠类认知上的变化
在1894年鼠疫病因明了之前,云南民众并没有把鼠疫发生的原因归结于老鼠,而普遍认为这种疾病或者是源于“地鬼”,或者是一种“天灾”,由此在不同地区衍生出两种不同的信仰和应对措施。这在清代地方志的记载中亦有所体现。在清代云南地方志中,至少有14部关于鼠类的记载。虽然各地地方志书编者对于当地鼠类的记载并不详细,也不是按照现代分类学标准编写,但仍可以从中窥见当时人们对于鼠类的认知。
清代志书中关于“竹鼠”记录最为普遍,这是因为竹鼠乃当地民众喜食之物。光绪三十年《顺宁府志》卷十三《食货志三·物产》记载:“小猡猡(景东厅)……薄种山地,捕鼠鸟,樵采木植,以佐生计。”民国《新平县志》有更详细的说明:“竹鼠,脂肪甚富,肉味浓厚,邑人多捕食之。”地方志亦记录“飞鼠”,是因为在各种鼠类之中,它显得极为特别,民国《路南县志》记载:“身体酷类鼠,因生双翅,可任意飞翔,故俗谓飞鼠。”
嘉庆二十五年《定边县志》卷五《田赋志·物产·兽属》除了记载“兔鼠”(硕鼠)等鼠类外,着重描绘了“黄鼠狼”和“黄鼠”:“地猴一名黄鼠狼,形极小,人驯养之,纵入其穴,则衔黄鼠啄曵出之,味极肥美,或曰黄鼠,交冬封穴而蛰,春和复出穴,马艾虎亦捉黄鼠,惟腰较黄鼠狼粗大。”这里的“黄鼠”,应是田间鼠类之一种。光绪《顺宁府志》记载:“采访:有家鼠、黄鼠、竹鼠”,宣统二年《楚雄县志·食货·物产·毛类》亦记载:“鼠(有田鼠)、竹鼠、灰鼠”。从上述地方志的记载来看,清代地方志之“黄鼠”,指的是“田鼠”之一种。
相对于对家鼠和田鼠的熟视无睹,清代地方志编者更关心的则是“鼠害”。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气象考三》收录了云南历史上的鼠类特殊活动,如下:
万历二十四年,云龙州硕鼠长尺余,群食禾稼,且尽。《旧通志》
顺治十六年,姚安鼯鼠遍野。《旧通志》
乾隆三十三年,镇雄田鼠大作,岁饥。《镇雄州志》
嘉庆九年,蒙自有鼠大如豚,成群过黎花江,食蒌实尽。阮修《通志》
道光二十年,大姚鼠伤稼。岑修《通志》
道光二十年田鼠伤稼的事件不止大姚县一例,康熙《大理府志》卷二十九《艺文上》也有记载:“君不听,未几,田鼠害禾稼,山有虎辄伤人,定为赏格,使人捕之乃息。”“定为赏格,使人捕之乃息”应指除虎行为。而对于田鼠害稼,只能听之任之。另外,乾隆三十三年镇雄田鼠大作与“岁饥”同时发生,野鼠上述异常活动很可能与灾荒有很大关系。
然而,在民国时期地方志中,对于老鼠的危害,再无害稼之描述,而全部转向了“家鼠”以及其为鼠疫传播之宿主。云南蒙自,不仅为云南率先开埠之区,也是鼠疫流行严重的区域。在全省疫势减退之后,该地仍然继续流行,1902年、1903年在城关镇流行,1911年再次流行。宣统《续蒙自县志》编者,不仅指出了老鼠为鼠疫之贮存宿主,还提醒要时常进行捕灭老鼠之活动。
鼠:背褐色,脚短,尾长,毛质柔滑,虽小穴亦易出入。穴处人家,夜出窃食。其生殖能力甚大,生百日即产子,每年四产,每产多至十头。各国因其为黑死病传染之媒介,且毁损器具、仓谷之数,统计甚巨,故常注意捕灭之。
按《续蒙自县志》宣统元年业已完成部分初稿,民国时期王锡昌等人进行重修编纂,这一段文字具体编纂年份不详。民国二十三年《宣威县志稿》卷三《舆地志下·物产》在“鼠”下做了如下的注解:“穴处人家,夜出窃食,生殖力甚大,百日即能产子。每年四产,每产五头至十头,为黑死病传染之媒介。”《宣威县志稿》的记载可能抄自《续蒙自县志》。
在清代,鼠疫在当地最为常见的称号为“痒子”和“红痰”,即分别为腺鼠疫和肺鼠疫。随着鼠疫病因的普及,“痒子”、“红痰”、“黑死病”等病名,在民国年间被统一为了“鼠疫”,即由老鼠传播的瘟疫。不仅如此,地方志编者还尝试用新的鼠疫学说来阐释本地之前发生的疾病。民国九年《续修建水县志》卷十《祥异》记载:“此疫即同治年之痒子症,两次俱历二十余年始平息……对时立毙,医药罔效,今传至外洋谓为鼠症,亦称鼠疫。”宣统《续蒙自县志》卷十二《杂志》又载:“同治十二年癸酉六月大疫,此疫名鼠疫,又曰痒子症,能传染,先鼠死,人即继之,初发热或生核在腋窝胯间,或痰带血,一二日立毙,医药无效。”
用现代鼠疫病因学说解释疾病,并非只是在最先开埠的临安府地区,云南其他地区同样如此。民国《广南县志》卷一《大事记》载:“自光绪十一年后,每岁交立秋节则发生鼠疫,至双降节止,岁以为常,尤以二十六七八三年为甚,死者垒垒,夜无行人。甚有全家死无一人,幸免者其时不知预防,听命于天而已,死亡数在万人以上。”民国《姚安县志》卷六十六《金石志·附杂载》记载:“军兴之后多有疠疫,咸丰九年大乱之后次年鼠疫大作,人死如麻。”民国年间《鹤庆县志》编者在编写该县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疫情时,和广南、姚安县志编者一样,直接采用了现代鼠疫病学的观点,指出“鼠疫人,继之次年又疫”,把老鼠作为传染源。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最早记载“鼠疫”的,是光绪《永北直隶厅志》,该志卷1《祥异》记载:“咸丰八年戊时起子时落,是时发逆杜文秀倡乱前半年,时疫汗症大作,死者甚众。同治十二年癸酉时疫。光绪五年己卯时疫复流行。七年辛巳鼠瘟,南路一带疫作。十六年庚寅九月时疫。十七年辛卯八月南路鼠疫复作。”该志特别注重发病特征。光绪十七年的“鼠疫”,系“鼠瘟”之后“疫作”的缩称,并非今天之鼠疫病名。
在云南个别地区,如个旧,矿业素来发达,矿难事故亦较多,由此形成鼠类保护的独特风俗:“据云老厂有耗子庙,乃因早年矿洞倒塌,洞内六工人由于耗子打洞通气未遭死亡,为报其恩而建庙以敬之,不忍杀鼠,因而鼠类得以兴旺繁殖。”个旧县保护鼠类只发生在当地个别矿区,并非普遍现象。对于民国时期云南绝大多数地区而言,老鼠在地方知识精英看来,它已经成为鼠疫的代名词。因此,宣统《续蒙自县志》编者王锡昌提出,对待老鼠,“故常注意补灭之”。建水与蒙自毗邻。民国九年《续修建水县志》卷十《祥异》记载:“此盖研究此症,由鼠传染,故失死鼠,因逐户掘鼠,几无噍类。”这里的“逐户掘鼠,几无噍类”,应理解为一种消灭鼠疫的建议。
民国年间,通过捕灭老鼠的方式预防鼠疫,已经成为全省地方精英的共识。一位自称“边野下士”的凤庆邑人,为“呈为条陈捕鼠运动法,恳祈鉴核,函令推行,以消隐患而利地方事”,上《条陈捕鼠运动办法书》。内中提及,“顾敌机飞临,人咸惴惴,然畏而避之,盖恐遭受轰炸无辜,而罹死伤惨祸”,据此推知其上书时间系在日本飞机轰炸云南期间,即1938—1944年间。
作者首陈鼠疫之传染途径,即“查鼠疫即黑死病,由鼠体寄生之蚤传染”,其表述极为准确。他接着指出:“西人极为注意,每岁不惜耗用巨资,设法捕鼠,以防鼠疫发生蔓延”,用“西人”之成法,说明灭鼠之科学性和重要性。他认为捕鼠乃经常性预防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项:“鼠疫则不然,一旦发生,连邻比户,到处流行传染,其害无穷,依此比较,防御鼠疫尤为切要而不可缓迨,至发现始谋补救,何异见贼至而磨刀寻械,晚矣!”
在这次上书的“四年前”(约1934—1940年间),“吾顺因鼠过多,曾由警局劝捐收买死鼠,一次数在万余,得以弭患无形”。文中“顺”即清代顺宁府,首府在凤城县。四年前所采取的办法是“警局劝捐收买死鼠”,即由警察局向富户劝捐经费,利用这笔经费,给予上交死鼠之人以奖金,共收得死鼠万余。
此后几年,此类活动再未举办。但由于“今岁以来,鼠复增加,较昔为甚,识者忧之,以为若不早为捕灭防御,难免不作疫成灾”,于是他拟具捕鼠运动办法八条,认为:“以上各条办法,简而易行,伏祈鉴核,分别函令,组织推行,庶鼠类得以减少,鼠疫可望灭绝,地方幸甚,人民幸甚!”这一办法是否由地方官采纳和函令推行,不得而知。就其内容而言,和四年前做法相比,有三点变化:一是委员会规模更大,二是动员民众更广,三是措施更为强迫。
捕鼠真正成为一种政权的强制行为,是在1942—1944年腾冲被日本占领期间,“当时日本鬼子命令维持会的给群众派交活老鼠的任务,受派交活鼠的村寨直达梁河的河面片。这次我们去访问猛洪村,有位老人说;‘日本人在时叫交活老鼠,逼得没有办法,我是拆房子,翻草堆捉去交的’。”理论上,这样强力度的灭鼠,鼠疫应该减弱才是。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者认为:“可想而知,日本帝国主义逼着群众交活老鼠指的勾当了,所以日本败退后的次年,我县境内就有一些村庄大量发生自然死鼠和人间鼠疫。”
二、1910年—1930年的政府防疫:传统的延续
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北里柴三朗(Kitasato)和耶尔森(Yersin)在当地发现了鼠疫杆菌,成为人类科学认识鼠疫的开端。1894年病原、宿主发现之后,1897年绪方(Ogata)又发现跳蚤可染疫传播鼠疫,鼠疫传播途径和感染方式得以初步明确。虽然如上所述,这些新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传到云南,但是伍连德式的现代防疫措施并没有随之用于云南防疫实践之中。1915年10月30日《申报》在《滇南杂闻》记载是年滇西永昌杉阳镇发生鼠疫,情况如下:
永昌县属杉阳地方,本为腾永通衢,素有炎热症之发现,日昨有由该处来者,云近日忽然发现鼠疫(即滇省俗称之洋子症),是病传染颇速,患者不过一二日即毙命,亦非药力可治。现在该处人民,染此病而死者,已不下五六十人,因此生存者极为恐慌,纷纷迁避矣。
杉阳为腾永通衢,一直是周边地区鼠疫传播的源地,也被称为“痒窝子”。1915年此疫再次发生,幸存者也只是“纷纷迁避”。杉阳并非特例,1919年3月31日《申报》在《云南发现鼠疫说》中记载维西县的情况如下:
数十年前曾有鼠疫发现,死人无算,近二十年来,均未有闻,不料近两月来,先则维西县地方发现鼠疫,死亡枕藉,凄惨万状。据维西代理杨知事报告云:民国七年十二月十五六日间,瘟疫流行,受病者均是头痛咳啖发热之症,适商号传来。油印通用药方两单,均属清凉之品,病原亦甚相符。张知事审查合宜,即传地方慈善会,捐资配药分送,并传药方,地方人按方服药,亦甚有效。至二十五六日,病症传染遍城内,人民已至无家无人莫可幸免者。署中办事员书均已病卧不能入署,办事法警各役以及监押人犯,均无不病。张知事亦于二十六日染病。……闻之地方人言,此等劫数为从来所未有云云。
现任张知事罹患鼠疫死亡之后,可能为了寻求援助,暂代知事杨述信将维西县的惨况透露给了国内主要媒体,除了1919年3月31日《申报》外,1919年3月31日《民国日报》和1919年4月4日《大公报》都登载了杨述信的上述报告文。
上文可知,维西鼠疫流行时,张知事所采取的主要防治办法,为“即传地方慈善会”,按照“油印通用药方两单”,“捐资配药分送,并传药方,地方人按方服药”。这一做法也是当时云南省府的主要做法。1918年,广南县知事李文干“谨就平时所闻见暨经验而有得者,爰编《预防鼠疫白话篇》计共八章,录呈鉴定,并请转令警厅刊发,俾吾滇民共知防患于未然,不致临危失错”。云南省主政者接受了他的意见。省长公署发出训令,要求各地道尹“即便查照排印多份,通令所属,布告人民,一体遵照,并资各道尹查照,仍俟印竣检呈一本来署,以备查考”。云南蒙自道道尹于这一年9月24日,给石屏县知事聂培煋发出训令,令其执行。聂培煋执行了这一训令:“业经令饬警所将警务专令,发白话篇,照钞多份,张贴通衢,俾众周知,附卷可也。”
从维西县的案例来看,按方服药的方法对于阻止鼠疫用处不大。维西县鼠疫很快就向外传播,楚雄等地亦有鼠疫发现,1919年3月31日《申报》云:
近则楚雄县亦有鼠疫发现,死者难以计数,闻某小村共有男女九十余人,未三日即死亡八十余人,真有令人目不忍睹者。而此数目中,此种不祥之鼠疫又忽传染到广通县(楚雄距省六天,广通距省五天)患病者较楚雄更众,死亡尤多。现闻楚广官绅虽已设局防卫,而距省较近楚广又为迄西通省大道,来省之人甚多,现在省警察厅陈厅长对于此于此事认真防卫,已派员前至距省一站之安宁县,设立防疫检查所,对于迄西来人,须认真检察,并恐将遮断交通云。
为了防止广通和楚雄两县鼠疫传入省城昆明,云南省警察厅在安宁县设立防疫检查所。如果疫情继续恶化,将采取断绝交通的方法。
同一时期,远在几千里之外的上海,实施了与云南性质不同的防疫措施。1911年5月20日《时报》登载《检查鼠疫告示》一文,据此可知,查清传染源、细菌学检验确诊、收治病人、广泛医学检查等现代防疫措施,成为上海防疫的主要手段,这与20世纪年代的云南形成了迥然差别。
云南地区鼠疫防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系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及亚洲战局的发展,云南的地位迅速腾升,防疫工作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一份名为“云南省的防疫工作”称:
云南省自古即瘴气(恶性疟疾)著称,行人视为畏途。自抗战以还,该省顿成西南重心,国际交通要点,随交通线之关系,各种疫疠,乘机侵入。去夏霍乱盛行,形势猖獗。秋后滇缅公路境内,发现鼠疫,大有延入国境之虞。卫生署有鉴于此,特与省政府当局合作组织抗疟,防制霍乱,鼠疫等委员会,从事各项防疫工作,兹将各该委员会之工作情形,略述于后。
其中,鼠疫防制委员会的工作如下:“该会为防制鼠疫沿滇维缅公路,侵入国境起见,拟在边境各县,开始调查。其余如定制疫苗,设立情报处等工作,亦在分头进行中。”其实上一年,西南地区的传染病就引起了《北华捷报》的关注:“在云南缅甸边界,越来越多的腺鼠疫病人被报导。云贵边界的霍乱据说也是很严重的。云南卫生当局正在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疫苗注射,鼠疫防治机构正在准备血清。卫生当局看上去胸有成竹。”
三、抗战与20世纪40年代现代医学的介入
根据1944年云南省卫生处滇西鼠疫防治队的调查,滇西之鼠疫,于1875年、1885年、1915年、1935年曾有发生,但此系当地乡老所谈,缺乏“详细记载及科学之证明”。1940年经细菌学检验确有鼠疫发生,1944—1949年每年都在滇西地区散在流行。
1949年10月20日,已逃至台湾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司“以滇省蒙化县本年三、六两月份即已发现鼠疫”为由,向滇省卢汉政府发出公函,询问“关于首例发现地点、日期、性别、年龄、是否真性、用何方法检验及本年度鼠疫病例共有多少”。云南省府回电称:“查蒙化县本年三、六两月份即已发现鼠疫,当时该县并未县报省卫生处,直至九月初旬。”
内政部卫生司和云南省的这次公函往来只是例行公事。发现鼠疫病例后,由县级单位呈报省卫生处,再由省上报中央政府之卫生主管机构,这一制度诞生于抗日战争这一战时状态。1940年5月,国民政府卫生署、军医署、联勤总司令部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防疫总队,联合组成全国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负责从中央、省、市及县各级卫生机关及医疗机构收集应登记的传染病的报告,并进行制表分析。负责登记和报告传染病的基层机构是县卫生院。同时,有鉴于鼠疫和霍乱在十种应登记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中的特殊重要性,自1940年5月开始实施这两种疾病的电报报告。
云南虽僻处西南边陲,但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大后方,负责一县之内居民法定传染病登记报告的卫生院数量,发展很快。1936年7月,省卫生处成立,1937—1943年,在全省129个县中,设立卫生院的县分别有3、21、37、45、77、102、92个。大量县级卫生院及乡镇卫生分所的设立,以及县—省—中央网络体系的建立,为疫情的快速发现和及时防治提供了基本保障。
1949年10月至12月,是决定云南政治走向的关键时期。这一年鼠疫疫情的报告和防治工作虽然多少因此受到影响,比如蒙化9月初旬才上报疫情,但基本上仍然按照既有制度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1942—1943年,云南已经基本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传染病登记和防疫体系,1944年之后滇西地区再次出现的鼠疫疫情,是对这一体系和制度的极佳检验。1944—1949年间,云南省卫生处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登记报告、细菌诊断、检疫、紧急处理和环境卫生等,兹分别论述之。
1946年6月,滇西鼠疫流行,蛮市、腾冲、保山相继告急。实际上在此之前的二、三月间,在施甸人和镇东北二里余一个叫老关庙的村庄里,先发现较多的死鼠,二十余日后,即发现鼠疫患者,人间鼠疫持续了二十余日,死亡十七人,其中一家死绝。然而,对于这一突发情况,“当地乡镇保甲长均未注意及报告”。在老关庙鼠疫终止的一个月后,人和镇人和桥街上又发现死鼠二十余只,之后镇上群集草栅内的数名乞丐相继病死,继之居民亦发现鼠疫患者,且日有死亡,“至是方为地方当局注意且向有关机关报告”。云南省卫生处在接到报告后,于六月廿九日成立云南省卫生处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队,七月三日到达保山。此时,“保山县城内于六月二十九日,已发现鼠疫患者一人死去,县属人和镇地方,因鼠疫而死者已达三十余人之多,于是人心惶惶,群众谈虎色变,均感大难即将临头,不可终日之势”。虽然早期疫情有所延误,但还是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并进行了报告。
在疫情处治过程中,县政府不断向省卫生处进行报告,1946年11月14日,云南省卫生处收到了保山县卫生院院长柯啸秋的报告,云:“查保山发生鼠疫,迄今四月有余,截至十月底止,所有疫情统计理合制表,备文呈请鉴核备查等情。”在其所附《保山县鼠疫疫情统计表》中,按照地点、发现日期、病例、其中死亡、治愈和现有病人,统计了该县自6月26日至10月31日的207个病例。在云南省档案馆所藏同一个案卷中,还附有鼠疫旬报表格,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诊治日期、患病日期、症候、温度、注射次数、结果(预后)、备考等项。从1949年10月20日内政部卫生司公函来看,这些内容都需要上报。这从1948年下关卫生院的一份公函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案查十一月中旬下关鼠疫防治情形并病例表,曾从关卫字第110号呈报在案,兹谨将下旬及十二月上旬防治情形并病例继续呈报。”
1949年10月内政部卫生司公函中提及的一项内容是“是否真性、用何方法检验”,即细菌学检验是必须的流程。据1945年《滇西鼠疫防治报告》,1940年6月底,瑞丽垒九的飞机制造厂中,“有一印籍司机据谓同患鼠疫身死,电请本处及卫生署派员前往防治,惟各员于七月初到达该地时,已不再发现,仅检查得一确染鼠疫之鼠而已。”是年7月底,在瑞丽尾弄岛,“经死鼠及病人之解剖、检验及培养结果,证明鼠疫无疑。”1947年8月,保山鼠疫,“经职前往调查并抽腺液化验,查出有鼠疫形杆菌,乃立即派员在附近各街巷注射预防疫。”1948年,“至十月四日卫生院据报有仁民街苏姓小孩,类似鼠疫,经诊视后发现该病例右鼠蹊腺肿,高热,谚语,经淋巴腺穿刺,送请大理福音医院检验证实,故此病例即成为下关鼠疫之第一病人”。从上述记载来看,当时检验的普遍方法是“抽腺液化验”。
细菌学检验一方面可以对疾病进行确诊,另一方面可以排除类似疫情。如1946年7月20日,在保山县羊邑镇,“据报瓦房村、热水塘发现鼠疫患者,八月九日据报石龙坪(据羊邑东南八公里),八月十四日张家村,均报发现鼠疫,经驰往调查结果,均非鼠疫,而为其他疾患,仅当时予以治疗即行返回。”这一年保山鼠疫也引起了剑川的恐慌:“兹建议保山鼠疫已越过澜沧江,传至剑川弥沙井,昨接八月十八日来讯,自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二十余日间,弥沙井居民百余户中已经患鼠疫死亡十余人,其死亡率之大而且速,较之保山芒市各处情形尤甚,尚不速予扑灭,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然而经云南省卫生处防治队调查,“据剑川卫生院电报疫症,确系回归热非鼠疫”。
在疫源地理论出现之前,人们观察到鼠疫系由一个城市传播到另外一个城市,滇西鼠疫由缅甸传入的看说由此形成:“在据地方乡绅所告,约于一八九四年—九六年间,时值世界性鼠疫之大流行,滇西盈江、八莫、南旬、龙川、龙陵、保山等处六边,鼠疫光顾得病者二万人。”由于博南古道和滇缅公路上的商贸往来频繁,似乎更加印证了鼠疫由南向北、由西向东进行传播:“滇西鼠疫及滇南疟疾数年来猖獗未已,鼠疫自缅甸传入,沿大盈江及滇缅公路渐向内地蔓延。三十六年度,曾达保山城区及城区以北板桥等沿公路一带村落,十年在保山城区及其附近村落即发现患者三百五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三人,疫势有沿公路再向永平、下关一带蔓延之趋势。”尽管1944—1947年滇西鼠疫起源于云南鼠疫自然疫源地内,但是传播到省内其他地方的危险仍然是存在的,如1946年,“在防治期中,人和镇鼠疫恢复期患者陈定国因恐惧封锁及隔离后受苦,于七月八日夜间,只身逃逸,不知去向,均无下落,可能为其他鼠疫之导火球。”因此,当疫情变得严重起来,检疫就会成为防疫的一项重要措施。
腾冲为云南重要商贸口岸,也是云南重要的检疫口岸。因此,“腾冲在敌军占据前,卫生署即已设立腾冲检疫所。今腾冲业已收复,应请恢复此项组织,在中印滇缅两路交通点进行检疫工作,俾能防止各项急性流行病之传染蔓延”。1947年7月,保山疫情严重,“拟请暂禁昆关一带与救疫无关之车辆来保,并在霁虹、功果两地设站检疫,以免疫渡澜沧,更难扑灭”。该建议由云南省主席卢汉批准实施。保山的鼠疫流行,使处于滇西交通中心的下关民众深为忧虑,这是因为:“下关地处滇西中心,商贾云集,人烟稠密,因滇缅公路关系,交通频繁,自保山至下关,朝发夕至,证诸芒、腾、保疫情,既如上述,则安之今日保山鼠疫,不能明日传入滇西中心之下关耶,又安知不能由下关沿公路传入颠中之省会,而遍延西南川、黔、桂各省耶,若保山疫情,只达平息而未达绝灭,仍如过去互发互止,若断若续之阶段,悠悠来日,传播勘虑。”职是之故,成立检查站进行检疫工作:“案查下关成立临时防疫委员会,设置临时检查站,于九月六号开始检疫预防工作等情,曾以关卫字43号呈报在案。”
1946年6月,滇西鼠疫再次流行,蛮(芒)市、腾冲、保山相继告急,云南省卫生处派出防治队进行防疫,其中第三队工作负责保山的防疫工作。在其所提交的《云南省卫生处滇西鼠疫防治第三队工作报告》中,详细记录了保山人和镇、三岔河和辛街三个疫区的防疫经过。其中,人和镇防治经过如下:
七月四日职队赶往人和镇调查,当时尚有患者九人,其中一人尚疑似未确定外,其余八人经显微镜及病状证实为腺鼠疫之后,当时即施以初步之防治…… 七月五日,“防委会”(滇西鼠疫临时防治委员会)成立,决定防治方针后,即由职以经常驻人和镇防治,并由“封锁执行检疫股”派兵封锁该镇,直至无鼠疫病例发现二周(七月二十一日)方解封锁,…… 每日分数小组普遍施行与防治注射,先由镇内而及镇外村庄,所有附近发现死鼠之村落均一一普遍预防注射。又于发现患者及死鼠之家,逐户用DDT喷射灭蚤,及石灰填塞鼠洞之后,虽于七月五日至七日,继续发现患者三人,七日之后,即无新病例发现,所以患者,除孕妇及一妇女一少女三人外不治死去外,余均完全治愈。
疫情发生时所采取的紧急处理措施包括细菌学检验、成立防疫机构、军队封锁、普遍预防注射、DDT灭蚤、石灰填塞鼠洞、对患者进行治疗等。
人和桥首先发生鼠疫,三岔河和辛街继之。据保山县卫生院的报告,“人和桥系初发生,无从注射预防针,死亡率达73%。三岔河因事先注射预防针,死亡率即降为27%。”可见,普遍预防注射在20世纪40年代的鼠疫防治中作用突出。其他疫区也是如此。据云南省卫生处统计,1946年滇西地区发病人数592人,死亡人数138人,患者病死率为23.31%,和1894年之前患者几乎不治相比,病死率已经大大下降。1938—1949年间大理州发病人数944人,死亡人数209人,病死率为22.13%。德宏州发病人数10 300人,死亡4 654人,病死率为45.18%。1950—1955年间,大理州发病1346人,死亡152人,病死率为11.29%;德宏州发病2 950人,死亡633人,病死率21.45%。1946年滇西病死率和1950—1955年德宏州基本相同,说明普遍预防注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8年,云南省卫生处第三医疗防治队这样评价鼠疫流行期间环境卫生整顿工作的作用:“鼠疫发生之原因为鼠与蚤,而此二物之滋生,又与污秽等有关。”然而,环境卫生整饬面临巨大困难,如下关为滇西门户和商业繁盛之区,“惟环境卫生方面,任与其他边避村落并无二致。四千余户人家甚少自用厕所,而公厕又复阙如。一万五千余人口之镇市,即无公共垃圾箱,又缺乏清除垃圾之人员及经费,是故在市中心地带,如鸳浦街上的,即可久有形如山丘之垃圾箱,每当雨过天晴,臭气日益,引人掩鼻。”
下关尚且如此,其余地区更是糟糕至极。1944年,腾冲鼠疫,云南省卫生处派医师三人、环境卫生员一人前往,于是年十一月八日赶到腾冲。在腾冲南45公里的南甸,防治人员看到如下景象:“甚少较大家产居住一处,人畜杂居,煤抹垃圾遍布,仅一板上垫草席,床下箱柜杂置,卧室并无窗孔,白日也不见光,堂间即为灶房,各无烟囱,烟熏便屋,谷磨后亦放室内,器皿杂布,残食曾饲牲畜,屋内畜粪遍见。”云南省卫生处派来的环境卫生员,进行如下之卫生改良:“劝导居民增开窗户,至少每屋应有十分之一地板面积之窗洞,卧室内蚤类之骚扰只可减轻,并教居民以开沟派水之法而不致使鼠类自外侵入,并拟建公用焚穗炉及教主妇以厨残处理之方法,使最后做施肥之用。”可见,环境卫生整顿工作,其目的是配合疫情紧急处理,消除鼠蚤滋生的环境,而非平常状态下的预防。
四、美援卫生还是群众运动:1950年—1980年防疫的变化
中央大学毕业生过基同参与了1945年滇西地区的鼠疫防治。他指出:“中央卫生署和云南省卫生处派的防疫人员,联合进行防疫,承盟国捐款五百万元作为三十四年一至四月份的经费,工作实际包括灭鼠,灭蚤,预防注射,环境卫生改善。”其中灭鼠消毒所用氢化钙是美国氢化物公司的出品。采用碳酸钡进行毒鼠。1945年2月29日在腾冲九保镇实施了DDT灭蚤,其意义重大:“是我国民间大规模工作之第一次,也是我国防鼠疫时的第一次应用。”在治疗上,“在腾冲九保镇武庙内,曾设了防疫医院,收容病人,鼠疫病人的冶疗用药,大多采用磺胺嘧啶(Sulfadiayine)。第一剂量四公分,以后每隔四小时给一公分,直至热度退清为止。除磺胺嘧啶外,有时并用血清治疗。”美援卫生不只以上这些,还包括“这次防疫工作,美军团供给工作人员的交通工具,并派卫生人员参加工作,处处表示着同盟国的合作。”
1949年之后,美援卫生难以为继,防治鼠疫,医学介入和查找疫源的同时,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消灭鼠蚤,成为一项崭新的内容,虽然此项工作云南并没有如内蒙古那样进行得轰轰烈烈。1955年之后云南鼠疫停歇,查找疫源地成为一项新的重要工作:“根据中央鼠疫防治工作规划纲要及我省鼠疫防治规划(草案)和疫区调查计划的要求”,“在近二年(1956—1957年)内基本上查清全省鼠疫疫区,摸清疫区疆界”。在河口县,调查工作是在1957年10月份进行的,除了进行鼠疫动物学调查外,重点对人类鼠疫流行史和动物病流行情况进行详细科学的调查。云南其他县调查内容和方法与河口县相同。20世纪70年代,鼠疫专家又发现了云南剑川大绒鼠为主要宿主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它是目前已知云南存在的两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之一。疫源地的确立,证明云南人间鼠疫主要来自本地动物病,但由于云南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与越南、缅甸等国家连在一起,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仍然需要严防鼠疫从境外传入。
1977年,云南省红河州卫生局在接到云南省卫生局《关于严防鼠疫从越南传入的紧急通知》后,于是年5月31日向下辖各县(市)卫生局下发通知,提出预防鼠疫措施,包括提高思想认识、广泛开展群众运动消灭鼠蚤、掌握疫情动态和普遍预防注射四项。红河州所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杀鼠、灭蚤药物近年来比较紧张”,因此,一方面“正向省州有关部门积极反映设法解决”,另一方面,“请各县(市)充分发动群众利用一切现有可以利用的条件,积极开展工作”。
河口位于中越边境,这一年,河口县委、县革委接到红河州卫生局上述通知后,进行如下工作任务布置:
1.作好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非特殊情况禁止边民出境。对境外边民入境,劝其不得久留,对无入境手续者不准入境。
2.要求在全县人群(包括部队、流动人口)90%以上进行预防注射。
3.大面积的室内外和环境灭鼠、灭蚤,发动群众用各种方法进行。喷洒及毒鼠药物,由防疫站供应。
4.加强疫情监视和报告,注意自死鼠的检验(离卫生、防疫机构远的地方,用火烧处理),和对可疑病人的观察,对疫情要及时逐级报告,不报或晚报者要追究责任。发生鼠疫病人,就地隔离,就地治疗,不得外转。
第一条是禁止境内边民出境,控制境外人员入境和居留时间,属检疫措施。第二条要求对包括部队和流动人口在内的全县90%以上人口进行预防注射,上文已述,对鼠疫进行普遍预防注射,在20世纪40年代的云南,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第三条是大面积消灭鼠蚤,采取的方法是发动群众,从防疫站供应喷洒及毒鼠药物来看,河口应是红河州防疫重点地区。第四条首先加强对自毙鼠和可疑病人的监测,并强调登记报告制度,“不报或晚报者要追究责任”;其次,如果发现病人,采取的措施是就地隔离治疗,不允许转往县境以外地区,此系隔离措施。
在接到红河州的通知后,1977年6月6日,建水县卫生防疫站也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卫生局《严防鼠疫从越南传入的紧急通知》的意见”,提出五点贯彻意见,其中两项如下:
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以灭鼠、灭蝇为重点。灭鼠,以器械灭鼠为主(夹、压、关、拉、翻、套、勒、吊、刺、淹等方法)。灭蝇:充分发挥民间中草药的作用。在有条件的地区,可用药物来进行灭鼠、灭蝇,通过各种有效方法,消灭老鼠、跳蚤,大大降低鼠蚤密度。
加强疫情报告,掌握疫情动态。各公社疫情报告要加强,除此外要两报:老鼠死得多要报,无原因急死病要报。
发动群众灭鼠、灭蝇、灭蚤一项,只是在“有条件”地区使用药物,对于多数地区而言,则使用器械灭鼠和中草药灭蝇。
1986年,红河州下发今冬明春大面积灭鼠活动的通知,河口县成立灭鼠领导小组。这次捕鼠活动亦是因是年越南河内、海防和太原等地发生人间鼠疫,应成都军区要求进行的。根据部署,七月份发布灭鼠通知,通过广播、墙报等形式进行宣传。八月份捕捉活鼠用以测定鼠类密度和采集鼠血。十月份举办灭鼠培训班。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为全城区统一投放毒饵时间,至是月二十五日,据统计拣到死鼠2 213只,估算灭鼠8 852只以上。
河口县卫生局和爱委会对这次灭鼠活动自我评价较高:“这次大面积灭鼠,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此以前河口鼠害是严重的,老鼠活动猖狂,特别是在自卫还击后一阶段,老鼠比人还要多,有的老鼠长一市尺多长,重900克以上,猫见了都害怕,每户居民平均灭鼠二只以上,有些居民就灭鼠32只。”在“一九八六年卫生防疫工作总结”中,则如此表述:“这次大面积灭鼠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有的老鼠有一市尺多长,重900克,这次灭鼠,每户居民平均灭鼠二只以上,有的居民,一户灭鼠32只。”
在“一九八六年卫生防疫工作总结”中,1986年全县共灭鼠11 002只,计城关区9 108只,桥头239只,槟榔寨69只,蚂蝗堡农场1 562只。可见捕鼠以城区为主。就其灭鼠数量而言,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凤庆相似。1986年两份公文都强调此次捕鼠活动为河口县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如果所说为实,那么意味着1949—1985年间,人为控制鼠类数量并非一项主要工作内容。事实上,经过长时期的鼠间鼠疫流行,在鼠间鼠疫和气候变冷双重不利因素下,1894年之后云南省鼠蚤数量和密度都已经出现极大的降低。
五、结 论
清代后期云南临安(红河)与东南地区贸易往来已是比较密切,闽粤地区鼠疫流行时内服药物之法很快传播到这一地区。随着蒙自、思茅、腾越的开埠和滇越铁路的修建,云南越来越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鼠疫病因发现之后,很快就为云南精英人士所接受,他们在强调老鼠为鼠疫宿主的同时,也把控制鼠疫的重点放在了灭鼠之上。然而,1894年之后云南省鼠蚤数量和密度都已经出现极大的降低。
全面抗战之前,云南官府对于散在发生的或者由境外传入的鼠疫,其紧急处理的方法,与1894年之前相比,并没有本质变化。全面抗战之后,随着云南地位的变化和亚洲战局的发展,法定传染病上报制度和县级卫生院得以建立,同时在美援卫生的支持下,云南的防疫措施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随着美援卫生的结束以及云南鼠疫的消失,查找疫源地和防止境外输入成为防疫重点,除了现代医学手段之外,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消灭鼠蚤,成为一项崭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