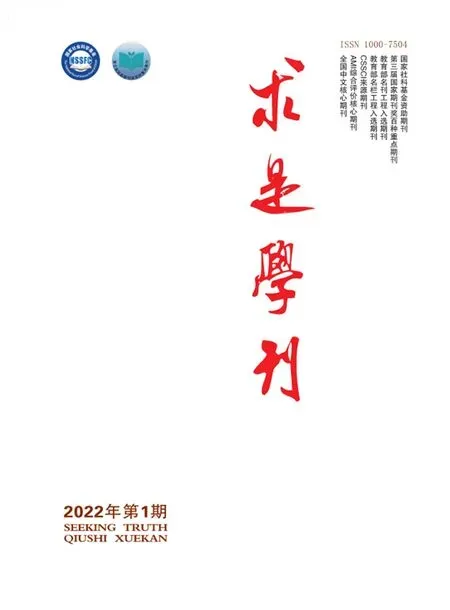晚清小说中的外星叙事及其现代意义
张 翼
仰观星辰是中国传统天文活动的主要内容,其目的不是探求星体的形态轮廓和运行规律,而是要以星相的变化来解释国家皇权统治的合法与否,所谓“天人感应”“天人之际”“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皆由此而来。受此影响,传统文学常常将日月星辰引入其中,作为文人寄思抒情的载体。以月亮为例,《诗经》以之譬喻美人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月出》)屈原《天问》仰望星空,向月追问云:“日月安属?列星安陈?”由探求星际奥秘升华出对终极存在的思索。李白《静夜思》借之倾诉怀乡云:“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苏轼《中秋月》睹月喟叹人生云:“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然而,到了近代,人们以相对科学化的认识论,褪去了这些星体身上的神秘色彩。反映在文学之中,就是近代文人不再将它们当作寄思抒情的载体,而是把它们当作“新民”的科学媒介。翻译小说《月界旅行》《世界末日记》《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原创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月球殖民地小说》《电世界》《光绪万年》等,或描写外星的样貌,或呈现地球的样态,或想象外星对地球生命之影响,均是“新民”主题的积极反映。
一、外星书写的维度
19 世纪晚期,晚清民众已受近代天文学影响,对外星有了初步了解。摩嘉立《论月》云:“(月)有大平原,有山有谷,其中最高之山,有十二里之则,一派绵长,与欧罗巴州之亚卑斯山、南亚美利亚加州之安地师山相似,其中山岭有大而圆之形,此乃火山,与地球之火山相同。”至于月球上是否有空气,当时也有讨论:“月中有空气否,天文士所论不一,或云有气,或云无有,至于江河洋海,似未之有,盖月自转一周,为一昼夜,即有水,彼日火曝之,亦化为气。”慕维廉《天文地理序说》论太阳云:“太阳周围轨道几有圆形,约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同时旋转本枢有偏向之方约在二十四时,如此即生相继之光景与结果乃为四季、气候、日夜等。此球亦有高低之处,泽海之水充于深下之所,且有空气在四周,更有几等使者,如湿气、电气、磁气、光亮行在地面。”与此同时,《谈天》《天文启蒙》等天文学著作,《万国公报》《申报》《格致汇编》《中西闻见录》等报刊,积极传播天文知识;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以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等新式学堂,也有对“天文学”课程的知识讲授,等等。这些均可想象晚清民众对太阳、月球、慧星等外星的了解程度。受此影响,邹弢在小说《海上尘天影》中就让主人公兰生做了一篇《日月星辰系焉》,其所言全为“泰西天文新说”,满篇都是“七星轨道,经纬度数,地球日球,星球大小”的数据考证。
考察晚清小说中的外星书写,大致呈现出三种维度:
其一是对外星做科学陈述。如周桂笙翻译的短篇小说《飞访木星》,借助博士与“余”关于陨石的对话,向读者普及天文学常识,使读者知悉陨石实为天空流星,而流星之所以坠落是受地球引力影响,与人间吉凶并无关联。《飞访木星》不仅向读者介绍天体运行规律,更重要的是借外星向读者传递科学的理性精神。博士去往木星的动机全然出自探索未知。他三十年孜孜以求的只是“试实验之学问而已”。此类小说除普及常识、彰显科学热情之外,文风也常常表现出客观的科学气质。《飞访木星》如此描述陨石的外观:“石作深黄色,而微带青灰,俨若新出炉之紫铜之色,而花纹腠理之中皆杂以晶结金类,光彩闪烁,有如矿苗。”此段叙述词汇浅白形象,句式简洁实用,与其说是文学描写,不如说是简介说明更为恰当。
其二是对外星做奇幻想象。晚清小说中的外星书写不乏科学陈述,也多有与科学相去甚远的奇思妙想。如《新法螺先生谭》对金星的描述,金星盖着“极软之球皮”,其形态“殆如带壳之大龙眼”,其上满是黄金宝石,各种腔肠动物、棘皮动物、软体动物、节足动物出没其中,也有羊齿类、蕨类、藓类等植被。科学观测已经证明金星是被一层高反射、不透明的硫酸云所覆盖,并无任何生物,“余”所见到的金星,显然出于离奇幻想。小说对金星的不实之写,或可从此时天文学知识仍存局限做出解释,小说中更荒诞不经的是,“余”早就声明金星此前并无人类踏足,然而在此“余”竟然发现了自己的日记。这一情节离奇到连“余”自己都无法解释。小说对金星的描述既有违背天文常识之处,也存在着难以阐明的自我矛盾,足见“余”所见之金星实属奇幻想象。
其三是对外星做理想设定。这是晚清小说书写外星的主要形态。《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儒生龙孟华把月球看作超越污浊现实的清白世界。因墨史迫害逃离故乡的龙孟华,在流浪途中遥望明月,愤懑感慨道:“月亮阿月亮!……从这肮肮脏脏的世界飞到你清清白白的世界里去。”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另一主人公科学家玉太郎看来,“月世界”是科技发达的现代之邦。玉太郎的气球只能在地球出没,“月世界”的气球却已能够自如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往来,“月世界”的科技发达可见一斑。玉太郎也因此对“月世界”产生了崇敬向往之情。《电世界》里的电大王黄震球对金星寄予了比科技发达更高的文明希望。黄震球创造性地运用“电”,使中国由贫弱变成富强,还通过开发南极、北极、海底彻底解决了地球上的饥饿、贫穷、居住空间不足、教育不公等问题,将地球变为了大同世界。可是,科技发达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无穷战争,带来了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不断报复的敌国士兵、失业的煤矿工人、横行海底世界的强盗,电大王困惑失落,寄希望于外星,建造飞船向金星进发,希望“周游行星世界,或者可得参观互镜,采些法子回来,慢慢的补全缺陷也未可知”。
当然,晚清小说中的外星书写绝非上文所述的那样简单。小说中往往出现科学、幻想与理想等维度之间的交错。如科学陈述与奇幻想象常常并存于同一文本。《飞访木星》里虽有关于流星现象、天体力学的科学解释,但向陨石灌注电力就能使它摆脱其他星球的引力却绝非科学方案。《新法螺先生谭》虽对金星的描述颇为离奇,但也夹杂着月球围绕地球运转、不同星体各有运行轨道等科学解说。一种维度又常常分化出多个小维度。如晚清小说多将外星视为理想飞地,可外星的理想却各有妙处,理想的不同又与人物交相辉映,成为人物性格、背景的解说。同一个月球,在性格怯懦的儒生龙孟华看来就是逃避之所,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可能免受人间疾苦,而在性格坚毅的科学家玉太郎看来,月球则是科学世界,科技水平远远领先于人类社会。同样是去行星探险,科学家博士是为了破解星际奥秘,将陨石送归太空,政治家黄震球则要去寻求文明密码,解决因物质丰富引发的精神空虚。
值得注意的是,《月界旅行》《新法螺先生谭》等,在近代均被命名为“科学小说”,正是对古代白话小说以“消闲”为主旨之观念的反拨。鲁迅《月界旅行·辨言》云:“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虽然能吸引民众之兴趣,但是却很难给予他们科学的助益。如果说鲁迅翻译《月界旅行》的目的是“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那么,当这些以外星叙事为主旨的科学小说出现时,其作者考虑的恐怕也正是要改变民众“智识荒隘”这一现实吧。
二、借助外星反观地球
古代中国典籍中并没有“地球”这一词语,与“地球”指称大致相当的是“地”。在中国的传统认知中,“地”总是阔大无边的。《管子》有云:“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山海经·中山经》也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尸子》认为“太极之内有君长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指明所谓“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是夏禹统治的地方,只是地的一部分而已。《春秋纬·命历序》所指之“地”大至“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吕氏春秋》则将数字放大为“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古籍中有关“地”的数字表述并非实测结果,只是为了突出地之阔大的夸张修辞,数字越大,越能证明古人经验观念里地之阔大。
近代之后,知识者基于考察已能科学地认识地球,甚至能做出各类环绕地球的旅行,已经突破了古人“地大”观念之局限。《小孩月报》载《乘轻气球游地球说》云:“任他升腾,渐升渐高,一直升到云外,往下一望,地上山川城郭,一目了然。御风驶行,顷刻千里,就可以看得见地球上有三分水、一分地。”在乘坐人的视野里,地球由大变小,这并非是地球发生了变化,而是观察者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小说中亦有这样的观察者,虽然脱离不了虚构的特征,但既然民众都已经知道“乘轻气球游地球”,小说家们将这一题材引入文中也就不奇怪了。所以,《法螺先生续谭》中有“瞩我向所仆缘之地球,仅似一丸梅核,以灿丽于太空”之言,《新法螺先生谭》更说:“余细察行向,知已闯出地球轨迹之外,遥视地球,如盆子口大小,一片光亮,隐隐有些黑影,想即是出岛、海洋,较之地球上望月,正是一般。”
考察晚清小说中的外星叙事,小说家们站在地球之外反观地球,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叙事者多有清晰的比较意识。叙事者倾向于让他的主人公发现地球并非宇宙之间的唯一存在,地球之外还有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慧星等,并通过主人公的游历,借助人物好奇的目光捕捉地球与外星之间的差异。《新法螺先生谭》中,当“余”的灵魂之身与水星成一直角时,“余”并无惊惧,反倒庆幸“正可细心考察,比地球有若干差异之点”。法螺先生与水星只是擦肩而过,所见所述都还只是浮光掠影。《月球殖民地小说》里的龙孟华、玉太郎等人与“月世界”里的人有了深入接触,他们对地球与“月世界”之间差异的发现就不只是地形、物种、植被、技术、制度等,还出现了地球人与外星人的差异。“月世界”居民知识程度极高,十几岁的孩童就已经掌握了完备的天文知识、科学原理。“月世界”居民也有高尚的道德,库惟伦等人乐于向地球人龙必大传授知识。当龙必大想回归地球时,库惟伦等人也充分尊重龙必大的选择,即便难分难舍也不做刻意强留。虽然上述外星与地球的不同之处基本上还是以地球为原型的虚幻想象,但小说如此表述足以说明晚清士人已然意识到地球并非宇宙中心。
其次,叙事者对地球的判断也逐渐分化。在不同的小说里,叙事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地球与外星的优劣强弱做出不同的判断。《月球殖民地小说》借玉太郎之口判定地球明显落后于外星。玉太郎原本以强国子民自居,可与先进的“月世界”进行对照之后,他幡然醒悟:“这个强国的步位,算来也靠不住的。”玉太郎由月球发达联想到:“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的文明种类,强似我们千倍万倍,甚至加到无算的倍数,渐渐的又和我们交通,这便怎处?”此种紧张情绪一方面打消了玉太郎夜郎自大之心,另一方面也使他产生了苦恼与虚无,他感慨“人生在地球上面,竟同那蚁旋磨上、蚕缚茧中一样的苦恼”,也怅然“究竟那英雄豪杰干得些什么事业?博得些什么功名?不过抢夺些同类的权利,供自己数十年的幸福”。并不是所有晚清小说叙事者都认为地球弱于外星。《新法螺先生谭》的叙事者就认为地球与其他星球是平等的,因此法螺先生在观看水星“造人术”时毫无忧虑惊惧,只是想到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将此引入中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重返地球,能在上海开办改良国人脑汁的公司,使这一技术为中国所用。《新法螺先生谭》的叙事者有时也认为地球胜于外星。当法螺先生发现金星上仅生活着低等动物,尚未有高级文明时,甚至认为自己或有可能成为金星上的人类始祖。上述各有侧重的判断说明因外星出现,叙事者对地球的认识已有差异。
最后,叙事者多赞同建立地球与外星之间的交流。叙事者常常借开辟星际航路的情节探讨地球与外星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月界旅行》中,枪炮会会长视建立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航路为“大目的”“大事业”,并且推崇这“大目的”“大事业”伟大如“哥伦波发见我邦一般”。《新法螺先生谭》中的“余”也认为建立太空航路当属人类创举,如能实现则“虽有十哥仑布,不能与余比美,余于此亦足自豪矣”。然而,会长与“余”建设星际交通的愿景一致,动机却存在微妙差异。会长以扩张国家版图为已任,他发动社中成员时特意强调,开通地球至月球航路以拓展本国疆域为目的,是要“把我合众三十六联邦版图中,加个月界给大家看”,含有征服甚至是吞并之意,因此小说中也时时夹杂“殖民”“人定胜天”等说辞。在受此思想影响的地球人的想象中,月界居民会以大礼迎接地球使节。“余”所追求的则是地球与外星合为一体,含有平等共存之意,因此“余”的规划里不仅包括地球与外星之间的航路,还包括外星与外星之间的航路。目的虽有不同,但重视地球与外星之间的交互已是不争的事实。
卡林内斯库在谈及现代性特征时,引用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话说:“现代时代是一种脱离……它忠实于其起源,是一种持续的脱离,一种永无止境的分裂……我们在他性中寻求自己,在那里找到自己,而一旦我们与这个我们所发明的、作为我们的反映的他者合而为一,我们又使自己同这种幻影存在脱离,又一次寻求自己,追逐我们自己的阴影。”卡林内斯库把它称作是“反对其自身的传统”的现代性。晚清小说中的反观地球也可做此解释。由于外星的加入,地球被重新定位,进而言之,中国亦被重新定位。魏源《海国图志》提倡:“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亦说:“今则环球通达,天下为家……即当合万国论之。”客观地说,小说中的外星与知识话语中的外国、外国人有着同构的功能,小说家们借助外星言说地球,其实也是在世界中重建中国的位置。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种“忠实于其起源”的“持续的脱离”,那么,地球人借助外星反观地球的做法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又一次寻求自己,追逐我们自己的”现代实践行动。
三、末日之思
1872年10月3日,《申报》报道了一则关于地震的消息:“昨八月二十九夜十一点钟,地复微动,约一二分时候。再闻近来十余夜西北角四更后现彗星一,有三角光芒。往上云此事,据西人所言,则谓彗星亦有轨道,无关灾祥。”彗星能否给地球带来灾害?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热点话题。《字林沪报》载《辩奥博士论彗星毁地球人物说》引奥地利维也纳博士云:“彗星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与地球相触。舆虽能存,地面人物必为彗星热汽烧毁,人物俱亡。”范曼伯在回答“彗星将触地球,人物必罹难”是否属实的问题时说:“余生不过数十年,闻地球将为他星撞毁之说,已经五次。”梁启超译《世界末日记》叙述太阳失却热力,地球逐渐毁灭。包天笑所作同名短篇小说《世界末日记》也呈现因太阳光消热尽,地球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情形,并增加了月球撞击地球的情节。心一创作的《黑暗世界》则描写一颗不知名的流星悬于日地之间,阻隔太阳光线,使地球陷入无尽黑暗。当流星移动,人们以为地球得救时,流星却撞上地球,使地球毁于一旦。吴趼人《光绪万年》写慧星与地球擦肩而过,巨大的冲击力改变了地球原来的昼夜寒暑。
外星究竟能否撞上地球,这本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家对此已有回答。但是对于刚刚觉醒的晚清知识者来说,情况或许更为复杂,晚清小说中的外星叙事常常描述外星撞击地球所引发的灾难。首先,外星破坏了地球原有的自然规律。梁译《世界末日记》极力渲染地球因太阳热力衰减而遭遇的极寒天气。气温急剧下降以至于寒带不断延伸,南北极几乎与赤道重合。原本水量充沛的亚马孙河也逐渐成为冰河,昔日繁华的欧洲完全被冰雪掩埋。心一所作《黑暗世界》则描述因流星遮挡太阳,昼夜交替不复再现,地球陷入漫漫暗夜。失去阳光的照射,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原本鲜红的苹果成了淡绿色,原本翠绿的蔬菜成了白色。吴趼人的《光绪万年》全写颠倒,南北半球对调,梅花在六月盛开等反常现象频频出现。其次,外星瓦解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自然异常势必引起人们生存方式剧变,原有的社会秩序随之分崩离析。梁译《世界末日记》写极寒造成人类繁衍难以为继,人们因此再无求知动力,也无发展要求,人与人之间交流不断减少,世界活力不再。《黑暗世界》主要写法律失效,道德涣散。伦敦陷入长久黑暗之后,犯罪事件频频发生,因法律已无约束力,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罪犯,民众成为暴徒,社会普遍陷入混乱、失序之中。最后,外星将会毁灭地球。小说常常用大量笔墨,从不同角度刻画地球灭亡的瞬间。梁译《世界末日记》用寂寂无声表现末日荒凉。故事终结于人类都已死去,文明荡然无存,失去人类的地球兀自运行,光热殆尽的黑色的太阳仍悬于太空,使读者苍茫寂寞之感油然而生。包天笑《世界末日记》以喧嚣写末日惨烈。当月球撞向地球,风声、浪声、撞击声、嘶喊声此起彼伏,“凡入于耳者,无非惨厉之音,令人悲咽”。嘈杂之声正可见出人的失措无助。《黑暗世界》则极尽叙述之能事,一波三折地写地球末日的来临。先以黑暗使人绝望,又借短暂的光明给人希望,最终在人希望重萌之时,让流星撞击上了地球,以“已而砰然一声,流星与地球相触,陷入撒哈拉沙漠者数百千里”结束全文,给读者留下了因果无端、意犹未尽却不得不戛然而止的遗憾。
晚清小说之所以细致摹写地球受外星影响走向“末日”的历程,其目的在于写“末日”对人情绪、精神的影响。置身于地球的“末日”巨变之中,人们不得不从原本稳定、安适的环境中陡然转向未知、危险,普遍感觉到了恐慌。从听闻地球即将毁灭开始,人们就因不知自己肉身、思想将寄托何处而陷入焦虑、忧虑之中。包天笑在《世界末日记》开篇即混合叙事者与人物的口吻,发出“呜呼!太阳灭亡,全地球之人类,归于何所?凡仆缘大地者,咸思我之住所何存?我之运命何系?”的哀叹。《黑暗世界》充斥着“慑惧”“怖极”“大骇”“怖惧已极”等字眼。小说也写人们因恐惧而来的狂欢,既描摹群像,呈现人们走上街头,靠破坏宣泄绝望的暴乱场景,也做人物特写,描写雷煤德伯爵之妹与意色白公爵尽情共舞以及时行乐逃避灾难迫近的情节。特别是小说通过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了二人围绕末日将临、人将何去何从的一番对话,道尽了人绝望疲惫的末日之感。恐惧之外,人们也因文明尽毁而感到虚无。三部小说都将叙事空间置于繁华之都。梁译《世界末日记》中被冰雪掩埋的罗马、巴黎、伦敦、维也纳、纽约等,都是曾经的名都巨府。包天笑《世界末日记》中众人讨论月球撞地球的同盟会议所就建在东西大陆之中心点,巍峨壮阔,足以容纳一亿万人,却无法逃脱化为齑粉的结局。心一虽是中国作者,却将《黑暗世界》的地点定为伦敦。末日惨剧上演于繁华之都,营造出了层次丰富、效果显著的对比。其中既有昔日繁华与末日疮痍的对比,越是写文明的繁盛发达,越能见末日的破坏彻底,又有文明理性与灾患无端的对比,末日的来临看似是科学预测,实则也是偶然或是宿命。两重对比叠加,常常使叙事者徒生“一向经营,全归泡影”、“今日全地球只赢得雪中一大荒冢而已”的怅惘。
晚清小说之所以写外星引发地球“末日”,除受近代天文学输入的影响,也与西方的世纪末思潮有关。梁译《世界末日记》就来自于Flammrion的日译本《世界の末日》(德富芦花译)。包天笑《世界末日记》虽名为创作,却也有可能与Newcomb及其日译本《暗黑星》(黑岩泪香译)之间存在着联系。上述晚清小说中的“末日”情境、“末日”情绪,与西方的世纪末思潮多有相似之处。但晚清小说的“末日”情绪并非一味模仿,也有其独特之处。晚清小说一方面写地球困境、文明毁灭,一方面写人类没有一味地坐以待毙,即便明知灭亡在即,也仍然不懈寻找新生,使小说往往在绝望之中仍透露隐约希望。人们或寄希望于先进技术。梁译《世界末日记》中幸存的人类决定造飞船,派出探险队去寻找能够繁衍生命的女性。包天笑《世界末日记》里出现少年物理学家,在众人沮丧之时振臂高呼,提议造新式飞船,将人类运载到其他星球之上。还有人献计,可利用杠杆原理撬动地球,使其飞逸太阳系统之外。技术之外,人们对制度也有期待。包天笑在《世界末日记》里成立“新世纪建设同盟会”,汇集各阶级议员与科学家共同探讨地球出路,小说多为人物宣言,颇有各抒己见的民主之风。然而无论技术还是制度,都无法将人类带出末日泥沼。飞船即便造成,也还是无法扭转地球极寒的趋势。庞大议会也只是众声喧哗,议员们多是自说自话,根本于事无补。当技术、制度于事无补之际,小说也常常提出精神救赎的方案。此一方案虽无法使地球逃脱毁灭的命运,却可抚慰人焦躁、绝望的情绪。梁译《世界末日记》中,借少女爱巴劝慰爱人阿美加的言语开导读者放下生死执念:“爱根终当断绝,爱根终不得不断绝。”译者更是在故事之外现身,以注解的方式提示读者应以拈花微笑的心态来释放悲喜:“以全智全能者之慧眼,微笑以瞥见之‘爱’之花尚开。”包天笑《世界末日记》则安排天文学家向众人报告,地球灭亡已无可挽回,但他从进化论角度将灭亡解释为“进化之一现象,蜕旧易新而已”,因破毁之后还会重生,那么此时的恐惧也就不再可怕了。
如果将地球自比,那么地球的末日也就意味着自我的死亡。竹内好在谈及现代主体的建构时曾这样说:“个体不是通过掠夺其他个体而支撑自身,个体必须在自己内部产生出通过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个体的立场。……只有通过行为,只有依靠自我否定的行为,创造才会发生。只有以行为支撑的观念才是真正的观念。”在竹内好的语境里,一个没有经历过否定的自我是很难成长为现代个体的,这是他从鲁迅的身上所体验到的后发性国家现代性发生的方式。清末小说中的外星叙述对于外星毁灭地球的重视,也正蕴含着中国独特的经验,小说家一方面要尊重新知,却又不能完全依靠它来建构自我,这是一种交织了传统个体成长为现代个体的那种集希望与绝望于一身的情绪表达。就此而言,它们所传达的体验是真实的,也是现代的。
结语
晚清小说中的外星叙事是现代知识如何修正小说家知识结构、观念立场以及表达方式的真实体现。晚清小说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效果,与西方科学知识在晚清的大力输入密切相关。小说中的外星书写不仅渗透着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也混杂着物理学、数学、化学、医学、天演论、进化论等诸多现代知识。现代知识的输入为晚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对象,更重要的是现代知识改变了小说家对于外星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晚清小说家们逐渐在西方近代天文学发展的脉络中认识到宇宙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他们不仅借此“宇宙”空间重塑“中国”形象,更由此产生了蕴希望于绝望的现代情绪。
当然,晚清小说家依然留存了中国固有的格物致知的思维模式,不时地将形而下的“科学”引申为形而上的“道”,即是其最典型的表现。《新法螺先生谭》明明讲述太空冒险,但叙事者在结尾时有意或无意地将此命名为“余之历史”,将科学概念换作了“历史”。梁启超译《世界末日记》也在结尾处指出,翻译此作的目的是“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此文”。这些有意或无意的文本表现说明,在晚清小说家的心目中,现代知识固然刺激,但形而下的“知识”若不引向形而上的“历史”“哲学”,其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一方面接受现代知识,另一方面却又不放弃传统观念,正是居于过渡时代的小说家们知识结构的特有表现。这正是晚清小说外星叙事的复杂之处,它们所展现的知识可能是现代的,可是所表达的观念却又恰恰是传统的。如此交织着现代与传统的叙述,正是此一时代精神的真实反映,这是这些小说的复杂之处,也是它们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