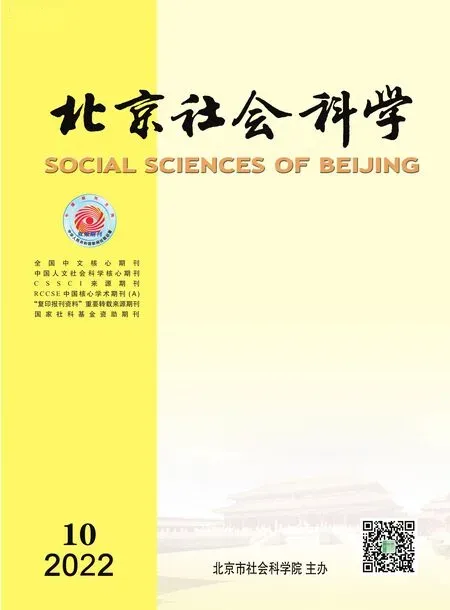运河与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
王建伟
运河是一项庞大的、跨流域的复合水利工程,在中国,运河的发展也是一部政治演生史,其兴衰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环节。北京地处中国版图的东北位置,从一个北方地区的边地军事重镇,至元代跃升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随后的明清两代仍然保持国都地位,这其间运河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其转捩之机,皆在于运河”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争战催生出运河的出现。隋唐之前,北京是中原王朝经略北方地区的军政重镇,长年驻扎大量军队,军事色彩浓厚。但一方面受地理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因其处于农牧交界地带,常受北方游牧民族侵扰,北京地区农业产量有限,无法为当地驻军提供稳定而充裕的粮草军需。
东汉初年,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太守王霸利用水路向北京地区输运粮草,这是史籍中较早出现的明确记载。东汉末年,曹操为征伐乌丸,平定辽东,先后开凿平虏渠和泉州渠,以短程渠道沟通天然河流输送军需,从而使军粮可以从南向北通过船只直抵幽州城下。这是第一条专为打通北方物资供应渠道而开凿的人工运河,此后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仍断断续续发挥作用,为后来的隋唐大运河的通行奠定了初步基础。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大规模征讨高句丽。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至涿郡(治今北京西南),向辽东运送士兵与粮草。幽州成为中原政权向东北方向开展军事活动的重要基地及物资中转驿站。隋唐时期是北京历史上的大转折时代,由于永济渠的开辟,北京第一次与江淮地区建立了相对便捷而稳定的水路交通。从地理意义上说,北京不再是一个完全孤悬塞外的“端点”,其在地理空间上的“边缘性”因大运河得到了明显修正。在此之前,北京因其特殊的战略位置,主要是作为中原王朝统御北方的军事边镇,对于王朝政局的整体影响比较有限。唐朝初年在边镇地区设立五大总管府,北京是其中之一,区域地位不断提升。
唐末安史之乱引发五代军事混战,但从幽州联通中原的运河没有完全中断,中原王朝仍然可以通过运河维系对幽州地区的统治。辽金时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已经转移至江南,先前的政治中心关中地区与中原腹地陷入持续衰落,原本一直处于中原王朝边缘地带的幽州进一步崛起,相继成为辽、金两个北部中国政权的陪都或国都。城市角色与功能的变化及人口的增加对物资供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运河成了无可取代的水上运输动脉,辽、金两朝都把完善运河系统作为站稳北方、进军中原的重要依托。
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称中都。以此为标志,北京正式成为北部中国的政治中心。海陵王在迁都之前就组织开凿以燕京为中心的人工漕渠,并于天德三年(1151)将漕运枢纽潞县升格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后来又为扩大水源,引卢沟河之水入运河,并开通闸河连接通州到中都城。北京政治地位得到不断提升,运河功不可没。
经过数百年分裂之后,元代再次形成大一统王朝并将国都置于北京,国家的政治中心正式由关中转移至华北平原,此后延续近七百年,“其转捩之机,皆在于运河。”正是因为大运河的存在,国都的确定与迁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进而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
政治中心的确立也可以改变地理条件,把原本处于“边缘”的地带变成“中心”。北京虽然地理位置偏北,但自元代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之后,通过国家政令,利用陆路与水路,构建起一套辐射四方、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提升了中央政权对全国范围内物资流通与军事力量的调配能力。
作为政治中心的元大都与作为经济中心的江南相距甚远,元朝政府重启大运河系统。新开通的会通河采取“截弯取直”的方式,从大都起,直穿山东、江苏全境,径抵江南。这条线路设计虽然可以缩短南漕北运的距离,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也意味着要与黄河、淮河、长江三大自然水系的流向对抗,同时还需深入到南宋初年黄河改道之后已成一片泽国的两淮地区。明人丘濬对此评价说:
运东南粟以实京师,在汉、唐、宋皆然。然汉、唐都关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势,中间虽或少假人力,然多因其势而微用人为以济之。非若会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创为之,非有所因也。
实际的情况是,终元一世,这一庞大的工程也未能完全竣工,但却为之后明清两代长期沿用的京杭大运河线路奠定了基础,这也可以视之为元代运河的历史贡献。
明代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前后,先后两度重新疏浚元代的会通河,并继续以高昂的成本维持其运转,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与富庶而遥远的江南再次连接。明代对大运河百余年的治理,是确保明、清两代500余年大运河繁荣的重要措施。
二、“天庾正供”的生命线
国都是消费重镇,皇室、勋戚、官宦、富商大贾等形成了异常庞大而高端的消费群体。北京在元代第一次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各项物资消耗呈几何级数上升。但北京偏处中国版图的东北,区域内部也并非以物产丰饶著称。不仅本地的粮食产量远远无法承担京师之地的各项消费,而且很多物资在精致程度方面也无法满足国都人士日益增长的需求,仍需倚靠江南供应。《元史·食货志》对此有详细描述:“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发展至明代,这种状况也未得到明显改善,“京师之地,素称瘠土,衣食百货仰给东南,漕河既废,商贾不通,畿甸之民,坐受其困”。
元代海运虽然比较发达,但仍投入了巨大人力与物力疏浚、改造隋唐运河旧道。至元三十年(1293),由郭守敬设计、连接大都和通州的通惠河建成,至此,经河道或海道北上的南方漕船经由通州溯流而上,直抵大都城内。终点“海子”(今积水潭—什刹海)码头呈现出桅杆林立、千帆云集、“舳舻蔽水”的繁荣气象,天南地北各种各样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水上“漂”来,浩浩荡荡的船队载满漕粮和各地物产穿行大都城中,既造就了商业的异常繁盛,也营造了万邦来朝的宏大场景。
元代每年经由大运河输送的漕粮约为几十万石,至明清时已经增至四五百万石。明代规定,漕船除运载固定的漕粮外,每船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土特产)随船售卖。江南大量的财政贡赋源源不断地运到京师,维持着中央庞大官僚机器的运转,北京的城市生活也因丰富的外来商品而更加充盈,甚至远达广州的商品也能出现在京师的市场上,“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
明初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之后,开启了大规模的城市营建。新建宫殿、陵寝、园林、坛庙需要大量木材,且对材质要求很高,这些木材多从四川、湖广、云南等地采伐,通过运河输送而来,即所谓“皇木采办”。砖瓦是又一项大宗建材,主要烧造地是山东临清、苏州等地,临清烧造城砖,苏州烧造金砖,同样需要利用漕船顺带。相对于元代,明代对运河的依赖程度更高。
明代大运河对于北京的物资保障作用不仅在于满足达官显贵的奢靡消费,更重要的是将漕粮输往北方长城沿线的边防要地。所谓漕运的“国用军需”,一方面特指供养京城的统治阶级和管理机构,另一方面则是满足军事所需。元代末年,蒙古族统治集团放弃对中原的统治,元顺帝退守漠北,形成“北元”,和明朝对立超过百年。明朝开国之初,多次派遣以骑兵为主的远征军追击北元残部,同时在北方长城沿线长年驻扎重兵。为解决由此带来的粮草、装备等方面的需求,明廷一方面在北方边地实施大规模的军事屯田,另一方面则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输运漕粮物资,双管齐下,以维持基本的兵丁粮饷及日常补给。明朝官员描述:“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运河对于巩固北京的政治地位,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清朝定鼎北京,官吏实行汉满双轨制,中央机构更加庞大,尤其是驻守京师的八旗驻军及其家属均需朝廷供养米粮,京师对粮饷及各项物资的需求远超过前代,解决办法仍然是依靠运河。朝廷每年从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征收钱粮和白银,运贮北京通州各仓,以供皇室食用和王公官员俸禄及八旗兵丁口粮。清初学者孙承泽在所著《天府广记》中总结道:“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清代通州学正尹澍目睹漕运盛况,曾赋《万舟骈集》诗:“天际沙明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虽带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其写实意义也不能忽视。
三、“治水者,治天下也”
德国人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在其《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东方专制主义往往呈现为“治水帝国”(Hydraulic Empire)的形式,治水行为本身可以成为控制和动员社会资源的工具。在这里,魏特夫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不能仅仅从交通、物流等直观功能来界定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更需要从政治因素挖掘大运河开凿背后的动力,“治水者,治天下也。”
总体而言,运河的走向、分布与中国政治中心的变动轨迹基本吻合。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之下,国都的确立与迁移对于运河的建设具有直接影响。在北宋之前,王朝政治中心主要位于关中地区,运河也多沿今西安—洛阳—开封这一轴线移动,大致呈东西走向;宋辽金之后,北方地区逐渐崛起,北京逐渐发展成为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则转至江南,元明清时代的大运河呈现南北格局。但无论如何变动,大运河两端连接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基本规律不变。
大运河在本质上是一条政治河。元朝定都北京之后,其物资供应虽然有相对发达的海路运输做保障,但仍投入了巨大的成本疏浚隋唐以来已经淤积的旧河道,重新规划修缮运河。明清两代的漕运制度更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维持漕粮河运、修浚运道,设置职官、修造漕船、设置屯田等都是极大的开支。如果仅从经济因素上考量,已经无法解释中央政府的这一决策。所以,考察运河不能仅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
元明清三代均建都于北京,这一孤悬华北、缺乏呼应的地域,正是由于大运河的存在,构筑起一套水运交通系统,强化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大区的联结纽带,一方面可以汲取各项物资资源,源源不断地将南方的财富输往京城,国都的各项职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借助这条通道,中央建立起便捷的信息收集系统,可以及时捕捉南方各地的社会动态,而且有利于政令的通达。大运河调剂了天下资源,支撑了都城北移的格局,中央政府虽然远在北方,但其触角无处不在,能够对广土众民进行有效管辖与控制。南北之间的频繁往来有利于增强南方对中央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国家政权的影响力渗透到运河沿岸各地,北京原本在地理区位及经济环境方面的缺陷通过大运河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运河之于一个政权,犹如血管之于人体,血液的良性流通有助于身体健康,同理,运河的高效运转不但可以保障政权的稳定,同时也是政权统治力量的具体表现。认清了这一事实,就可以理解明清以来中央政府对运河运转的持续巨量投入,同时对运河的政治属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运河甚至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压舱石。
自秦汉以来,建基于中原的王朝断续地进行着两项宏大工程,一项是在北方修筑长城,另一项就是开凿连接南方与北方的运河,北京正好位于两项工程的相交点上。有一种比较形象的比喻,长城犹如矗立在北方边地的“巨型盾牌”,大运河则是中原地区向北方插入的一把“长矛”,二者密切配合,构成了一个稳固的防御阵型。尤其是在明清时代,大运河为明长城防御体系及清朝控制塞外疆土提供了重要的后勤补给,是保障两朝各自长达两百多年统治的基础性战略工程。运河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经济意义上,更体现在政治意义上。
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大运河无疑是联系中国南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进入清代后期,黄河改道与太平天国战乱成为大运河的重要破坏性因素,衰弱的国力无法为运河治理与运行提供充分的政治与经济保障,大运河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也是在同一时期,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强势冲击,西方文化逐渐渗透,上海、江浙等地凭借口岸的地缘优势成为接收先进知识与西方思想的前沿,不仅经济优势不断凸显,在政治及思想文化等方面也开始挑战国都的地位。清末,蒸汽火车、现代轮船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兴起改变了原来的经济地理格局,彻底颠覆了大运河作为南北运输主动脉的地位。此时,清政权奄奄一息,北京作为国家中枢的地位不断弱化,各种因素叠加,大运河故道逐渐淤积,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