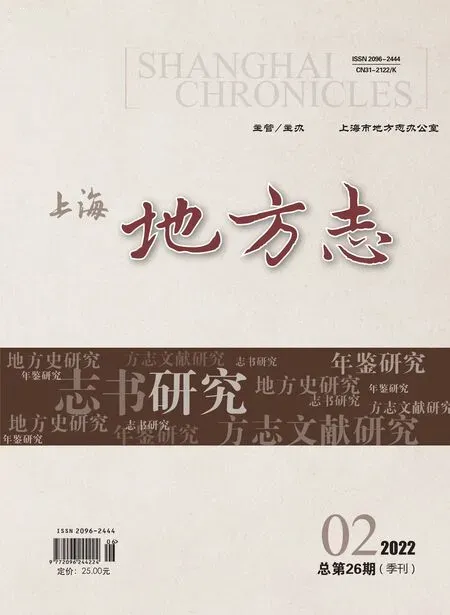儿童社会化中的宗教:上海广东浸信会日光会的宗教儿童观与儿童宗教教育
苏志伟
1960年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一书的出版,开拓了关于儿童观念演变研究的新领域。时至今日,儿童观研究已经成为儿童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关于中国近代儿童观的研究,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儿童的历史,对于当下认识理解儿童和改进儿童教育都有着重要意义。国内关于中国近代儿童观的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包括儿童观的演变、中西儿童观比较、儿童观与近代教育学等的关系、重要历史人物的儿童观等方面。在这些研究中,儿童或被视为一个整体,或被分为男女童进行比较,对于一些特殊的儿童群体却缺乏充分的研究。教会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中特殊的存在,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对儿童群体也多加关注,以往对这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教会的慈幼事业,对于教会的儿童观和儿童宗教教育关注较少。本文试以上海广东浸信会所属日光会为例,探讨宗教儿童观的内涵和儿童宗教教育的内容,关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宗教因素的影响。
一、上海广东浸信会日光会简介
上海广东浸信会下属的日光会,是由上海广东浸信会设立的,以崇德女校附属小学的儿童学生为对象,进行宗教教育活动的团体组织。上海广东浸信会于1905年4月30日成立。1905年,汤杰卿牧师创办明德男女学校,1910年,在该校基础上建立崇德女校与仁德义校。教会学校的建立吸引了大量儿童和青年入学,正是在崇德女校发展的过程中,日光会被建立起来。
在浸信会内部,本身就有少年团的组织,浸信会少年团的组织制度为四级,分别是高级、中级、初级和幼稚级。其中“幼稚级就是日光会,是由六岁至九岁的孩子们共同组织的”。上海广东浸信会下属的少年团成立于1926年3月,但日光会的活动在崇德女校附属小学发展过程中早已开始。附属小学在1905年明德男女学校成立时便已创设,直至1920年增设幼稚园“而完全小学乃大功告成”。在附属小学发展的过程中,日光会被作为课余活动嵌入到小学教育之中。广东浸信会在初小各年级和高小一年级都设有日光会,并将年龄限制放宽,使得六岁至十岁的儿童皆成为日光会的活动对象。各级的日光会都设有会长、书记、司库职务,并将儿童分为四队,各设有队长。在实现儿童自我管理的制度上,另配有教员作为引导,称为“日光会领袖”,日光会领袖一般由深谙宗教知识的女性基督徒担任。在日光会领袖的引导下,定期于每周星期六上午十时至十时半举行日光会聚会,开展儿童宗教教育活动。
二、“儿童的发现”与宗教儿童观
(一)近代中国“儿童的发现”
“儿童教育总是以一定的儿童观为前提的”。所谓儿童观,是人们对儿童的根本看法与态度。“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现代儿童观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并基于自身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逻辑而被逐步发现的”。传统中国社会中,儿童是成人的附庸,儿童被当作“小大人”,在传统伦理纲常的约束下,成为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工具。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影响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开始反思对儿童的认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发出了儿童改造的宣言。清政府曾颁布《癸卯学制》,制定《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提出“保育教导儿童,专在发育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使之远于浇薄之恶习,习于善良之规范”的教育目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潮迎来高潮,五四时期“人的发现”也呼唤“儿童的发现”。这一时期,在欧美各国,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潮蓬勃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广泛的影响。杜威来华讲学,他认为儿童教育应该从以教材和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儿童为中心,即“儿童中心主义”。杜威关于儿童教育的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周作人《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提出了“儿童本位”的儿童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中也发出“幼者本位”的号召。1919年起,上海青年会、女青年会等团体掀起了儿童健康运动。1927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成立后,上海市的儿童卫生运动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1935年8月1日,召开全国儿童年上海开幕典礼。儿童愈发引起社会的关注。
(二)日光会的宗教儿童观
虞永平认为儿童观有三种形态,分别是社会主导形态、学术理论形态、大众意识形态。宗教儿童观也是大众意识形态儿童观的重要一面,并深受社会主导形态儿童观和学术理论形态儿童观的影响。五四时期提出“儿童本位观”的同时,也推动了国民政府对儿童的关注。民国政府支持中华慈幼协济会的工作,成立童子军和设立四四儿童节,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下,试图将儿童塑造为救国图存的希望和新一代国民。但作为宗教组织的日光会,其宗教属性又决定了日光会儿童观与其他儿童观具有本质的区别。
1.儿童定位:上帝附庸与儿童中心
日光会儿童观的核心是将儿童放在上帝的附属地位,这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圣经》中全能的上帝耶和华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基督教倡导神性,大肆宣传神道主义、蒙昧主义、禁欲主义,用对上帝的认识代替对人的认识,以对上帝的无限信仰为基础解释人性、人道、人的解放和尊严等问题。把人当作上帝的附属物,认为神性的存在决定了人性的存在,而人性的存在,恰好证明了神性的先知和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无限能力”。在这样的神学传统下,儿童也无法剥离对上帝的依附。日光会的使命是把儿童培养成基督的信奉者、传道的小助手、教会的小信众,“使儿童及早将自己献给主用”。
在日光会的宗教儿童观中,儿童天然是上帝的附庸,是上帝的小子民。以此为前提,日光会将儿童放在一切活动的中心位置,类似于“儿童本位观”中以儿童为本位进行一切教育活动。日光会的聚会,除日光会领袖外,其余皆为儿童,并将儿童分为四队,设有一定职务,要求儿童自我管理,发挥儿童的主动性。
2.儿童权利:童年价值、主体发展和男女平等
中世纪的宗教儿童观认为儿童是有原罪的,因为人生来就是罪人。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后,“儿童原罪”的观点越发得不到认同。受到五四时期“儿童发现”中对儿童合法权利承认以及《新约》中对儿童论述的影响,日光会否定儿童生来性恶,反而将儿童看作是最宝贵、最纯洁的存在。日光会领袖所秉持的观念是“神给我们特殊的权利和福气”,使她们能与儿童接触,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成为其儿童观的重要内涵。
日光会承认儿童童年的价值,在聚会中安排充足的游戏和娱乐时间。在聚会讲课时间结束后,日光会便成为了儿童的游戏天地,仅在日光会的活动教材《日光会秩序》中明确列出的游戏就有15种,还有其他各种出游踏青的活动,日光会还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特点,设计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活动。其次是推动儿童德智体协同发展,智识的增长更多的是对宗教知识的把握和灵性的培养,手工和游戏活动锻炼了儿童的体力和智能。最后是培养儿童主体性力量,在以儿童为中心的活动中推动儿童自我管理,在讲课中注意儿童的主动提问,发挥儿童自我主体的力量,承认儿童是主体精神的个体。日光会尊重男女平等,保护女童的权利。日光会的儿童基本为崇德女校附属小学的学生,全部为女童。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中,女童的权利基本无法保障。崇德女校和日光会为女童教育创设了场所,为女童的未来提供了新的可能。
3.儿童责任:家庭、教会和国家
在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基础上,日光会强调儿童宗教责任的承担。与社会主导形态下民国政府希冀儿童成为救国图存的希望不同,日光会更多地培养儿童在宗教方面的责任意识。对于家庭,希望儿童“帮助父母,做自己所能做的事”,反对将儿童摆在家庭的私有物地位,认为儿童是家庭的一员,是家庭的重要力量,希望儿童能带自己的父母来守礼拜、参加主日学。对于教会,日光会每次聚会都有捐款活动,“他们将买零食的钱储蓄起来捐助”,“日光会当把一年中所认定的捐项捐足”,用以帮助上海广东浸信会的发展,实现经济自立。对于国家,日光会也把儿童视为救国图存的希望,只是这里的“国”是“基督中国”。近代教会势力在华传教的终极目标就是变中国为“基督中国”,儿童也应当承担起传教的责任。日光会倡导儿童“带人到主日学守礼拜”“搜集主日学画片,制成画本,送给贫民医院里生病的孩童”“沿路分送布道传单”。儿童成为教会的小传道人。
日光会的宗教儿童观,将儿童当作上帝的附庸,在“儿童本位观”的影响下,把儿童置于宗教教育的中心地位,肯定儿童的童年价值,保障儿童的发展权利,维护女童的合法权利;在把儿童视为救国图存希望的社会主导形态儿童观的影响下,将儿童视为传教事业的未来,强调儿童对家庭、教会和“基督中国”的使命和责任。
三、日光会的宗教教育活动
在宗教儿童观的指导下,日光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教育活动,把从小培养基督信徒,贯彻宗教教育作为自己的任务。
(一)以儿童为中心、宗教为归属的教育方针
儿童因其心智和身体的不成熟,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在责任意识、奉献精神、丰富学识要求下的日光会领袖,力图从儿童自身、家庭、日光会、教会四个层面,将儿童带领到神的面前,成为合格基督信奉者。对于儿童自身,培养具有良好宗教道德的儿童;对于家庭,要求儿童积极帮助父母;对于日光会,需要儿童辅助日光会的发展;对于教会,教授儿童宗教知识,在外辅助传道。在多层次的宗教教育下,将儿童培养为一个个基督耶稣的“小日光”去普照万方,成为基督教新的生力军。
(二)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日光会的活动主要是定期的聚会,每星期聚会一次,每月4次,一年48次。另有野外旅行和联欢会的活动。每次聚会秩序固定,活动众多。
日光会的每次聚会都有明确的中心题目,聚会的核心活动是日光会领袖讲述故事,故事的题目就是聚会的主题。所有讲述的故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圣经》中的宗教故事,二是介绍别国儿童情况的普及类故事。日光会领袖将《圣经》章节内容改为通俗化和简单化的故事,使儿童易于理解,如在1933年1月的第三次聚会上,用生虫的苹果比喻罪恶在人心生长,教导孩子孝顺父母、守安息日、做礼拜。部分深奥的故事还会以月为单位,将故事拆分为多个部分讲述。普及类故事多介绍别国儿童的生活状况和各国的风俗,如1933年4月份第四次聚会讲述了葡萄牙儿童的生活和葡萄牙农民的生活状况。这类故事在拓展儿童眼界的同时,往往要求儿童为别国儿童祈祷,并祷告传教事业在这些国家的顺利发展。在讲故事的基础上,一般要求儿童背诵与故事相关的经文,如果是普及类故事,则另选择简短的经文让儿童记忆。
为了让儿童熟悉宗教仪式,唱诗和祷告是聚会的固定环节。一般在聚会开始时,由全体儿童共同唱《日光歌》,为使儿童明白自己的责任,“要作小日光……大发亮光显出主荣耀”。在聚会结束时,全体儿童再唱《散会求福》,为每位儿童做祈祷,告诫儿童们“因信仰而得拯救”。祷告则穿插在不同活动之间,内容主要是向主表感谢、求祝福。在浓郁的宗教氛围里,让儿童不断接受基督信仰的熏陶。
聚会中比较特殊的活动是捐钱,如1933年9月第四次聚会,便号召儿童捐款帮助浸信会在东北地区传教事业的发展,并制造福音车式的存钱罐“带回家中……将每日零食的钱都放入福音车里,以备星期六日光会聚会时捐到他们自己一队的大福音车里”。教育儿童用实际行动辅助教会的发展。
为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提升聚会的趣味性,还有手工与游戏活动。手工的种类多样,纸工、泥工、木工、竹工等不限,往往根据所讲述的故事由儿童自由创作,允许合作或独立创作。游戏活动多在散会前进行,既包括体能型的游戏,锻炼儿童的体能,也有知识型的游戏,往往是就宗教知识进行问答,如“圣经中的人物”,把儿童以《圣经》中的人物名代替,进行换座,考察儿童的记忆能力和对《圣经》知识的掌握。
日光会通过定期的聚会,举办丰富的活动,在进行宗教知识教授的同时,帮助儿童德智体全面地发展,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培养基督信仰的小教众。
(三)适合儿童的教育方法
儿童有自身的特殊性,日光会采用适合于儿童的方法进行宗教教育。
一是在宗教知识上强调反复地诵读和精益求精。在聚会的经文学习上,往往只要求背诵一句,如1933年1月第二次聚会上,背诵经文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三十一节)。另外在聚会上,要求复习和背诵之前学习过的经文,以考察儿童的实际掌握情况。在重复记忆的情况下,帮助儿童掌握宗教知识。
二是简化深奥的宗教知识,转以质朴的道德要求。日光会简化复杂的宗教条文,提炼深刻的宗教内涵,以简单明白的知识道理和道德要求,直接教育儿童。在1933年1月第一次聚会上,以《创世纪》二十四章为基础,讲述了亚伯拉罕派遣老仆人前往美索不达米亚,为他的儿子以撒挑选妻子一事。该条文涉及人物的所作所为皆有不同的宗教内涵,但在日光会的讲述中,只要求儿童善待老人与牲畜。
三是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在宗教知识的教授上,鼓励儿童就所讲故事发表意见,在意见表达中,帮助儿童主动思考和理解宗教知识。在手工活动中,注重儿童的自由发挥。在捐钱活动中,教育儿童明白自己的宗教职责,主动积累日常零用,为教会发展捐献自己的力量。在强调儿童主动性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儿童对宗教的接受度。
(四)塑造理想的宗教儿童
在宗教儿童观的指导下,通过系列的宗教教育活动,日光会力图塑造理想的宗教儿童。一是拥有坚定的基督信仰。在日光会的宗教教育中,对经文等宗教知识掌握重理解、轻数量。日光会领袖注重经文的讲解,目的就是使儿童真正懂得基督耶稣的神性,在祷告、唱诗等所营造的宗教氛围中,将儿童培养成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者。二是具有基督教倡导的品德。日光会尤为注重儿童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培养,“愈帮助别人得快乐,自己的快乐便愈多”。从日常入手,从小处着眼,教导儿童与心中的恶作斗争,诸如“不孝顺父母,不听先生的话,不守安息日,不做礼拜”等行为都不被允许,在生活中逐渐培养起儿童具有基督教倡导的品德。三是具有开阔眼界。基督教具有全球性宗教组织的特点,因而在日光会的教育中,时常教授儿童关于其他国家的知识、风土人情和儿童生活。长时间浸润在国际视野的教育下,日光会的儿童自然比一般儿童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四是具有主动服务基督教的精神。无论是宗教知识的问答,还是手工活动,还是捐钱行为,强调儿童独立主动地完成任务。在为东北传道事业的捐助中,家庭富裕的儿童将零用钱节省出,家庭拮据的儿童在外做工兼职赚钱捐助。在这样的锻炼中,培养儿童主动服务基督教精神。
四、结 语
瑞典教育家爱伦·凯曾预言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儿童阶段“是每一个成熟的个体都必须经过的不可跨越的阶段,因此,对儿童的认识是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人类自我认识发育的重要标志之一”。发现儿童的过程正是人类发现自身的过程,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正是国民思想解放的表征之一。受限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儿童本位”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儿童观的发展并不顺利,但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大众意识形态下不同群体的儿童观。日光会的儿童观是宗教意识、民族意识和西方现代权利意识混合交织的产物,在将儿童视为上帝的附庸,华人教会自立和建立“基督中国”的希望的同时,尊重儿童权利,强调儿童责任。对于日光会中的中国儿童而言,在脱离家庭私有物地位和成人中心的同时,又被在童年世界中建立了新的权威主义。“耶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儿童永远是上帝的小子民。日光会的所有活动,都是这种宗教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单向投射,反射出儿童成长中预设的宗教前提。它会为上帝塑造真正的小子民,也可能带来对儿童心理世界的干涉和压抑,造成形式上的恭顺与服从。通过对日光会宗教儿童观和宗教教育的研究,为认识当时宗教群体内部对儿童的认识和儿童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