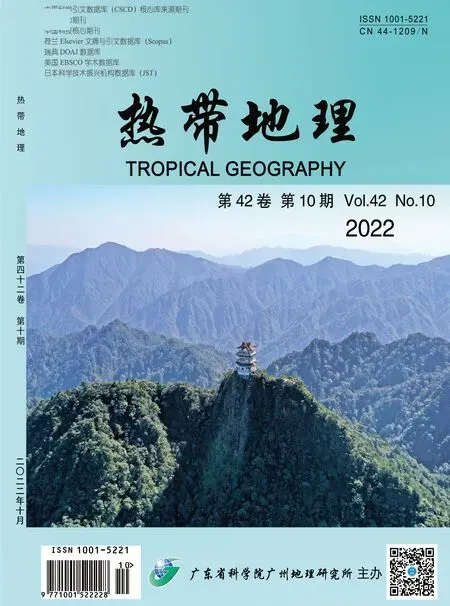文化城市群的时空演进及其动力机制
——以粤东城市群为例
沈陆澄,陈 中,侯璐 璐
(1. 汕头技师学院,广东 汕头 515071;2. 汕头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广东 汕头 515041;3. 汕头大学公共管理学系,广东 汕头 515063)
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其内涵与特征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作为城市空间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演化出的高级形态,城市群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有活力的空间组织单元,是各国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群的发展在于通过城市化的动态过程实现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李秋香等,2008)。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步入平稳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群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2021 年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未来中国要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的基本方略,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以19个城市群建设为抓手,全面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21)。这19个城市群定位不同、类型各异,而现有城市群理论多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群演变史,对中国各种城市群的适用性尚需细论。因而有必要以中国城市群,特别是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城市群为切入点,深挖城市群理论的文化差异,厘清城市群演进历程的本土化机制及影响要素,以促进中国城市群体系的合理布局与可持续发展。
粤东地区地处广东省东部,在最新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所属城市群从传统的“海峡西岸城市群”变更为“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其城市群定位从对接台湾省转变为面向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新的城市群定位更加突出文化同质性,这需进一步展开地域文化对城市群发展的影响研究;而传统的城市群概念多以城市间的经济合作为出发点,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文化效益,无法为新时期城市群差异化发展提供充分参考。文化城市群强调跳出传统经济效益导向的分析框架,从社会文化视角探讨城市群时空演进的地方特色与基本规律,有望对中国多种本土文化影响下的多元城市群建设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因此,本文尝试以文化城市群为视角,结合粤东城市群演变特征,探讨文化城市群时空演变的阶段性及动力机制。以期丰富当前城市群理论中文化要素的研究内容,为其他地方文化城市群发展提供参考。
1 文化城市群
1.1 从城市群到文化城市群
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研究美国城市空间不断扩展形成大都市片区的现象时,首次明确使用希腊语中的“Megalopolis”表示城市群的概念(Gottmann, 1961),其核心特征是地理位置接近、社会经济联系密切。实证研究中,经济联系往往被置于更突出的地位,特别是人流、物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分析中罕见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Florida et al.,2008;Shen,2020)。不论是惠贝尔的走廊理论(Whebell, 1969),还是布鲁恩和威廉姆斯的大都市带研究(Brunn, 1983;顾朝林,2011),都从经济发展造成空间扩张的角度探讨城市群的演进。也有学者认识到城市群的意义不只是过分膨胀的单个大都市区或多个都市区的简单组合,而是有着综合效益发生质变的城市群体有机整体(冯垚,2006)。沙里宁在有机疏散理论中提出,集中式发展更多地是为实现集聚带来的经济效益(Saarinen,1943),而城市群的发展应由无序的集中转向有序的疏散,使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得以协调发展(Lynch,1980;Neuman et al.,2009)。
毫无疑问,城市群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概念必然涵盖经济要素与社会文化要素,然而,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群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侧重城市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如何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忽略了社会文化要素的作用路径,只在探讨城市群经济效益时偶然涉及。如弗里德曼等(1965)以工业化发展水平为指标打造的城市群发展4阶段论,即工业化前的农业社会、工业化初始阶段、工业化成熟阶段及工业化后期阶段,并在讨论中注意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科技联系越来越重要;史育龙等(1996)则强调“Megalopolis”是都市区而非城市建成区的连绵,其社会文化的连续性不应被忽视。此外,荷兰的Randstad模式中,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和乌得勒克4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中并没有主导性中心城市,但其网络集群化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地区综合竞争力,成为当代世界城市群新的发展模式之一(邱瑛,2010),而文化要素正是促成其网络协作的重要粘合剂。总的来说,学界正逐步认识到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文化要素的重要性。
1.2 文化城市群的讨论
初期的城市群研究中文化部分一般作为影响城市群经济的要素之一。如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理论深入探讨了由多个城市构成的都市化片区的特征、功能、形成的影响因素和发展阶段(Gottmann,1961)。他的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的变动、人口分布、劳动力构成及土地利用形式等方面展开。直到1990年,戈特曼才补充了早期研究中忽视的社会文化要素,认识到文化要素对城市群空间可能产生的正向凝聚性(Gottmann,1990)。此后,越来越多学者开始注意到城市外围地区以及城市之间的发展问题。特别是技术创新改变了区位原本的竞争能力差异,空间的竞合关系也由经济效益转向更复杂的全方面因素。
城市群发展的动力机制多以经济学视角结合地理特征展开,分析城市群经济要素的相互联系与耦合机制,主要包括集聚/扩散论,聚焦城市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Fang,2019);政策论,关注行政力量干预下的城市群形态演进(俞万源,2007;方创琳,2012;刘云刚等,2018);经济要素论,研究不同经济要素在空间中的流动与整合(张学良等,2014)。早期多由劳动地域分工角度看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基本认同城市群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布局形式,是一种新的“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形式。而从20 世纪80 年代起,新制度学派和人类行为经济学分析理论相继出现,社会文化特征等开始得到重视。城市群发展理念也出现了变化,即认识到城市首先是人类居住的适宜性空间,在实现经济功能同时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功能(约翰斯顿,2010)。人本主义的流行使学界认识到不应将城市群空间演化看作是单纯由经济、技术因素驱动的行为,其演化中的文化要素同样重要。
中国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族群众多,城市群中的文化表现更加复杂。刘士林(2013)提出中国沿海地区城市群是在信息通讯技术、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独特的政策制度等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空间上呈现独特的分散性区域集聚,这与传统城市群认知并不一致。方创琳等(2018)认为中西部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相应的服务能力及产出却严重不足,城市群应通过资源文化建设城市群品牌,探索基于多元文化的新模式。城市群生长发育的“育树成林”规律也体现了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强调通过协调城市之间的“养分”与“空间”以实现一体化共同生长(曾万涛,2008)。也有学者发现缺乏有效的文化交流与心理认同机制是当前很多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面临的主要瓶颈(俞万源,2012;郑艳婷,2020)。而中国大部分城市群也很难复制长三角、珠三角模式,城市群的内涵式发展需从土地等传统物理要素驱动转向制度、知识、技术、服务创新驱动,这些无不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城市地缘文化将持续发挥影响(Comunian,2015;刘士林,2015),具有鲜明层级体系和积极协调的城市群文化机制势在必行,即通过重建不同区域的“小文化”推动城市群体系发展方式的转变(曾冰等,2020)。
在中国的城市群规划实践中,城市群的划分更多地基于地理空间的相近,其社会文化属性的考虑往往不足。城市群并非是将地域空间相近的城市划归到一起就可以自然而然形成,而是需充分考虑其内部城市间同步协作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已有研究表明,许多空间临近的城市,其文化并不一定相似,而文化认知、地方归属感、地方保护主义、制度壁垒等都是影响城市群效益的核心要素(盛蓉等,2015)。当同一地域文化内的城市构成城市群时,城市群建设会得到有力促进;相反地,如果城市群涵盖从属不同文化圈的城市,激进的建设模式反而容易成为地区发展的阻碍。因此,城市群建设要重视地域文化的研究与分析(王伟,2010)。文化城市群的概念可以与经济城市群对照而来,即前者是在形态和模式上由经济、交通和人口主导的城市群,而后者更加强调文化、社会生态和空间品质(李秋香等,2007)。
城市群概念的提出距今已逾60年,需进一步丰富其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内涵。国内外城市群研究都开始认识到城市群发展中文化要素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城市群研究的必要性,但目前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在此,本文将文化城市群定义为特定区域范围内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共同或相似的文化基础,促成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多方面密切联系而形成的城市集合体。
2 研究区概况
粤东地区属潮汕文化区和潮语方言区,北临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南临珠三角城市群,东临南海,与台湾省隔海相望,主要包括汕头、潮州、揭阳、汕尾4 个地级市,总面积为15 516 km2(图1)。根据2020年广东省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数据①http://stats.gd.gov.cn/attachment/0/421/421309/3283428.pdf,该地区总人口1 632万人,GDP共计约7 054亿元,其中汕头、揭阳、潮州、汕尾4 个地级市人口分别为550.2 万、557.8 万、256.8 万、267.3 万人;GDP 分别为2 730.6 亿、2 102.1 亿、1 097.0 亿、1 123.8 亿元,人均GDP最高的为汕头市,约4.96万元。汕头市是该地区的中心城市,承担公共服务与商贸中心职能;揭阳市是该地区主要的产业基地;潮州市是该地区历史文化中心;汕尾市则以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的职能为主。4 个城市发展较为均衡,彼此间差异小。此外,独特的移民史和城市发展历程形成了集潮汕文化、半山客文化、畲族文化和谐共存的文化集合。该地区以潮汕文化为主,核心区域位于潮汕平原,主要集中在汕头、潮州和揭阳3市;而作为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过渡带的半山客文化,主要分布在粤东的东北部、西北部山区;畲族文化则主要分布在潮州市凤凰山区一带。
3 粤东文化城市群的时空演变
3.1 区划演变
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与历史政权建制共同影响了粤东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和分布。秦汉时期岭南地区设置郡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 年)开置古揭阳(为与今揭阳市区分,将揭阳县称为古揭阳),是潮汕文化区最早的行政区划,并成为汉文化的扩散地;东晋时期,古揭阳设置义安郡,隋开皇十一年(591 年)原义安郡改称潮州,随着朝廷官宦被贬职于此,为潮州儒家文化奠定了基础;宋代,潮州接收的南移人口猛增,促进了当地农业文化的发展,宋宣和时期(1121 年)潮州增设揭阳,与潮阳、海阳合称“三阳”,初步奠定了粤东城市群的框架;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改州为路,潮州路辖海阳、揭阳、潮阳3 县;明代洪武二年(1369 年),潮州改称潮州府,期间梅州改称程乡县,隶属潮州府,并在南澳设副总兵府,基本形成现在的城市群格局;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汕头建立军港,咸丰十年(1860 年)汕头正式开埠,1921年汕头市政厅成立,1981年汕头设立经济特区;1991年,汕头、潮州、揭阳3市分别设立行政区实行各自治理,结束了长期作为一个政区的历史(图2)。
3.2 格局演变
粤东城市群的空间格局大致经历了“带状—人字状—梳状—圈层式”的演变过程(图3、4)。潮汕文化区自秦汉时期出现行政建制,南海郡的古揭阳人口和城市建设规模较小,聚落多沿江集聚,呈沿江“带状”分布特征(图3-a);至隋唐时期,南迁移民不断增多且河流淤积,人类居民点不断向河流的下游即地区的东、南方迁移,至宋元时期出现移民高潮,海岸线相比秦汉向海洋大幅拓展,沿韩江下游及海岸线出现多个新兴城镇,如海阳、揭阳、潮阳、海宁、绥安等,城市空间形态表现为沿江、海分布的“人字”状(图3-b);明清时期城镇建设范围进一步扩大,沿黄冈河、韩江、榕江、练江及沿海分别设立城镇和港口,如饶平、澄海、汕头港、蓬州所、普宁、海门所、靖海所等,城镇空间形态表现为以海岸线为“轴”、四水系为“齿”的“梳状”分布特点(图3-c);现代陆路、航空等交通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内经济的繁荣为粤东城镇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城市群空间形态逐渐向“圈层式”发展,即形成以汕潮揭同城化为内圈和粤东城镇一体化为外圈的空间格局(图4)。
3.3 总体特征
粤东城市群的空间分布与自然成陆的趋势一致,也与人多地少、向海拓展的地方生产生活方式相关,形成沿主要河流由内陆、内河向海洋,即由西、北向东、南逐渐推进的特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设县时间,沿韩、榕、练三江流域的海阳、古揭阳、潮阳均在宋代以前设县,而沿海的饶平、惠来、澄海等则在明代设县,聚落分布呈现由内河向临海发展的趋势。2)各县治的迁移,古揭阳城从设县之初的留隍(今属丰顺)迁至玉窖(今榕城);潮阳县城东晋设于临昆山麓(今棉城西北和平镇),唐迁至新兴(今棉城);饶平县城明代设于弦歌都下饶堡(今三饶镇),至1953年迁至黄冈;普宁从明代设县洪阳,至1949年迁往流沙,政治中心普遍表现为由内陆向临海迁移的趋势。3)粤东政治经济中心变迁,由晋代设郡之初设于鸭湖(今潮安归湖),至南朝梁时迁至现潮州市,至解放初期汕头市逐渐取代潮州,成为粤东地区的职能中心,表现出沿韩江向下游江口、河口不断推进的轨迹(图5)。
3.4 阶段性特征
城市群地域结构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中城市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规模等级、职能分化、空间分异等因素是塑造阶段性规律的重要原因(朱英明等,2002)。一般认为,城市群地域结构中的市场化联系是推动城市群结构递嬗规律形成的核心要素,进而形成四阶段式的演化模型,即分散发展的单核心城市阶段—城市组团阶段—城市组群扩展阶段—城市群形成阶段,也可根据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特点划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前工业化时代—工业化时代—城市化时代(姚士谋等,2006;2016)。整体上,粤东文化城市群的发展也符合第一种阶段性规律。
基于粤东城市群地域结构发展历程发现,其时空演进具有传统经济网络影响下空间递嬗的普遍性,同时也具有地方文化要素作用下的特殊性。“精细”“重商”“外向”和“融合”这4个文化要素先后在粤东城市群塑造中发挥核心作用,其中,“精细”和“重商”深刻影响城市群个体化发展时的物理空间,“外向”和“融合”引领与控制城市群集团化发展态势。
在粤东城市发育初期,“精细化”作为潮汕文化的核心对城市微观经济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塑造了城市核心地区的带状空间格局。粤东地区背山面海,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地理格局;来自北方的大规模移民迁入使得地区人口不断增长,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人地关系愈发紧张。因此,潮汕人养成了“精耕细作、精打细算”的土地/空间使用习惯,如“绣花式”的农田景观、“精而不奸”的商业行为、精雕细琢的木雕和陶瓷、精美奇巧的建筑装饰等,塑造了城市发育初期小规模、精细化、密布局的带状空间特征。
城市由“个”向“群”的成型时期,“重商主义”极大地推动了粤东地区城市组团的形成与发展,并在以商业为核心的区位特色下依次形成人字状、梳状2种模式。粤东经济发展对水路交通较为依赖,一旦港口或河道出现淤塞,商业活动即转向下一处可供通商的新港口。以水路交通为纽带、以港口为依托的城镇成为城市组团的主要节点。粤东地区最初的核心节点是唐代以前作为韩江出海口的潮州,食盐、陶瓷等商业活动依托此遍及海内外,并进一步拓展到造船业和制瓷业等地方产业;尤其在明代开始,重商意识成为主流,民间贸易逐渐合法化,潮商群体所经营的工商业日趋繁荣。
“侨文化”与“新潮商文化”引领城市群圈层式发展格局。因独特的地理区位,粤东地区的海外贸易繁荣,明清汕头开埠后以及近代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出现向外迁徙高潮,移民遍布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潮人圈”与侨文化,总人口超过1 000 万。大量潮汕海内外移民促进了潮汕侨乡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蔡海松,2012),并鲜明地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餐饮、建筑、宗族、语言等共同文化底色使得城市间的侨文化逐渐趋于同一性。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潮汕华侨回到家乡参与城市建设,投资地点与投资行为形成以家乡为核心、由内而外圈层式弱化的侨资建设模式;在更大尺度上形成本地、海内、海外“3个潮汕”。
融合型文化塑造新的城市群景观,开放包容的文化城市群活力日益凸显。潮汕文化起源于古越、成型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昌盛于明清、创新于现代(黄挺等,2001),是古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共同孕育发展的文化;不仅受传统百越原住民的影响,还融合了历代中原居民迁入所带来的中原文化,以及从中原迁入福建再从福建辗转迁入此地居民所带来的闽文化。因此,潮汕文化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以及超越空间毗邻效应的新潮商文化圈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活力,并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客家文化与畲族文化为补充、兼具海外元素的综合文化。不同文化的碰撞引导城市形成“多元化、小而全”的景观风貌,如城市群内多处可见儒、释、道、基督教等宗教建筑临近布置的现象;同时,融合型文化也塑造了极强的地方归属感,如潮汕商帮的凝聚力及反哺城市发展的贡献与热情。
4 粤东文化城市群演变的动力机制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提出空间并不局限于物质空间属性,其社会空间属性的演变是解释社会构建的核心要素(闫梅等,2013;肖竞等,2014),不同城市景观是在文化沉淀影响下,由城市空间形态演进所形成,且与城市群发展的地域结构递嬗规律相契合,反映文化城市群演变的动力转换。受潮汕文化影响的粤东城市群,其文化体系的不同要素在城市群演进的各阶段发挥着不同影响,塑造出不同类型的空间,而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间又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城市群的内在同一性,表现出与其他城市群迥异的文化属性(图6)。在单核心城市时期,经济结构与人地关系认知的文化相结合是城市形态发育的主要动力;随着城市间关系逐步密切,规模等级与职能分化开始成为多核心城市组团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群形成后并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时刻处于动态调整中,此时,社会文化、发展政策更加显著地作用于区域内部空间分异及城市群的可持续性。随着城市形态持续发展,文化要素的影响力逐渐从微观建筑建设层面扩大至中观城市景观层面,最终形成基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城市群层面。
阶段一,单核城市阶段,文化城市群发育初期,文化要素主要作用于微观尺度的城市空间,农业资源禀赋决定了文化城市群的初期形态。粤东地区表现为沿水紧密排列的带状城市格局,形成了“负阴抱阳,依山面水”的建设原则,而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导致潮汕文化推崇经济空间的精耕细作;同时在宗族体系影响下,同姓家族聚族而居,围合式聚落对内开敞、对外封闭,以共同开发自然资源、抵御自然灾害。而在城市空间上体现为街道格局、建筑形态等集约性突出,城市建设以单向布局为主,大多坐北朝南、集中布局、相互毗邻、排列整齐、四周街巷围绕(杜松年,1994),呈现严整、封闭的特点,将潮汕文化的空间精细化推向新高度。同时期自上而下的政策行为主要以管控为目的,但自下而上的农耕文化是塑造微观与中观城市景观的主要动力。
阶段二,城市组团阶段,商业文化不断发展,从微观、中观2个层面再造人地关系,推动商业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基于区位价值重新整合产业空间结构。新兴商业主体突破微观尺度的产业定势,从地区角度提供经济效益的最优空间解,即基于利益考量参与交通线路建设,重塑中心城市腹地,依托交通线网整合已有聚落。在粤东地区表现为“潮汕”取代潮州成为文化城市群的新名片,其中汕头地位的上升正是其商业职能重要性不断提高的结果。粤东商业文化成型主要依托水运交通,岸线持续外移造成港口变迁且汕头本地商会发展不断壮大,使得汕头埠在城市群中的地位逐步赶超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潮州,特别是1860年汕头港正式开埠后,“潮汕”这一新兴地理概念迅速发酵。同时,政策的下行目标由控制转变为控制与引导同步进行,迎合地方经济发展新需求,如鼓励新兴内河水运码头发展、注重海港建设、采取填海造地等措施扩大城市土地面积以供商业发展。
阶段三,城市群形成阶段,新兴工业文明将文化要素的作用提升至城市间尺度,工业文化的本地化过程以及实现本地化后的族群连锁迁移使得文化空间迅速膨胀,促进城市群空间的外向性圈层拓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相辅相成,经济与空间的一体化空前加强,产业的集群化、规模化发展使得土地利用模式也转向城市间合作。粤东地区工业化主体是海外华侨投资的民族工业,带来了西方规划手法和南洋骑楼式样相结合的舶来工业文化,在城市中心形成环形放射状骑楼街区;村镇则在自有华侨资源的帮助下,走上就地城镇化的路径。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强化城镇对港口、机场等重大对外交通设施的需求,城市群内部通过公路网络增强城镇间交通设施联系,进而形成基于文化圈的圈层轴带式城镇格局。从更宏观的尺度看,粤港澳大湾区及福建等地形成了新潮汕群体,粤东也凭借其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人华侨群体成为华南地区对接东盟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该阶段政策转变为通过空间规划引导经济建设,但与文化之间对话较弱的状态容易隐藏危机。
阶段四,城市群优化阶段,信息时代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了传统社会经济关系的空间表达。文化要素不论在空间利用还是在经济协作等方面扮演的角色日趋复杂,空间、文化、经济等要素间的黏性加强,即空间的经济效益越来越难以剥离其文化属性。文化对地方城市群发展的推动力持续增强,城市群圈层化的格局也由传统的沿交通线扩展变为跳跃式扩散,诸如“新飞地”“新飞人”模式。该阶段,地区文化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决定着文化城市群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即能否基于文化共识实现信息的快速流转与增值,赋予文化城市群突出的地方竞争力;如无法实现多元文化协调,则容易在经济发展无法实现惠及全域的状况下,城市间更强调文化差异而进行恶性竞争,这也是很多城市群在发展中后期合作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因而在政策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中,政府的协调作用愈加重要。信息时代的城市群发展应重点打造文化城市群的概念,如粤东城市群应凸显“潮汕文化”而非“潮州文化”“汕头文化”等分裂性文化概念,进一步统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利益。其中,多文化腹地交叠区域有可能成为重要媒介,如粤东的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重启“侨”元素吸引海内外潮商投资;深圳与汕头深度合作是以粤港澳大湾区潮商主导的一种跨区域“飞地”合作,这些可看作整合地区多元文化的积极尝试。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文化城市群研究视角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通过系统梳理粤东文化城市群的发展历程,探索粤东文化城市群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粤东城市群的空间形态随潮汕文化发展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而发生改变,呈现从西北逐渐向东南拓展的特征,单个城市空间形态表现为精细化、密布局的特征,城市群空间格局则经历了“带状—人字状—梳状—圈层式”的演变。2)粤东城市群空间格局演变与潮汕文化中精细、重商、外向、融合的4个核心文化要素密切相关,并在文化城市群演变的不同阶段分别发挥主导作用。精细化布局塑造了潮汕地区传统城市核心地区的带状格局;重商主义极大地推动了依托河网港口形成的合作型城市组团;潮文化与侨文化使得文化城市群的影响力突破地方、远抵海外;新时代潮汕文化的包容性大大提升,粤东城市群的腹地与影响力呈现圈层式拓展。3)粤东文化城市群的发展是经济结构与文化要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尺度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并由微观尺度上升为宏观中观多元尺度。农耕文化是人地关系最初期、最核心的表现,从单体建筑、空间布局、街区结构等方面影响建成区景观;商业文化影响下空间被赋予更多经济性内涵,城市间竞合关系成为城市间形态演变的核心因素;工业文化空前地实现了多种资源的全方位整合,将多个城市捏合为密切嵌合的城市群;信息时代的科技进步更是扭转了传统地理结构中的核心−边缘关系,将文化城市群的优势发挥出来。城市文化要素在潮汕文化的影响下,粤东城市群特征突出,一体化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基于文化同质性构建文化城市群势在必行。但部分地区由于存在一定的文化异质性,构建文化城市群经常面临困难,由此会成为城市连绵区中的“气泡”,典型的案例如汕尾,其城市建设与规划发展经常游走于珠三角城市群与粤东城市群之间,其工业文化的构建多基于深圳城市蔓延或飞地式发展,而社会文化传统又与潮汕地区关系密切,造成其在文化城市群中自我定位不明。
本文以文化城市群为视角、梳理文化城市群的基本内涵,通过分析潮汕文化影响下粤东城市群的演进,探讨了文化城市群的基本规律,提出文化要素在城市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展现不同特质,从多元尺度影响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文化属性会直接反映到地方政治结构中,并进一步产出文化区经济。不同文化城市群的政治结构如何运转、冲撞与协调将是未来深化文化城市群研究的重要议题。此外,文化城市群与文化区域、文化圈密切相关,二者关系也有待未来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