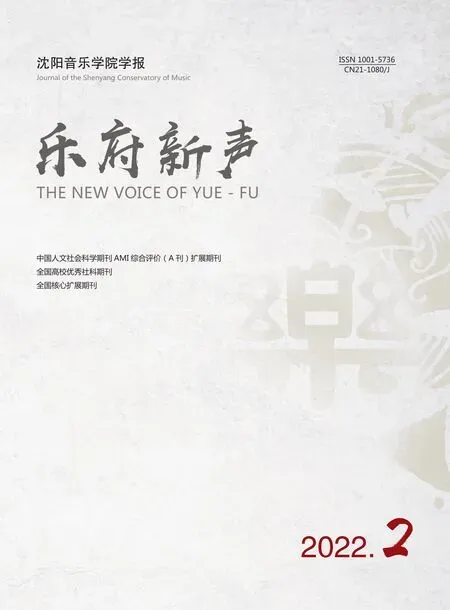社会学视野下“伦敦钢琴学派”价值重审
王莹 杨燕迪
[内容提要]伦敦钢琴学派是指18 世纪末至19 世纪中叶活跃于伦敦的音乐家群体,该群体创作的大量作品及其历史影响在风格史范畴内未获得公正评价。本文借助社会学视角考察伦敦钢琴音乐“大众化”、“多样性”的成因以及表现形式;分析伦敦钢琴学派基于英国钢琴表现性能开创的新语汇对维也纳同代人以及浪漫主义钢琴书写风格产生的影响;重审19 世纪伦敦钢琴音乐的历史价值。
纵观钢琴音乐发展史,学派林立,在所谓的德奥“正统”之音外,法国、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等都争相在世界钢琴舞台上发出属于自己的民族之音,建构本国的钢琴学派。18 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有一个活跃于伦敦的音乐家群体,即伦敦钢琴学派,该学派的艺术成就以及对后世钢琴音乐走向的影响长期未得到公正评价。本文首先分析历史偏见的成因,其次从音乐学、社会学多角度重新审思伦敦钢琴学派的价值和影响。研究伦敦钢琴学派,除弥补相关知识之不足外,也期待英国音乐学人重构伦敦钢琴学派之策略能为“中国钢琴学派”的建构与推广提供一些参照。
一、伦敦钢琴学派研究:偏见与价值重审
弗里德里希·卡尔克布雷纳(Friedrich Kalk brenner,1785-1849)1830 年曾评论道:“维也纳和伦敦的钢琴导致了两种不同学派的产生。维也纳的钢琴家在准确性、清晰度和演奏的速度上更胜一筹……英国钢琴拥有圆润的音色,琴键弹性也比较好,因此伦敦的钢琴家都采用一种更恢宏的演奏方式,那种优美的‘演唱’风格使他们别出一格”[2][英]戴维德·罗兰.钢琴[M].马英珺,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21.。
据评论可知,彼时批评家已对处于同一时期的维也纳钢琴和伦敦钢琴的乐器表现性能作出区分,并以演奏风格为依据提出“维也纳钢琴学派”和“伦敦钢琴学派”两种指称。
(一)伦敦钢琴学派研究溯源
对伦敦钢琴学派研究起推动作用的是英国本土音乐学家尼古拉斯·坦伯利(Nicholas Temperley,1932-2020),坦伯利一生致力于“19 世纪英国音乐文化”研究,积极推动伦敦钢琴音乐的复兴,20 世纪80 年代以伦敦钢琴学派为题推出20卷册曲谱,收录J.C.巴赫、克莱门蒂等49 位作曲家创作的800 余部钢琴作品。[2]Nicholas Temperley.The London Pianoforte School 1766-1860,20 vols.New York and London:Garland,1984-87.乐谱集收录了克莱门蒂、菲尔德、杜塞克、克拉默、塞缪尔·韦斯利(Samuel Wesley)、威廉·S.·本内特(William Sterndale Bennett,1816-1875)、伊格纳兹·莫谢莱斯(Ignaz Moscheles)、菲利普·科根(Philip Cogan,约1747-1833)以及乔治·弗雷德里克·平托(George Frederick Pinto,1785-1806)等作曲家的代表作;同时还将海顿、韦伯、门德尔松与伦敦音乐生活相关联的作品纳入曲集。坦伯利教授一生积极推广伦敦钢琴音乐,缘于他意识到伦敦作为一个时代重要的音乐城市,其成就和影响被严重低估。
(二)历史偏见中的伦敦钢琴学派
“伦敦”即“英国”。在传统学术观念中,英国音乐自亨德尔后进入漫长的“黑暗时代”。“由于新作数量以及对风格化作品鉴赏力的衰退,英国被冠以‘没有音乐的世界’的名声,时至今日在欧洲大陆仍被有失公正地强化着”[3]Paul Henry Lang.Music in Western Civilization.W.W.Norton &Company,1941:p.687.。保罗·亨利·朗的上述评论揭示出一代学人的偏见。作为一个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朗虽然意识到欧陆学者“有失公正”,但他的著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成书于1941 年,其个人观点难免不受整个时代学术氛围的影响,行文中出现前后矛盾的论调,例如他虽承认18 世纪最后30 年英国音乐生活的绚丽辉煌,但认为其“辉煌下面掩盖着(从)独创性作曲的衰落,发展为普遍的衰落”[4][美]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顾连理,张洪岛,杨燕迪,汤亚汀,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606.。朗将其归咎为英国人缺乏结构想象力,致艺术音乐传统逐渐衰落,“只剩下大众音乐,以前遭人看不起,如今被认为是18 世纪英国音乐的唯一有生命力、真正的本地音乐”[5]同上,2009:602-603.。
上述结论低估了19 世纪前后英国音乐的成就及其对欧陆音乐的影响。就钢琴音乐而言,“正是在那个所谓的‘黑暗时代’……伦敦钢琴学派创作了数量惊人且形式丰富的钢琴杰作,只是不为现代钢琴家和大众所熟知”[6]Nicholas Temperley.London and the Piano,1760 -1860.The Musical Times,1988(Jun.) pp.289-293.。坦伯利的研究将众多被遗忘于历史中但对19 世纪钢琴音乐风格走向起预示作用的“小作曲家”,以及他们未能进入核心保留曲目的作品推向学术前沿,很多作品如今已成为音乐会的常演曲目。[7]R.Larry Todd.The London Pianoforte School 1766-1860:Clementi,Dussek,Cogan,Cramer,Field,Pinto,Sterndale Bennett,and Other Masters of the Pianoforte by Nicholas Temperle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1991(Spring):pp.128-136.
伦敦钢琴学派的成就和影响之所以在随后到来的19 世纪被严重低估,笔者认为其原因隐藏于西方音乐“核心保留曲目”(the core of the repertory)机制以及“经典化”意识的建构过程中。从1810 年起,欧洲音乐界兴起一股崇尚贝多芬的潮流,各地音乐组织(演出团体或教育机构)的建立和目标都以完美“呈现”贝多芬的交响乐作品为前提。[1][奥]布劳考普夫.永恒的旋律——音乐与社会[M].孟祥林,刘丽华,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80.例如,1828年巴黎音乐会协会建立就是为了恰如其分地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1817 年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音乐学院以培养乐队合奏技术为主要目的。“李斯特也早在30 年代就开创了钢琴家在音乐会曲目中纳入‘历史性曲目’的趋向”[2]莉迪娅·戈尔.音乐作品的想象博物馆——音乐哲学论稿[M].罗东晖,译.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269.。可以说,指挥家、演奏家、作曲家、评论家以及音乐机构拧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塑造着音乐生活中的“严肃趣味”,意将那些迎合大众的流行风格、轻松体裁、炫技风尚排除于主流正统之外。“经典化”意识的建构亦可以看作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和大众在艺术观念、审美趣味方面的一场持久的较量。到了19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艺术观念中基本已形成一套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等为中心的“核心保留曲目”机制,同时也意味着西方艺术音乐完成了“经典化”意识的建构[3]赵婉婷.音乐 经典 博物馆——西方古典音乐“经典化”历程[J].人民音乐,2020,3.。不难看出,“核心保留曲目”稳固地建立于德奥音乐传统的衣钵,浪漫派作曲家对“经典”的诠释带有明显的地域偏见,往往限定在“维也纳古典乐派”,在某些约定俗成的观念中,维也纳的大师才代表了真正的古典风格,才称得上永恒的“经典”。
长期以来,我们对音乐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古典和浪漫时期,常无意识地投向音乐会节目单上反复出现的曲目,尽管伦敦一些作曲家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维也纳同代人,但是一场场繁华的音乐会落幕后,那些往来穿梭的巡演音乐家以及他们炙手可热的作品即刻被忘却,较少有像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作品那样进入后来的核心保留曲目。因此,在传统风格史叙事背景下,作为一个整体的伦敦钢琴学派被同时代的维也纳大师的伟岸形象所遮蔽便不难理解。
(三)伦敦钢琴学派价值重审
20 世纪后音乐学研究进入多元化时代,音乐社会学的发展为音乐史学研究打开一片新的视域,学者以开放的态度将音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予以考察。大量社会学成果证明,在那个所谓的“黑暗时代”,英国音乐生活异常活跃:英国的自由经济孕育着欧洲最富生命力的音乐演出市场;伦敦的钢琴制造业遥遥领先于欧陆国家;音乐出版业的繁荣局面反哺着音乐创作者的热情;广泛的音乐教育为伦敦培养大量具有良好艺术修养的听众,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英国有别于欧洲大陆的音乐文化风貌。
在社会学视域下重新审视学界对英国音乐的评价不难发现,所谓的“缺乏结构”是在维也纳古典乐派特别是贝多芬“宏大结构”的参照下得出的,这种偏见将英国音乐“大众化”直接等同于艺术品格“低端化”,更忽视“大众化”对艺术“多样性”的积极作用。“大众化”艺术不是娱乐的产物,更不是审美的低级水平,而是伦敦作曲家针对中产阶级艺术趣味和情感特征发展出的不同于维也纳乐派的语言系统以及与之相符合的音乐载体,如变奏曲、幻想曲、即兴曲、舞蹈音乐等。虽然这些“小作品”未能进入“核心保留曲目”,但是新的钢琴写作风格、弹奏技巧以及特性体裁被同代及浪漫主义作曲家借鉴吸收,并提升到更高的审美水平——J.C.巴赫与莫扎特、克莱门蒂与贝多芬、菲尔德与肖邦之间,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不可辩驳。罗森深悉浪漫风格之本源,他指出:“虽然浪漫派极其崇拜贝多芬,但浪漫风格却不是来自贝多芬,而是来自他同时代的一些小作曲家——以及,来自巴赫”[4][美]查尔斯·罗森.古典风格[M].杨燕迪,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44.。就此问题罗森虽然没有进一步展开,但凭学术经验不难判断他笔下“小作曲家”必定指向或者保守地说必然包括伦敦钢琴学派成员。
手机是抵御聒噪的神器,根据聒噪的级别调节不同的节目。比如对方的语音语调和风细雨,不影响我刷屏看文字,就首选微信微博;如果对方语音高亢语调激昂,逼你入脑入心,分心的方式就只能是看淘宝;如果对方的言辞激烈,好像你欠他2000元钱似的,这就是在逼我出手了,只好在购物车里划拉,对自己好一点吧,该买的就买,否则咋办?人家已经对咱这么不客气,咱自己总得对自己客气些吧?
综上,研究伦敦钢琴学派这样一个本身带有强烈跨学科性质的课题,从社会学角度考察音乐风格“大众化”、“多样性”在特定环境中的成因,是在风格史叙事框架内评价其成就、影响的前提,只有打破单一维度,秉承多视角的研究策略才能对伦敦音乐的价值予以重审。
二、伦敦钢琴音乐“大众化”与“多样性”的社会学考察
(一)中产阶级“奢侈”消费观与伦敦音乐“大众化”
伦敦钢琴音乐“大众化”的物质基础是处于上升时期的中产阶级以及他们的文化消费诉求。光荣革命后英国进入一个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快速腾飞的时期,社会各阶层不断分化、整合。18世纪处于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在等级制度中稳固自身地位的同时,希望在精神方面“向上流社会看齐”,通过文化上的“奢侈消费”实现身份认同。[1]曹瑞臣.18 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崛起研究[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中产阶级的文化诉求促进了伦敦音乐文化生活的繁荣,也是伦敦钢琴学派崛起的必要条件。
“奢侈”在音乐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有必要重新评估。道德批判上的“奢侈”就如同音乐批评中的过度装饰与炫技,被看作是节制与美德的反面备受诟病。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奢侈”实现了现代转型,学者以客观的态度区分“创造性奢侈”和“非创造性奢侈”。[2]曹瑞臣.近年来西方学界对英国消费社会兴起问题的研究[J].世界历史,2014,6.在音乐社会学视域下,“创造性奢侈”诉求对于音乐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得到公正评价。
文化上的“奢侈”需求加速伦敦城市音乐空间的扩展,除剧院、音乐厅等传统彰显身份的消费场所,商店、咖啡馆、小酒馆为中产阶级享受音乐提供另一片天地。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文化生活方式也被中下层市民争相效仿,“到18 世纪,观看戏剧和音乐会的观众增长迅猛,剧院的经理发现低收入的工人也观看他们的戏剧,于是他们在定期演出之后,以便宜的价格推出‘加时’演出。一些小剧院则完全面向这类低收入观众。”[3]李新宽.17 世纪末至18 世纪中叶英国消费社会的出现[J].世界历史,2011,10.劳工阶层参与文化消费领域,反映出18 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奠定英国音乐“大众化”的发展方向。
(二)文化商业机制与伦敦音乐“多样性”
受英国自由经济传统影响,英国文化艺术较早开启商业化经营模式。商业市场对艺术品质的影响向来受悲观主义者诟病,指责经济的驱动会降低艺术品质,妨碍艺术家对艺术作品道德层面的关照,并进一步认为自由市场致使伦敦(钢琴)音乐走向“大众化”,相比之下维也纳这座“受爱好音乐的贵族们保护的音乐城市”,因其音乐发展的动力主要依靠宫廷和贵族的赞助,所以较好地维持了贵族艺术品质。[4]夏滟洲.社会学对于音乐史学的几个切入点——以18 世纪维也纳音乐生活并莫扎特为例[J].中国音乐学,2013,4.
上述观点近年来颇受质疑,越来越多学者试图从社会学、经济学角度证明发育良好的文化商业市场能够孕育出各种机制促进并支持文化的多样性。
首先,发育良好的文化商业市场有利于发展出多样性的音乐表达。单一赞助体制下音乐环境相对封闭,虽巩固了所谓的“高雅品味”与统一风格,但就整个社会层面看,缺少丰富与多层次的音乐表达。下文以18、19 世纪之交伦敦钢琴学派作曲家掀起的一股“铃鼓风尚”为例,证明音乐家获得自由身份后,可以挣脱主流艺术品位的束缚,根据自己的兴趣、才情以及市场需求进行创作,使音乐市场上同时存在表达多种艺术观念的作品。[5][美]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0.
在18 世纪末的英国,铃鼓有特殊的社会隐喻,它与上层社会女性的理想形象和音乐修养相关,铃鼓始终是家庭音乐中重要的伴奏乐器,经常出现在文学和绘画作品中。克莱门蒂、丹尼尔·施泰贝尔特(Daniel Steibelt,1765-1823)等作曲家都专门创作铃鼓伴奏的钢琴音乐。克莱门蒂作为一个颇具商业慧眼的作曲家,紧锣密鼓地创作出版两部由铃鼓、三角铁伴奏的华尔兹舞曲Op.38(1798)和Op.39(1800),足可见其热度。[1]参见Luca Lévi Sala,Rohan H.Stewart-MacDonald.Muzio Clementi and British Musical Culture[M].Routledge,2019:164-184.笔者注: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伦敦作曲家创作的有铃鼓伴奏的钢琴作品数量极为可观。布罗德里普(Broderip)、威尔金森(Wilkinson)以及约瑟夫·戴尔(Joseph Dale)等当时知名出版商出版的此类作品至今仍可见于大英图书馆,主要是华尔兹、进行曲、回旋曲、流行曲调、歌剧咏叹调或管弦乐作品改编曲等小型体裁。这些面向大众的钢琴作品由于结构短小、技巧平实已无人问津,然而在社会学视域下,钢琴部分频频出现的滑音音型(glissandi)(见例1)与铃鼓的关系则十分值得关注,克莱门蒂借助滑音音型模仿铃鼓的颤音和滚奏声,在作曲技法上探索钢琴与铃鼓相得益彰的效果,表明多层次的艺术需求有利于作曲家发展新的创作技法。
例1.克莱门蒂《为钢琴、铃鼓、三角铁而作的12 首圆舞曲》 Op.38 之9 钢琴部分片断[2]谱例出自朗曼&克莱门蒂版,1800 年。

由于乐器自身的局限性难以与19 世纪新的钢琴音乐语言相融合,铃鼓音乐逐渐走向衰落。然而,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社会音乐现象具有社会学研究意义,它作为作曲家与社会关系的文献证据,表明伦敦作曲家能够在商业和艺术的动态平衡中探求更为多样的艺术表达。即便回归风格史框架,“铃鼓风尚”依然提醒我们:一些被视为纯粹技术性的问题(如本文的“滑音”技术),实际上也潜藏着复杂的社会关系,而这常常被忽略。
其次,发育良好的文化商业市场有利于生成音乐家和大众的对话关系。[3][美]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0.“在文化领域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不仅仅是为顾客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市场给予生产者很大的自由,以便培育他们的受众。”[4]同[3],2005:32.以往,我们过于强调作曲家对大众音乐品位的迎合,较少提及作曲家对大众音乐欣赏能力的培育。19 世纪初伦敦音乐市场率先出版大量钢琴练习曲,一方面是作曲家在商业市场上“逐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曲家培养大众音乐欣赏能力的责任情怀。另外,作曲家充分察觉到大众对音乐会上经典旋律曲调的痴迷,将大量管弦乐曲或咏叹调改编成难度适宜的钢琴曲,如“克莱门蒂1800 年出版了根据约瑟夫·海顿的《创世纪》而改编的钢琴和声乐总谱”[5][英]戴维德·罗兰.钢琴[M].马英珺,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127.,表明作曲家有意提升大众专门化音乐欣赏能力使之与市场共同成长。
关于音乐家和大众的关系,有一种悲观主义论调认为伦敦钢琴学派作曲家为迎合大众喜好,放弃了“宏伟”、“深邃”、“艰深”等审美追求,以便让自己的作品在首次聆听时被理解或记住,“使自己的作品适合具有中等——而不是极高——音乐修养的听众”[6]同[3],2005:143.,甚至批评伦敦钢琴学派作曲家在体裁上优先发展短小、优美的“特性小曲”,致使奏鸣曲、协奏曲等大型体裁不再流行。
以宗教徒般的虔诚捍卫某一“伟大”体裁的永恒价值和不朽生命从来不是作曲家的使命,在伦敦这样一个商业化市场,作曲家发展与中产阶级情感相契合,与英国钢琴表现性能相一致的小型体裁,并不意味着艺术品质的倒退和艺术家人格的屈从。任何大型体裁的兴衰消长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以钢琴协奏曲为例,19 世纪30 年代后,当钢琴作为独奏乐器其表现力足以独当一面时,即便是古典时期盛极一时的大型体裁也终将衰落。舒曼深知其理,他在1839 年的一篇评论中就曾指出钢琴协奏曲新作数量减少、体裁内部乐队和钢琴脱节的原因:“藐视交响乐,当代钢琴演奏以它自己的方式,并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求统治。”[1][德]罗伯特·舒曼.我们时代的音乐:罗伯特·舒曼文选[M].马竞松,译.漓江出版社,2013:172.因此,评论家们如果一定要以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大型体裁为参照,苛责处于同一时期的伦敦钢琴作品的历史价值,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伦敦钢琴家只是提早一代人的时间终结了那些在19 世纪中叶注定失去光彩的大型体裁的生命力。
三、伦敦钢琴学派成就与影响的音乐学考察
有别于其它钢琴学派在弹奏方面的突出成就,伦敦钢琴学派的成就体现在音乐创作方面,主要影响在于进步的踏板技术对浪漫主义键盘习语的引领。
早在18世纪70 年代伦敦制造的大钢琴已经显示出后来英国钢琴所固定的两个踏板的标准——弱音踏板和延音踏板[2][美]泰勒·考恩.商业文化礼赞[M].严忠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5.,由于中产阶级音乐爱好者对“器乐音乐声乐化”的偏好,在钢琴上表现歌唱性旋律是伦敦学派钢琴家和钢琴制造师共同追求的理想,艺术和工业在目的上的高度契合激发伦敦音乐家较早探索适合延音踏板效果的理想音型和新织体,开创了有别于维也纳的新的作曲音型法。
新的趋势从左手伴奏开始,维也纳乐派键盘作品中不常见的左手大跨度伴奏音型在18 世纪90 年代施戴贝尔特和杜塞克的作品中十分普遍。这种写法很快被同代人借鉴,例如菲尔德标志性的“夜曲风格”,即在延音踏板共鸣效果的支持下,左手伴奏声部和右手的装饰性旋律声部共同完成一种抒情而细腻的风格表达。菲尔德的《夜曲》(1812 年出版了第一首)常被看作是最早的浪漫主义钢琴音乐,夜曲风格后来被肖邦等浪漫主义钢琴大师借鉴并升华,发展为表达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基本习语。
延音踏板技术是伦敦钢琴学派对古典及后世钢琴音乐发展的重要贡献。对比同一时期维也纳音乐家,海顿晚期作品开始使用踏板,他荣休后两次造访英国,与伦敦音乐生活结下紧密的联系。1791年访英期间借用布罗德伍德大钢琴用于演出,这使得海顿更习惯于英国钢琴的表现力。[3][英]John-Paul Williams.钢琴鉴赏手册[M].王加红,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46.最后三首奏鸣曲完成于第二次访英期间,《bE 大调奏鸣曲》(Hob.XVI:52)开篇的和弦仿佛是对英式钢琴性能的探索和检验,证明英式钢琴以及伦敦钢琴学派(特别是克莱门蒂)在钢琴织体方面对海顿产生影响。再看贝多芬,追求纯净风格的胡梅尔曾经批评贝多芬对延音踏板的滥用是制造噪音,相比于莫扎特和海顿,贝多芬对延音踏板的使用要多得多,研究也表明了贝多芬的踏板技巧很多方面受益于伦敦钢琴学派的启发。[4][英]戴维德·罗兰.钢琴[M].马英珺,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37.克莱门蒂对贝多芬的影响,特别是对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影响已经达成共识,然而菲尔德、杜塞克等伦敦钢琴学派成员的新语汇对贝多芬的影响目前在国内学界仍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杜塞克的成就在通史叙述中往往被一笔带过,但是那些专门研究19 世纪钢琴音乐的学者们从不吝惜对杜塞克的溢美之词,视杜塞克为浪漫主义键盘语汇的“预言家”,不仅影响了菲尔德等早期浪漫主义钢琴家,对贝多芬也有深刻影响。再看约翰·菲尔德,我们习惯寻找菲尔德和肖邦之间的承袭关系,却忽略了菲尔德对贝多芬晚期作品慢乐章的影响,在贝多芬的《E 大调第30 钢琴奏鸣曲》Op.109 最后一乐章主题与变奏中,祈祷性的主题,第一变奏动人的歌唱风格,很可能受到菲尔德“夜曲风格”的影响。[1]Alexander L.Ringer.Beethoven and the London Pianoforte School[J].The Musical Quarterly,1970(Oct.):pp.742-58.
总体而言,伦敦钢琴学派对延音踏板技术的探索,其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18 世纪末当欧洲大陆作曲家普遍创作“羽管键琴和钢琴”皆可演奏的键盘作品时,伦敦作曲家已率先开启真正的“钢琴写作”时代;另外,踏板技术的普遍应用引发了作曲家对钢琴音型法和钢琴新语汇的探索热情,成为推动浪漫主义钢琴风格走向成熟的一项重要因素。当欧洲同行仍然实践着古典键盘语言时,伦敦钢琴学派早在18 世纪90 年代就开始探索彰显浪漫主义精神特质的钢琴语汇,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限于篇幅,以上对伦敦钢琴学派成就和影响的讨论仅是匆匆一瞥,更多问题有待深入。例如,对伦敦音乐“娱乐化”的偏见妨碍我们正视19 世纪30 年代出现的一股严肃创作之风,这主要反映在威廉·斯特恩代尔·贝内特(William Sterndale Bennett,1813-1875)和西普里亚尼·波特(Cipriani Potter,1792-1871)的作品中,二人的创作与舒曼、门德尔松等欧陆音乐家的风格十分接近。另外,近期关于19 世纪英国钢琴协奏曲体裁的最新研究显示,莫扎特和贝多芬等维也纳同代人对英国钢琴协奏曲的影响一直被学界高估,英国人对真挚情感的期待远胜于对协奏曲绚烂技巧的热情,这也解释了19 世纪初音乐会节目单上少有钢琴协奏曲的原因。然而贝内特和波特19 世纪30 年代完成的钢琴协奏曲显示出,他们力求在体裁框架内探索抒情和技巧间的平衡以符合英国人对大型体裁的审美期待,这些研究内容十分值得关注[2]Luca Lévi Sala,Rohan H.Stewart-MacDonald.Muzio Clementi and British Musical Culture[M].Routledge,2019:pp.200-216.。最后还需指出,即便是我们自认为熟悉的作曲家、作品,现有成果仍未尽全面。例如,克莱门蒂的《艺术津梁》(Gradus ad Parnassum)被视作练习曲体裁的开山之作,“在肖邦的练习曲问世之前,它是钢琴弹奏技巧的百科全书”[3]周薇.西方钢琴艺术史[M].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94.。不可否认,陶西格(Carl Tausig)1865 年编定的单卷本《克莱门蒂钢琴练习曲29 首》对一代代钢琴学子技术成长功不可没,但基于教学目的的选编版势必有碍于后代对这部作品的完整认识,多萝西·德·瓦尔(Dorothy de Val)近年来从作曲角度考察,认为《艺术津梁》代表着克莱门蒂作曲技术的最高成就,展示了高超的对位技术、丰沛的情感表达,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作曲技术指导大全。[4]Therese Ellsworth,Susan Wollenberg.The Piano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Instruments,Performers and Repertoire[M].Routledge,2016:p.69.以上例子充分表明,直至今日我们对伦敦学派或者说对19 世纪英国钢琴音乐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足。
四、立派依据:质疑与辩护
部分学者对伦敦钢琴学派的立派依据提出质疑,驳斥观点有二:第一,群体性连接较弱,该学派的大多数作曲家非英国本土成长,以客居者身份参与伦敦的音乐生活;第二,共性特征不足,学界普遍认为构成学派的首要条件是在特定时间范围内风格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正如托德(R.Larry Todd)所言:或许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指称。林格教授首次提出伦敦钢琴学派时便明确了时间界限,特指18、19 世纪之交活跃于伦敦的钢琴家——作曲家群体,强调他们的群体性旨在与维也纳学派相对比,以便研究这一群体对贝多芬的影响。而坦伯利远远溢出林格确立的边界,从J.C.巴赫1766 年出版的六首奏鸣曲Op.5 到贝内特最后一部标题性钢琴奏鸣曲《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eans)Op.46,被纳入学派的成员有49 位之多,其作品跨越百年有余。[5]Nicholas Temperley.London and the Piano,1760 -1860[J].The Musical Times,1988(Jun.) :p.289-293.坦伯利指出:伦敦钢琴学派应延伸至贝内特最后一部作品《奥尔良的姑娘》出版的1873 年。托德直言:立派之依据需重新审视,“学派”之指称更需仔细斟酌,与其说他们是根据风格原则或美学信条结成的学派,不如说是以地域为中心结成的音乐家群体。[1]R.Larry Todd.The London Pianoforte School 1766-1860:Clementi,Dussek,Cogan,Cramer,Field,Pinto,Sterndale Bennett,and Other Masters of the Pianoforte by Nicholas Temperley[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usicological Society,1991(Spring):pp.128-136.坦伯利也积极回应质疑,认为在一个专业音乐创作泛欧化的时代,作曲家的国籍只有在民族主义者看来才重要。[2]Therese Ellsworth,Susan Wollenberg.The Piano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instruments,Performers and repertoire[M].Routledge,2016.参见坦伯利撰写的序言。
笔者大胆推测,坦伯利所确立的伦敦钢琴学派在语境上完全不同于林格教授提出的同名学派,后者所指的是与维也纳钢琴学派形成对比,基于英国钢琴性能发展出的音乐风格和技术语言形成的音乐群体,仍属于传统“风格学派”范畴;而坦伯利建构的伦敦钢琴学派其关键词是“伦敦”,他的伟大事业可视为一个心怀祖国的音乐学家的文化理想,他将伦敦视作一个文化空间,研究这个商业性城市(非政治性城市)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对音乐的多样形式、风格的锐意创新起到的积极影响。在此层面,伦敦钢琴学派研究可看作是伦敦“城市音乐”研究的一部分,钢琴音乐映衬出这个城市空间里和钢琴有关的社会关系。因此,坦伯利的伦敦钢琴学派研究倾向于音乐社会学范畴。
综上分析,坦伯利建构伦敦钢琴学派的意义和研究路数则清晰明了:他的研究突破了单一视角和单线叙述的局限,跳出传统“风格学派”关注共性技法和通用体裁的思维定势,借助社会学视角展示伦敦钢琴音乐的多样风貌;通过揭示该学派对早期浪漫主义钢琴书写风格的影响,完成重塑19 世纪英国音乐文化价值的学术使命。
坦伯利倾注半生心血推广本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学术担当令人敬佩且发人深思。钢琴作为一件舶来品,在中华大地已积淀百年,时代为中国钢琴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建构“中国钢琴学派”,用情用力“让钢琴说中国话”,是几代音乐人共同追求的艺术理想。除创作大量能彰显中国审美旨趣和气质神韵的优秀作品,使之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外,时代还呼唤更多的音乐学者借助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势力以开放的姿态阐释和推介中国当代钢琴音乐作品,与创作者和表演者共同推动“中国钢琴学派”的建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