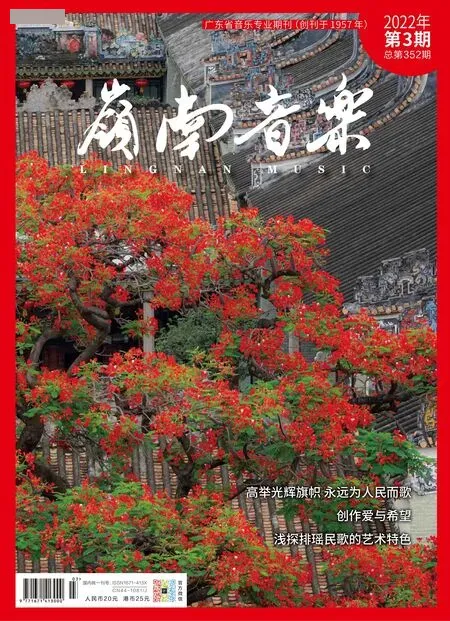瑶族音乐研究现代转型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民国时期的粤北瑶族调研
文|王伽娜 肇庆学院音乐学院
我国在20世纪上半叶就实现音乐研究现代转型的少数民族极其稀有,瑶族算是一个。何为音乐及其研究的现代转型?为何在众多少数民族中瑶族率先实现音乐研究的现代转型?这与民国时期数十年对粤北瑶山的调研有关。具有西学背景和现代意识的研究者长期调研,为瑶族音乐研究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框架。
1.音乐研究的现代转型
社会历史走向现代,始于文艺复兴。随之,音乐及其研究走上现代转型之路。沃尔德等人对此多有记录。其一,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现代科技发明,音乐论著和作品传播范围加大,速度加快。“15世纪,印刷机的发明使得16世纪初第一次出现了成功地通过活字印刷而出版的音乐……到16世纪末,已出现了大量印刷出版的音乐作品”。其二,巴洛克时期,自然科学方法显著影响到音乐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在巴洛克时期的重要性得到了大大的提升。通过引用归纳性的思维逻辑而得到的发现在生理学、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些领域科学研究的成功也影响了音乐家,促使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音乐问题”。其三,古典主义时期,社会愈发制度化,音乐赞助制度和出版建制已相当完备。“出版社的建制已相当完备,对作曲家和公众都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出版商不仅使音乐作品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而且对某些作曲家予以支持和拥护”。其四,浪漫主义时期,商品经济极大地影响到音乐及其研究,作曲家、出版商、演出经理人、评论家合纵连横,形成强大的音乐产业。同时,学校特别是高校成为音乐教育和音乐研究的基地。“音乐教学成为一种固定职业,这一时期建立了许多优秀的音乐学院和音乐学校来培养表演和创作人才。音乐史和音乐理论的研究在19世纪末被引入到多所大学”。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现代转型,西方音乐研究也逐渐在传播载体、思想方法、建制、人才、机构方面呈现出现代特征。
2.瑶族音乐研究现代转型的实践基础
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现代意义的瑶族音乐研究成果,建基于现代意义的田野调查。从20世纪初开始,一批具有西学功底的研究者,开始用现代学术方法对粤北瑶山进行田野调查,包括音乐采风。中西学界已经先后八次以上调研粤北瑶山,积累了丰富的音乐素材,现记录如下。
1910年,西人开启粤北瑶族研究。德国教士F.W.勒斯尼尔(Leuschner)三次进入粤北乳源瑶山田野调查,写成《华南的瑶族》,开启现代西学研究瑶族的先河。对此,国人一方面赞赏有加,西人用现代科学精神研究中国苗夷是“学术上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国人对此多有疑虑和焦虑:“今日国人研究苗夷民族者,反而要依赖外人调查报告的书籍,这不仅是国人之耻,而亦是一种极大危机”。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反倒让西人走在前面,而西人的研究“对种族间往往存有一种主观的见解”,调查数据也不尽客观准确,如勒斯尼尔“谓瑶山瑶人数近十万,这是太过大的估计”。有鉴于此,国人进一步开启了以现代西学为榜样的本土瑶族研究之路。
1924年,国人开启粤北瑶族研究。山西大学毕业后到英国南威尔斯大学留学再归国的张景良,其一行五人到粤北连南八排瑶考察,与瑶民同吃同住三日,记录了当时瑶族几近原始的生活状况,并对瑶歌有所评述。每年四月初八,八排瑶族都要举行盛大的相亲婚配仪式,重要的环节是男女对歌,“男左女右,各不相混,王与庙祝南乡立而监之,令彼男女,此歌彼答”。不过,张景良对歌唱内容多有异议,谓“词极秽亵”。这种对瑶歌的偏见,随着后来更多的田野调查,在深入交流的基础上获得澄清和改善。
1928年,瑶族研究全面启动。一方面,瑶民代表访问广州;另一方面,中山大学师生兵分两路,分别调研两广瑶山。年初,中山大学陈锡襄、钟敬文、容肇祖、杨成志等人相约接待到广州开国民党党员大会的连南瑶族代表一行八人,代表均为连南排瑶各排瑶长。瑶民代表应邀跳瑶舞、唱瑶歌,陈锡襄观后评价“婉转和谐”。连阳化瑶局局长莫辉熊还应邀发文《八排瑶民之历史状况概要》,在“风俗”部分介绍瑶族典型的歌舞仪式“耍歌堂节”。年中,中山大学师生兵分两路开展瑶族田野调查。一路人马赴粤北瑶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容肇祖和商承祚在韶关黄茶坑探寻古物七日。另一路人马赴广西瑶山,中山大学生物系辛树帜、任国荣、石声汉、蔡国良、黄季庄等人,历时两个多月,收获颇丰。除了采集生物地理资料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搜集到瑶歌两百多首,为以后的瑶族音乐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1930年,粤北瑶族研究音乐素材明显增加。中山大学生物系田野调研从广西转向粤北瑶山,黄季庄、庞新民、姜哲夫、辛树帜等十余人历时近一月,采集标本,记录风土人情。在写成的系列文章中,包含丰富的音乐记录。采集队记录《种田歌》一首;庞新民记录《造酒歌》等瑶歌两首,记录瑶族丧葬仪式上的歌舞和乐器,常用锣和牛角;姜哲夫记录瑶族法事歌舞、宗教歌曲、唱本二十余部,记录千年歌堂、长鼓舞、拜王堂歌。
1936年,粤北瑶族研究从音乐搜集扩展到音乐分析和应用。中山大学联合文科研究所各部师生十人赴粤北北江瑶山考察一周。深谙现代西方人类学的杨成志带队,师生分工协作,从社会、历史、经济、生产生活、人种、宗教文化、音乐、服饰、建筑方面分别撰文,专业细分了瑶族研究领域。这次考察,除了像以往一样搜集整理记录瑶歌之外,明显增强了对瑶族音乐的分析评论和应用。其一,瑶族音乐评价。杨成志在《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中对瑶歌总体评价正面,谓“合乎节拍、音调,以表现其调和”“引人入胜”“民间文艺在无文字教育的瑶人社会上,确系一种口传文化最宝贵的利器”。刘伟民在《广东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中虽觉瑶歌“声调悠扬美妙”,但缺点明显,包括歌词不美,不够抒情,内容浅薄,大多不押韵、不工整、不合韵律。其二,瑶族音乐功能。江应梁在《广东瑶人之今昔观》《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中讲到瑶歌娱乐相亲、丧葬法事功能。其三,瑶族音乐应用。杨成志《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王兴瑞《广东北江瑶人的经济社会》、刘伟民《广东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三篇文章通过分析瑶族音乐题材内容,探寻瑶族起源、迁徙、历史、分布、生产生活状况。
1939 年,粤北瑶族研究愈发西化。岭南大学外籍教师霍真(R.F.Fortune)带领社会学系和中文系师生一行八人,在当地传教士带领下,考察了连南排瑶社会文化各方面,包括语言、教育、礼俗、宗教信仰、经济生活、社会组织。这是近二十年来最为西化的一次瑶族调研,领队和接待都是西人,撰写的六篇文章皆英文,发表期刊是英文,立场倾向西方,“有民族歧视性语言”。
1940年,粤北瑶族研究持续进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胡耐安带领粤北边疆施教区巡回施教队在连南支教,启蒙教育开化瑶民,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完成《粤北之山排住民》一书,对排瑶音乐多有记述,包括记录耍歌堂节、长鼓舞,记录瑶族乐器如花鼓(长鼓)、响角(牛角)、口哨。
小学生对新颖的事物、听说而没见过的事物都感兴趣,“好奇”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那么我想只要合理利用网络技术,就可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教师在每节课的开始前都要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利用网络技术比如PPT或动画,创设一个学生喜欢的情景,再自然地引入新课,就可以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课堂学习。
1943年,胡耐安和杨成志分别带队在前次的基础上再次深入粤北曲江和乳源进行田野调研。
回顾三十年粤北瑶族田野调查史可以看到,伴随着瑶族研究不断深化和西化,瑶族音乐研究提上议事日程。研究者搜集、记录日益丰富的音乐素材,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分析、评论,为瑶族音乐研究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当然,正如伍国栋言:“我们不能将这些民族学调查报告本身和所涉及的音乐调查划归独立音乐学范畴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但这些附属于科学民族学范畴的学术性调查研究,却影响、带动和派生出今天看来却极具民族音乐学特点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产生。换一个角度说,真正具有音乐学意义的专门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是依存于20世纪初中国人类学所属民族学、民俗学的兴起而开始萌芽的。”的确,瑶族音乐研究现代转型的成果,一方面奠基于田野实践调查,另一方面来自对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分科如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音乐学等理论的吸收和应用。下面,具体考察一下瑶族音乐研究得以兴起的现代理论准备情况。
3.瑶族音乐研究现代转型的理论准备
仅仅只有田野调查,搜集记录整理音乐素材,还不是现代意义的瑶族音乐研究。如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记》,虽然走遍连阳瑶山,对瑶歌、瑶族乐器多有记载,但没有现代学科理论视野结合瑶族音乐素材进行分析评论运用,所以仍然归属于传统范畴。这种情况从20世纪初开始改变,现代研究机构和期刊兴起,研究人员及理论方法更新,雨后春笋般的生发出一系列瑶族研究成果,为现代意义的瑶族音乐研究做好了理论准备。限于篇幅,不罗列成果的详情,只做统计归纳。
20世纪上半叶粤北瑶族研究从1911年德国教士F.W.勒斯尼尔发表《华南的瑶族》开始至1949年中山大学曾昭璇发表《粤北瑶山地理考察》止,38年间来自12所学校(主要是高校)的32位研究者在18种期刊或出版社发表论著成果52篇。其中主要高校是中山大学,研究成果39篇,占比75%;核心期刊是《民俗》,发表成果20篇,占比38%。这种以现代高校为基础的教研模式,以现代期刊为载体的出版模式,造就了充满现代学科意识和专业精神的研究者。他们所受大学教育的现代学术专业分科特点明显,来自中文系(国文系)的有陈锡襄、胡耐安、黄锡凌,来自西文系的有容肇祖,来自社会学系的有江应梁、霍真、李季琼、梁钊韬,胡耐安,来自历史系(史学系)的有商承祚、江应梁、王兴瑞、刘伟民、杨成志、罗比宁、梁钊韬,来自哲学系的有容肇祖,来自生物系的有石声汉、庞新民、辛树帜、姜哲夫、顾铁符,来自地理系的有张景良,来自人类学系的有江应梁、王兴瑞、杨成志、梁钊韬。这些现代专业研究者,或分科,或协作,或跨学科综合,研究成果丰硕。
更有部分研究者西洋取经,开拓视野,将西方最新科研理论方法带回国内。如国内瑶族研究开拓者张景良留学英国,毕业于南威尔斯大学;石声汉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访学德国柏林大学;陈锡襄留学英国;辛树帜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柏林大学;杨成志留学法国巴黎人类学院、巴黎大学,赴美访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胡耐安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他们联合各大学师生、研究机构、期刊、出版社,将现代西学引介、应用于中国,让瑶族研究焕然一新。
现将粤北瑶族研究的西学引介、应用情况列举如下。其一,瑶族研究引入英文翻译和写作模式。如杨成志在《民俗》季刊《广东北江瑶山调查专号》中专门用英文写成《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霍真带队写成的六篇连南排瑶研究论文全部用英文写成,并发表于全英文的《岭南科学》杂志。其二,瑶族研究倡导民族学。杨成志在考察北江瑶人后写成《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导言》时强调,“在中国今日要写作一部完善的民族史”,“离不开科学的民族学或民族志”。王兴瑞在瑶族考察时写的《北江瑶山考察团日记》同样强调,“民族学是史学的一种重要辅助科学”,广东瑶人“是民族学的宝藏”。其三,瑶族研究引入人类学。杨成志在《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中说道,“在未说及本题以前,对于文化本身的解释,应先具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人类学为探讨人类文化的科学”,“文化的所以然”。人类学被当作瑶族文化研究的理论来源和解释方法。其四,瑶族研究引入民俗学。写成《瑶民访问记》的陈锡襄较早在《风俗学试探》的研究中倡导民俗学,“风俗之被人学术地注意,社会学很有相当的功劳,然而民俗学或民俗学引动实使这注意增加,渐成为普遍化与系统化的”。民俗学方法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受到推崇,“他们对边疆民族尤其是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比较进步”,“倾心于此种新的研究方法”的江应梁,在《我怎样研究西南民族》一书中写成北江瑶族六篇论文。当然,因为参与的大学院系专业众多,无法一一列举各个学科理论在瑶族研究中的引介和应用情况。仅列举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是因为它们与瑶族音乐研究转型为现代意义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关系最为密切。
民国时期粤北瑶族音乐调研以现代高校为教研基础模式,现代期刊为出版载体,充满现代学科意识和专业精神的研究者为主要阵营,在田野实践调查的基础上吸收和应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音乐学等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为瑶族音乐研究的现代转型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才会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专门的瑶族音乐研究论著。
[1]前述引用自米罗·活尔德等著,刘丹霓译:《西方音乐史十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8、81、127、152—153页。
[2]杨燕迪:《音乐的“现代性”转型——“现代性”在20世纪前期中西音乐文化中的体现及其反思》,上海:《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60页。
[3]江应梁:《广东北江瑶人的生活》,北京:《东方杂志》,1938年第11期,第40页。
[4]张景良:《连州瑶山旅行述略》,北京:《地学杂志》,1924年第15期,第6页;张景良:《八排探瑶记谈(风俗)》,北京:《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926年第17期,第97—99页。
[5]陈锡襄:《瑶民访问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35—36期,第70、73页。
[6]见容肇祖:《韶州调查日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第39期,第13—19页。
[7]见石声汉:《瑶歌》,广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46-47期,第34—38页。
[8]见庞新民:《理科生物系第一次广东北江瑶山采集日程》,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0年11月22日。
[9]见国立中山大学理科生物系瑶山采集队:《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少数民族卷 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10]见庞新民:《广东北江瑶山杂记》,载刘耀荃、李默编:《乳源瑶族调查资料》,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86年,第329、331、332、334、336、341页。
[11]见姜哲夫:《记广东北江瑶山荒洞瑶人之建醮》,载刘耀荃、李默编:《乳源瑶族调查资料》,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86年,第342、346—349页。姜哲夫:《拜王》,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1932年第1期,第89-119页。
[12]王兴瑞:《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北江瑶山考察团日记》,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少数民族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35页。
[13]对瑶歌的搜集记录,见江应梁《广东瑶人之宗教信仰及其经咒》记录丧葬法事中的歌舞、乐器;刘伟民《广东北江瑶人的传说与歌谣》记录瑶歌26首;王兴瑞《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北江瑶山考察团日记》记录瑶歌2首。以上载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二编 少数民族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51-263、311、341页。
[14]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等编:《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八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1页。
[15]伍国栋:《综述·述评·田野·方法论:伍国栋民族音乐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