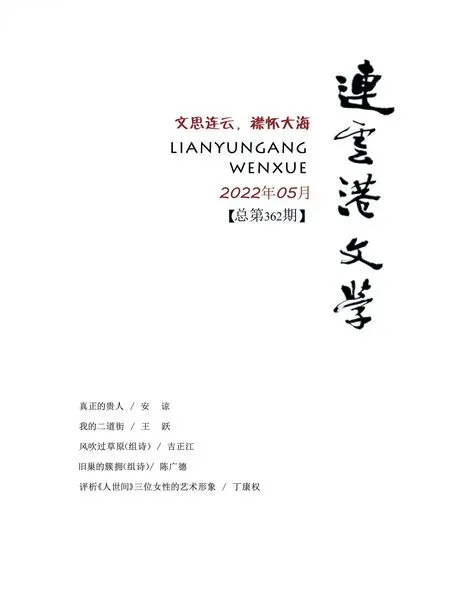鼓浪循梅听琴声
何洪清
喜欢厦门,是因为舒婷。三十多年前,读她那首《致橡树》,在日光和春雨里,我常常做着木棉花盛开的梦;后来,有同学到厦门安家落户,厦门便在我心里生出了牵挂。前不久,听说厦门的秋天,三角梅火一样开遍了蔚蓝的海岸,我就决心,一定要去一次厦门,观三角梅如炬,看木棉花似蝶。
就像到杭州要去看西湖,到苏州去看虎丘,到厦门怎么可以不去鼓浪屿。
于是,从筼筜湖边拦了一辆车,直奔国际邮轮中心。邮轮在600 米宽的鹭江中迤逦斜行,20 分钟后到达三丘田码头。
来鼓浪屿前,我千百次地想象着鼓浪屿的模样,浪花与白鹭同飞,琴声与鼓浪齐鸣。遍布岛上的老橡树像盼子归来的母亲,直立在岩石上打着手势望向海面,橡子如铃悬在在高高的枝干上。上得岛来,我也能如儿时,上学路上,爬到月牙桥边那棵孤独的大橡树上摘一兜橡子,插入玉米桔上剥下的篾皮,课堂上调皮地敲着前排同学的头。
可是我错了。踏上鼓浪屿,我才知道,海水簇拥的鼓浪屿,既不像洞庭湖中白银盘里一青螺的君山,也不似太湖中那座长满了枇杷青梅柑橘和茶叶的洞庭山,鼓浪屿的海面,碧波轻漾,如同夏日里我家门前千亩稻田,婆娑着层层绿浪;鼓浪屿,与其说是海中花园,毋宁说是一位学成归来的少年,西装革履,透着民国范的翩翩处子向着他的家乡厦门踏浪而来。
从三丘田码头上岸,兜头撞见的当然还是那窈窕淑女模样的椰子树,椰子树的对面总是站着壮汉一般的棕榈树,才子与佳人,他们真是天生的绝配。夹岸的三角梅正举着火把欢迎我的到来,敦实的凤凰木上结着长长的皂荚,像极了儿时奶奶的酱缸里腌着的那几根大扁豆,早饭桌上,切一小碟,一节节的,那断面就如自行车的链条一样,看上去很可爱。
离三丘田码头不远的黄家渡码头据说从前是何姓码头工人的聚居点,不知道厦门的何姓与香港澳门新加坡的是否出自同一支脉,我猜想,南亚岛国的何氏一族或许也是从鼓浪屿下的南洋吧。对面不远,三明路26 号就是1844 年美国设立的领事馆旧址。1840年后到十九世纪末,外国人设立的十多家领事馆遍布了岛上的角角落落,这其中,比较醒目的有漳州路5 号1843 年的英国领事馆,鹿礁路与环鼓路交汇处1864 年的德国领事馆,此外还有1850 年的西班牙领事馆,1852 年的荷兰领事馆,1860 年的法国领事馆,以及挪威、日本、比利时、丹麦、葡萄牙、瑞典等,鼓浪屿简直就是一座清末领事馆博物馆。这些领事馆旧址的存在,一方面见证了鸦片战争后帝国列强们觊觎中华大地的触角,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厦门作为华夏之门得到了世界认可。
出三丘田码头左拐,沿延平路前行不到500 米,就是钢琴码头,为了诠释鼓浪屿的音乐之岛形象,码头被设计成张开的三角钢琴状,鼓浪屿显得更像是琴岛了。钢琴码头是岛上居民来往厦鼓之间的生活轮渡码头,码头对面几棵老榕树如张开的巨伞为来往的游客遮荫纳凉,那浓密的气根似褐色的瀑布泻下来,又如老中医悬壶济世的银针扎到了大地上。树下的大屏上循环播放着张暴默的《鼓浪屿之波》,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舀不干海峡的思乡水,思乡水鼓动波浪。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思乡啊思乡,谁能不思乡,六十年前,于右任站在对岸的玉山上也唱思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钢琴码头的前身就是著名的“猪仔”码头。许多年前看萧乾的《梦之谷》,大约记得这部爱情小说里面有个章节描述老华侨们当初下南洋的情致,一个个年轻人被当成猪仔一样地赶进船舱,小船像一片树叶在海上漂泊流转,闷罐一样的船舱里蒸笼似的透不过气来,吃喝拉撒全在那一个窄窄的地方,遇到狂风大浪,有的人会晕死在舱里。一船一船的,他们被当成牲口一样贩卖到南亚岛国。在那儿打拼奋斗,发迹后,这些长成大树的华侨和后代们,忘不掉扎根的故乡,纷纷回到家乡安家落户。
鼓浪屿上,有黄家花园的印尼糖王黄奕住,菽庄主人林尔嘉,圆顶八卦楼主人林鹤寿,还有木材大王李清泉的容谷别墅,黄荣远堂主人黄仲训。离乡愁浓,归来情重。在鼓浪屿上那一座座民国风韵的小楼,正是南洋人看得见的乡愁。
于钢琴码头,沿龙头路前行百米,一座砖混结构的三层白色小楼即是印尼糖王黄奕住1922 年开办的中南银行鼓浪屿办事处,起名中南,即含有中国与南洋汇通之意。其所在的龙头路商业街,也是由黄奕住投资建设的,全部是砖混结构建筑。100 年前,黄奕住还联合股东投资兴建了厦门自来水公司、漳厦铁路,清淤筼筜港。
走鹿礁路,过蜡像馆,上漳州路,隔着一丛丛的三角梅,远远地就看见一尊巨型石像立于延伸到海中的礁石上,这就是漳州路3号皓月园中高15.7 米的郑成功花岗岩石像。不过这皓月园之名就有点意思了,一说是取自郑成功的诗句“思君寝不寐,皓月透素帷。”然而我查了一下,此句却出自《延平二王遗集》系郑成功之子郑经的诗作《效重重行重重》:昔与君别离,杨柳绿依依。今我来相思,雨雪已霏霏。岁月易如驰,音书一何稀。相隔万余里,何从知音徽。朝愁南浦云,暮惊孤雁飞。思君寝不寐,皓月透素帷。中夜起踯躅,自屋霜四围。芳年度华月,良人归不归。可是,亦有人从诗句上分析,此诗不该是郑经所写,应该是他的小妾思念郑经时写给他的情诗。
漳州路是一条环岛路,平日里一定极其热闹,但今天还算幽僻。一路的榕树遮天蔽日,看着这些挂满气根美髯公一般的榕树,我惊叹于世界上还有这么有生命力的植物,能把一棵树长成门垛的,也只有鼓浪屿的榕树了。
过了皓月园,是我国妇产科医学奠基人林巧稚的毓园,毓园对门是漳州路5 号原英国领事馆旧址。再往前走,在一片芙蓉树和木棉花的尽处是厦门音乐学校,然后是漳州路42 号菲律宾木材大王李清泉旧居李家庄。漳州路48 号是林语堂故居,那年,漳州和平里坂仔村的青年林语堂在这儿迎娶廖家二小姐廖翠凤,娶亲仪式上林语堂懵懵懂懂地把茶碗里的桂圆也一起吃了下去,让廖家兄妹取笑了这位幽默大师好多年。
林语堂旧居隔壁,漳州路的尽头是以传教士马约翰命名的广场,广场边上漳州路64号是一座两层小楼,据说是钟南山院士的外婆家,小时候他常来此小住。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与林语堂夫人廖翠凤的楼房紧邻,想必两家为同宗同祖的廖家人。鼓浪屿每一个门洞都藏着一个故事,这些故事里有很多女主角,革命者秋瑾、医学家林巧稚、作家谢婉莹、学者黄萱、指挥家郑小瑛、诗人舒婷。
港后路7 号的菽庄花园建于1913 年,位于鼓浪屿南部,面向大海,背倚日光岩,原是中山时期的候补参议员,厦门市政会长林尔嘉的私人别墅,园主人仿其祖上台北板桥花园而建,以他的字“叔臧”的谐音命名花园,“有白水洋水景风光,有火山岛之礁石,又有兔耳岭高山草甸之美”。
花园内设置眉寿堂、壬秋阁、真率亭、四十四桥、听浪阁、顽石山房、十二洞天、亦爱吾庐、观潮楼、小兰亭等十景。
站在山岩上,看着浪拍水岸,风鼓浪飞,这如泓的水声,大概也只有在菽庄花园才能真切感受到鼓浪屿这岛名的意境了。突然也很想写点枕上听潮的诗句,无奈缺了舒婷的才气。
园内有一石碑,隶书刻写园主林尔嘉的建园小记:“余家台北故居曰板桥别墅,饶有亭台池馆之胜。少时读书其中,见树木阴翳,听时鸟变声,则欣然乐之。乙末内渡,侨居鼓浪屿,东望故园,辄萦梦寐。葵丑孟秋,余于屿之南得一地焉。剪榛莽,平粪壤,因其地势,辟为小园。手自经营,重九落成,名曰菽庄,以小字菽臧谐音也。当春秋佳日,登高望远,海天一色,杳乎无极。斯园虽小,而余得以俯仰瞻眺,咏叹流连于山水间,亦可谓自适其适者矣。林尔嘉记”。
我到菽庄花园的时候,不知是不是因为星期天的原因,位于菽庄花园的钢琴博物馆没有开放。
因为多年做茶的原因,我每到一地对水井特别留意。日光岩下有一古井,称作国姓井,一看井名,就知与郑成功有关。鼓浪屿的井还有很多,豆腐井、豆菜井、水牛埕井,最有意思的是皓月园里一口覆鼎古井,离海岸仅十余米,井里却汩汩涌出的是甘甜的淡水。我不懂覆鼎之意,只记得宋·苏舜钦《了语不了语》诗中有句:“公餗欲成忽覆鼎,银瓶汲绝还沉井”。不过,在闽北有个盛产白茶和白琳红茶的那个福鼎我倒是知道的。
站在日光岩上,秋天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就像南明延平王在操练着的水军,身上披挂了金铠铁甲。那年延平王发一声呐喊赶走了台湾岛上的占领者,然后回转身,与清兵对垒。突然,我明白了,厦门从前为什么叫思明。
暖阳如春,有风吹来,似乎带着浓浓的酒香。对面的金门岛是一个出产高粱酒的地方,每次,同学从厦门回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酒。其实我不好酒,但每次闻着那带着宝岛风味的酒香就会想起我年轻时候夏天在高粱地里割草,秋天看着父亲在地里一棵棵放倒了的高粱,母亲扦下一个个沉甸甸的高粱穗,留下一根根长长的梃子,背回家,串成盖梃,放饺子当锅盖。我没有喝过家乡的高粱酒,但听过爷爷讲的故事,从前,欢墩埠的镇子上,一个开酒坊的大户人家,年年酿着高粱酒、玫瑰露。酒坊里规矩森严,规定了伙计不准私自喝酒。可是那老板会来事,每天收工,总会拉住一个伙计悄悄地说,明天早点来。那伙计就真的早早来了,东家舀一碗新蒸的高粱酒,赶紧喝了,莫与外人道。这伙计就以为东家格外开恩自己,干活也就特卖力。后来,满酒坊的伙计出了门都在讲东家的好,都以为自己才最受老板器重。谁会想到,伙计们喝下去的高粱酒里,一碗一碗的盛满了东家的心计。
晃岩路31 号的黄家花园,是黄奕住的私家别墅。黄奕住有一女儿,也许你不太清楚,但说起一个人,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岭南大学作为陈寅恪的助手,协助几近失明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等著作的人,就是黄奕住的女儿,她叫黄萱。黄萱后来嫁给了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周寿恺,是不是在这别墅完成的婚礼不得而知。但说起鼓浪屿的婚俗,倒是挺有趣。新娘离开娘家要过米筛,自家兄弟背上花轿,进入婆家要跨过红炭炉,新郎抱进家门,这在许多地方都有的习俗在鼓浪屿也不例外。但在鼓浪屿,不管谁家娶媳妇,都要绕岛一圈。有一对年轻人,本是邻居,从小青梅竹马,他们相爱了。结婚的时候,即使两家只隔一道墙,男方也要吹吹打打绕鼓浪屿一圈到女方家去迎娶新娘。鼓浪屿上多是坡路,主要运输工具是二轮平板车。新娘出嫁了,临行前妈妈交待到婆家要勤快少说话。嗯,少说话,没人当哑巴,新娘记住了。新郎抱得美人归,吹吹打打,平板车搭成的花轿拉着新娘绕岛一圈回家了。一墙之隔,婆家一干亲友秉烛以待,等着新娘到家跨火盆。一等再等,新娘就是不下轿,掀开轿帘车上空空的,哪里有新娘的影子。一家人赶紧四散开来满岛地去寻,结果,就在来时的路上,一个斜坡处,新娘蒙着盖头坐在席子上一动不动。人问缘故,原来是坡陡席滑,上坡时连人带席一起滑了下来。那你干嘛不喊一声啊,妈妈交待要少说话。
如果有一条路最能与鼓浪屿接地气,非龙头路莫属。转了一上午的人,又累又饿,龙头路是绝对值得一走的。这儿不仅是鼓浪屿的小吃一条街,海鲜店一家接着一家,还有各种鼓浪屿风味美食,蟹黄包,豆包仔粿,碗糕粿,芋包,鱼丸汤,扁食汤,烧肉粽,沙茶面,米线炒饭。一份炒面一碗汤,老板吆喝着只收你十元钱,在这样的厦门,在远离市区的海岛,这价格,厦门人真是够实诚。不过肉燕就是咱们的小馄饨,你别真以为会给你端上一碗小燕子。
龙头路上开着各色店铺卖着各种特产,海鲜珍珠片仔癀,紫菜贝壳姜母鸭,厦门珠绣和以古法錾刻技艺被列入了厦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刺绣店里,一温雅女子在绣台前一针针地做着绣品,银器店里有叮铃当啷的声音传来,那是工匠们在锻造银器,各种银镯、挂件,耳饰琳琅满目摆满了柜台货架。我不懂厦门人对银器也是这么喜欢,在我的家乡,银器被当成了消灾驱邪之物,带着月光之色的银器也是一种纯洁。至今,我还收藏着我小时候母亲给我定做的一顶童帽,除了上面布满了母亲一针一线绣制的各种猴子吃桃、小鸡啄草、牡丹怒放等图案,帽檐上钉缀着不同的银菩萨、银观音等银饰。脑子里也突然闪过惠安女和云南苗家女子戴着银饰的那一种姣好。
龙头路上茶叶店也多,闽南人喜欢的工夫茶在厦门尤其兴盛,在厦门开店,卖的最多的还是武夷岩茶和安溪铁观音,像我这种做绿茶生意的人,大概在厦门是没法生存的。厦门人喝功夫茶是有传统的,二十多年前看电视剧《康熙王朝》,福建总督姚启圣上任伊始,一脚踏进总督府,热热的喝了一口铁观音茶,来了一句回味无穷回味无穷啊!赶三千里路,就为了一壶铁观音。从前姚总督回味着乌龙茶的观音韵,如今轮到我们回味那段起起落落的历史。后来,姚启圣的二儿子姚陶知淮安,康熙49 年到云台山赈灾,写了《登云台山记》,也算是姚家与海州的一段佳话,把福建沿海与古海州连在了一起。
龙头路的尽头,在179 吃茶的小店门前,我好奇于这样的店名到底是吃茶还是吃饭,随手把一直拿着的导游图垫在屁股下坐在路边与街边人闲谈,走时匆忙,把那张导游图忘记在了路牙石上,如今我想循着导游图写点文字的时候却成了遗憾。
站在鼓浪屿港仔后海水浴场边上,深秋的天里,看着一群孩子在金色的黄沙上玩耍,海水泛着银光,耳边似乎响起了年轻时流行的那首校园歌曲,小螺号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吹,阿爸听了快快回。
南宋最后那位小皇帝赵昺沿海岸线一路仓皇南逃时,鼓浪屿还是个被海沙环抱的馒头状小岛,便依葫芦画瓢起了个名字叫圆沙洲。后来有个姓李的渔民出海打鱼,常在此躲避风雨,再后来干脆就定居于此,渐渐地形成了李姓聚集区,李厝澳演变成了内厝澳。在中国,除了植物语言和族群带有浓浓的地域性外,地名也是非常有地域性的称谓,在河北山东,庄被广泛运用,那个赵子龙的故乡常山如今被称为国际庄的石家庄,还有高家庄,马家庄,张庄李庄大店庄等,而在浙南山区,岙的地名就很多有凰山岙、映山岙等,在苏浙皖交界的山区,岕则比较普遍,如八都岕、周吴岕等,进而连茶都用了岕茶的名字,在厦门,厝的地名就很常见,比较有名的就是曾厝。鼓浪屿上,红砖红瓦的四落大厝如今已经成了文保单位。
来鼓浪屿前,同学告诉我,游鼓浪屿就和上故宫一样,要慢慢走,细细看,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景点,每一间屋子都有故事。同样是旅游,同样是小岛,七年前,同学三家在哈尔滨,松花江上的太阳岛,岛子不大,印象里似乎就一块太阳石和一个俄罗斯风情园,没有多少景点的太阳石前留下了我们的合影,没有多少故事的太阳岛,留下了我们多少的欢声笑语。在厦门,我独自一人循着三角梅开遍的小径,打马如飞的走过鼓浪屿,可真算是走马观花了。从一对对恋人身边超过,看着他们欢快悠闲的身影,我突然想,鼓浪屿是适合恋人来的地方。
当我站在离开鼓浪屿的游轮上,白云飞过厦门的高楼,海水荡漾着绿波犹如一张极大的荷叶平铺在海峡中,鹭鸟飞去的身影里似乎看到了殷承宗的手指划过了琴键,一曲《黄河》响起,你听,黄河在咆哮,是不是也如鼓浪屿上,潮水涌过鼓浪石,也是一番鼓浪洞天。
心里装着三角梅,离开鼓浪屿。不知道为什么,魂,却像那张丢掉的地图,落在了鼓浪屿。